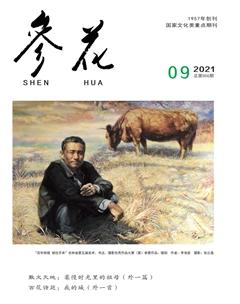柔慢时光里的祖母
一个慢字,缠绕了祖母的一生。
她小时候缠过脚,旧时光旧传统旧思想对她的熏陶根深蒂固,所以我小时候上学,总是迟到,因为天天早上五点左右,祖母总是自告奋勇地送我。天黑得像煤像炭像乌鸦,家到学校的路并不太远,我跟着她,通常她在前,我在后,她总是踱着方步,我只能亦步亦趋,生怕她摔跤。我从小便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不反叛,知道心疼家长。
祖母年轻的时候也是国色天香的角儿,沁河发水,从武陟县西往新乡方向逃荒,无奈流落到县东,无路可走,饥饿难忍,流落到了前牛村。时光恰恰好,她遇到了刚刚扶正的二奶,二奶是一个唱戏的,一唱三叹,字正腔圆,人家家里缺丫头,祖母便留了下来照顾二奶的起居。爷爷不是个喜欢在家的人,通常躲在太行山的煤矿里给德国人打工。祖母来时十八岁,熬了七年,二奶吸了大烟,家里整日里烟雾缭绕的,二奶吸光了爷爷置下的万贯家财,祖母本来想跑,可是,病危的二奶突然间醒悟,她临死前扯着祖母的手让她留下来,古家没后,她觉得对不起爷爷,而当时,爷爷已经年近花甲。
祖母的传统思想非常严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祖母算是在怜悯中点了头。二奶死后,她完全可以跑,可以走,可以回自己县西已经建好的家园,可是,她没有,她的骨子里藏了一種善良的基因,她跟了爷爷,没有仪式,一穷二白。她的父亲从家里跑来找她,让她跟他回老家去,她走了两回,不放心,又跑了回来,她一直记着二奶死前的眼睛,那是一种至亲至纯的嘱托,她应了,就不能反悔。
任凭她父亲打她骂她,包括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她还是不走了。恰逢自然灾害,树叶、皮带成了主粮,村里许多人开始食用观音土,无法,她当了从娘家带来的仅有的一枚玉镯,生了父亲,对爷爷对古家算是恩重如山。她说:玉镯当了,我真的回不去了。
晚年的爷爷也曾经忏悔过,不过没用了,他年轻时候挣下的钱已经全没了,二奶花光了他的所有积蓄,他晚年始终活在失落和后悔的阴影里。在父亲八岁时,爷爷作了古,从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只有孤独陪伴奶奶,她说自己不苦,她没有眼泪可流了。从此以后,她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父亲身上,他们相依为命。
当时家里已经没有多少家当,原来有一套高档的楠木家具,被二奶当给了古氏宗祠,现在,它依然安生地躺在古氏祠堂里供我们后辈们膜拜瞻仰。我长大后,祖母曾经拉着我的手到了祠堂,她告诉我:这曾是我们家的东西。
我曾经认真俯下身去,吮吸那种隔世的芳香,那种曾经无比荣耀和离经叛道,现在却是让人无限怅惘的爱恨情仇。我知道,是非荣辱早已经是过眼云烟。
爷爷走后,家徒四壁,房子在一场大雨中倒塌了,什么都没了,只剩下现在,只剩下黄土,过去被埋葬了,要活,要努力活,精彩地活。
年轻的祖母与十岁的父亲自己动手盖房子。
正是盛夏时分,为了盖房子,祖母拉着车,父亲在后面推车,车上带着干粮,他们前往太行山拉石料。他们走得慢,累了就歇,四十里的路,走了两天,回来又用了两天,用麦秸、沙子和土和泥,脱成土坯,他们用了两年,盖了一座正屋。土坯建的房子,坐北朝南,门狭小,窗户用白纸糊住,夏天上面充满了蝇屎,冬天漏风。我听过单田芳的评书后,经常用舌头舔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房里经常有老鼠胡闹,我最喜欢与奶奶一起逮老鼠,老鼠跑我也跑,祖母说要想逮住它,你得跑得过老鼠,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战胜过一只老鼠。我生在那儿,从那儿长大,走向芸芸众生,他们就这样慢慢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强且鲜活。
多年以后,祖母依然能够记得二奶教给她的豫剧《桃花庵》中的戏词:
“蝴蝶儿双飞过墙外,想起来久别的奴夫张才。”
从未上过学的她还从二奶那儿学会了一阕词,是李清照的《声声慢》: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她念了一辈子,有事没事时,便是随口而出,以至于我从小便对戏剧和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了我以后,祖母又认真地活了一回。
她说本来已经觉得无望了,我的到来,让她重新觉得世间可活。
所以,她拼命地下地劳作,与岁月争斗,与时间赛跑,她把所有的希望从父亲身上转移到我的身上,她不希望我出人头地,只是希望我一生平安,顺便得个一官半职,从而使得我们家门庭若市,让死去的爷爷知晓:她培养的孩子比他强。
由于各种缘故,我从小便与她睡在一起,她老是喜欢给我讲故事,年轻时的趣事,她讲得太慢了,我睡着了,她还在讲,一周以后,她的故事还没有结尾。
她没有赢得时间,我们所有人在时间面前,都是失败者。
她一直到了晚年,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给我提过爷爷,她对爷爷只是一种报恩,没有爱可言。有一天,我在她的箱子里找她藏起来的钱,因为我渴望着学校门口的冰糕,我发现了一张照片,这可能是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他与一个德国人站在一起,那个德国人据说是煤矿的东家,长得不太耐看,爷爷倒是眉清目秀,瓜子脸,尖下颌,傲骨英风,与我一个模样,怪不得村里的老人见了我,总我说长得像爷爷,祖母不太喜欢,因为她觉得我长得应该像她,爷爷是过去式了,现在,她才是家里的主角儿。
我总是在阳光下告诉她关于我的抱负与理想,我说等我将来出息了,她会待在城市里安享天伦。她只是听,偶尔摇起蒲扇,驱赶着要命的苍蝇与臭虫,她不会说勇往直前的话,更不敢隔着代去阻挠关于我的种种前途,她只是喜欢让时光慢点儿走,我好多些时间留在她的身边。
她没有等到我兑现我的斩钉截铁的诺言,便病入膏肓,与世长辞。我赶回家里时,白花纷飞,当时,正是春季,她说她喜欢春天,她十八岁逃至家里时,也是草长莺飞、姹紫嫣红。
中国的祖母们,对孙子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缘,溺爱也好,宠爱也罢,她们恨不得将自己年轻时候失落的幸福,统统收集好后安装在孙子们身上。
中国祖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关于传承的文化,她们有时候不想前进,裹足不前,她们其实是在渴望另外一种美好。
因为世事安然。
所以似水流年。
父亲的马车
父亲曾经拥有过一辆马车,马与车是“标配”,再加上父亲,他们的组合简直就是“顶配”。
想起那辆马车,我总会想起杜甫的诗句:野田人稀秋草绿,日暮放马车中宿。
在一九八八年,农村开始流行马和车,因为有了马车后,不仅可以服务于农业生产,更可以做生意拉货,而在当时,这是一种发财致富的捷径。
父亲是个万事“慢半拍”的人,他与祖母的思想一脉相承,母亲说他的思想至少落后半个世纪。
村里一大帮的同龄人开始置办马车时,父亲还是照常在田地里释放自己的青春,他喜欢乡土,我曾经看见过他将土捧在手心里,闻上半天。
我想到了《黄河东流去》里的徐秋斋,他们都是视土地如命的传统人。
我上了学,家庭经济持续落后,缴了学费便捉襟见肘,光靠土地只能维持正常生存,却没有额外储蓄,而父亲曾经发誓要使家里的孩子出人头地,因此他想到了置办马车,然后往北边的太行山拉砖拉煤。
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驯服过马,算是一个不错的驯马师,许多人遇到关于马的棘手问题时,父亲总是津津乐道,购置马匹他在行。
他与母亲并肩走在县里的马市上,马市里“人仰马翻”,好像古代的戰场。
父亲相中了一匹枣红色的马,他对红色情有独钟,父亲说红色吉祥,看起来舒服,而这匹马壮实,有些像大汉朝的汗血宝马。
我下学回家时,便发现墙角多了一座马厩,这是一座简易的房子,一匹高大的马正在马厩里旁若无人地逡巡,父亲正雀跃着喂马。马与父亲不熟,开始时不配合,父亲软硬兼施,不停地用手摩挲着马的鬃毛。等到我做完作业时,马已经开始吃草了。这是父亲从地里割来的青草,由于草里有刺,父亲像个孩子似的,坐在草丛里择刺,由于他不喜欢戴手套,好几颗调皮的刺扎进了他的皮肤里,一道道血红色的痕迹映现入我的眼帘,让我有些心痛。
一周后,一辆马车又出现在院落里,不是新车,新车太贵了,用一辆旧车改造的马车。父亲手巧,旧车不比新车差,巧夺天工的那种。父亲买了漆,自己上漆,由于他不谙油漆作业,将马车油成了五颜六色,远远看去,像是春天被人打翻了,各式各样的花朵与色彩流淌在征途上。
当时是春天,年关刚过,柳絮轻舞,杨花漫天,时光简单柔软,东风侵略了人间,掠过小院和父亲的脸。父亲执着地套上马车,在全家的殷殷期盼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征程。
一九八八年,我们全家的年收入大约三百元,而马与车,足足花费了五百元钱,当时我不解,曾经怨过父亲的愚与母亲的傻,花这么多钱,何时才能够收回成本?而多年以后,当我做生意失败时,突然间回到了那个温暖的春天,父亲告诉我:只有舍,才能得。
父亲第一次出车时,要到修武县去拉砖,那儿零散地存在着许多小砖窑,我曾经随着父亲去过那儿一次,高墙林立,像监狱,圈满了梦想、富丽和堂皇。当时,我对这种奇怪的建筑充满了畏惧,总觉得这个地方是用钱堆出来的,钱太多了,反而不好。
父亲正襟危坐在车辕上,像他的半辈子一样小心翼翼,这是他的所有家当儿,他小心谨慎,生怕出现丝毫的差错,他像在赌博,押了所有的本儿,一心要赚个盆满钵盈。
他开始时走得很慢,努力控制住车速,第一趟车,他跑了两天,等到第二趟时,他轻车熟路,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满载而归。
父亲老实,但聪慧,他总是将所有的危险想到前面,他在车上焊了一个工具箱,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包括饭菜和水,他总是在带在身边,他没有在外面吃饭的习惯。
“小心驶得万年船。”父亲驾着马车,走在人生路上,他就这样行驶了五六年,他人缘好,虽然不爱说话,但货拉得瓷实,砖一块也不会少人家,料总是足足的,让人见后心生敬佩与信任。因此,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其间,发生过一次意外事故,马在厩里发生了意外,得了马蛔虫病,这是一种急性病,马失去了斗志,虚弱不堪。父亲想了各种方法依然无效,叫了医生,农村没有专门的兽医,医生说需要去县里的医院买消炎针剂,当时老天下着犀利的雨,骑不了车子,父亲步履蹒跚地跑往县城,母亲想一同前往,可是执拗的父亲早已经冲进了雨中。当时没有柏油路,一条崎岖泥泞的土路通往县城,父亲在雨中来回走了两个多钟头,回来时,已经是子夜零点时分。他浑身湿透了,母亲熬了姜汤,他顾不了喝,叮嘱医生快点用药。好歹苍天佑人,马通人性,知道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拼命与疾病斗争,很快转危为安。父亲却为此得了一场大病,但他总说遇难呈祥,果然,他病愈后没几天,几笔生意,便赚够了我高中一年的学费。
小三轮车开始在公路上奔驰,它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取代了马车的地位,它们速度快,一日千里。
马老了,父亲舍不得卖掉,父亲也由中年迈入老年,父亲情愿一辈子活在慢速的年代里。父亲有些迷茫,他的活儿越来越少,直到后来,老马病了,无药可医,死了,他失魂落魄,看着快速发展的时代迷茫不自信。我宽慰他:生老病死,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您也奋斗一辈子了,该休息了。
他苦笑,看着闲置的马厩,他不肯拆掉,只好让它残酷地存在着,至少这是一种丰满且无奈的记忆。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完了大学,父亲也老了,他不愿意再接受任何新生的事物了。我与母亲劝不了他,总要有一些旧的事物存在,时光老些就老些吧,我们走累时,可以回到慢条斯理的伞翼下休憩。
父亲也曾信誓旦旦地抗争过,他买过一辆三轮车拉土赚钱,可是,他总是一脸落寞,机动车不是马,马是生灵,可以训斥,可以沟通,可以培养感情,三轮车只是个物体,在父亲的眼中,这是个死物,没有灵魂。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话语,来形容马车的伟大与沧桑,就像承载着一个民族迫切却又不得不脚踏实地的命运。
马车是一种象征,证实着父辈们的伟大,也是那个时代农人渴望兴旺昂扬向上的见证者,有了马车,便有了希望,更好像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马车,托起了农村走向城市的理想。我相信:每个那个时代的父亲,都做过一个关于马车的美梦。
想起了一首关于马车的诗:
一个夜晚,
我踢破了门,
沉睡中,
马跑光了,
在这漫漫的隆冬,
我墙上挂着一把皮鞭,
院的角落,
停放着我的马车。
作者简介:古保祥,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散文》《散文百家》《短篇小说》等杂志,著有长篇小说《世外逃缘》《幸福躲在时光深处》等,出版各类书籍40余部,作品曾获岳阳楼文学奖、韩愈文学奖、冰心文学奖。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