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惊涛骇浪中突围脱险
吴景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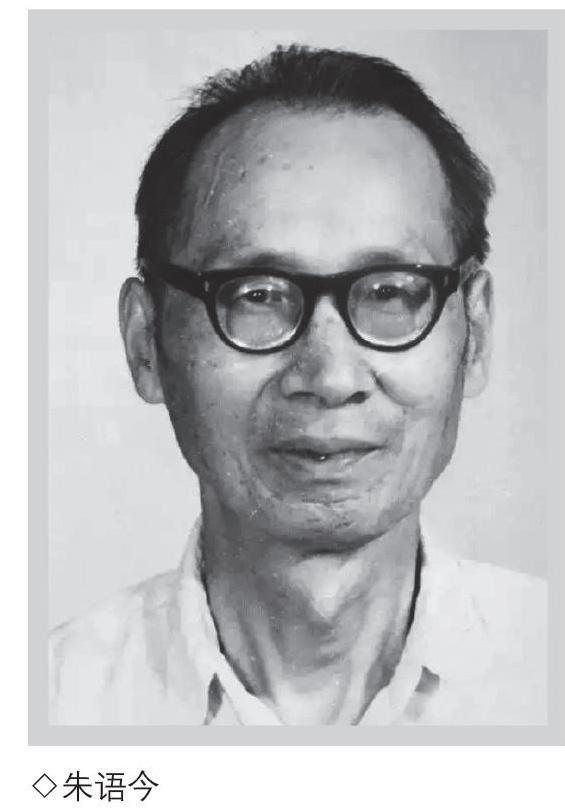

我的公爹赵隆侃是一名地下党员,担任过中共重庆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曾用名赵令芹、赵硕生、曹羡芹、吴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九龙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博物馆馆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
以笔作枪鞭挞黑暗社会
1922年,公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富有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赵宝鸿是清朝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学了10年化学,回国后担任江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
抗战时期,当日军快打到南昌时,公爹和家人匆匆作别故园,踏上了逃难的火车。之后,他和姐姐来到广西求学。在南昌、桂林读中学期间,公爹读过《新青年》、鲁迅的杂文以及毛泽东论抗日战争的相关著作,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后来,公爹考入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入校不久,他便与几位豪情热忱、勇敢坚毅的同窗结为好友。在频繁往来中,公爹慢慢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受其影响,公爹积极参加武大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46年,公爹来到重庆,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中学做教员,接触到重庆地下党的骨干廖意林。在她的领导下,公爹参与筹划、编辑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本刊物《反攻》。它是《挺进报》之外,地下战斗的另一种呐喊。
1947年10月,公爹用笔名“念”在《反攻》创刊号上刊载檄文《杜斌丞烈士殉难》。他血脉偾张地说:“在新的志士的鲜血面前,中国人民包括他们卓越的代表,各阶层的先进领袖,将洗清最后残存的一丝幻想,更坚决地团结到反蒋的义旗下面,进行毫无反顾地决死斗争……”
公爹还以新华日报社通讯员的身份,与该社《青年生活》专刊负责人刘光、编辑朱语今接触。他们成为公爹的引路人,鼓励他把笔磨得锋利些,如同鲁迅那般投枪、匕首,与黑势力搏击。
正义的力量激发出公爹熠熠的才情,《新华日报》上经常可见他的文章,文风犀利、充满硝烟,鞭挞和揭露当局的丑恶面目。他在《啼笑皆非录》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因为在野蛮与横暴之中,立下史诗般雄壮功勋的“八百壮士”流落在街头;被敌伪特工的狼犬撕死了的先烈的寡妇孤儿在啜泣,没有谁留给他们生活费用,政府没给过教养子女的恩典!因为兵士们还在被驱上另一战场,而和平的村庄泛滥着饥饿!
因为在野蛮与横暴之中,成千累万的青年不知根据那(哪)一条法律被拘捕起来:不须审判,无权辩护,更无所谓法庭。深夜里传出非刑逼供的惨叫,无尽的劳役磨尽他们的志气和青春,镪水池子或狼狗们的口腹是他们葬身之所……
我们要控诉这些。因为它们冒渎了民族独立的尊严,怒火已经烧得如此旺大啊,血火中,我们一定要再度新生,而且将锻炼掉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切!
在敌人眼皮子下斗争
1948年,因主要领导人被捕、投敌,重庆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大量组织被破坏,许建业、江竹筠等共产党人最后牺牲在黎明前夕。公爹是这段血写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勇敢的突围者。
对于当时的情况,公爹的学生和部下——老党员宋笠回忆道:“街上到处贴着‘肃清匪谍的标语;抓人的汽车鸣着警笛在马路上横行;报上天天是捕获了多少人的消息与通缉的命令。”
那时,不但重庆市委、川东地下党核心机关遭受了灭顶之灾,由党领导的北碚区学运特支、沙磁区学运特支也遭到了破坏,唯有南岸区学运特支保持了组织完整。而公爹是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
几十年后,公爹在《难忘的1948年》中,详尽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切。
1948年4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及学生运动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联系人张某(即冉益智,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急匆匆到渝中区捍卫路中学找公爹。他抹着汗,喘着粗气说:市里有个重要干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后叛变)被抓了,你们特支有危险,要着手准备应变,通知已暴露的转移,赶快疏散家属。
几天后,张某又满头大汗地来找公爹。这次他显得更加紧张和焦虑,连衫衣的纽扣都扣错了。他左右一顾,说:我得离开市区一段时间,我们过些天再联系。他附在公爹耳边匆匆交代了下次接头的地点和时间,就慌张离去。
张某刚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重庆渝女师一姓刁的反动教员,用太平洋通讯社的名义在报上发消息:该校学生罗宗哲“受共匪煽动下乡打游击”去了。放下报纸,公爹嗅到了不祥气息:罗宗哲是公爹的姨妹,他们存在公开的亲戚关系。而罗宗哲只是离校,在江津白沙镇小住。谁在捣鬼,为什么?公爹一激灵,立马送走快生产的妻子罗宗濬,然后赶到白沙镇让罗宗哲撤往成都。
一周后,公爹回到渝中区捍卫路中学。刚进校门,便有好友给他递眼色,悄声说:快走!前几天就有宪兵来抓你。公爹环顾四周,的确有些影影绰绰的陌生人在徘徊,直觉告诉他——自己暴露了。因为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他东弯西拐,就消失在蛛網密布的山城小巷。那一瞬,他对张某产生了怀疑。
到了接头的时间,公爹仍冒着生命危险到达指定地点,因为那是唯一能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通道。他躲在一个角落等候张某出现,直到太阳偏西,已超过约定时间几小时,却始终不见张某的人影。情况不妙,他得撤退。他明白,自己领导的特支已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
当晚,他找到特支主要成员商量,决定通知所有骨干从就职的单位和住地撤走。但撤走不是溃散,要与特支保持联系,随时待命。他指示,主要成员不能走远,选择好新的隐蔽点和联络点;尚未暴露的人员坚守岗位,继续观察;让擅长做生意的党员做点小买卖或变卖一些家产筹集转移等活动经费;想法从外地找到党组织。
7月底,重庆各大报纸刊登了张某叛变的自首书。张某出卖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硕生和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等。一时间,抓捕公爹他们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
战友们忧心如焚,劝公爹赶快撤离,投奔解放区。公爹说:我们走了,特支其他党员怎么办?党员都走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那些学生积极分子怎么办?谁来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让他们得以安全?我们共产党人在这种时候要有责任感,不能作鸟兽散。上海那样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我们的人都能潜伏下来,重庆还怕没有办法?党组织的上层出了叛徒,只要基层不乱我们就有希望……
那段时间,公爹和战友向洛新、黄冶、尹荣福、王大昭、石大周、刘承才、李诗强、李诗秾等从未停止战斗。他们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党组织,而黄冶、石大周悄悄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变卖,李氏兄弟起早贪黑地做生意赚钱,以备组织不时之需。南岸私立仁济高级护士学校职员宿舍成为特支的新联络点。每次相聚,公爹会分析时局,让大家看清前景。他还给大家讲解如何判断是否被敌特跟踪、联络地点是否安全,遇到特务盘查如何作答,一旦被捕怎样去承受审问、编造供词。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公爹表现得机敏睿智、乐观爽朗。他的朋友杨心惠回忆:“陈然被捕后不久,老向(向洛新)就转移到我所在的重庆私立仁济高级护士学校来当文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局怕洋人,不敢随便来这所加拿大教会办的学校放肆,相对而言要安全些。有一天我见到赵硕生与另一人坐在我的宿舍谈事情。赵憔悴无比,一脸病容,一问才知竟是最近吐了血。我问赵:‘安全有无问题?赵微微一笑,掏出钢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以捉迷藏的战术与彼周旋。”
我也问过公爹,怕不怕?他取下老式黑框眼镜,露出腼腆又神秘的笑容:当然会怕啊!但人被逼到崖壁了,每天都高度紧张,好像就忘了怕这件事情。他说,自己无数次从敌人的通缉布告前走过,看到上面写着“赵硕生”三个字,便会低下头抿嘴一笑——没想到这个名字竟会用到这里。
突围路上机智策反
即使公爹与同志们百般谨慎、万分小心,意外还是发生了。
1948年9月初,公爹和两名同志用化名,以养病为由,托朋友租房住到当时江北县龙兴场。那里成为南岸特支的新联络点。一天晚上,一群乡警突然涌进他们的住宅,以户口不实为由,将公爹和王大昭(还有一位同志恰好去了镇上)押到乡公所。原来,王大昭带去的一本苏联日历引起了房东的亲戚——一位县参议员的注意,认为他们有共党嫌疑,于是密报乡公所。但乡里并不知道,他们逮住的竟是叛徒冉益智正带着大批特务急于想抓到的赵硕生。
公爹他们被关押在乡公所黑牢里快一周了。牢房是打不穿的,没有里应外合,想跑是天方夜谭。可乘之机在哪里?看着天天在他们眼前晃悠的看守,他们决定利用各种机会与看守攀谈、接近。
一众看守中,有个小警察引起公爹的注意。他叫吴大明,只有十六七岁,面庞白净,说话时语气温和,还带着这种环境中难得的热忱与恳切,但神情里藏有与他年龄和身份很不相称的沉郁。公爹与他交谈,发现吴大明竟和自己的学生——育才学校的冯鸿甲是好友。话越发投机,往深处去,公爹便察觉这位青年对警所的黑暗不满,对自己的差事很厌恶,对未来的人生忧心忡忡。
公爹把监狱当成课堂,给吴大明讲起古今中外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他们追逐理想的奋斗与牺牲,生而为人的操守与底线。公爹慷慨激昂的正气,激发了这个青年警察内心的良善。
公爹拍着他的肩说:“你还这么年轻,在如今的世道混,得长个心眼哦,谁知明后年又有什么变化啊?我们小老百姓都得为自己留条路。”吴大明点点头,悄声应道:“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押你们,但能认定你们是好人。”
公爹试着让吴大明去处理租房里值钱的家什,变些现钱。后者利索地照办了,把所得的钱如数交来,并报信:乡里要把你们押往市里,会在朝天门住一夜。公爹他们决定,一定要在几十里徒步途中或在朝天门停留的时候跑掉,否则在市里遇上叛徒就完了。
启程前,公爹拜托吴大明找个“好说话”的警察作为押送人员,并告诉同行的警长,路上的费用由他俩“生意人”包了。警长异常欢喜,以为撞到了一桩肥差。
一路几十里,三个警察押着两个共党嫌疑犯赶路。被吴大明押着的公爹磨磨蹭蹭,故意掉到了后面。公爹压低嗓门对吴大明说:小兄弟,设法帮我们逃走。吴大明惊诧,举棋不定,额头上满是细汗。公爹理解他的犹豫,但仍循循善诱地给他讲道理。
所剩里程越来越短。吴大明看着远处模糊的街市,咬牙道:好,我帮你们,但有个要求,我要和你们一起走。公爹激动地攥着他的手。
当晚,他们住进朝天门的旅馆。公爹给了警长一些“辛苦费”,警长便出去花天酒地,半夜才踉跄而归。趁警长不在,由吴大明搭线,公爹他们又做另一位警察老李的工作。老李是穷苦人出身,良知未泯,愿意放走他们。但放人,自己是要坐牢的,老李只希望家里生活有个安排。公爹大喜过望,立马答应给他二两黄金作安家费。
钱从哪儿来?在吴大明的“押送”下,王大昭立即去找在《中国晚报》当记者的“亲戚”石大周筹款。因没找到人,王大昭只好打电话给在华康银行上班的张遐君,用暗号请其转告组织弄一笔钱来营救他们。
脱身的计划差点失败。张遐君当晚没找到特支的同志,也没法筹到钱。好在第二天早上,警长嚷着自己还有公干要忙,让吴大明等看好疑犯。警长前脚出门,公爹他们后脚便由小吴和老李“押着”,暂到小什字大同茶社喝茶,寻机再与“亲戚”联系。巧合的是,特支委员向洛新刚路过这里,就看到公爹一行人走进茶社。
向洛新马上找到在附近泰裕银行上班的李诗强,两人随即向茶社走去。向洛新在《难忘的一段经历》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刚跨进茶社,赵隆侃就立即起身招呼说:‘我们做生意欠了钱,赶快在两小时内拿××元钱来,否则一切都完了。我和同行的李诗强便分头行动。我找到住天福巷的宋笠同志,他动员母亲拿出金膀圈等首饰去作抵押,换回二两黄金解了燃眉之急。我又赶回大同茶社把钱交给赵,他即刻交给李姓乡丁。然后赵隆侃、王大昭、吴大明和我一起离开了茶社,脱离了险境。”
事后,警察老李被关押了一阵,算是惩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而跟着公爹離开的吴大明,随后到育才学校读书,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1948年的惊涛骇浪中,南岸学运特支避免了被破坏,完好无损,没有一位同志被捕和牺牲。通过严格审查,他们还陆续接管了一些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党员和六一社成员。到该年10月,特支的党员由十几人发展到30多人,六一社成员也由几十人增加到200多人。
暗度香江与党联系
寻找上级党组织,一直是公爹所在特支成员的心声。他们曾试图找上海和川西地下党组织接头,皆因情况复杂未能成功。
他们从报纸上得知,敌人正在搜捕两个“胖子”,一个姓邓,一个姓萧,说这两人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角色。公爹他们尽量打听邓、萧的信息,以分析他们是不是组织派来的领导人。
公爹又打听到他的老领导朱语今转移到了香港。于是,他以曹羡芹之名,给自己最好的朋友、香港《大公报》文化副刊编辑罗孚(罗承勋)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引用一句唐诗:“故国遗墟在,登临想旧游。”称自己很孤独,十分想念远在香港的朋友。罗孚回信:“四海非不宽,可语今几人。”并说“嘱打听的荣君已知其下落。若来港,请顺带一点‘太太豆瓣,因此间不易得”。公爹明白,罗已联系到朱语今,且朱让他立即赴港。他回信罗孚,用了李白的诗“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暗示会尽快启程。
公爹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收到香港来信的心情:“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
1948年11月中旬,公爹从重庆白市驿机场飞赴香港。见到朱语今的一瞬,他鼻子酸楚。
公爹迫不及待地汇报了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朱语今连连叹息。过了两天,朱语今带来一位领导。他30多岁,带着江浙口音,一见面就紧紧攥着公爹的手说:受苦了!活着就好哇!我们也急着想与重庆、川东地下党重建联系,让党少受些损失。
他简明扼要地向公爹布置了任务:一、回去尽快与邓照明(即邓胖子,时为上川东工委书记)接上头,以后南岸特支由他领导;二、通知邓照明和萧泽宽(即萧胖子,时为川东临委负责人),尽快有一人来港接头;三、向邓照明传达上级关于《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他叮嘱道,因为危险重重,文件不能带走片纸只字,你要认真领会、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同志转述。
公爹晚年,仍可以把这份文件一口气背诵出来。除了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更在于每个字已经烙入他的内心。
返渝后,公爹和邓照明在化龙桥的适存商业专科学校接上头。公爹在《难忘的1948年》中写道:“从我来说,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孤军苦斗8个月之后,终于与当地党的领导机构接上了关系,真像是乱离后亲人的相聚,一颗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消失了。更何况照明同志热忱、坚毅而机敏,给人一种阅历颇丰的成熟感。”
1949年3月下旬,邓照明约公爹在李子坝一家茶馆接头,神情庄重地向公爹传达了组织的决定,提名他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庆代表,从香港转赴解放区出席会议,并把重庆的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
公爹飞抵香港后,不但与朱语今重逢,还认识了党的隐蔽战线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钱瑛大姐。之后,公爹跟随钱瑛绕道烟台、济南、天津,于4月中旬扺达北平,他们一行住进了中南海。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公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他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尽情共享了解放军攻克南京那一夜的欢腾,他们翩翩起舞,热泪盈眶。
革命初心一生追随
公爹的长文《难忘的1948年》,发表在1992年《红岩春秋》第1期上。文章刊出时,公爹已离世近半年。也就是说,在接近生命尽头之时,公爹深深缱绻着的仍是自己青春年华的日子和与之共赴信仰之路的人与事。
公爹曾给我讲起江竹筠。他的声音低沉,像老电影放映时,时不时会发出的那种滞笨的嚯嚯响动。
公爹说,他只见过江竹筠一面。那是1947年深秋的一个疾雨黄昏,公爹在渝中区捍卫路中学教职员宿舍正准备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廖意林。此时,门被叩响,他开门看见一位个头不高、单薄瘦弱的女子。她穿灰蓝色旗袍,罩了件驼色毛线编织的背心,冲他一笑。她轻盈地闪进门,把滴着水的伞靠在门边墙根,便径直找了张椅子坐下。公爹知道这是党组织派来的入党监誓人。这位女同志向他扼要讲解了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随即口授誓词,让他宣誓,没有任何的陈设和仪式。宣誓完毕,他们热情握手,但互相不问姓名就匆匆告别,这是当时的组织纪律。重庆解放后,公爹才得知自己的入党监誓人是江竹筠。
公爹也讲起他亲眼见到许建业与李大荣被敌人五花大绑押着游街,在重庆大坪就义的事情。那天,许建业、李大荣在刑车上,公爹隔着攒动的人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悲壮赴死却无法相救。许建业一直高呼口号,声音从洪亮到沙哑,他以这种方式与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告别。公爹跟着刑车走了很远的路,默默地为两位战友送行:“作为他们的同志,我无比自豪!他们真称得上是意气扬扬,慷慨赴死!我也知道,许建业他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的明天。但也就是个死。死也要推翻这样黑暗的政府。”
晚年,公爹常说:“当年我们好些人啊,都没有活到能看着自己孩子长大的时候。像许建业同志连婚都没结,更别说能像我这样儿孙满堂、颐养天年,我知足了,知足了!”
我相信,那些挥之不去的画面,一直住在公爹的生命里,与他形影不离。
1988年9月,公爹即将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岗位上离休。组织上与他谈话,问:离休前对组织还有什么要求?公爹笑答:有的人把党组织视为“银行”,把自己的工作经历看成是在这个银行存了钱,退休时便要连本带利取出来。而我在这个“银行”里没存钱,所以我对组织没有什么要求。
公爹对我们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他还说:人的怨怒都是与他人比出来的,关键是拿什么来作参照物。那些躺在歌乐山土地下的烈士哪個不是青春昂扬、才华横溢的人?有些人还是富家公子和小姐。如果说捞世俗的这些东西,他们又捞到了什么,他们又划不划算呢?但人来世间走一遭总得要完成一种使命。我们这代人推翻了一个黑暗腐朽的政权,我们已体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1991年,公爹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69岁。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