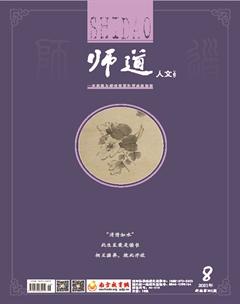略谈小说中隐性人物的审美想象价值
包云锋
在经典的小说中往往存在着一类只被人提及却不出场的隐性人物,作家设置这一类人物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美学韵味,更影响着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审美想象。他们在悲喜剧这一美学范畴中不断地提升作品的心理美学价值,唤起和突破读者的期待视域,防范读者的心理厌倦,引发读者对作品美的心理反应。
人物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塑造人物自然成了小说创作的基点,小说阅读教学中对人物的分析品悟是一个重点,而对小说人物的理解似乎都有规律性的定位:主要人物(主角)、次要人物(配角),对他们的分析是我们小说阅读和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但在一些经典的小说中还存在着一类隐性的人物,如《孔乙己》中的丁举人、《社戏》中的八公公、《变色龙》中的将军等。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基本“不开口”“没行动”,对他们的勾勒只存在于故事的叙述或小说主配角的言谈描述中。细品这些隐性人物,他们往往也是作者努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们身上并不缺乏审美价值,但我们却经常忽略和遗漏。心理美学注重于受众对艺术作品的美的心理反应,余秋雨先生认为“心理美学也就是接受美学,又可以称为观众审美学”[1]。他有别于我们一般意义的“审美”。本文就试着对这些小说中隐性人物对受众(读者)的审美想象影响,略谈一下它们在这一范畴的美学价值。
一、基于悲喜剧范畴的审美想象价值
美学的首要范畴是什么?在西方的古典美学范畴中界定为“悲剧美”和“喜剧美”,余秋雨先生认为“由于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继承性,这对范畴自然在心理美学中占首要地位”[2]。不难看出这个戏剧理论中的美学论断在小说中同样是通行的,在小说的审美想象中我们也可以借助悲剧喜剧这一美学首要范畴的有关概念。但在实际的小说阅读中对作品这些范畴的把握,也就是说读者对它们的审美想象影响并不是很清晰,小说中隐性人物恰恰具有帮助读者明晰这些心理美学价值的功效。
(一)校正小说悲喜剧的界定
对于小说是悲剧或是喜剧的界定,往往形成于小说阅读中对文本情感的初步把握环节,读者获得对小说的初步印象,更确切地说是对小说最初的审美想象。这一想象会对阅读行为中相继的环节,如对小说的主题、人物等或浅或深的分析都起到影响甚至是支配作用,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阅读时我们对小说基调的把握,纵观整个阅读过程,这种最初的审美想象可以不到位,可在以后的阅读中不断丰富,但它的准确性却至关重要。
在实际的阅读中,有些小说作品的悲剧、喜剧的内涵是变化的,形成我们并不罕见的“悲喜剧”;有些作品由于读者对作品背景不清晰、阅读视角的偏差、时代审美感的介入等造成了对悲剧、喜剧的误读和争论。我们虽然提倡主体性行为下的阅读,“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对小说根本性的审美发生偏差却是我们所不期望的。小说中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的隐性人物恰恰对小说悲喜剧的界定起到了强大的校正作用,同时也凸显其心理美学价值。在《孔乙己》的教学中,对孔乙己这个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也倾注了丰富情感的主角人物时,不少学生初步审美想象发生了偏差,由于学生所处时代的优越感淡漠了作品时代的凄苦,学生在文本关注上更多感同身受于“好喝懒做”“窃书挨打”等部分,得出了“悲剧不悲”,甚至是“罪有应得”式的喜剧审美想象反应。而利用“丁举人”这一隐性人物进行对照,诸如“丁举人中举前后和孔乙己的身份的异同”“丁举人毒害孔乙己的特权来自何方”等等的引导,迅速校正学生阅读时的错误审美想象,加深“悲剧之悲”的审美体悟。
(二)實现小说悲喜剧的融合
小说的文本和文字存在是客观的,它并不需要受众的审美经验,但经过读者的阅读加以审美想象使文字由枯燥的心理感受转换成无限生成的美的心理享受。因此,一些经典小说作品往往通过悲喜剧的不断融合,加大这种美学效果,使悲剧美在毁灭中更具庄严的元素,喜剧美则在荒诞中更具现实的成分。但在作品中实现两者的融合,实现两者的重叠和互相渗透,达到“悲即是喜,喜即是悲”的效果并不是一件易事。在一些大家的小说作品中往往通过塑造这些隐性人物在“无声无息”和“了无踪影”中实现了两者的融合,让小说和这些人物的美学价值得到了升华。
在小说《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这一形象给受众更多的是喜剧的审美想象反应,这个人物角色展示的美“以压倒性的优势撕毁着丑,对丑进行揭露和嘲笑”[3],在夸张和变形等艺术手段下营造出浓厚的喜剧效果。但在关注“将军”这一隐性人物时不仅获得是“变色龙之变”的原因,从深层次上来说更是作品背后的“悲剧味”,笔者教学中也碰到了学生中存在的一种包含有合理感受的误读,如奥楚蔑洛夫也展示了职场中小人物的悲哀,虽然并不赞同,但至少看到了读者对这一隐性人物在悲喜剧转变中的价值。其实如果抓住将军这一人物分析,明确他的利益不可损失是这一小说中“人物群”达成的“共识”,那喜剧效果从奥楚蔑洛夫这一个点扩散至包含赫留金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那社会的这种整体弊端作用于读者发出的更是悲剧式的喟叹,在此刻审美想象中喜剧和悲剧实现了互通互济,读者呈现的不是喜剧的“含泪的笑”,更多的是悲剧的“笑中含的泪”。
(三)调配受众悲喜剧的视角
余秋雨先生认为“从深层心理上说,悲剧美和喜剧美,对应着人类对社会物象的仰视需要和俯视需要”“对悲剧美的仰视和对喜剧美的俯视是受众一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最高实现方式”[4]。其实对于仰俯视角确定这一审美行为在小说阅读中并不是一件难事,选择俯视还是仰视这种审美想象反应,读者一般都会依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作出本能的选择,其正确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对这些人物俯视和仰视的角度却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美的感受程度,这也自然成为了教师教学引导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小说中的隐性人物真是在对这些角度的调配中体现了它的价值。
在小说《故乡》中,通过对闰土这一人物前后变化的研读由浅到深地获得悲剧的审美想象体验,但闰土的“毁灭之悲”在这种视角下品悟是远远不够的。在人教版的教材中此篇课文的课后习题中曾经列出过“悲剧轮回”这一主题提示,这一难点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淡化或生硬地传授,其实在此篇小说中存在着一个类似隐性人物的角色——闰土父亲,对他们父子的人生历程的相似度的比对,还有文本中“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等细处的研读,自然会感受到“悲剧轮回”,对闰土仰视的角度陡增。同样在《变色龙》中,正是将军这一隐性人物的无声的专横让奥楚蔑洛夫由狡诈多变的“变色龙”向趋炎附势的“走狗”转变,对这一人物俯视的角度的拉大的同时对作品的审美想象感悟得到了提升。
二、基于期待视域范畴的审美想象价值
一部作品“其实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5],所以一部经典作品从更深层次理解它是为受众创造的,甚至要达到“一部作品要流传下去,它就得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进行对话”[6]。但受众主体的审美能力是审美发生的重要前提,他们在接受作品美并作出审美想象反应行为前并不是真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读者的期待视域。余秋雨认为“期待视域就是一种预置结构,这个预置结构由明明暗暗的记忆、情感积聚而成,与作品的结构相撞击,并在撞击过程中决定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并决定是否突破这种预置的心理结构,把审美活动推向新的境界”[7]。小说中的隐性人物同样具有甚至超越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在此方面的美学作用和价值,他们通过预告、修正、突破读者的期待视域实现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想象感受升级。
(一)预告作用下唤起期待视域
对任何作品的审美活动必须链接到作品所折射的时代,同时对于作品创造的作者来说他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艺术心理定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者习惯的知识、经验和思想等。作品一般“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供一种特殊的接受”[8]。在此方面中,其实小说中的隐性人物和其他人物一样在起到预告作用来唤起读者正确的期待视域,《孔乙己》中丁举人、孔乙己和短衣帮们一样调动着读者以前的审美经验,回忆起鲁迅小说常见的主题、写作目的和小说创作技法等。但隐性人物在加深期待视域的价值是其他人物所无法比拟的,同样是《孔乙己》正是丁举人的身份唤起了读者的阅读记忆,期待视域定位加深到“科举制度”这一区域,在审美想象过程中更好地调动了相关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
(二)修正作用下突破期待视域
宗白华先生在《艺术欣赏指要》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看来,美学就是一种欣赏。美学,一方面讲创造,一方面讲欣赏”。在艺术作品的审美活动中读者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只在欣赏,更是在品美的过程中运用个人的审美倾向和趣味等积累对美进行创造。他们也不会单纯地保持预告下形成的阅读期待,往往会发生不断的改变甚至重新定位等修正行为,突破原有的期待视域,使阅读深入,审美过程深入。《社戏》中“八公公”这一隐性人物在这一方面作用尤为突出,当然其心理美学价值也尤为突出。在鲁迅笔下这群农家少年展示着可爱、淳朴的一面,让读者可以形成类似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真、自由的审美想象。而八公公这个小孩眼中“很细心,一定会知道,会骂的”的厉害人物,竟“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使审美想象瞬间上升到了:平桥村民风淳朴,所有的大人和小孩一样朴实无私;甚至稍加串联就可以去区分《故乡》中同是故乡景色的描写,为什么前面的是记忆中的而后面是理想中的故乡;当然《社戏》中的平桥村更是鲁迅理想世界的勾画,在连环式的修正中期待视域被不断地突破和扩容。
另外,当一部作品初步感悟后展现的内容和你的期待视域十分相近时,这部作品就会显得浅显和低劣,往往不会让读者产生深刻的审美愉悦的心理反应。经典的作品往往会注意让人物不至于一览无余,会在作品深入中让内容和读者的期待视域发生冲突、对峙,甚至有时会让读者对人物、作品形成“误读”,让你的审美想象产生新的困惑点和兴奋点,然后在不断地多方修正中形成新的期待视域。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小说隐性人物的“被出现”或“被描述”往往是这些突破的节点,这些审美想象的“掘进过程”自然让他们自身的美学价值不断增色。同样是《孔乙己》中的丁举人,在文章的开始他作为成功的“穿长衫的”读书人出现,让同样是读书人的孔乙己感到可鄙;在孔乙己對他留给自己伤疤的辩解中,让读者对孔乙己感到可笑;在小说结尾他对孔乙己的毒害,却让读者对孔乙己感到可怜、对社会感到可憎,在丁举人行为的牵动下对他和孔乙己等人物的感受在冲突和修正中不断深化,期待视域不断突破,对人物的美学价值的反应也不断地增强。
三、基于对心理厌倦防范范畴的审美想象价值
在审美过程中作品通过内在的或生成的各种机制有效地调动着读者的审美状态,让他们主动和亢奋,但对于审美这种心理感受过程来说,它不可能持久地维系。正常情况下,在一段审美高潮后必然会面临心理厌倦的困惑。因此优秀作家在作品中总会想方设法地在审美过程中防范读者的心理厌倦。常见的方式是运用诸如让小说情节更复杂,人物更善变等手段,但从我们的审美心理过程来看,这并不是一条有效而科学的途径,复杂化只会增大读者审美过程中的疲劳感,从而累积心理厌倦感。
小说的这些隐性人物,他们或是淡淡几笔,或是随口几句,他们与浓墨重彩的主角和不乏笔墨的配角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想象体验,他们所具有的心理美学价值有效地防范了读者在近乎相同类型或渐渐可以预期的美感刺激中的钝化,有效地转变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了心理适应后的可能退化的对美的敏感度。
(一)心理对比下的美学防范价值
小说在情节设置的冲突中彰显人物的不同类型,人物间往往可以形成相互的对比,这样也营造出丰富的单个人物或人物群体,这也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物塑造时应重视的人物美学价值。小说中隐性人物由于篇幅较少,加上近乎缺乏的描摹在这种对比心理程序下让读者激发的审美想象价值是微弱的,和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不具有可比性。但在一种特殊的对比心理程序下喷薄着异样的心理美学价值,更有效地防范了审美过程中的心理厌倦,那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美学价值呢?
余秋雨先生认为“一种包含着足以抗击观众心理厌倦的‘免疫力的对比性心理程序”,就是需要作品中“使观众猛烈地意识到日常生活的存在,正常理性的存在”,因而“陡然产生人性体验和魔性体验的强烈对比”[9]。在小说的审美过程中,通俗地说就是让读者在虚构的情节和人物之中能体会到如在现实中的心理领受和体验,这样虚与实的对比性心理程序,让观众即便是一次次、一遍遍地重复阅读,也不会产生心理厌倦。相对来说情节、人物的丰富手法可以在首读、初读时起到防范心理厌倦作用,但随着阅读行为的深入和重复,防范效能几乎绝迹了,小说也能成“经典”了。经典小说中隐性人物恰恰体现了作者塑造他们的苦心孤诣,他们的身上正具有这样的心理美学价值。契诃夫的《变色龙》旨在揭露19世纪的俄国沙皇统治的黑暗,但就是现在的我们对奥楚蔑洛夫形象也很快会形成共鸣,似乎在你的身边或社会上或多或少能捕捉到奥楚蔑洛夫的“化身”,难道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社会都是孕育奥楚蔑洛夫的温床?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是不是和小说中塑造的将军这个隐性人物代表的“特权之上”有关呢?社会不会雷同,恰是将军式的“特权遗毒”让你在阅读虚构小说中无形地和现实进行了比对,这种电击式的审美想象反应自然让作品百读也不厌。
(二)虚实蓄势下的美学防范价值
小说塑造的人物的美学价值,我们可以借鉴戏剧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一级作家梁秉堃在谈曹禺的戏剧创作时,强调了曹禺先生的观点“戏剧美在于含蓄”。确实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详略结合、虚实相生,让人物摇曳多姿,唤起了读者丰富的审美想象,在赋予人物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也一定程度地防范了审美的心理厌倦。小说中隐性人物在这方面也同样和上文提到的人物对比一样,显示着这样的防范价值,但同样很微弱。可它在人物的虚实结合中所具有的蓄势作用昭示着这些人物特别的美学价值,让心理厌倦得到更有效地防范。
余映潮先生認为“小说的蓄势指的是运用一定的手法,一步步地描叙事物,形成氛围,以达到小说高潮的到来进行充分地足够地铺垫。同时蓄势让情节更显得扑朔迷离……,故事就非常有韵味,就有着十分引人的魅力”[10]。在一些小说中那些旨在虚写的隐性人物往往被多次“点到”,这种最简单强化方式就是一种有效的“蓄势”,这些特殊人物自然会让情节波澜起伏,但同样也生发了读者对他们探究的渴望,读者不自觉地对他们进行自我色彩的人物填充,为这些人物自身的美学价值、小说的美学价值不断积蓄能量,直至小说高潮处集体性地爆发。这些虚写笔调下的隐性人物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过程不断蓄势、増趣、聚变的过程就是其对美学心理防范价值的全面体现。我们再次来细品《变色龙》中的将军形象,在奥楚蔑洛夫由于涉及和不涉及将军利益的不断“变色”过程中,在围观的人对将军不断地提及中,让读者对将军的形象把握的兴趣不断激发,他的内涵也不再是“将军”这两字所能包含,在这样方式下的一次次蓄势中,对统治者的丑恶和专横,社会的黑暗等这些产生奥楚蔑洛夫的“变色”的终端不断熟悉,审美想象过程也随之不断向高潮进发。
总之,小说中的隐性人物由于其简略的原因,往往会在小说阅读和小说教学中被边缘化、甚至忽略,但他们所蕴含的美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在审美过程中同样对读者产生着不凡的审美想象影响,对他们虽然不需要过度的强化和拔高,也无需在教学环节中习惯性地刻意突出,但对他们美学价值的有效挖掘对小说整体的审美过程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2]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3]牛宏宝. 美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5]牛宏宝. 美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7]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8]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9]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10]余映潮. 欣赏小说的表达技巧[J]. 中学语文,2012(5):18-19
(作者单位:江苏无锡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