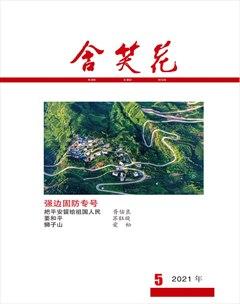大火焰杂记
陈刚
云南的七月,天是顶喜爱下雨的。去麻栗坡那日,天色阴暗,雾气包藏山峰,裹挟着雨水。车在山林间疾驰,穿梭,隐没,片刻不停。山高路远,采风的一行人到达麻栗坡县城后,做了短暂的休憩。
麻栗坡县城四周环山,山底有一条河,河水绿茵茵的,名叫畴阳河。城里人依河而居,在两岸修建了居所。受狭窄、陡峭的地形制约,各家的房舍占地面积虽不大,楼层却是建得极高。财力充盈的人家还建有地下室。城区的大致样貌与山城重庆形似。
麻栗坡多产麻栗树。城区四周山上的麻栗树,枝叶繁密的,四季常青。麻栗树的生长速度极慢,长至人高,便要花费去十余年光景。麻栗树生长虽缓,但山里并不乏近十米高的大树。麻栗树的枝干坚韧,水分少,砍倒了不需要经过晾晒便能生火,且耐燃。砍伐时,刀斧若是不够锋利,是极难撼动的。除外,麻栗树还具有防虫蛀的特性,不易朽坏。路边商贩售卖的各式农具中,使用到的木料部分,也多是用麻栗树制成的。走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用至“包浆”的锄柄。
深秋时节,麻栗树的果实成熟后,果壳呈青灰色。放牧的人见了,会择取些,待回到家后,便将其置于火塘内烤。麻栗果坚硬的果壳,经过炭火炙烤,会变得香脆。吃的人坐在火塘边,用火钳夹出果子,边吹气降温边剥壳,清理洁净后送入口中。烤熟的麻栗果颜色宛若羊脂,口感香脆,但不易消化。
麻栗坡年轻的妇女,体态纤细,爱美。她们捡到圆润的麻栗果,不忍一吃了事,会用纳鞋底的锥子将果体钻通,刻上各式纹理,做成饰品。
沿河走了一会,我们继续乘车往大山深处行去。下午五时许,我们到达了大火焰村。彼时,天色尚且明朗,四处皆有蝉鸣。我们一行人在农户王荣天家吃晚饭,大家都喊他老王。老王家的住宅旁,有一条自崖壁上倾泻而下的山溪,水落地上的声音很是清脆。随风飘动的水汽滋养着岩块上的青苔,使其显得格外油亮。
大火焰村居于谷底,山高,天黑得快。树上的蝉仍在奋力地鸣叫,室内却早已亮起了灯火。饭毕,我便留在了老王家。其他人则继续乘车前往其他村庄。半个小时后,夜降下了它的帷幕。湿润的雾气在黑夜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浓厚了。
次日晨,浓雾散尽,大火焰村的原貌得以显露。村子依山而建,前有一条小溪,背靠山石。村口的公路自各家门前经过,蜿蜒向前,连通越南。
老王留短发,人长得黑壮,爱抽水烟。喂完牲口,他见我起了,便邀我喝早茶。他将水烟筒递给我,我觉得呛,没接。我递纸烟给他,他说劲小,也没要。我二人相视一笑,坐在火塘边喝茶,闲聊,各人抽着各人的烟。我生性内秀,不擅长言辞。老王却与我相反,他话题极多。聊到大火焰,老王说村子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说着便起身拿墙上相框里的照片给我看。在西南地区,过去有一句俗语:“汉族在街头,苗族在山头,壮族在水头。”老王一家是苗族,过去的村落建筑与现在的砖楼自然不同。老王称自己在山头的村落为寨子。寨中建筑多用木材修建的。老王家的房屋有三层。一层由几根粗直的圆木柱子搭建的墙壁构成,用于圈养牲口。较之一层,二层与三层多了木墙与木扉,分别用于生活起居,堆放粮食。屋顶盖的陶瓦,呈深灰色,有筒瓦与板瓦两种。板瓦是曲面方形的,筒瓦則如同刨去半面的竹筒。好的瓦片,应是色泽一致,无破损,缺边,掉楞,裂纹等缺陷。瓦片的铺设工作极简便,却需技巧。铺设时,屋脊应平直,脊与瓦接触的缝隙处得严密。才能使瓦在屋面上“坐窝牢固”,无下滑的现象。其次,盖瓦的人,应不恐高。为避免人从高处跌落,居下打杂的人,只静默地做着自己的事:不敢高声语,恐惊盖瓦人。一座好的瓦房,常是两者俱佳——形似飞燕,质若鱼鳞。
苗族的寨子,多是由这样一间间同多异少,相互依靠的榫卯式房舍组成。在苗寨里,唯建在寨子中央的宝塔式建筑,能让人一眼寻出许多的不同之处。此宝塔式的建筑,最下层由杉树或松树立柱支撑。立柱外圈18根,内圈4根,共计24根。宝塔共计十一层。每层各皆是八边形制,覆有青瓦,瓦沿扁长。逐层而上,塔身渐小,且每层都有屋脊兽。居于最高的两层,间距逐渐增大,形制为一至九层的逆转,似僧帽。屋脊兽种类极多,常见的有龙、天马、凤、狻猊、獬豸等。据传,苗族是蚩尤的后代。老王寨子里宝塔上的屋脊兽便是蚩尾。蚩尾,也称鸱尾,是水之精,修之,能辟火灾。此宝塔式的建筑,有个极贴切的名称,叫八角塔楼。八角楼的一楼,有木质靠椅供人歇脚,却只在喜庆的节日使用。因其内可存放芦笙,亦称作“芦笙楼”。楼内有能够伸缩的楼梯,人可由下往上攀爬,存取芦笙,或是对楼身进行修葺。但因楼内空间狭窄,人置身其中,得蜷缩着身体,无法长时间地逗留。
老王看着照片里的图景,神情怀念,低头“咕嘟咕嘟”地吸口水烟。“既然舍不得寨子,为何还要搬迁?”我如是问老王。老王复吸了口水烟,答曰:各有各的好处。山上的寨子是族人世代生活的住所,时间长了,难免生出感情。而今迁进的新居,盖房时国家给了补贴,且距离越南近,交通便利。当然,最重要的是村里人和“大火焰”这个村名没变,虽不似故土那般熟悉,却可以做边贸生意。
抽完水烟,老王起身去宰鸡。我在一旁给他打下手,用水壶接院里的水放在火塘的三脚架上烧,给他烫鸡毛使用。清理好鸡,老王说鸡得用子母泉的泉水煮,肉质才鲜美。我二人带上打水的工具,行至村口,便见到了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卡点。守卡的是大火焰村的村民,每两户人家轮值一日。我与老王去时,守卡的是三个妇女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我穿着白T恤,黑色运动裤。他们穿的都是苗服。隔着十多米远,他们便对我这个衣着“怪异”的外地人有了警惕,纷纷戴上口罩。走近后,经老王的一番解释,我在卡点依次登记,量体温,扫了防疫的二维码。因天气热,我出门时并未戴口罩。办好手续,我正欲往前走,他们却问我为何不戴口罩。询问声入耳,我面带愧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们见我的踯躅样儿,忍俊不禁的。笑毕,他们给我讲了边境防疫的规定,并赠予了我一只新的口罩。
子母泉在村后的山坳里,四周长满翠绿的树,杂乱的青草,穿过一片玉米地便能看到。子母泉镶嵌其中,宛若两颗猫眼石。积蓄泉水的池子由石头砌就,一小一大,小的是母泉,大的为子泉。母泉修在高处,蓄有一方水,偏矮的一侧开有小孔,幽凉的水自孔洞内流出,而后汇入子泉。母泉如同一位正在哺育子女的母亲,流出的水平缓,而又竭尽全力,不知疲倦。较母泉的狭小,子泉则大了不少,只深度,目测就有三米深。泉内有两群黑头短尾的蝌蚪,一上一下的,静止不动。我看了许久,蝌蚪仍无半点动静,不禁疑心是假的。我随手在路边折取了一棵象草,欲一探真假。象草在麻栗坡各处的乡村极常见,几乎每户农家都会在石漠化严重的荒地,路边,或是地埂上种植。以给牲口提供草料,养护水土。
剔去象草肥嫩的叶片,我将其伸入水中搅扰蝌蚪。看似距水面只有半尺深的蝌蚪群,任我用细长的草茎如何去够都无法触碰到。直至我的手肘没入水中,蝌蚪方才缓慢地游动了一下漆黑的躯体。它们只游动了几厘米便停下,似乎是在对我的行为表示不屑一顾。好在我得以确定它们是活物了。
天气虽炎热,可子母泉的水却是清冽的。老王用自家中带来的水瓢舀水。水在泉里是淡绿色的,在木瓢内是褐色的,到了桶里是天蓝色的,并无半点杂尘。打好水,我与老王二人各提一桶回家去了。关于子母泉,大火焰村还流传着两则传闻。一则是:孕妇饮子泉水,得男孩儿;饮母泉水,得女孩儿;若是两水混合饮下,便能生双龙凤胎。这则传闻,老王是不愿相信的。可当儿媳怀有身孕,老王与他的老伴却又是每日到子母泉取水给儿媳妇饮用。儿媳妇生产时,果然诞下了一男一女。第二则传闻,是大火焰村的村民在子母泉内放养了金鱼引发的。据传,金鱼入池内后长势极快,鱼身有巴掌宽。泉内的水自金鱼放入之日起,便日渐浅了下去,最后竟有了干涸的势头。那年,大火焰村近三个月滴雨未落。村里的老人说,不下雨是因在泉内放养了金鱼所致,村民便将信将疑地取出了金鱼。是夜,天空中果然落下了滂沱的雨。
午饭的主菜是老王煲的三七鸡。饭后,老王的老伴与儿媳二人洗过碗筷,复坐在了缝纫机上。老王到院里喂牲口。我无事可做,便坐在一旁看婆媳二人缝制衣物。缝制的布料是从镇上批发商手里买来的。婆媳二人的工作是布料上“撒花”。听多了他们用苗语交流,加之老王的教导,渐渐的,我也学了几句像吃饭、再见、你好这样的常用苗语。苗族的支系众多。从老王一家的穿着来看,应属于白苗。老王的儿媳与我同姓,且都是单名,叫陈燕。陈燕人长得水灵,爱笑。婆媳二人缝制的图案中,动物有龙、凤、老虎、蝴蝶等,植物以梅、兰、菊、桃为主,色泽艳丽,对照强烈。缝制图案时,针法讲究疏密聚散的变化,采用了满地花的方式,注重服饰整体的协调感。陈艳她婆婆缝制的图案,则显得庄重华贵,有牛马、花木,生活劳作以及节庆时的场景。看上去热情奔放,饱含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陈艳缝制的服饰,图案虽不似婆婆那样花哨,却也含有着许多的寓意。如林黛玉进贾府那般,处处精心,针针有意。在陈艳的介绍中,我还了解到苗族服饰中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元素。譬如:褶裙上的线条,是苗族先人迁徙时跨过的河流,翻越的山岭;花腰带上的“马”字纹和水形波纹,是迁徙时万马奔腾的景象;背牌上的方形环纹,是古时他们曾经拥有却又失去的土地。
陈艳只读过初中,义务教育完成后就回家一边务农,一边跟随母亲学习刺绣。这些民俗知识,她便是在这段时间里学到的。陈艳边缝制衣服,边与我交谈。在我二人的谈论中,她提及最多的,属苗族的花山节。
苗族的花山节,也叫踩花山,跳花,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初六举行。届时,来自各个村落的人,便潮水般地涌入花山场。围绕“花杆”跳三步舞、蹬脚舞,打“芦笙架”,跳狮子舞,斗牛。青年男女则穿着苗族色彩艳丽的衣服,对唱山歌,倾吐钟情,一旦相爱,即互赠信物,直至缘定终身。
陈艳与她的丈夫,便是在花山节那日,通过对唱山歌的方式认识的。最终,两人相互倾慕,并结了婚。我知道壮族青年在对唱山歌双方中意后,女子会将自己缝制的鞋垫赠予情郎,作为见证双方爱情的信物。至于苗族会送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向她打听具体唱了些什么内容时,她面带羞色,只说“用苗语诉说爱情,你听不懂。”其余的便不再多言。而关于信物的事儿,更是只字未吐,只顾着低头掩面而笑。
陈艳讲的踩花山中,我最喜爬花杆那段。
花山节无杆不成花山。花杆是用一棵粗直的杉树做成的,高约30米,刮去树皮,修去枝叉,仅留顶尖上青翠的树冠。花杆用绳索立直,埋于选好的花山场中心。活动的举办者会在距杆顶两三米的地方,挂上红、黄、蓝、白四色寓含喜庆的长幅彩旗,以及芦笙、猪头与几斤白酒。爬花杆不仅需要充足的体力,还得性格坚韧,讲究技巧,方能登顶。杆上凡是爬杆者能够摘取的物品,皆为其所有。当然,大部分的爬杆的人并不具备这些能力的,多是因为力竭,爬几下就顺杆滑落,做了无用的功劳。
生活在农村的人,是离不开土地的。大火焰村的村民,虽然各有各的营生门道,平日里却也种点儿庄稼。老王家种的是玉米。忙完家务,老王收拾农具,预备着去地里薅草,让我在家闲着。我不喜静,想随他去。他便让我提了桶红色的油漆。
老王家的地石漠化严重,如若不是石缝里长了翠绿的玉米,我想在地的前面加上个“荒”字,或许定义的更准确。地里的玉米植株矮小,加上花穗,才刚有我的肩膀高。穗叶包裹的玉米棒,也只有我家乡的三分之一。自老王的父亲去世后,老王有巡边的习惯。只要家中无大事,他每日外出劳作时,都会沿着大火焰村附近的界碑走一遍。薅完草,天色尚早。我二人便朝边境线走。大火焰村的山从远处看不高,山势也平缓。可当开始攀登时,我才知道其中的艰险。山里遍地是坚硬、突兀的石头,杂草与带刺的藤蔓充塞其间,每走一步,都需要借助刀棍开道。老王在前用刀开路,我紧随其后,用粗硬的象草秆拍打戳人的藤蔓。时近三点,天干气燥的。我与老王每隔十五分钟左右,轮流饮一次行军水壶里的水。水才下肚,便立马转化成豆大的汗珠从身体里冒出。行军壶里的水,也渐从清凉转为温凉。
时近两点半,气温到达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水很快就被我二人喝完了,然而身上的汗却还在不停地流。我与老王二人各用象草叶做了一顶草帽遮荫。爬到山顶,我的衣服贴在了皮肤上。“那里就是越南的寨子了。”歇了口气,老王指着前方山脚下的村庄说。我从背篓里拿出望远镜,聚焦一看,发现越南的村落与大火焰村很相似。
村里有穿苗族服饰的人在活动。老王说那八成是从他家买去的。仔细观察,越南的村落与大火焰村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墙上挂的是黄星红旗,大火焰村挂的是五星红旗;越南村落里的建筑较之大火焰村简易,显得落后不少。在405界碑,老王一直朝四野观看,似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我循着他的方向看过去,前方除了山,别无他物。老王看了一会,显得有些失落。他从背篓里取出一块洗到泛白的毛巾擦拭著界碑。我不知道该为他做些什么,便用锄头清理界碑附近的杂草。清理好界碑,老王开始用油漆给界碑上的字增色。看着变得缄默的他,我试着找些话题。老王一边刷漆一边与我说话。从谈话中,我得知毛巾是他父亲平日里洗脸用的。刷到最后一下,老王说:“我父亲的腿就是在这被炸没的。”
我想,老王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如果他父亲没有触雷的话,应该还健在。人死不能复生。老王懂得这个道理,故而他通过这种方式纪念逝去的父亲。回到家,我将在界碑附近捡的小石头送给他。他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收下了。
余下的几日,老王带我到大火焰村附近的各处边防哨卡走了一圈。返程的车队抵达大火焰时,老王给了我一个礼盒。车再次启动。老王站在家门口笑着向我们挥手,动作显得有些生硬。我回以同样的礼仪,同时,说了句从他那学来的苗语:“再见。”
返程的路上,我反复猜测着盒子里的东西。盒子里放的许是一件苗服,许是子母泉的水,许是一只杀好的母鸡。最好是母鸡,想到此,我不禁有些羞愧,又为没有烹饪的锅具而苦恼。回到出租屋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礼盒。静置在盒里的是:半块洁净的石头,以及一株柔嫩的象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