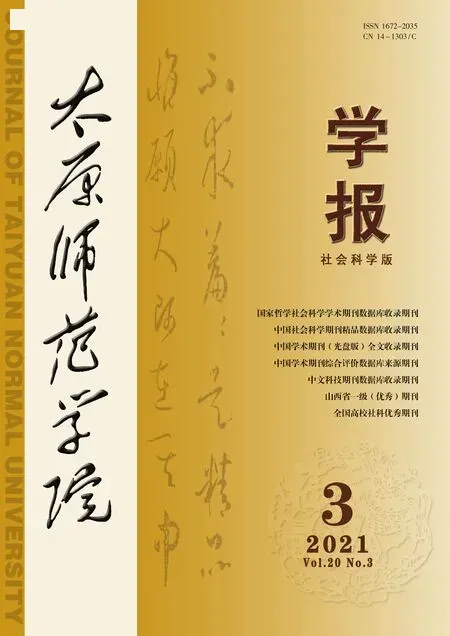《论语》“素以为绚兮”诗义考
——兼论“绘事后素”与《周易》“白贲无咎”之义
白 凯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素以为绚兮”出自《论语·八佾》,其文曰: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是《卫风·硕人》的第二章后两句,“素以为绚兮”一句不见于今本《诗经》而仅见于《论语》,向来被当作逸诗。
过去研究者对“素以为绚”的解释众说纷纭,他们大多将“素”与“绚”理解成容色和礼仪、美质和华饰、素粉与众饰的对举,约而言之,不外道德教化与容貌服饰两端。就道德教化言之,郑玄、皇侃、邢昺等认为“素以为绚兮”是喻指庄姜既有娴雅容貌又能以礼自修,恰如五彩得素白之色彰显而鲜明生动。如皇侃曰:“素,白也,绚,文貌也,谓用白色以分间五采使成文章也。言庄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礼自能结束,如五采得白分间乃文章分明也。”[1]31就容貌服饰言之,戴震谓“素,以喻其人娴于仪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2]90,刘宝楠则认为“当是白采用为膏沐之饰,如后世所用素粉矣。绚有众饰,而素后加”[2]90。这些解释都把“素以为绚兮”看作是对《硕人》第二章的总括性评价,有未达一间之憾。同时,研究者往往将“素以为绚兮”与“绘事后素”联系在一起解释,“素以为绚兮”的诗义反而不彰。
笔者试图通过《毛诗》与《韩诗》对《硕人》“美目盼兮”的不同注解探究“素以为绚兮”的诗义,并重新探讨《论语》“绘事后素”与《周易》“白贲无咎”之义。
一、“素以为绚兮”诗义考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毛诗》与《韩诗》对“美目盼兮”的注解不同。其中,《毛诗》注曰:“盼,白黑分。”《韩诗》则云:“盼,黑色也。”[3]3112宋代王应麟《诗考》中辑引《韩诗》,《硕人》条下也有“盼,黑色也”[4]602。清代陈寿祺和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也著录了此条。然而研究者多从《毛诗》,却甚少注意到《韩诗》的意见。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毛诗》《韩诗》解释不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认为许慎从《毛》不从《韩》。实际上,不仅毛韩两家对“美目盼兮”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我们通过比较这两家对“盼”的注解,还可以揭橥“素以为绚兮”的诗义。
理解诗句需要我们回到原文。“美目盼兮”出自《诗经·卫风·硕人》第二章。其文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郑玄笺注曰:“此章说庄姜容貌之美,所宜亲幸。”(《毛诗正义》)这几句都是对新婚女子外貌的描绘,赞美了新婚女子姣好的容貌和典雅的气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是形象地刻画出新婚女子的动态之美。马融曰:“倩,笑貌,盼,动目貌。”孔颖达注“巧笑倩兮”曰:“以言巧笑之状。”(《毛诗正义》)
关于“美目盼兮”的注释,《毛诗》曰:“盼,白黑分。”《说文解字》亦曰:“盼,白黑分也。《诗》云:‘美目盼兮’。从目分声。”[5]254《玉篇》也有:“盼,《诗》云‘美目盼兮’,谓黑白分也。”[6]83《字源》也认为“盼是会意兼形声字,从目从分,分亦声。表音兼表意的分亦是会意兼形声字(从八,从刀,八亦声)。从刀从八会分别意,表示盼的本意与分别有关且表音”[7]275。同时,“盼”字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战国古文字中始见盼字,楷书作盼,是小篆的笔势变化,《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所收盼,实为‘脉’字,本义为眼珠黑白分明”[7]275。可见“盼”的本义是眼睛黑白分明,《毛诗》注释准确无误。马融所谓“动目貌”是对黑白分明的引申,正因为黑白分明,才能看出庄姜眼波流转。所以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目流眺”为“流眺,睛盼也”[8]1311并引“美目盼兮”为证。
盼的本意是指眼珠与眼白黑白分明,那么,《韩诗》“盼,黑色也”作何解释呢?陈乔枞在《韩诗遗说考》中说:“白黑分,则矑之黑色益显,故《韩》以黑色言之。”[9]555正因为庄姜眼睛黑白分明,所以眼白才更能衬托出眼珠的乌黑光亮。也正因为眼珠乌黑光亮,才能让人看到庄姜眼波流转。《毛诗》关注的是黑白颜色的对比,《韩诗》则强调了庄姜眼睛中被凸显的引人注目的黑色。因此《字源》也认为“《诗·卫风·硕人》‘美目盼兮’,《毛传》训‘白黑分’,引申指黑眼珠,青眼。”[7]275
理解了“美目盼兮”之后,再看“素以为绚兮”。何晏注曰:“绚,文貌。”[3]2466皇侃注曰:“素,白也,绚,文貌也,谓用白色以分间五采使成文章也。”[1]31“素以为绚兮”本指绘画中素白之色对五彩的修饰衬托,使色彩绚烂。(1)“素”,《说文》曰:“白緻缯。”《玉篇》:“白也,本也,廉也,白致缯也。”《说文解字注》曰:“缯之白而细者也。”“素”本义指没有染色的细密的丝绸,引申为白色、本色、纯朴等。“绚”,马融注《论语》“素以为绚兮”曰:“绚,文貌也。”郑玄注《仪礼》“皆玄纁,系长尺绚组”曰:“采成文曰绚。”《玉篇》“绚,文貌”即引自郑玄注。《字源》:“绚,本义为有文采,引申为色彩华丽。”这与《韩诗》对“美目盼兮”的理解正好一致。“素以为绚兮”是素的衬托使众多颜色更灿烂夺目,“盼,黑色也”强调的是眼白的衬托使眼珠更乌黑光亮,二者的意思是相同的。陆九渊即曰:“‘绘事后素’若《周礼》言‘绘画之事后素功’谓既画之后以素间别之。盖以记其目之黑白分也。谓先以素为地非。”[10]402可见,“素以为绚兮”是紧接着“美目盼兮”的意思,继续对庄姜眼睛的描绘。“美目盼兮”正面描写眼睛黑白分明,“素以为绚兮”是诗人借用绘画的手法作比喻,以素对绚的衬托类比眼白对眼珠的衬托,写出眼珠在眼白的衬托下乌黑光亮。“素以为绚兮”是对“美目盼兮”的生发与呼应,再次赞叹庄姜眼睛顾盼生辉,具有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情调。(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美目盼兮”条下注曰“韩说曰:‘盼,黑色也’。《鲁》此下有‘素以为绚兮’句。”可见,《鲁诗》与《韩诗》都知道“美目盼兮”之后有“素以为绚兮”。
约而言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诗人顺着情思一贯而下对庄姜神态的描绘,“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两句共同描绘了庄姜眼睛的顾盼生辉,波光流转。素与绚对应的是眼睛的白与黑,诗人借绘画中素对绚的映衬比喻眼白对眸子的映衬,使庄姜的眼睛更美。通过《毛诗》《韩诗》对读,寻绎出“素以为绚兮”的诗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绘事后素”与“礼后乎”。
二、由“素以为绚兮”看“绘事后素”之义
《论语》“子夏问《诗》”中除“素以为绚兮”之外,“绘事后素”也是《论语》研究中聚讼不已的问题。郑玄、孔安国、皇侃、邢昺等皆以为孔子是“以素喻礼”[11]159,用“先绘后素”来比喻礼对人的成就作用。郑玄云:“凡画绘,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也。”[3]2465朱熹则谓“绘事后素”是“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用“先素后绘”强调必须先有忠信的品质才可学礼。此后学者对“绘事后素”的理解渐次增加,大致分为“先绘后素”与“先素后绘”两派(3)参见凌廷堪《校礼堂文集》“《论语》‘礼后说’”与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续》“绘事后素”条。。
前文对“素以为绚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绘事后素”之义。子夏问《诗》,显然是不明白“素”何以能为“绚”。孔子答之以“绘事后素”,自然是为了解释“素以为绚兮”。因为“素以为绚兮”是诗人借绘画手法形容庄姜眼睛黑白分明,眼白衬托得眼珠更加乌黑光亮,所以在孔子与子夏对话的语境中,“绘事后素”当是孔子借绘画手法解释为什么“素”可以为“绚”。因此,“绘事后素”意思上应当与“素以为绚兮”相同。郑玄认为“绘事后素”是“凡画绘,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就是绘画时先画其他颜色,最后用白色勾边,使各种颜色的界限更清晰,色彩更分明。与郑玄同时的荀悦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中也说:“孔子曰:‘绘事后素’成有终也。”[12]408可见荀悦明白“绘事后素”是指绘画的完成要靠素白之色点染勾勒。“素”对“绘”(4)绘,《考工记》曰:“画绘之事杂五色。”《说文》:“会五采绣也。”《释名》曰:“画绘也,以五色绘物象也。”《玉篇》:“綵画也”。绘本义是五彩的刺绣,后引申为绘画。的修饰成就作用相当于“素”对“绚”衬托的成就作用,“绘”的效果与“绚”又都是众彩缤纷颜色鲜明。陆九渊认为“绘事后素”是“既画之后以素间别之,盖以记其目之黑白分也”[10]402,所以“绘事后素”的意思与“素以为绚兮”是相近的,郑玄对“绘事后素”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过经学家往往在经文中灌注微言大义,将“绘事后素”的侧重点放在“礼以成人”上,遮蔽了“素以为绚兮”的诗义。
近年来不断面世的出土文献有效地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解决学术难题提供了转机。邵碧瑛结合历年出土的东周漆画、帛画再次证明“绘事后素”确乎如郑玄所言,是“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13]。雷学淇分析“绘事后素”时也说:
周秦以前,无以绢素作画者,绘画之事,或施于衣服则以元为质(5)元即“玄”,黑色,时人避玄烨讳,故改。,或施于旗常则绛纁为质,或施于器皿则以漆为质,唯施于正鹄有白质者,有赤质者,此白质亦事之仅有,非绘事必皆粉地也,故礼云,五色六章旋相为质。[14]545
上古之时,作画的材料不是白色绢布,而是质地颜色各不相同的材质,所谓全是粉地并不存在。再有“绘事后素”也见于文学作品中,如潘岳《夏侯常侍诔》“如彼随和,发彩流润,如彼锦缋,列素点绚”[15]2449与颜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爰自待年金声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绚”[15]2487中,“列素点绚”“素章增绚”都是用“绘事后素”典故来形容文采斐然,文章灿烂,李善也皆注以《论语》“子夏问诗”,足见魏晋时人所见亦同于郑玄、何晏,“绘事后素”当是时人人所共知的。
仔细推究孔子与子夏的对话,由“素以为绚兮”到“绘事后素”再到“礼后乎”,对话的重点在“素”,“礼后乎”强调的是“礼”,师徒二人是将“礼”作为“素”来看待,这样二人对话的逻辑才合理。若依朱熹的解释将“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都理解作先“素”后“绘”,那么“礼后乎”中“礼”的功用就被当作“绘”的功用来理解,这样前两句所强调的“素”,和后一句所强调的“礼”,没有形成对应关系,是脱节的。按照朱熹解释“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论语集注》),那么“礼后乎”中“礼”不过是对忠信的文饰,朱熹认为强调的重点是“忠信”,那么“礼后乎”并不能启迪孔子,而且孔子与子夏并没有就同一个说话中心展开有效对话。
最后再看“礼后乎”。子夏能由“绘事后素”发明诗意,悟到礼对于社会人生的作用,所以孔子大为欢喜,感叹可与子夏言诗。子夏之所以能由“绘事后素”迅速联想到礼的作用,这与孔子日常对弟子的礼乐教育以及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分不开的。
孔子特别重视礼维护社会秩序与在个人成仁成德方面的作用。比如孔子谈及化育百姓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马融注曰:“齐,整齐之也。”(《论语注疏》)朱熹注曰:“齐,所以一之也。礼,谓制度品节也。其浅深厚薄不一者,又以礼一之。”(《论语集注》)孔子强调教化百姓时,礼的作用在“道之以德”之后,礼发挥的是约束规范的作用。孔子论何以成人时则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颖达疏曰:“言加以礼乐,乃得成文。”[3]2510朱熹则曰:“成人,犹言全人也。言兼此四子之良,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欲内,而文见乎外。”(《论语集注》)孔子说在具备了知、不欲、勇、艺之后,以礼节制,以乐调和,而乐又归属于礼。孔子在告诫子路何以成人时,也着重强调了礼对具有众多品德的人的成就作用。再如《论语·雍也》有云:“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颖达注曰:“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检约,则不违道也。”颜渊也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皇侃疏引孙绰曰:“既以文章博我视听,又以礼节约我以中。”[3]596由“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则可见孔子教人之次第,也可见礼在教育中所发挥的约束规范的作用。《颜渊》一章,弟子数人问仁,孔子却独以“克己复礼”告诫颜回。马融注曰:“克己约身。”[3]2502《论语注疏》引刘炫曰:“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3]2502所以,礼在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中,是很高的道德境界,一日克己复礼则可以成仁,这就充分证明礼在道德学习中规范节制的作用。这也就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境界。因此,荀悦才说“‘绘事后素’成有终也”[12]408。
孔子以《诗经》作为礼乐教化的文本来引导和启发学生。《论语》中除“子夏问《诗》”外,还有“子贡论《诗》”,子贡引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表示人在学问与道德上要像打磨玉器一样,不断精进不断提高。再如南宫括经常念诵《大雅·仰》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孔子就做主将侄女嫁给南宫括,孔子通过南宫括吟《诗》看到了他对人格的追求和对仁德的向往。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诗经》对人的教育作用中,自然包含礼乐文化与道德的感发联想。所以,子夏由“绘事后素”想到礼在成仁成德过程中的修整约束的作用。孔安国有云:“孔子言绘事后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3]2465。戴溪在《石鼓论语答问》中对孔子以“绘事后素”启示子夏有详细解释:
后素之意,虽有彩绘之色,非用素以间次之,则采缋不彰。《论语》注云:以素分布其间是也。彼画绘之事当以五色为上,今乃以素分布其间,始成藻绘之饰,甚哉,素之有益于人也。推其类观之,则反本之论当有所归。子夏因此遂悟得后素之义。知圣人制礼之意乃是以素饰尽之意,则素者为礼,而文者非礼也。此夫子所以喜之与,盖谓其展转发明不只就一处上见。[16]61
戴溪上述论述说明了子夏由“绘事后素”领悟孔子“后素之义”的思想脉络。
总而言之,《论语》“子夏问《诗》”中孔子子夏师徒由绘画手法联想到礼对君子成仁成德的重要作用,礼与成仁成德的关系犹如白色与众色的关系,礼能够使其他品德发挥更好的作用,子夏由绘画中白色与众色的关系想到礼与成仁成德的关系,使孔子受到启发,所以给予子夏高度褒奖。
三、由“绘事后素”看“白贲无咎”之义
自宋代以来,治《周易》者往往以经文互证的方法借“绘事后素”解释《贲》卦“白贲无咎”。但由于对“绘事后素”的理解存在分歧,因而在解释“白贲无咎”时相应地也存在不少争论。在梳理清楚“绘事后素”之义后,我们再来寻绎“白贲无咎”之义。
研究者们对“白贲无咎”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由文而质”与“由质而文”两种。最早将“白贲无咎”与“绘事后素”联系起来解释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认为“白贲无咎”是“绘事后素,居上而能正五彩也”[17]684。刘牧看到了“绘事后素”与“白贲无咎”的相通之处,认为上九爻白贲是对前五爻的修正和凸显,恰如古人绘画时先布五彩再施以白色,使颜色分明。吕大临亦曰:“以阳居上,至白之象也,绘画之事后素功,众色淆乱非白无以别之,绘事至于素功,饰之道尽矣,上之志得也。”[18]531之后冯椅、胡震、惠士奇、惠栋等治《周易》者论述多同于此义。
与之相反,南宋林栗在《周易经传集解》中则认为“白贲无咎”是“无质者不可有其文”,也就是说白贲所起的是基础的作用。他是最早结合《考工记》《诗经》来解释“白贲无咎”的。他说:“《记》曰:‘甘受和,白受采。’《诗》曰:‘素以为绚兮。’子曰:‘绘事后素。’皆谓无其质者不可有其文也。”[19]128林栗将“白贲无咎”“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都解作先有质后有文。杨时、郭忠等人也有相似观点。今人高亨也在《周易大传今注》中明确“白贲,无咎”是“白色之素质加以诸色之花纹。此喻人有洁白之德,加以文章之美,故无咎”[20]231。
在梳理清楚“素以为绚兮”与“绘事后素”之后,我们试图分析“白贲无咎”之义究竟是“由文而质”还是“由质而文”。
“贲”的意思,高亨先生结合《吕氏春秋》《山海经》等考证“贲”当解作“以杂色为文饰”[21]224,此说当无误。然而林栗、杨时等都将上九爻辞“白贲,无咎”理解为“由质而文之象”,究其原因是将“白贲”理解成素底上施以文彩,即在“白”上“贲”。不过,此说不仅从《贲》卦爻辞、卦爻象等诸多方面来说,都扞格难通,而且也与前文所证“绘事后素”之义相违背。
首先就《贲》卦爻辞来看,《贲》卦爻辞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六二“贲其须”,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上九“白贲,无咎”。六爻中“贲”之义皆为动词,是装饰、文饰之义。如高亨先生考证之详细,则“贲”为“以杂色为装饰”,字义更为精确。“贲”是以杂色为文饰,那么“白贲”则是强调拿素白之色为文饰,“白贲”当解作用“白”来“贲”,强调上九爻是用素白之色进行文饰。结合“贲其趾”“贲其须”“贲于丘园”的词序来看,若将“白贲”解作素底施以文彩,则当写作“贲白”(即“贲”于“白”)才与其他爻辞一致,显然“白贲”强调的并不是在哪文饰,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文饰。即如杨简所说:“贲饰至如此极矣,上九超然于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贲,一以白为贲焉。”[22]183俞琰亦曰:“上九白贲非无饰也,以质素为饰耳,贲极而返本,如此故无过饰之咎。”[23]64
再从《贲》卦爻位分析,上九爻处《贲》卦六爻之终,前五爻皆言文饰,“致饰然后亨则尽矣”(《周易正义》),故第六爻以素白之色为文饰,是对前五爻文彩不断修饰的修正与补裨,正与《系辞》谓“无咎”为善于补过相合。同时也与《周易》过犹不及、盛极而衰的思想一致。结合《乾卦》上九爻象辞“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则“白贲,无咎”之义越发显豁。故而程颐《伊川易传》曰:“上九,贲之极也。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惟能质白其贲,则无过失之咎。白,素也。尚质素则不失其本真,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24]175朱熹亦云:“贲饰之事太盛则有咎,所以处太盛之终,则归于白贲势当然也。”[25]1781再如谢灵运自注其《山居赋》“宫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亦曰:“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贲最是上爻也。”[26]1743
再就《贲》卦彖辞而言,其文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正义》)。“刚柔交错”在卦象上除了“阴从上来居乾之中,文饰刚道交于中和”[27]566之外,更如孔颖达所言“贲,文饰也。刚柔二象交相文饰也”[3]75。《系辞》曰:“物相杂,故曰文。”(《周易正义》)“文”唯有“文”“质”交错才能显出“文”。“色者,白立而五色成”[28]247。正因为有留白,才能显出错画之文,正因为有了素白之色,才能显出杂色文彩。若全部施之以文彩,又何谈文饰,又何以显现文饰之美。恰如宋代冯椅所说:“上九白贲终于致饰成文之象,白贲即绘画之事后素功也,无咎占谓能以白贲五采则无咎。”[18]56张惠言亦言:“画绘之事后素功,以白为贲则贲之成也。”[29]14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颖达疏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周易正义》)故而“文明以止”也是启示人们明白进退之道,懂得适可而止,正如上爻白贲以平衡五爻的杂色文彩,避免了一味文饰华奢之过。《贲》卦卦象,上卦为艮,下卦为离,艮为山,艮者止也,如果自初爻至上爻都在不断装饰,是知进而不知退一味向前,则上卦艮止之义无处着落。所以不是在第六爻继续在素白之底上继续施以文彩。项安世曰:“白贲者以白文之,如斫琱为朴。”[30]155再看《贲》卦象辞“白贲,无咎,上得志也”,史征注曰:“上九白贲无咎者,处饰之终,终乃反素矣。他人以色为饰,而我以素为饰,守志任真,得其本性,何咎之有哉”[31]202。
此外,从卦序上看,《贲》卦在《噬嗑》之后,居《剥》卦之前。《序卦》曰:“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3]95《剥卦》在《贲》卦之后,也正是对《贲》卦上六爻“白贲,无咎”的延续,是因为“白贲”“无咎,善补过”,是对文饰过度的纠正和补裨,故而继之以《剥》卦,损之又损。《杂卦》亦曰:“《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周易正义》),“无色”也正是由上九爻“白贲,无咎”而来,如杂卦所言是“饰极无色,雕琢返朴”之意。朱熹曰:“贲极反本,复于无色,善补过矣,故其象占如此。”[32]51同时,《贲》卦与《噬嗑》卦爻翻覆,“《噬嗑》卦讲欲盛伤身,《贲》卦讲饰极反朴”[33]756,《噬嗑》《贲》卦意思也正相对而合。就如王弼《周易注》所云:“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患忧得志者也。”[3]38
约而言之,“白贲”当指以“白”为“贲”,将素白之色作为文饰;“白贲,无咎”即如王弼“处饰之终,饰终反素”与朱熹“贲极反本,复于无色”,是对文饰过度的补裨修正。《文心雕龙·情采》“《贲》象穷白,贵乎反本”[34]538正体现了这种思想。
四、结论
综上可见,“素以为绚兮”是赞美庄姜眼睛黑白分明,借绘画的手法比喻眼白衬托出眼珠的乌黑光亮。“绘事后素”是绘画时先施以众色,再用白色分布其间,是白色使颜色鲜明生动。“礼后乎”是子夏以“素以为绚兮”发问,孔子以“绘事后素”启发子夏领悟到礼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约束规范作用,强调礼对君子立德成仁的重要性。“白贲无咎”是以“白”为“贲”,将素白之色作为文饰,是上九爻对前五爻的修正与成就,“无咎”是因为白贲对文饰过度的纠正。五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等五组关系对照表
“白贲无咎”中,强调《贲》卦功成于白贲,“绘事后素”强调绘事功成于素,“礼后乎”强调成仁成德功成于礼,在逻辑上都凸显了“白贲”“素”“礼”对整体的修饰成就作用。此外,“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讲的是用文明来规范人类的行为。所以先贤才以“绘事后素”比况“白贲无咎”,并引《论语》“礼后乎”为证。惠栋在注释“白贲无咎”时对三者的相似性作了精当的阐释,其文曰:
《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谓画绘之功素在后,盖皎皎者易污,故画绘先布采后加素,然后五色宣明,故曰素功,言功成于素也。子夏问《诗》“素绚”,孔子以“后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礼。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其不学礼故,虽有美质而终不成,然则画绘之功成于素,忠信之质成于礼,上九,贲之成,故曰:白贲无咎。[35]52
综合“白贲无咎”“绘事后素”与“礼后乎”来看,功成于素恰似忠信之质成于礼,孔子与子夏所强调的是礼的规范成就作用。
《周易》是群经之首,深藏着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与处世态度。从“白贲无咎”中就透露出古代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和对敦本尚质之美的推崇。张载对“白贲无咎”有如是理解:“画绘之事,文采既极而以素功为后焉,岂非反天下之文以归于质耶?《易》之贲曰:白贲无咎,夫贲之极以白,总是欲归质也。”[36]1119李光地在《周易观彖》亦曰:“以白为贲则敦本尚实,华靡之习不足以累之。君子之志在乎反古之道,居卦上文穷之时,还于质素,得志可知矣。”[37]122古人将复朴归初到了极致就是天地自然的状态。李商隐在《容州经略使文集序后》评价元结文章全然出于自然也借用“白贲无咎”为说,他认为元结文章“其绵远场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太虚无状,大贲无色”[38]2256。《周易·系辞》有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则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85,《周易》正是上古先民对天地自然的模拟和效法。陈梦雷有言:“盖文质相须者天地自然之数,贲之所以成卦而质为本文为末,质为主文为辅,务使返朴还淳,则圣人所以系之辞而维持世道之心也。”[39]210在文艺思想上,《文心雕龙》中由“黄唐淳而质”到“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明证。
此外,这还体现了中国人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人生智慧。杨万里说:“易穷则变,文穷则质,上九居贲饰之极,文之穷也,救文之穷,其惟质乎!”[40]143蔡清亦曰:“上九居贲之极,凡物极则反,夫贲,文饰也,贲极而反则复于无色,所以为白贲之象。”[41]474繁华绚烂与宁静朴素相互成就循环往复,才能构成文质彬彬的尽善尽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