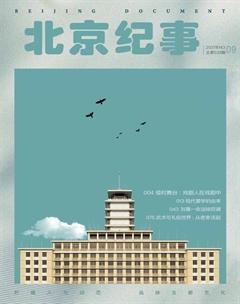果靖霖:为人民服务,就是市场
叶阿果

似乎很难去了解一个完整的果靖霖。
网络上,关于他的采访并不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隐匿状态:不接受采访,不录制综艺,极少使用社交平台。他从不在乎所谓的“流量曝光”,也不喜欢刻意去向大众展露自己的生活。站在镜头前,他完成作为明星的阐述,而余下大部分的闭关时间,则是以读书、写作、喝茶来消度,填补作为演员之外,那部分欠缺下来的表达。
不能否认,“华表影帝”果靖霖,正在试图撕掉“演员”所特殊持有的种种标签。如今,51 岁的他,更愿意用“艺术工作者”去定义自己——这种立足,在当下的娱乐圈,虽略显老旧,但却带着几分错失已久的执着和敬畏。
“相较于从前的演员身份,我觉得作为艺术工作者,我的天地更广阔了。”他这样对《北京纪事》的记者说。
是多元的经历,让艺术因子,在果靖霖身上积累出更多的分量。回溯他的演艺生涯,16岁出道拍摄电影,后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戏剧舞台上,他演过无数先锋话剧。2006年,凭借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走入大众视野。三年之后,因成功饰演袁隆平院士,摘得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男演员奖。在电视剧《新亮剑》《生活启示录》中他演绎了多样人生,在文艺片《狗十三》中,他成功饰演了一位让人“爱恨交加”的父亲。但他不甘于此,开始做编剧,喊来张嘉译、姜武,一起完成了自己创作的剧本《生逢灿烂的日子》,收获好评无数。
现在,他更愿意站在这些作品的前面,去聊它们背后的艺术性。关于曾经过往,他反而不愿多提。当一名艺人不再同意被标榜为“艺人”的时候,更多有趣的话题,开始涌来,比如去探讨精英文化、探讨小说作家、探讨人生价值……
“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就要先成为一个世间的清醒者和一个灵者。”他指了指办公室墙上爱因斯坦的照片,“象征智慧,这是我最喜欢的。”
鲜少与大众见面的果靖霖,这一次决定畅聊。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探讨被舆论裹挟之外的娱乐圈,和他的漫漫艺术人生。
寻找航灯
我是1990年上的大学。当时中国文艺处在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伟大的复兴时期。那时候的当代艺术家,在我们求学、树立艺术观的阶段,就像大海上的航灯,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们孜孜不倦,我们是很努力的一代人,可能比现在年轻人对艺术更加执着、更加刻苦。但2000年以后,新时代来临,情况开始发生了逆转。悄然无声的商业时代来临,当我们似乎长大了的时候,却发现海里的很多航灯都过早熄灭了。我们忽然间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动力,这一代人开始四分五裂。
我该怎么办?其实那时候,也是我的一个事儿。我已经在海里了,划着船,只能继续往前,只能按照记忆中航灯的方向继续前行。
现在处在一个大娱乐时代,从一个商业的时代到商业帝国建立,到一个娱乐时代的崛起,到最终艺术家的迷失。曾经艺术是一种信仰,能说起来是信仰了,门槛是有的。但现在不然了。
文艺应该有正确的文艺批判,面对作品,你要先赞叹艺术精神。但现在的网络环境,观众极不快乐,极不爱护。一个民族,它的文明体现在哪儿?就是你是否能够包容和爱护艺术家,你要知道他们跟你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就本着我的艺术初心,我的初心就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至少知道方向在哪儿。
2016年我拍了《生逢灿烂的日子》,那是我写的、我拍的,我拿了奖项,老百姓特别喜欢,这多好。现在,我又做了一个北京的大戏,《铁马豪情的日子》,我在准备下一个作品——《生逢灿烂的日子2》,十年前后我写了几百万字了。
为人民服务,就是市场
谈及当下的“市场”概念,果靖霖认为可以用一个近义词替换——人民。“作品为人民服务,就是市场。”
他36岁出名,39岁获得影帝,44岁做出了《生逢灿烂的日子》,一些关乎价值观的思考,正是在那时候骤然来临:
我走上过中国电影所谓的最高领奖台——华表奖,但我演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获得那些物质硬壳吗?
这回归到哲学问题。您打哪儿来?我就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工人家庭的孩子。你到哪儿去?我喜欢文学、小说、艺术,励志成为一个有名的艺术家。你是谁?我就是普通人家的小孩,就是个老百姓、平民。你该干吗?我该去追求艺术。你为什么能从那儿走到这儿来?谁滋养了你,你得报答谁。
突然间想明白了,实际上滋养我的,就是那条胡同,就是胡同里那些形形色色的百姓。我的种子就是在那个胡同里发的芽儿,那里有根,人不能忘本。所以我开始写关于北京的作品,那是我最熟悉的生活。
赏识你的最终是谁? 是老百姓。当我做完《生逢灿烂的日子》,我走在街上,老百姓看见我说:“哟,果靖霖,你那戏好看,我们喜欢。”“这不老三吗?三哥!”“哟,果师傅!”我觉得特乐。这感觉像是回到了曾经的胡同生活,邻里街坊般的亲热,这跟之前你当明星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娱乐。
我现在拍戏很少,对剧本要求高了,粗制滥造的戏不会参加。我要的是人生价值,我人生的目的,是能够看到人民群众走在街上对我笑、对我亲。
艺术家的职责
这个时代是需要真正的艺术的,我坚持做认真严肃的艺术作品。
艺术家需要清净和单纯,如果你不够清净,你的心是乱的,你的作品不会太高级;如果你做人做得不干净,你太贪财,同样你的作品也充满了铜臭气。
从艺术观来讲,我更欣赏的是我的前辈,那些老先生们。比如,获得七一勋章的蓝天野先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蓝先生也是个大画家,画鹰画得非常好。再比如,李宝田先生,大雕塑家,画画好,文笔好,他们不停地用艺术的子类来充实自己,这样做出来的艺术,肯定是要比别人高的。
学习和充实,是每一个艺人应该做的事,所以我很佩服那一代艺术家。
现在概念不一样了,很多人说,我是“娱乐圈”的,我们那时候叫“艺术圈”,或者我们被称为“文艺工作者”,基础都是文学,然后才是艺术方法,根在“文”上,现在一“娱乐”,全成“乐呵”了。
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基本上,我不接受采访,不吃不必要的饭,不做无聊的事,不拍广告,不拍综艺,我更不可能直播带货。
作为一个文艺者,你是有责任的。即便海上的一些航灯过早地熄灭,但浩瀚大海,我们还在前行,就要当好掌舵人,要时刻擦亮我们的那盏灯。作为世间的清醒者和灵者,你要提醒别人,春华秋实也很美,可能比你看一小道消息有意思,去养养眼吧,去看看花落花开。
就像我做《生逢灿烂的日子》时,提到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用这首诗,唤起很多人对诗人海子的回忆。我告诉大家,你要面朝大海,你要看春华秋实。
忠于艺术
现在,我每天恒定跟上班一样。整个下午到晚上就是在写剧本,几乎每天保证几千字的速度。
目前的想法,就是把我要寫的东西,或者说想写的东西完成。做演员,有时是完成不了我的艺术表达的,有时候只是演了一个剧中人,但未必是我想要的,从完成度来讲,只是完成一个角色。
虽然我这人不娱乐,但这个时代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就是我的空间变大。我的范畴大了以后,艺术表达的可能性更多了,更自由更多元了,我觉得比以前更灵活自在了。
按以前,你们知道我是个演员,这是单一的,也有人说我是剧作家。但如今,面对好剧本,我可以选择去演戏,脑子里有灵感和画面了,我可以选择去导戏,有表达的欲望了,我可以选择执笔去写戏。我会把我的表达,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载体,我觉得我更广阔了。
反正一直是在我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游荡。这让我感觉到还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