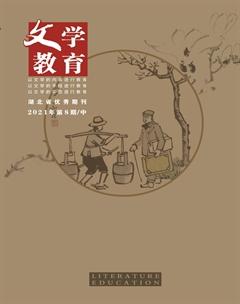《北上》中以运河为视点的双重视角研究
刘佳茗 张若昕
内容摘要:“运河”意象是贯穿徐则臣小说书写的符号,从无锡出发,经过镇江、扬州、淮安、济宁,最后抵达通州,运河作为城市的脉搏,与大小支流交织成五光十色的水网。延续徐则臣一贯的“到世界去”主题,小说沿着运河的河道展开情节,以“藕断丝连”的“整体感”呈现不同时空的“运河与人”。徐则臣并不满足根据单一的地理线索记事,而是创意地运用了中外、南北的双重视角讲述时间与河流的秘密,呈现“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关键词:徐则臣 运河 《北上》 双重视角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溯流而上的可能。
相较于其他作家文学书写中的地理空间,徐则臣的表现空间是相对单一的。在徐则臣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他都毫不掩饰对于运河这一地理空间的专执。如《耶路撒冷》中运河小城“花街”,《王城如海》中余松坡对于“鱼”的偏好,到了《北上》则将汤汤的运河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放大其中的历史意味和民族记忆。
在《北上》中作者将时代的事件作为运河历史的分界,从20世纪初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起步,到义和团扶清灭洋,日本侵华战争,文化大革命,最终来到大运河申遗成功的2014年。百年间的历史在运河的倒影里、时间里、土里、水里,形成了对历史追溯与传承的观照。同时徐则臣也并不满足单一的叙事视角,他创造性的将意大利人小波罗作为第一视角,以异质的眼光和世界的史观呈现百年间运河的面貌,而百年前的北上又与百年后的南下相互交错,古与今,中与外的双重视角沾染着水的气息、河的流影,展现了兼具文化包容性与历史的追溯性的运河文化。
一.“北上”线的跨文化视角建构
“北上”线又是小说中的历史线。“北上”的世界是向外扩展的,他们在沿河北上的旅程中用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视角观察与经历沿河风土、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观照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到世界去”的行为写照。
(一)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意大利人小波罗作为异质文化的直观反映者,在“北上”中承擔了一种跨文化研究的责任。小波罗的形象是“跨文化研究”中比较视野的形象学理论的外化。“比较形象学强调他者的意义,“‘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相反,自我形象则首先是作为他形象的反面呈现出来的。”[1]意大利人小波罗作为“他者”,势必与本土文化发生冲撞,在这样的冲撞中呈现了日常化,生活化的运河故事。
在路过邵伯闸口时,摄影成为了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的聚焦点。“照片所摄取的人物、风景安慰了时间流逝所形成的悲伤,也在后来者的生活中承担着复活记忆的纪念功能,”[2]这是源于西方的技术手段。然而当小波罗在油菜花田提出为大家拍照时,却遭到了不愿被拍的中国语境。
“拍你的照片,小心那玩意儿把你的魂勾出来。”
“据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就是先用那东西对着义和拳和皇帝皇太后一阵猛照。拳民一个个倒下了,咱们大清国的皇帝和皇太后没倒下,也丢了半个魂儿。”
小波罗的浪漫主义情调和本土人民对摄影的抗拒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反差。在这里异质文化通过摄影的方式具象化,与古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形成冲撞。与此同时,本土文化也通过味道和行为的方式影响了异质文化的介入:如小波罗爱吃“麻婆豆腐”,收集旧雕版,读龚自珍的诗,数茶叶等。
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是带有“马可波罗”式的浪漫幻想的,如小波罗随身携带的《马可波罗游记》,文字记忆和语言记忆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却是根据视觉记忆和体验记忆产生,如小波罗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异质性愿意被中国人观看。两种文化互为他者的写作方式形成了小说内在的文化间离效果,构建了一种世界性的观照。
(二)异质者眼中的漕运衰落史
《北上》故事的落点在1901年,现代中国的巨变和漕运的衰落都在这一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最初关于这种国家危亡漕运衰微的感受是中式的:
“漕运到了这一天,稍微懂行的人都知道没戏了,只是宣判死刑早一点晚一点而已。造船厂也没了劲头,几副漕船的骨架戳在巨大的厂房里,几个月无人问津。”
“等灾民三五成群沿河而下,他知道又出大事了,华北旱灾。等他在运河边看见更多灾民顺水而下,更有一贫如洗的灾民船都坐不起,义和拳的红衣黄衫已经飘满北中国。”
中式视角下的漕运衰落史由于观察者的阶级立场和身份更像是旁观者的白描:破旧的漕运总督中隐隐约约出现衰败的迹象。他对漕运的衰落不免参杂着政治立场和社会思考。而异质视角则相对客观,小波罗以不参杂政治考量和民族歧视的视角成为漕运衰败史的亲历者,他并没有像马可波罗那样看见王朝的鼎盛,而是目睹了东方神话的破灭,这样的情节无疑带有轮回的隐喻,这样古今交错的丰富性也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式。
外乡人小波罗不懂政治,所以他作为异质视角观察中的漕运衰落史被割裂成具体的物象和事件碎片,这也赋予漕运衰落史的新定义: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这样碎片化的衰落史如:戊戌变法时小波罗北上过闸的优先条例,刻有龚自珍《己亥杂诗》的雕版,茶馆众人谈论的八里台之战与聂士成之死,官船上传出的“最后一趟”传闻等。这样细碎的消息有别于“正史”的记载,因为生活化而显出无限的丰富,给“正史”提供了一种“运河与人”的文化视角的补充。“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3]
(三)不同叙事人称下转换中的“政治无意识”理论
在《北上》中除了小波罗的北上,还有弟弟费德尔的北上之路。比起哥哥小波罗的“观光之路”,弟弟费德尔的北上之路更像“逃亡之路”。对运河并不感兴趣的小波罗与运河融为一体,对运河痴迷的费德尔隐姓埋名过完一生,这样错位的命运决定了他们观察视角的不同。小波罗的北上故事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费德尔则是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分别代表着1901年中国境内外国人的两种处境:游客与侵略者。将兄弟二人的视角重叠,可以更为完整的窥见时代历史的全貌。
《北上》这种用人物视角切换串起历史的结构受美国批评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影响。詹姆逊认为,文学文本是“社会象征行为”,而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文本、心理语言和结构的分析都属于具体技术手段。《北上》中的情节不仅注意明确的叙事,更注重未说出的东西,如《北上》在兄弟视角切换中并没有直接谈及戊戌变法,而是用兄弟二人在不同时段受到他人的不同态度来影射。正是在探寻这种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再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及必然性。这样将故事置于历史的大潮中,也使历史文本本身恢复了“充分的言语。”
不同人称的切换同样也是为了调和“个人主义和集体历史”中无法比较的要求。《北上》中讲究故事情节与历史背景的共时性。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故事独立成篇,又与历史政治的要求有密切的关联,个人的命运是国家命运的缩影。兄弟二人的遭遇之间又有整体性的关联,从这种异质文化的接受程度的对比和变化中可以研究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效能和用途。
二.“南下”线的乡土寻根视角建构
“南下”线是小说中的现代故事。“南下”的故事视角是收缩的。百年前与运河有关的人在河边生存繁衍,子子孙孙也从事着与运河有关的事业。他们以一种新时代的视角南下寻找生命与河流的联系,与父辈浪漫主义的开拓视角不同,儿孙辈对运河的观照是具有文化意味的寻根视角。
(一)从北京到花街的代表空间叙事
在徐则臣的创作中“花街”与“北京”是常见的地标,“花街”是《水边书》中运河南岸的小城青年们的悲欢,“北京”是《王城如海》中的京漂笼罩在雾霾与沙尘中灰头土脸的生活;“运河”则是游离于“花街”与“北京”两个地标之间的故事载体。与常见的从“花街”到“北京”的情节安排不同,《北上》的故事是由“北京”回到“花街”,运河作为两个地标之间的沟通,通过孙辈的寻找讲述了沿岸的风情,“既打通了歷史的关联性又以时空交错叙事塑造了现代空间中“运河”带来的历史纵深与空间横向交流”[4]。
“一条弯曲的巷子,间或一条流水穿过房前屋后;不少老房子在拆迁,房梁斜架在残垣断壁上,走道上不时冒出一片废墟,通往花街的地形因此变得极为复杂。”
“她的手越过船头,一直指到里运河的拐弯处。两条岸石镶壁,整齐划一。岸边的景观树也统一了风格,像同一颗种子发的芽,像同一棵芽长出的苗,同一棵苗长出的树。”
《北上》中的“花街”延续了徐则臣作品中一贯南方小城的潮气和破败感,虹桥里,五福里,金彩巷,张仙洞等小城景观隐约体现了百年前运河边陲的烟火气,与北上线中繁华的漕运相呼应,此外“花街”中曾驻节清江浦的总督故居也与百年前形成了有意无意的互文。但相比花街的破旧,作者对街边的运河赋予了带有人工痕迹的整创。运河在百年后丧失了漕运的功能,作为城市建设的风光带,像一个溜墙根晒太阳的老前辈,无力引领生产力的新方向。
“这一段运河当年是大闸口,是漕运的襟喉,堵上了,漕船上不去也下不来……过闸时绞关的闸工根据闸上的锣声缓急来用力。如今大闸口水流平和,也极少有船来穿行,1959年在城南开挖了南运河,往来船只都改城外过了,穿过市区的这段老河改成了里运河,来回走的都是电动的娱乐游船。”
雄踞天下的十里长河在漕运废止后日渐凋零。这是从北京一类的“发达”行至花街这般“欠发达”的直观体验。逆行的视角由面至点,将世界收缩聚集到运河中的一段,形成了“破碎的整体感”[5]“运河与人”的文化格局具象化,伴随着空间狭窄带来的是视角的拉长,在几近凝滞的水波中浮现百年前的文化记忆。
(二)水上意象的现代化延续
为了将百年间的故事有效的连接在一起,徐则臣将百年前运河的痕迹更多地以道具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带有水上意象的道具对剧情的发生发展、烘托背景与现场气氛、表现人物特征与个性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血缘的身份证明,更是运河文化的现代化延续。
“孙过程拿了柯达相机和哥萨克马鞭,邵常来要了罗盘和一块怀表。大陈喜欢那杆毛瑟枪,帮弟弟小陈做主拿了勃朗宁手枪。谢平遥如果可以希望留下小波罗和这次运河之行有关的资料,包括小波罗的记事本。”
这些与运河有关的道具或是以一种婴儿抓周的形式,或是以临终托付分发到每个与运河有关的人手中:小波罗的笔记本,《龙王行雨图》雕版,相机,罗盘与怀表,这些道具兼有文化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选择,穿插起祖先和后辈的关系。如邵常来拿走的罗盘便成了邵氏家族与运河关系的信物:
“我爷爷娶我奶奶时,我爷爷他爹把这个罗盘传给了我爷爷,我爹娶我妈时,我爷爷把罗盘传给了我爹……今天是星驰和小宋结婚,我按照祖上的规矩把这个罗盘亲手交给星驰。”
道具是凝固的艺术。世代船民的邵氏家族将罗盘代代相传,即使儿孙辈已经决定不再从事祖先的漕运事业。时代要求船民“上船”后又因为漕运的衰落不得不选择“下船”,但“水上的祖先”就像无形的绳索,牵引着代代人与河的因缘际会。
与此同时,除了罗盘其他的道具也在现代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孙过程的后人因为相机拍摄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作品,谢平遥的后人延续了从文字中观照河流的视角,用影像记录起现代的运河传奇,拥有小波罗笔记本的周氏兄弟则世代学习意大利语,自觉地承担起收集运河文物的博物馆使命。因为道具,人物的命运与大运河纠葛在一起,为漕运衰落的今天提供了运河文化的现代意义。
(三)运河文化的新时代解读
整个“南下”过程中对运河文化的观察是一个“历史复原”的过程,起初是从器物的角度运河文化进行解读,如故事开篇中考古报告罗列的历史文物:
“清嘉庆年间沉船骨架一副,船板若干;宋瓷若干;双鲤荷叶枕一件;明清仿汝窑粉青釉三足洗一件;青铜镇尺一件;明宣德铜像一件……另有考古现场民间发现文物若干。”
这便让百年后的复原工作与百年前的历史原貌明显得区分开来,百年前是人与人的关系,百年后则是物与物的观照。通过物与物之间的故事寻找人及人的活动,才能赋予运河以灵魂和历史感。新一辈的运河人用新媒体的视角发掘物与物的关联:谢望和用拍摄纪录片《大河谭》、孙宴临以“时间与河流”为题举办画展与摄影展,周海阔在运河边建立博物馆式民宿。
新时代的观照深陷于人与人之间和物与物之间的孤立状态之中,忽视它们之间的隐秘或神秘的人文关系。“他想以大运河为中心,但大运河在其中只起着穿針引线的作用,真正使得围绕大运河的人或物活起来的力量是文学和文学中的故事讲述法则。”[6]继而由“物与物”的关系超脱,走向新一轮人与人的相认。
在新的相认中,考古报告中出土的意大利信件赋予了冷冰“死物”鲜活的人文气息,凸显出人的主体作用,新一辈人互为主体与他者,产生了对运河新时代的解读。通过联想,他们发现威尼斯的运河和中国的运河同构,他们共同作为故乡的形象连接中国与意大利两个国家的旅人,从马可波罗时代绵延至大运河申遗成功的2014年。这样文学性的联想,将运河、故乡、意大利、中国和世界变成一个整体,走向世界,回到花街,有河流的地方便是乡土。
三.双线结构下的比较视角
《北上》中“北上”与“南下”两条线几乎并行,徐则臣让身为异邦人的迪玛克兄弟作为“他者”形象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中国历史中,洞悉运河的秘密,进而在比较视野中将运河的历史进行了生活化的表达。”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结构中发现多种对比关系,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代乃至图像与影像技术上的对比都一一展现。
“外域视角”与“本土视角”并行讲述中国历史的叙述方式在当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种创举,这与徐则臣一直以来致力于的“到世界去”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同时这样的比较视角也丰富运河的文化内蕴,试图用一种世界的格局来回顾和审视晚清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对文化事件进行整理和反思。在反思的同时《北上》也对历史进行不断的复现,在运河两岸不仅有建筑的历史,还有人文情致和非遗项目的网罗。如京剧大师周信芳、淮海戏、彩绘、刻画雕版、宣德炉、杨柳青年画、北宋汝窑、镇海口、大闸口、文通塔、清江浦、漕运总督府接连登场,串起了运河的文脉。以此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向世界展示了民族自信。
参考文献
[1]狄泽林克,方维规.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62- 164.
[2]李徽昭,徐则臣《北上》:河流、历史,及“比较”的小说写作[J].十月,2018.(12):23-25.
[3]蒋肖斌,徐则臣《北上》:京杭大运河流淌着中国近代史[N].中国青年报,2019-01-19.
[4]李枞,历史·道具·跨界——徐则臣《北上》中“运河”意象分析[J].名作欣赏.2019.(14):56-59.
[5]徐则臣,小说的边界和故事的黄昏[N].文艺报,2013-09-06.
[6]徐勇,物的关系美学与主体间性[J].绿色批评,2010,(5):65-68.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2020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0299215Y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学院)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