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王国维与陈寅恪》
刘梦溪
我研究王国维与陈寅恪,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想把钱钟书和王国维、陈寅恪放在一起,探讨一下现代学术这三大家的学术思想和彼此的异同。方法很原始,就是按部就班地读他们的著作。最先读的是钱钟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也积下好几册。然后读陈寅恪。没想到进入陈寅恪的文本世界,竟流连忘返,抽身不能。结果对三个人的研究变成了对陈寅恪一个人的研究。
研陈前后持续二十年,写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二是《陈寅恪的学说》,三是《陈寅恪论稿》。但陈和王的学术连带实在太紧密,研陈的过程中无法不涉及王的思想和著作。涉及哪一个问题或哪一方面的著作,就找来阅读,不单纯为取资,而是读就读竟全篇或全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出版的《王国维遗书》,成了我的案头必备。此书共十六册,多年翻检,不断圈划夹条,如今已膨胀得面目全非。还有中华书局版的《观堂集林》四册,虽然《王国维遗书》已收录,为查找方便,仍备于手边。包括各出版社印行的各种王著的单行本,以及文集、选集之类,也都是出来就买。港台的关于王的著作和资料,也尽量搜集到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的书信部分,让我大感惊喜,可惜从此再无下文,不免为之怅然有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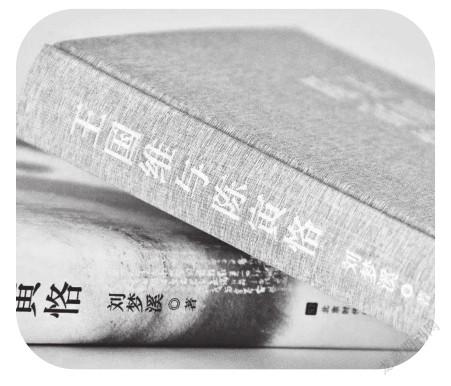
就是說,在相当一段时间,我的研陈变成了王陈同时阅读、同时研究,写陈的过程,也写了多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老辈学者有称本人为“王陈并治”者,概源于此也。钱钟书的著作也多有涉王的话题,说明当初试图将三人相提并论,不是没有缘由。他们都是顶尖的学术天才,共同特点为一个“通”字,即他们都是通儒。分而论之,王是文史兼通,陈是文史会通,钱是文史打通。研治范围和研究题域,则各有擅场。王方面广,开辟多,每治一学,都有发明。早期介绍和研究康德、叔本华,随即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的成果问世。继而治诗学,则撰有至今洛阳纸贵的《人间词话》。转而治戏曲,又有后人无法绕行的《宋元戏曲史》。王的诗学、戏曲两书堪称不世出的经典。后治古史,著作之多,令人赞叹。就中西学问而言,王、陈、钱都是中西兼通,而且认为“学”无须分中西,尤不宜自划畛域。
他们都是学者兼诗人。要问谁的诗写得最好,我未免嗫嚅不敢言。词当然静安第一,因为陈、钱都不填词,故没有二三。诗就不好说了。王诗成就之高,陈、钱自不会否认,但若以一二三排序,他们不一定认可。据友人汪荣祖《槐聚心史》透露,钱对陈寅恪诗颇为赞许,倒是前此不曾想到。赞许归赞许,不等于承认己诗在被赞许者之下。此无他,盖王、陈、钱都是自视极高之人。陈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是为静安立传,犹称尚无任何著作的自己“敢与时贤较重轻”。王自撰的《人间词》甲乙稿序,更称即使宋代的大词家亦少有能与之比肩者。钱的高才绝世,更应该是“名下士无天下士”了。当然在翔实的证据面前,在真才实学面前,他们又都很谦逊。称美和荐拔后进,不遗余力不足以形容。他们追求的是真理,探讨的是历史的本真,但开风气不为师。学术观点容或不同,但绝无丝毫的门户之见。他们都对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指斥的“党同异,妒道真”的风气深恶痛绝。而涉及道究天人、通古察今的洞彻高识,义宁之学又远远地站在了静安之学和槐聚之学的前面。
王陈钱的话题,永远也说不完。今次特从以往研陈和研王的文字中辑出十篇,都为一编,即以《王国维与陈寅恪》为书名,请熟悉我研治状况的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书稿早已于2019年8月排出清样,封面也完成设计。我因特殊缘故,未能及时校核复命。殆至庚子岁,又值大疫发生,越发延宕下来。
而此时,迄今搜辑最齐全的《王国维全集》业已出版,《王乃誉日记》也影印刊行。购置后即情不自禁地翻检浏览起来,不意有不少新收获,足以补本书第二部分《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之所不足。此次等于将此章重写了一遍,增加了很多新论述,特别对王国维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得出更加合理的死因诠解。此第二部分原稿只一万八千字,现经过修订和增补,已达五万言之多,几乎可以独行单出。作为本书的作者,心情以此安适了许多。
(源自《中国文化报》)责编:王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