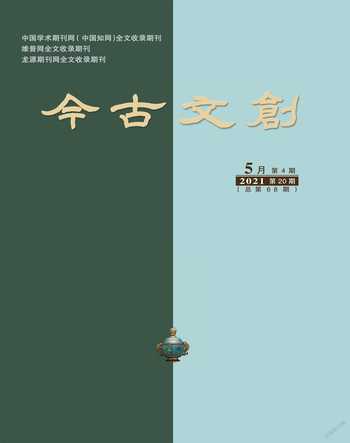论曹禺早期戏剧的原罪意识
张潇予
【摘要】 基督教对曹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作品中的基督意识不仅体现在《雷雨》序幕和尾声营造的基督氛围,《日出》开篇八段《圣经》引文等对基督文化的直接表现,还体现在其戏剧创作中包含的原罪意识、忏悔与救赎,表现对神秘的憧憬与困惑。曹禺吸收基督文化资源构建自己的悲剧世界,丰富了其戏剧创作的审美内涵。
【关键词】 曹禺;基督教;原罪;救赎;神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0-0042-02
曹禺早期的戏剧《雷雨》《日出》《原野》都受到了基督文化的影响,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与曹禺忧郁型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忧郁而热烈、自卑而奔放、内省而超越, 这精神个性就有接近宗教的可能”[1]。曹禺曾有一段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圣经》文学的经历,宗教带给曹禺关于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意义的启示。“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经常去教堂,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2]可见,从青年时期起,曹禺便通过宗教展开了对于人生与生命的追问。曹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外来宗教相碰撞,带着对人生问题的思索,曹禺将基督文化精神带入到创作中,丰富了其戏剧创作的审美内涵。其作品中的基督意识不仅体现在《雷雨》序幕和尾声营造的基督氛围,《日出》开篇八段《圣经》引文等对基督文化的直接表现,还体现在其戏剧创作中包含的原罪意识、忏悔与救赎、表现对神秘的憧憬与困惑。但曹禺并非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始终抱着理性的态度来思索人生、关照现实,又对宗教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疏离。
一、原罪意识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生来有罪。在《创世纪》中,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下了识别善恶的果子,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从那时起,人便有了“原罪”。在曹禺构建的悲剧世界中,充满了原罪与各种人性的罪恶。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犯下了基督教中不可饶恕的淫乱之罪,《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的主仆之恋,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的乱伦都犯了淫乱之罪。《圣经 · 利未记》中关于处罚悖逆的人中写道:“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他的姐妹, 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 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3]《圣经 · 申命记》中关于违命必受诅咒中则明确写明:“与继母行淫的,必受诅咒”“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诅咒”[4]。《圣经 · 哥林多前书》中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5]《原野》中的花金子也罪在情欲的张扬,犯了淫乱之罪,成为杀害自己丈夫与小黑子的帮凶。《日出》中的陈白露,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用肉体换取金钱与名声,虽然她也有自己的无奈,但她还是在贪欲指引下一步步走向堕落。潘月亭、李石清更是自私自利与欲望的化身,潘月亭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心狠手辣损害“不足者”,李石清迷恋财富与地位,不择手段向上爬,甚至置亲情于不顾。他们都印证了《日出》开篇的《圣经》引文,“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上帝便审判“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6],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7]《原野》中的仇虎,他罪在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对情欲的占有,焦阎王的死是上天替他做了了结,可他与上帝的疏离使他只关注于自己的复仇欲望的满足,从而犯下了更大的罪,重演了焦阎王的罪行。而大星与小黑子作为焦阎王的后代,上一代所犯下的罪必然由他们这些后代来承受,大星与小黑子的惨死正是这种原罪意识的显现。《雷雨》最终真相大白之际周萍向周朴园发出“你不该生我”的呐喊,也契合了基督教人生来有罪要受到惩罚的原罪论。“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8]
二、忏悔意识与宗教救赎
人生来带有原罪,人与上帝的疏离又使人常常忘记自己带有原罪,还犯下了本罪。“而上帝则一方面命定人犯罪,另一方面又竭力引导人皈依”[9],基督教信奉向上帝忏悔可以获得拯救。《雷雨》中曹禺借周冲之口写周萍的忏悔,“可是哥哥现在有点怪,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气很暴,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不知干什么?”[10]周萍出入教堂,已经暗示了他要将自己交给上帝,通过忏悔来洗涤自己的魂灵,拯救自己犯下的罪过。罪恶深重的周朴园犯下了许多罪,最初他的忏悔主要体现在对侍萍的纪念。周朴园与鲁侍萍三十年后重逢,周朴园在慌乱之际表达自己对侍萍的亏欠,“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11]他所做的一切纪念侍萍的举动都是源于他清楚自己始乱终弃所犯下的罪孽,希望以此弥补自己的罪过,获得一丝心灵上的慰藉。此时的周朴园还未皈依宗教,他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感的忏悔。而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忏悔,它要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耶稣为了拯救人类的罪恶替人类赎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人们面对自己的罪,要主动向上帝忏悔,祈求上帝的拯救。序幕和尾声的设置显然都是为了表明周朴园已经皈依宗教,表现宗教救赎的主题。“一些大资本家,甚至大军阀到了晚年,荣华富贵享受尽了,杀人杀够了,就想皈依宗教,什么佛教,什么天主教,从宗教里寻找寄托。” [12]孩子们死了,侍萍与繁漪也疯了,目睹了这一切悲剧的周朴园清醒又痛苦地活着,他将周公馆卖给教堂做医院,静静地聆听着尼姑诵读《圣经》,抱着忏悔之心来为此生赎罪。“《雷雨》序幕让周朴园走进教堂,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像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13]《日出》中的陈白露,既厌恶上流社会纸醉金迷、钩心斗角的生活,又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无法自拔,她的罪更多的是在折射上层社会腐朽势力的罪恶,她清醒地堕落着,她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自己的罪,只能在皈依上帝中拯救自己的靈魂,白露临死前,房间里射进来了满屋阳光,陈白露在上帝之光中获得灵魂的拯救。
三、对宇宙神秘力量的憧憬与困惑
曹禺的戏剧常常被解读为社会问题剧,但曹禺在《〈雷雨〉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14]《雷雨》融合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与易卜生的社会悲剧等多种悲剧因素,《雷雨》的命运悲剧正是表达了作者对于宇宙间那不可知的神秘事物的憧憬与困惑。“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15]繁漪对于窒息无爱的生活的逃离,使她紧紧抓住周萍这根救命稻草以至于陷入情感的漩涡难以自拔,在歇斯底里中走向疯狂。周萍悔恨于和继母难以启齿的乱伦关系,想通过四凤解救自己的灵魂,开始新的生活,却不知不觉引向了更深层的罪恶。《雷雨》中的人物深陷罪恶的泥淖,他们都拼命地想要抓住对方力图不下沉,可是他们越努力、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在互相拉扯中走向了毁灭性的结局。人物的挣扎与挣扎的绝望,对自己命运的主动把握与命运的难以把握所产生的冲突,都印证了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他们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又是谁在背后主宰着这一切?这斗争背后的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称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16]《原野》中逃出监狱的仇虎想报仇而不得,复仇对象的消失让他原本是正义的复仇变为了虚妄,可他对于血债血偿的复仇的执念,又使他杀死了大星,间接害死了小黑子,困在自己的“心狱”中为自己的心灵背负沉重的十字架。那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鬼魂,永远无法走出的那片黑林子,再现了焦阎王罪行的命运轮回,都显示了宇宙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主宰着人类,可以说推动曹禺创作动力就来源于对宇宙间这种神秘力量的憧憬。基督教中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主宰着世界,曹禺的创作中也暗含了命运是被上帝主宰的思想。但曹禺并非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始终抱着理性的态度来思索人生、观照现实,《〈雷雨〉序》中曹禺谈及周冲时说:“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17],这似乎又传达出命运没有被上帝主宰,因为上帝并不公正,是对基督教一定程度的疏离,所以其创作既有与基督教相通的一面,又有疏离的一面。但纵观其作品中的原罪意识、忏悔与救赎主题等内容,依然透露出曹禺作品中深厚的宗教意识。
参考文献:
[1]王本朝.曹禺与基督教文化[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1,(03):41.
[2]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32.
[3][4][5][7]圣经[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113,192,188,237.
[6][10][11]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93,46,91.
[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2-353.
[9]高浦棠.“升到上帝的座”上重新审读曹禺的《雷雨》——《雷雨》本源真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48.
[12]曹禺.论戏剧[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449.
[13]曾广灿,许正林.曹禺早期剧作的基督教意识[J].文史哲,1993,(01):85.
[14][15][16][17]曹禺.曹禺研究专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6,17,16,21.
作者简介:
張潇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