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论齐白石:“人民画家”话语再观照
刘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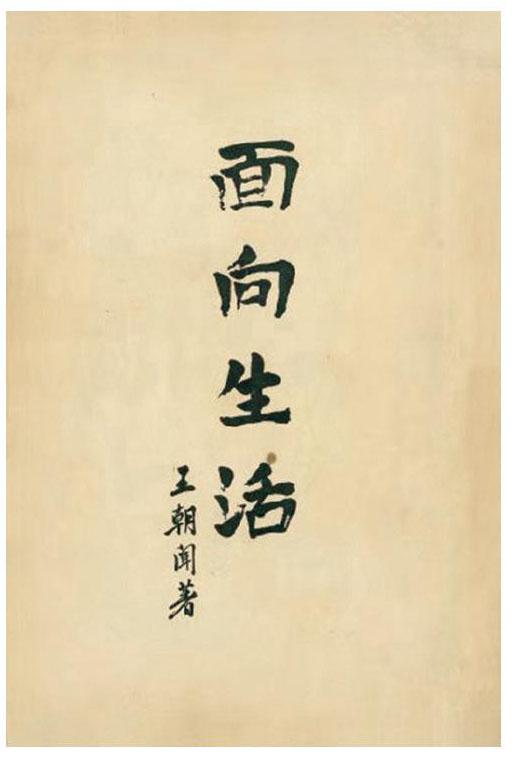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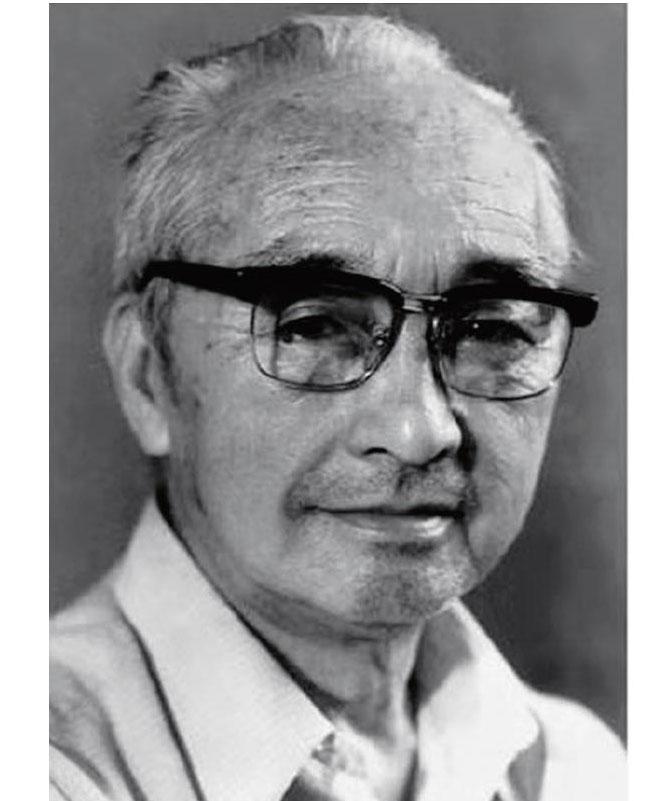
【摘 要】 1953年,王朝闻提出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是在当时居主导地位的人民话语体系中,立足民族艺术谱系,充分论证齐白石艺术杰出性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础上,史论结合得出的结论。这与将其置于1957年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苏联模式”和再度走强的阶级话语体系中,视为一个“以论带史”式的强制阐释性结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问题启发我们在艺术史人物分析和不同史学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结合,史论结合。
【关键词】 王朝闻;齐白石;“人民画家”论;苏联模式;人民话语;阶级话语
王朝闻先生(1909—2004)是我国当代卓越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建设工作,出版了雕塑研究、美学研究、创作方法研究和艺术评论等领域30多部著述,指导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美术工作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坚定的人民美学、人民艺术倡导者,他熟谙艺术创作规律,学术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艺术评论面向生活和人民大众,将艺术创造、欣赏和艺术规律探索融为一体,为人民群众和艺术工作者喜闻乐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基于文艺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个人的学术兴趣,王朝闻的工作重心逐渐由雕塑创作转向文艺理论研究。作为这一转变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自1949年春开始,他连续10个月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美术评论文章52篇(后结集为《新艺术创作论》出版);二是在50年代初期,从人民立场出发,提出了齐白石“人民画家”论,在齐白石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来,有学者从齐白石的个人话语出发,对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论断是一种虚构,是阶级话语和“苏联模式”强制阐释的产物,是“以论带史”史学路径的一个典型学案。[1]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存在着理论话语错位的问题。因为王朝闻提出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是在当时居主导地位的人民性话语体系中,立足民族艺术谱系,在充分论证齐白石艺术杰出性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础上,史论结合,得出的结论。这与将其置于1957年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苏联模式”和再度走强的阶级性话语体系中,视为一个“以论带史”式的强制阐释性结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话语错位”也引发了我们对如何评价艺术史人物和不同史学研究路径的思考。
一、《杰出的画家齐白石—祝贺齐白石的九十三岁寿辰》的版本问题
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主要出自《杰出的画家齐白石—祝贺齐白石的九十三岁寿辰》(以下简称“《杰出》”),其版本状况较为复杂,需要加以辨析说明。
其一,《杰出》一文普遍被认为系“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文”[1],而这篇文章实际刊发于1953年1月8日,是《人民日报》报道文化部齐白石寿辰庆祝活动的系列内容之一。王朝闻生前出版的《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王朝闻集》第二卷(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朝闻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中,均将此文发表时间标记为1952年1月8日。经笔者查找、核实,《人民日报》是日未刊载此文,次年(1953)同日第3版载有此文,而齐白石93岁寿辰庆祝活动即在前一日(1953年1月7日)举行。王朝闻对此文发表时间的误记早在1954年出版论文集《面向生活》(艺术出版社)时就已经形成,以致以讹传讹,流布很广。[2]
其二,《杰出》一文报纸刊文和结集本刊文内容存在差异。《人民日报》刊文大概4000字,而结集本收录此文多为7000字左右,字数相差近一倍。《人民日报》版刊文论述存在内容断裂、跳跃等问题;而结集本刊文较为完整、全面地呈现了作者的观点。
其三,此文在不同结集本中内容也多有不同。比如《面向生活》和《齐白石研究》(力群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所錄此文在开篇认为,齐白石是“人民画家”都是“因为他的精神劳动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艺术才能,因为他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使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因为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对于美术工作者具有示范作用”[3]。其中,第三个“因为”在1979年后《王朝闻文艺论集》中改为“因为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许多方面值得美术工作者学习”[4]。为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展开研究,本文以力群编《齐白石研究》所录《杰出》一文为讨论对象。
二、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
齐白石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与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齐白石荣誉奖章和王朝闻发表《杰出》一文有关。与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明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不同,1953年1月,文化部授予齐白石荣誉奖章主要是祝贺寿辰的一种形式,这可以从奖状的内容看出端倪—“齐白石先生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 在中国美术创造上有卓越的贡献 兹值先生九三寿辰 特授予荣誉奖状”[1](原文无标点)。奖状肯定了中国人民对齐白石老人的尊敬和喜爱,肯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卓越贡献,同时也点明了为他祝寿的主要目的。[2]
王朝闻撰写《杰出》一文与此次祝寿活动相关。纲举目张,全文基本围绕着确证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及其创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展开。王朝闻认为,齐白石的艺术史意义在于“他生在形式主义绘画统治中国画坛的时代,他的绘画作风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既不使艺术成为自然现象的机械模仿,又能把当时信笔涂抹的‘写意画从似是而非的陷阱中拯救出来”。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扩大了题材范围。相较于“前辈的‘写意画家的题材比较狭窄(如金冬心长于画梅,石涛之长于山水……)”,齐白石感兴趣的东西很多,曾有“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的说法。王朝闻认为,齐白石“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物象,扩大了题材的范围,小鸡、丝瓜、白菜、豆角,也成为作品的主角。由于他取材不受任何成见所限制,他的许多富于抒情味的作品,显出艺术形象的多样性,证明水墨画能够适应多种题材”。齐白石除了“在取材上突破了士大夫画家的套子”“发展了水墨画的特长”之外,“他那浓丽的色彩的大胆运用,更接近中国民间美术在用色上那种明快和强烈的风格,也和强调色彩的轻淡的一般的文人画大不相同”。齐白石既在取材上不使用士大夫喜爱的梅、山水等题材而采用劳动人民熟悉的瓜果作为主角,在风格上又不同于文人画的轻淡而更接近中国民间美术的风格,这与他来自民间又长期劳作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王朝闻认为齐白石“用这特长来描写许多不被他们重视而符合人民趣味的事物,是他的优点之一”。
二是作品有趣味。王朝闻认为:“齐白石的作品的优点之一,是有趣味。”“有趣味”有两种内涵:其一是“使作品成为有趣的艺术”,取得“状物与抒情的一致”;其二是“表现了健康的人的趣味”。王朝闻强调,这种趣味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他说,齐白石的“题材多是花鸟虫鱼,可是,这些题材的描写,不产生引人出世、使情感颓废的坏作用,而是表现了健康的人的趣味的”。而这种健康趣味是一种客观效果上的呈现,“尽管现实生活不只向我们提供齐白石作品那样的题材,尽管人民不只要求齐白石式的绘画,而花鸟虫鱼这些题材是人民喜爱的,一经他用传神的笔墨加以描写,产生了使人感到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美丽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这样,这些花鸟虫鱼的描写才得到爱生活的人民的欢迎,也才能够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三是齐白石在民族艺术谱系上的创造性。王朝闻认为,齐白石艺术上的创造性表现在突破笔墨游戏和形式主义的滥调,注重真实的细节,造型上更精粹、更洗练、更具概括性,作品具有诗意特点,是自觉自由的创作等。王朝闻说齐白石“不仅扩大了取材范围,而且运用了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使同一类的题材具有许多变化”,“他创造那些既真实又活泼的艺术形象,完全是自觉的,有明确目的的,而且很自由”。王朝闻用艺术辩证法分析认为,齐白石能够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就在于他一方面尊重前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的表现法则;另一方面又重视打破陈套,反对因袭,“反对因袭陈套,其实就是为了灵活运用法则。不机械服从法则,其实正是尊重法则”。王朝闻用相当大的篇幅(包括注释),重点介绍了齐白石对徐渭、朱耷、吴昌硕和石涛等人的尊敬(“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和在他们基础之上的创新,强调齐白石在民族艺术发展谱系上的顺承关系和创造性价值。在此基础上,王朝闻进一步强调了齐白石对于美术工作者的意义:“祝贺他的九十三岁寿,不仅表示对他的热爱和尊敬,而且将是美术工作者认真学习他在艺术上的成就的开端。学习他如何承继和发扬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学习存在于他的作品中的被承继和被发扬了的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
据此可以看出,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是以齐白石作品突出的艺术特征、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创获、艺术史意义及其与人民的关系、民族艺术的关系为立论基础的,这是《杰出》一文的学理所在,尤其是美术史、艺术史的视角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王朝闻总结道:“齐白石,人民的画家。他不仅用作品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而且用他的作品参加了保卫和平的神圣事业,因而更能引起人民对于他的尊敬。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方法和态度,他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他的灿烂的才华,早为人民美术工作者所热爱和尊敬。”
三、“人民画家”论的话语性质及其意义
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话语性质是人民话语,代表了王朝闻个人艺术评论的较高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艺术评论的较高水准,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史和齐白石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发展历史来看,阶级性、人民性批评话语作为主流,交替出现、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还贯穿着一条民族话语、国家话语脉络。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冲突,导致20年代末开始盛极一时的左翼文艺阶级话语,在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逐渐向民族话语过渡。到了40年代初,人民话语逐渐超越阶级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成为重要的和首要的批评话语,其理论代表是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中阐述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讲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强调,文艺是为人民的。[1]因此,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艺和共和国文艺一般被称为人民文艺。毛泽东文艺思想被概括为“人民文艺”和“人民文学”的概念范畴。“从此,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概念一起,成为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倡导的文艺方向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2]在民主主义者方面,1945年5月,闻一多在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论证“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提出了“人民至上”这一口号,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时代和思想背景下,“人民”“人民文艺”“人民艺术家”逐渐成为一种最强势和最高荣誉的批评话语,在“人民至上”的口號下,“人民艺术家”也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1]的最高名号。
在理论建构方面,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到1949年7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艺观和人民性话语体系基本构建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朝闻、张庚等学者进一步将人民话语向各个艺术门类推进,对人民性话语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
结合人民话语谱系的建构,观照《杰出》一文,我们会发现王朝闻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评价齐白石艺术价值的,其话语性质是人民话语。当然,这里的人民话语不是对阶级话语的否定,恰恰相反,它是以无产阶级话语为领导权的。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2]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人民话语和阶级话语及其历史。
其次,1949年后一个时期,文艺批评领域人民话语的发展与对激进阶级话语的批评是共存的。1949年11月25日,《文艺报》刊登了一封北京中学生的来信,信中问:在今日一切都走向工农兵的时代,文艺当然也如此,并且要比其他学科还要显著一些,学习写作者与爱好文艺者,都要学习工农兵的文章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的文章,但是中国的旧文学像诗、词等,是否也可以学习呢?它们也有文学遗产的价值,并且文学技术方面也是很高超的。对于中学生的来信,同期有杜子劲、叶蠖生代表叶圣陶做了简单的答复: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具有现实性的新文学,对旧文学,只可做有选择、有批判、有目的、有指导的阅读,并说旧文学的技术并不见得高超,现在更已步入绝境了。[3]这一答复引发了一些讨论。来自延安的文艺理论家陈涌是较早发表文章主张发掘古代文学人民性传统的理论家之一,此后,他在《文艺报》上发表《对〈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的意见》,认为简单否定过去诗词的遗产价值,“是有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它反映了一部分新文化工作者至今还存在的轻视乃至否定中国的历史传统那样的思想残余”。陈涌指出,这样一种历史的教训,在延安整风以后就得到了理论上的解决,只是“真正有计划地去学习历史的优秀传统,实在还没有开始”,但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现在一定要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学也正如外国的和民间的文学一样,至少有两方面是可以学习的,这就是一切属于人民性的内容和属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从陈涌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延安文艺在经验和理论上解决了对待民间文艺、古典文艺、外国文艺的态度和认识问题,它也更能处理好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左翼文艺传统的关系,而且较好地解决了阶级话语问题。
相比之下,来自国统区的艺术理论界反而更为强调阶级性。比如195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和赵景深《民间文艺概念》两部研究民间文学的著作,它们都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的价值,努力探寻民间文艺中的人民性传统,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在写作指导思想上努力向《讲话》精神靠拢。但由于两部著作存在从民间文学形式、形态上(比如强调口语性)去挖掘民间文艺人民性倾向,只在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完成“民间文学”向“人民文学”的转换,因此很快引发批评,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关于什么才是“人民文学”,怎样来看待民间文学的一场讨论。[1]
应该承认,来自解放区的人民文艺理论是自信的、包容的,人民性批评话语积极在维护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与反对庸俗化阶级论之间维持着平衡。1953年,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是在人民话语理论体系最盛时期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50年代初期我国艺术评论的较高水准。
最后,从人民话语和阶级话语的辩证关系及王朝闻个人艺术评论的经历来看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和左翼文艺理论是典型的阶级文艺论,这种文艺论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也容易出现激进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等历史局限。40至50年代,在总结革命文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人民话语成为主流话语,但到了1957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激进的阶级话语突起,人民话语受到批判,阶级话语重回主导地位并一直延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邓小平发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后,激进的阶级话语受到抑制和批评,人民话语重回历史前台并一直延续至今。祝词“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转向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思想基础。中国文学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转向了为人民服务,从反映阶级斗争转向了书写经济建设与人的命运。”[2]
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王朝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理论研究和艺术评论中也存在着政治功利化、主观化等弊病,尤其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阶级话语再度兴起之后,这个特征比较明显。比如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于1980年的《论凤姐》一书,就存在着泛用阶级分析、政治话语等现象。书中大量使用“阶级斗争”“阶级关系”“阶级意识”“阶级倾向”“阶级烙印”“阶级性”等概念和术语进行艺术分析。这和《杰出》一文中,王朝闻通篇未使用阶级批评话语,在分析齐白石艺术杰出性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人民性话语分析形成鲜明对比。当然,阶级话语的过度使用有其政治和社会根源,王朝闻也不能完全避免。因此,当我们把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放回到1950年代批评话语的延长线上去比较,自然会发现“人民画家”论代表了王朝闻艺术评论的较高成就。
四、“人民画家”论与“苏联模式”辨
不同于上述分析和评价,对《杰出》一文和“人民画家”论,有批评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认为“这篇七千字长文在围绕‘齐所以成为齐白石时,通篇套用的是当年盛行的苏联理论模式之‘立场‘方法‘观点,来穿凿其花鸟写意之‘为何画‘怎么画‘画什么”[3]。齐白石“从世间所得到的,与其内心最憧憬的并不对称。不仅不对称,其实尺码相差甚远。症结在于,那套抬举齐为‘人民画家的尺度,既不源自华夏文化传统,也无涉中国水墨艺术谱系,而纯属苏联模式的‘强制阐释,无怪齐有理由微词‘其究何所取,且几近直言那群自以为是的‘知之者对齐白石画未必‘真知”。“王朝闻遵命为齐筑一‘人民画家的光荣亭,他所树起的‘农家身世‘观察现实‘民间趣味这三柱子,无一不扎根于苏联模式的地基。”[4]笔者认为,这些解读不但不符合文本实际,而且以“苏联模式”来批评“人民画家”论也缺乏合理性。
首先,批评者认为《杰出》一文中存在着支撑王朝闻“人民画家”论的“‘农家身世‘观察现实‘民间趣味这三柱子”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杰出》一文提到了齐白石的农家身世、注意物象细节的真实、有趣味,但它们(尤其是后两点)和“这三柱子”在内涵上相差甚远。其一,批评者将王朝闻对齐白石客观的生平介绍等同于“苏联模式”的唯阶级成分论,“苏联模式不是指令大凡肯定某历史人物,须看其‘立场是否革命或进步吗?那么,在激情燃烧的战士眼中,谁离革命挨得最近?谁最能跟上时代的进步呢?当是饥寒交迫的底层百姓。这是火红年代的第一人际要领:‘讲成分。于是‘农家身世,也就成了王朝闻为齐加冕为‘人民画家的第一理由”。为了证明这一认识,批评者从《杰出》一文中摘出的论据则是:“他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家”,“小时只读过半年书。在二十七岁之前,当过牧童,作过十五年木匠”;“这位劳动者出身的艺术家,一贯热爱自己的工作。除了不得已的原因,从来不间断自己的工作”;“木匠出身而能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早年是乡间画匠“掌握了工细的技术,可以逼真地画出从纱衣里透出来的袍上的花纹”。而这恰好可以看出,王朝闻认为齐白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画家的主要原因:一是勤奋,二是早年乡间画匠的技术基础。王朝闻对齐白石农家身世、早年生活经历的介绍是一种客观描述,并不是“讲成分”的阶级分析,王朝闻并没有认为它是齐白石成为杰出画家的根本原因。其二,批评者将齐白石对花鸟虫鱼的细致观察等同于“苏联模式”的唯物反映论,“苏联模式不是指令大凡肯定某历史人物,须看其‘方法是否倾心唯物论反映论么?……王朝闻是左翼艺术评论的佼佼者,也是很早仰望克里姆林宫星光的弄潮儿。于是‘现实观察,也就成了王朝闻为齐加冕为‘人民画家的第二理由”。批评者从《杰出》一文中析出的论据是:“不论是作品,还是言论,都显示着老先生认真观察对象的主张”;“除了前面提到的青蛙、螃蟹之外,其他如透明的外硬内柔的虾体,欲跃的蚱蜢和蝈蝈的动态,正在振动着两翼的蜜蜂,饱和液汁、光泽耀目的樱桃,富于弹性的松针和挺拔坚实的松干,梅花那正侧向背的种种姿态和有变化的枝干的穿插……这种真实感的形成,不能不归功于他观察的精细和深入”。重视艺术细节的真实体现是王朝闻总结的反映齐白石艺术杰出性的一个方面,但显然,批评者将艺术家对表现对象的细致观察等同于唯物反映论,这在学理上无法成立,因为这里主要是对具体物象细节的观察,它和唯物反映论所强调的对社会关系的“现实观察”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三,王朝闻认为有趣味是齐白石作品的一个优点。他强调的“趣味”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并不是一般的“民间趣味”。但批评者则将这个优点等同于“苏联模式”的独尊现实主义论,甚至将“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论等同于民间论,“苏联模式不是指令大凡肯定历史人物,须看其‘观点是否青睐现实主义么?左翼艺坛对现实主义一词的解读,很少能将它纳入十九世纪巴尔扎克为符号的叙事语境去反刍其本义,而更愿惯性地将它简化为‘写实技巧+现世关怀,即主张用写实笔法来‘接地气,且由此衍生出‘民间‘民粹‘民俗诸概念。王朝闻难免其俗。于是‘民间清趣,也就成了王朝闻为齐加冕‘人民画家的第三理由。”[1]由此可见二人对“趣味”有著不同理解。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批评者虚构了“‘农家身世‘观察现实‘民间趣味这三柱子”的内涵,并刻意将“人民画家”论与阶级话语和“苏联模式”接驳,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性的误读和“强制阐释”。
其次,批评者批评王朝闻时使用的所谓“苏联模式”一词内涵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的“苏联模式”,一般指的是以反映论、阶级性、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等理论为基础的,主要起源于苏俄及苏联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尤其是简单化)的文论体系。这种文论体系直接或者通过日本影响到我国。不同时期的“苏联模式”有不同的内涵,比如20世纪20至30年代影响左翼文论的“苏联模式”主要是“拉普”,但它显然不同于后来苏联“日丹诺夫”意义上的“苏联模式”。有学者指出,“十七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来就没有完全苏联化过。因为无论是在整个文艺理论界,还是高校文学理论课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毛泽东文艺思想始终指导着理论和教学。毛泽东思想是在汲取1930年代以来‘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失败的教训后形成和崛起的。”[1]笔者认为,作为文艺理论批评领域的所谓“苏联模式”应当限定于1957年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且更多地应当限定在文艺理论教科书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教科书)模式”出现得很晚。1954至1956年,教育部请来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班讲授文艺理论课,为我国训练了一批文学理论教师,这批学员毕业后便迅速充实到全国各地高校的文艺理论教师队伍中。培训讲稿《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反映论和阶级性(包括文艺理论内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影响了我国艺术理论,阶级性成为艺术的第一社会属性。阶级性决定思想性、思想性决定艺术性、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等分析模式在1957年至1962年之间被不断强化和固化,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突破。而在1957年之前,我国艺术批评领域一要摆脱苏联文论影响,走民族化发展之路;二要摆脱如影随形的各种“左”的错误。两种努力一直客观存在,否则不会出现1956年的“双百”方针,不会在1957年上半年还出现大量后来被冠以所谓“修正主义”的文论。因此,如果有所谓“苏联模式”存在的话,它的完全确立应当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显然,批评者使用所谓“苏联模式”阐释“人民画家”论,不仅在理论内涵上存在差异,在时间节点上二者也并不同步。
因此,笔者认为,批评者将王朝闻1953年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归结为一种虚构的结果和使用所谓“苏联模式”强制阐释的产物是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批评理论语境的错位,没有将王朝闻的“人民画家”论放在当时已经居主导地位的人民性批评话语体系之中,而是置于1957年之后才出现的所谓的“苏联模式”和再度走强的阶级性批评话语体系中,进行错位批评和强制阐释,这必然造成其论述失效,进而影响其证成目标的实现。
五、艺术史人物评价与史学路径选择
在批评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时,批评者认为:“王朝闻、娄师白、李可染、贺天健们将白石老人硬拗成‘人民画家的所有说辞,皆属‘过度阐释”,“因为只须翻阅1948年‘脱稿的《白石老人自传》……能有效解构‘人民画家说的史料俯拾皆是”,“‘以史鉴论的非苏式路径真当感念《自传》,因为它酷似风月宝鉴,一下让‘人民画家说露出马脚”。[2]笔者以为,批评者认为“人民画家”论是根据所谓“苏联模式”来评价艺术史人物,是一种“以论带史”的史学路径。这引发了关于艺术史人物如何评价、史学路径如何选择的两个艺术史论问题的思考。
首先,关于艺术史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指导下常用的方法。但对于一些作家、作品和艺术现象而言,阶级分析方法有时又确实不那么普遍、适用。因此,对于阶级分析方法的不足,艺术理论界在50年代开展了“中间人物”论、“带有中间性作品”论大讨论。所谓“中间人物”“中间性作品”,主要指的是阶级性不强或者不明显甚至根本就没有的作家、作品。比如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讨论的结果或者说讨论中形成的主要共识是:从人民的角度,承认中间性作家、作品的存在,并且积极肯定了中间作品的人文、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1]
“人民画家”论的批评者认为,齐白石“在生前为其画集所写的一段自序,却又流露了另番夙愿。有识者既可将它读作他写给艺术史的郑重遗嘱,至察者则可从中听出隐衷:即艺术史对齐白石未必不存亏欠,因为他一直在等历史对其终身成就有个经得起证伪、能真正知晓其诗画之底蕴、至少能让齐自己信服的‘百年公论,然‘今将百岁矣,他叹未等到”[2]。批评者忽视了齐白石自我期许的评价是偏于艺术水平的评价,王朝闻的“人民画家”论是一种总体评价,便揣度认为齐白石并不会认可王朝闻的“人民画家”论,继而以齐白石的个人话语来拒止对齐白石作客观评价、历史评价。这种以个人话语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个人自述和艺术本体契合就是艺术家“垂范千秋之奥秘”,那么这种艺术家在历史上何其多也!但历史和人民又曾记住了几个这样的艺术家呢?
馬克思曾在《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3]虽然马克思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论述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完全或主要依据个人话语进行艺术史人物评价是不合理的。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批评方法[4],这对于评价艺术史人物的立场和方法也有重要指导意义。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艺术史论经验的新的总结,更是我们党的文艺路线方针不断调整、愈加科学、符合实际的体现。因此,关于如何评价艺术史人物,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分析方法,科学客观地评价艺术史人物;二是像马克思一样辩证看待人物的自我评价或者自我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评价艺术史人物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以论带史”“以史鉴论”两种史学路径也值得思考。学术研究一般强调“史论结合”“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应用到史学研究,被称为“史学路径”。“以论带史”“以史鉴论”是典型的、具有张力关系的两种史学路径。“以论带史”指以一定理论作为指引来处理历史现象或史料;“以史鉴论”指理论应该经得住史料和事实的检验。如果将“以史鉴论”作为“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对立面来理解,对于一些空泛的、人云亦云的学术研究确实构成一种批判,强调二者的张力关系有其特殊意义。但如果为了强调“以史鉴论”而刻意否定“以论带史”则没有必要,笔者认为,所谓“以论带史”不应该被完全否定。
在传统学术中,类似“以论带史”“以史鉴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争论存在已久,但至今也没有见到某一方被完全否定。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是互补的。“以论带史”和“以史鉴论”的结合就是“史论结合”“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论带史”体现了普遍规律性和学术主体性。如果完全不承认“以论带史”,也就等于完全不承认有客观规律,不承认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存在,不承认有前人认识经验的积累,会陷于特殊性、差异性和个别性,在形而下的感性泥泽中丧失理论家的主体性。
“以论带史”的关键在于如何“带”。如果将其理解成一种“无条件性”的“带”,这种“带”就是“唯‘论是从,不在乎‘史之本真的”[1],这种“带”我们肯定是要否定的(但批评者将其用于批评王朝闻的“人民画家”论无疑用错了对象)。如果“带”是一种处理材料(包括史实)的科学态度和方法,经得起“以史鉴论”的检验,那么这个“带”就是正确的方法。如果只是让材料单纯地去适应主观之论甚至是外来理论,或者反过来根据主观之论或者外来理论来选择史料甚至制造假史料,则无疑是错误的。同理,“以史鉴论”也存在选择什么“史”、如何“鉴”的问题,有许多规定性。因此说,“以论带史”“以史鉴论”两种史学路径在艺术史论研究方面都具有学术价值,关键在于如何科学、正确地使用。
结语
学术研究贵在实事求是。人民话语、阶级话语、苏联模式、以论带史、以史鉴论,在“是其所是”的意义上,都有其历史和逻辑上的合理性,也都有其在实际上适用性的不足或局限,尤其是在被极端化和简单化对待的情况下。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应预设某种话语、模式、方法绝对或必然优于另外一种话语、模式、方法。
回到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探明其话语性质和理论意义,并不是为了贬低阶级话语、苏联模式或者以史鉴论的史学路径,单纯为人民话语辩护。应该承认,極端的阶级话语在王朝闻理论研究和艺术评论中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存在,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做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状。但毕竟瑕不掩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王朝闻的齐白石“人民画家”论在当代艺术理论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艺术理论话语发展的轨迹及其背后的逻辑,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发展和构建当代的艺术理论和民族的艺术理论史。
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2020年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院级学术研究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1-2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