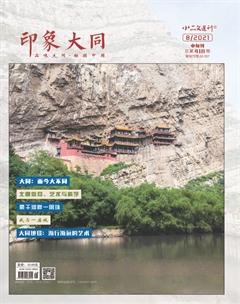新的审美向度与生存困境的抒写
马桂君

时代纷繁复杂,今天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形式呈现多元分化的状态,经典文学创作的份额被切分。再加之理论上的文学原型和母题早已在太阳底下摊开几千年,新锐的各路文学写手又无孔不入地翻熟了通俗到高雅的可耕地,作家想要创新突围越来越困难。今天的严肃写作及写作的成果,在众多芜杂的数字娱乐自媒体中使传统文学守住了一席之地,描摹时代面影的同时葆有诗性的审美价值,并给予多层次阅读需求深度体验和评论研究的延伸,这些都是传统作家写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石囡(史龙跃)的两篇新作《子虚镇的蝙蝠人》和《蜜蜡是个流氓》,可以作为一个系列来分析。前者是儿童视角,而且是特殊儿童的视角;后者则是少年视角,合在一起可以命名为“成长罗曼司”系列。革命的罗曼蒂克,指的是将革命和恋爱结合的写作模式,而“成长的罗曼司”,则是从孩提到少年,幻想中的黑道风云、城市超人和现实生活的灰暗污浊、贫乏平庸相对照。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今天的罗曼司和过去的罗曼蒂克都仅指涉想象和言说,照不进现实。
《子虚镇的蝙蝠人》最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意象——蝙蝠人,并随之发展出新的审美向度——介于审丑和暗黑之间。从未知国度流浪来的蝙蝠人既像一个工业时代的废弃品,又像是娱乐时代的文化怪胎。它有多面立体的行为表现,画画、读书、说外语。“异人”自唐宋传奇就多有记载,自古便是文学创作天然独特形象的来源。出现在子虚镇背景下的它,在展示自身的同时也展示了时代的荒芜:天气恶劣异常、工厂不景气、学校破败不堪,官僚主义横行。它作为时代的废弃物,只能看到什么吃什么,因为无从选择。这又让我们想起了卡夫卡《饥饿的艺术家》,他徒劳的抗争与蝙蝠人的屈从有一定内在的关联。
但是子虚镇的蝙蝠人既不像变成甲虫的格列高里,又不是石头崩裂造出的神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幻想和现实交叠后的产物。蝙蝠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用来标记我们的时代,说是时代烙印也不过分。因为我们的时代印记,不应该仅由政治社会事件来命名划分。文化娱乐形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员,它们作为人人熟知的共同记忆,可以视为一个个标签或者时代的象征物来分割历史。所以我们的文学话语中会自然而然出现这样的表达:那是在遥远的2021年,李焕英正在各个城市里面引得人们痛哭流涕……。
谐谑并消解城市超级英雄的故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融合,把跨越了地域文化限定的大众形象移植、再生,进行再利用再创作。可资书写的资源已经不仅来自现实生活,还包括既有的精神创造。今天的城市没有神话,神祇跌落到人间象征着文明发展的抛物线。超级英雄落难,是因为现实不能提供英雄生长的土地和空间,就像污染干涸的河水不能再养育出游鱼。
其次,小说形象化地表现了农业社会在工业化冲击下生命的存在困境。污浊、干涸、怪异的生存世界像狰狞的荒原,与传统理念架构下的温柔敦厚优美和谐形成对照,言说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作者配合魔幻超现实的手法,以类似现代聊斋志异的怪异人物荒诞故事为中心,传递出来的已经不仅是个人化的情绪体验,而是上升为寓言性的人的整体存在困境——异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荒诞及不可理喻,作家本能地感知到,但是传统的手段在此刻显得无力,因为既有的话语经验难以表达尚未表达的空间。既有的表达信息输出者和接受者已经在建好的轨道两端,沟通瞬时完成。而“孤独”“漂泊”“失语”等等诸多已有词汇都不足以表达存在本质上的荒诞性。语言的尽头是意象,于是独特的意象被创造出来,蝙蝠人如同一个苍老的先锋,独行在现实的荒原。
如果非要提炼一个主题的话,我的揣测是文本试图通过一个美国故事里的形象代码,植入对环境异化的思考,当然也包括人的异化问题。一个超级英雄类的传奇人物,被迫吃进各种垃圾,异化为长着脓包的怪胎。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里面被污染成腐烂神的河神。焦化厂、棉毛厂、废水等词汇,都和工业化的后果相关联。可惜的是这样的主题意念太过陈旧,关注环境保护,早已过了提出问题的阶段。现在面临的是如何积极应对的现实选择问题,如碳中和、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等等。
作者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影响的焦虑(来源可能是马尔克斯、寻根文学、陈染林白某些私人写作等),再加上创新的焦虑。如果主体想要表达的观念很急迫,往往在文本中体现为多线索触角。作者使用拼接的手法,让故事和记忆的点滴随机组合。既然康定斯基让我们认识到可能没有形式才是最深刻的形式,所以随机拼凑或许比人为刻意摆布能达到更合理更现实的结果。生活的非本质性让逻辑和规则丧失了统领性。作者在此观念上又配合儿童视角的形式,以无先验性理论填充和认知建构的懵懂头脑、不解的眼睛、无法言说的限定(因为皮皮只哑不聋),来看怪诞荒芜的现实。三重叠加后文字的折射散射效果,因光线多次变形,波互相干扰,形成光怪陆离的繁复画面。
《蜜蜡是个流氓》呈现的则是曾经年代留在记忆里的场景,包括物质贫乏年代关于贫困的个人记忆和成长的烦恼。小镇上的少年,幻想和凡俗平庸生活逻辑不一样的“黑道”社会,打打杀杀快意恩仇。香港黑帮电影实际是传统武侠小说与现代言情文掺和后的产物,在个人英雄历史中加入了情爱纠葛的元素,满足平凡卑微孩子的英雄幻想。渴望成人世界大概是每个少年体内都必须要有的生长素,同时也可以成为催生艺术创造的力比多。
到了后半部分,幻想中的反日常还是掉落到了平庸的日常中。关于群殴过程两种矛盾的说法,一种可以代表想象的电影式的场景,另一种则是真实的日常的场景。既没有真刀真枪的流血牺牲,更没有惊世骇俗的桃色事件,蜜蜡既没有成为流氓(这里流氓约等于英雄),连偷窥女生洗澡的小插曲都轮不到他主唱。
对于个人而言言说过往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碎片是仅存的记忆填充物,作者展示出来,是期待读者阅读后产生共情,如果愿望达成,那么作品可以说是充实立体的。这要求基于个人成长背景下的成长记忆,要实现对社会历史的还原、勾连的有机建构。言说记忆如果没有形成具有个人性的、艺术化的表达,或者说在别的作品里面有更形象化的方式表现过了,记忆碎片的价值要大打折扣。简言之,没有典型化的环境和典型化的人物,个人记忆会因缺乏深度而降低辨识度,人物形象也无法鲜明立体,容易湮没在时代的混沌底色上。
典型的环境加上典型的人物,依靠艺术性的转化方式,创造出新的意象或者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必由之路。对比《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的写作过程,说到底还是因为创作主体真正地经验了生活,实现对生活由细节部分的纹理到整体逻辑的把握。作品缺乏典型性,首先是因为生活的限制。创作一方面来自生活,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虚构。具体的创作主体如果生活经历不能体验到足够的“典型性”,缺乏历史的深度,那就要扩张虚构的能力。可是虚构归根结底又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必须建立在符合生活逻辑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的批评是为了让一个有希望的作品更加完善,所有我说的大部分都是问题。我想作者最大的问题是回避了现实主义,他的回避直接原因是缺乏生活现场的经验,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只能从印象中捕捉到零散的意向进行演绎,导致发力點不是形象自身,而是作家自己的虚构能力。实际上当形象按照自身的逻辑站立起来后,作家的主体性对历史逻辑、人物性格的掌控几乎失效。马列主义文论强调“现实主义的胜利”,能够成为现实镜子的作品,就是因为充分把握生活的现实和人们的精神意识以及社会生活矛盾冲突的本质,所以表现的东西超越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比如托尔斯泰生活在沙皇年代,他代表的是地主阶级,但是他的作品能传递出资本主义甚至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信息。
作者在创作中勇敢地进行了形式方面的创新。但是形式创新的空间相对比较狭窄。以形式开启文学创作的先锋性,只有第一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后面跟随的都是影子,大多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另一方面,缺乏历史内容创作会流于现象的层面,局限在个体的天地,走上自然主义的小径,而现实主义却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就上述两篇作品来看,如果将应有的历史深度和典型性有机关联,提炼出能表征时代和社会的主题意象,加上石囡富有诗性的语言功力,相信他的创作会更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