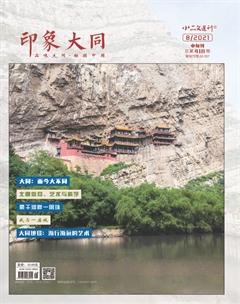吕新,带着伤痛荣辱的文字抵达故乡
蒋殊

吕新的记忆里,没有初中。自1971年进入小学后,连续读了七年半,之后突然在一个“正经的秋天”升入高中。
吕新的少年时期,只零零碎碎看过一些红小兵画册,大多是抓特务,抓地主,以及控诉旧社会一类。而一些“正经”的书,只有少数大人才有。他也曾有机会偷看过,但没有足够从容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比如《三侠五义》《水浒传》这些作品,就是在忐忑和惊慌中看完的。
1986年,山西省作协举办了为期半年的“赵树理作家班”,23岁的吕新成为其中一员。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写作者,掀开了人生中较为关键的一页。也就是这一年,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在《山西文学》刊发。
两年后的1988年,吕新又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瓦楞上的青草》。1989年,更是一口气发表了18个短篇及两个中篇。
吕新的名字,迅速进入全国读者视野。自1992年尤其是1993年以后,他的作品几乎都成为中篇小说,并开始了长篇小说写作。
正当读者对吕新越来越期待的时候,他却在2007年之后来了个急刹车,发表的作品大幅度减少,最多时一年只有一个中篇。面对读者的疑问,他说“某些时候,写作如同搬家,一辆独轮车,或许一个绒毛玩具就装满了。”而吕新,好似一个一生都在毁坏又在不断建造的人。他需要那种辽阔,坚固,载重能力强,同时又适宜于长途跋涉的载体。他坦言,中年以后少了年轻时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热情减少,考虑的问题更多了一些,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衷于发表。“如果不能很好地交代自己,不能够说服自己,是不会动笔的。也许还会问自己一声,这个东西写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意思?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得不到答案,就不会开始。”
熟悉吕新的读者都说,从《那是个幽幽的湖》一路走来,吕新的作品本质上都没有变。也有评论家说过,“吕新的小说似乎只是一种稍微的调整,其‘本质一以贯之且依旧坚硬如故。”这一说法,吕新本人并不太赞同。他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就如一个人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从心态到情感再到眼光和行为,再到观点,观念,立场,审美,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甚至重新确立,笔下文字怎么可能没有改变?只是外人看见的还是那个人,还是那副模样,还穿着那样的衣服,这就必然会造成无限的隔膜和陌生。
年轻的时候,吕新的创作构思比较快。但写到一定程度后,他有意慢下来,甚至常常在写作很顺利的时候专门停下来,去做别的事。他就是希望思路冷却一段后再重新开始。
“就像铁匠打铁,总得有个淬火的时候,不能一直那么通红炽烈地干下去,打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用。”他这样解释。
在读者眼里,吕新绕不过“先锋作家”这个称号,更有人说他是“当下中国最后一位先锋小说家”。比如他2017年获奖的长篇小说《下弦月》,评价依旧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先锋技巧,再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的广阔图景。”关于这个说法,吕新依然是那句老话,“一千个人眼里可能会有一千个你。”他觉得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光看别人。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别人如何说自己好,都不能表示同意甚或鼓掌欢呼的,反之也不能因别人说不好而不同意。”
2014年,吕新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得“鲁迅文学奖”,这篇作品后记中,他这样写:似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纪念的性质和意义。他说,这个纪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吕新眼里,一生中可纪念的太多,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几代人,一个地方,一座房子,一条河,一片曾经开满野花的原野,一段路程、岁月,以及一些让人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往事。
吕新说过,写作的目的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他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身在何方,得意抑或失意,可能总有一扇门是朝自己开着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吕新和大多数作家一样,书写也是从故乡开始的。他的理解,故乡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发也可以随时返回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起飞,也可以不在那里起飞;可以降落在那里,也可以降落在他处。
吕新作品中的背景,大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说,回到六七十年代,有一种明显回到故乡的感觉。回到地理意义上的那个故乡,看见一处院子,会记起多年以前谁曾在这里发出过笑声,谁曾在这里撒手人寰。看见整个从前的故乡,一切都如同一幅微缩过的景观。“某一天傍晚,我在那些狭窄倾斜的街上行走,脚下虚虚实实,仿佛踩着一些昔日的灵魂。恍惚中听见有的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在下面说:‘你踩住我的手了!”
吕新自己觉得,能体现他创作改变的作品是《白杨木的春天》与《灰蓝街》,它们表面看是作品,背后却反映着一个人在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越来越会思考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大多数时候,他不相信历史是可以触及的,也不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在他眼里,不必有多远,即便是昨天乃至今天刚刚发生的事,也不一定能触及到,不一定能弄明白其中的因果、脉络、走向,包括某种突如其来的急刹车以及背离初衷的转折。
“我事实上并不想与什么过不去,更愿意宁静一些,可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出现了距离,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已经站到了一些东西的对面。”吕新这样说。
文字中,吕新是一个极其冷静的人,即便是诸如《白杨木的春天》《灰蓝街》中描写惊心动魄甚至是血腥无比的故事,也一样让读者觉得不动声色。他说,书写的时候,心情就是他们中间某一个人的心情,或者他们各自的心情。只要客观地描绘,真实地叙述,不虚假,不做作,不考虑是否有人看,更不管是否有人喜欢,不去管它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杜绝作品之外的杂音。同时可能也会把许多噱头,把装腔作势和张牙舞爪拒之门外。他不认为,怀着一种大佬的心情,可以讲述好一个穷人的故事。
写作的时候,吕新有时会沉浸在小说中的人物里。他记得,当年写《发现》,后来写《草青》和《阮郎归》等作品的时候有过那样的情形,“走在现实的街上,感觉却是走在1950年或1962年的某一条街上,满街金黄,幻觉般地看到小说里的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袱,正在敲临街的一个门,木板褐黄,上面却溅有猪血和雨水的痕迹。看见一个人扎着围裙,坐在一个小饭店的门口抽烟,心里想,还抽呢,一会儿就要出事呀。感觉血已从里面顺着门缝流出。”
在读者眼里,吕新的作品似乎总是远离現实世界。但他说,没有现实世界现实生活对一个人的强烈辐射,不可能有笔下的作品。他只是不喜欢描写公司,官场,股票,白领,投资,新闻,办公室;也不喜欢写谁给谁打了一个电话,谁请谁吃了一顿饭,谁和谁然后上了床,谁谁去旅行……等等类似的内容。大多数人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而他却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吕新眼里,这些不过是一些时间的泡沫而已,一觉醒来,满地垃圾。
选自《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