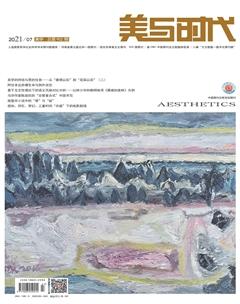“娜拉出走”的困境


摘 要:老舍的《月牙儿》与《阳光》分别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了旧社会中底层女性与富家女各自悲惨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文学界侧重分析《月牙儿》和《阳光》中的女性悲剧,对于小说中呈现出的鲜明的反讽特征则较少涉及。老舍巧妙运用西方反讽诗学中的夸大叙述、克制陈述、表象与事实的对照等言语、情景层面的反讽方式,对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解放进行质疑,也揭露了道德文明、启蒙教育中荒谬可笑的实质,使小说更具批判力量。
关键词:老舍;反讽;月牙儿;阳光;女性
作为语言大师,老舍擅长幽默与反讽,他的笔下不乏优秀的反讽作品,如《二马》《猫城记》《离婚》等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值得一提的是,短篇小说《月牙儿》和《阳光》以优美细腻的行文取代老舍惯常的幽默与油滑,以第一人称视角分别书写了底层女性和上层女性的悲剧人生,成为老舍构建的反讽世界中独特的“姊妹篇”。《月牙儿》中,母女两代的殊途同归,先后验证了底层女性沦为妓女的“宿命论”。《阳光》中的富家女浪漫的爱情理想在男权社会的轰击下灰飞烟灭。《月牙儿》和《阳光》在以女性第一视角自述时,也贯穿着老舍对女性解放、道德文明、启蒙教育等社会问题的质疑与批判。在互文性地表现女性命运的同时,又加以不动声色的反讽态度,使用“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1],使小说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反讽特征,获得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一、女性解放的反讽
女性对于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诉求,对主体意识、生存价值的关注,是新文化运动张扬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表现。《月牙儿》和《阳光》中诸多女性在解放之路上作了不同的探索,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对此,老舍以否定的态度刻画了女性潜意识中旧生活的印痕,着重对女性本体进行审视,反讽地揭示出导致女性解放失败的自身心理痼疾——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男权根深蒂固的依附意识。
在《月牙儿》中,对女性解放的反讽声音来自于“我”和一同在饭馆“受阅”的少女、一号女招待,以及女同学们对于“吃饭”的不同看法。许多高小毕业的漂亮女孩们却在“等皇赏似的,等着那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落选的则对“我”表示出羡慕甚至“含泪走去”。这里使用的是言语反讽中的夸大陈述,即虚情假意的夸张,实际上暗指相反的性质[2]155。“皇赏”是荣耀的,背负封建传统的女孩们,如宫女选秀一般将男性对自己的接纳视为至高无上的恩典,殊不知这份“皇赏”让自己丢弃尊严,出卖色相,成为男客们的玩物,换取他们的施舍。在她们看来,只有得到男性的认同才是女性无上的荣光,相反,落选意味着耻辱,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全方位否定。饭馆的第一号女招待更是对此大言不惭:“女招待嫁银行经理的,有的是,你当是咱们低贱呢?闯开脸干呀,咱们也他妈的坐几天汽车!天生下来的香屁股,还不会干这个呢!”“天生下来的香屁股”同样是夸大反讽,呼应前文的“皇赏”。女招待们不会明白的是,让她们引以为傲的女性胴体,不过是男性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具。和一号女招待抱有相同心理的还有主人公的同学们,她们乐此不疲地自觉遵守着男权社会的规范,努力将自己打造成男性完美的附属品,她们自作聪明地想攀附男人,用青春赌一个未知的荣华富贵。这群女性早已深陷牢笼却无知无觉,她们“愈盲目,反讽意味愈明显”[3]42。对于同一项肉体买卖事业,一号女招待和女同学们流露出“热爱”與“渴望”,而“我”在思想及行动上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厌恶,两种观点的对照构成耐人深省的反讽,暴露出女性依附心理的集体无意识。
底层女性是如此费尽心思地“吃饭”,《阳光》中的富家女在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中也只能无奈选择后者。当她想要逃离封建家庭、追求爱情的时候,她与家族抗争,一旦要剥夺她的身份地位,她却“自动停战”,其前后态度的转变形成反讽观照:女性在宣称自我的解放的同时,却轻而易举地投降于安逸的生活。当她抛弃了她后来发现实属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无所有之时,只剩“回想过去的光荣”,而“失去了明天的阳光”。此处又为言语反讽,她所理解的“阳光”“光荣”,不是作为新女性该有的独立意识,不是自由平等,而是家庭和丈夫带给自己的财富与地位。“明天的阳光”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代言词,而是冰冷的婚姻,是伪善,是利益。“过去的光荣”是遮蔽了理性光芒的虚荣,使“我”最终妥协,在无爱的温室中沦为家长制和社会规范下的傀儡。这样的想法和做法使女性堕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人生怪圈: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附意识使得依附男性成为唯一的选择,而依附于男性的后果就是遭到更严重的压迫。“光荣”不过是虚无,“阳光”实则是黑暗,然而这些被反讽的女性却并不明白,因此加深了反讽的效果。
除此之外,老舍在这两篇小说中都设置了男性“缺席式在场”结构,以此来加强对女性这种依附意识的批判。无论是《月牙儿》中几番改嫁的母亲、“眼溜着年轻男人”的“我”的同学们、被丈夫所骗也要从一而终的小磁人,还是《阳光》中向往爱情与自由的主人公,无一不是靠男性而活,或为男性而活,男性对女性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而《月牙儿》中的男性形容模糊,如同幽灵一般,生父登场即去世,新爸、馒头铺掌柜一闪而过,至于诱骗“我”的胖校长的儿子以及后来在文本中出现的男人,不过是谎称“道德”的迫害者、形形色色的嫖客。《阳光》中同样如此,理想的正面男性从未出现,有的只是糟蹋良家妇女的父兄、玩弄“我”同学的男人们、势利眼的丈夫、喜新厌旧的贵人等。老舍批判现代社会里不再给予女人以爱、温暖和保护的男人,他们使女性如同失去阳光的照耀而永远陷入黑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即使理想男性日渐沦丧,和谐的两性关系不复存在,失去自我与选择的女性依旧需要并且只能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月牙儿》中母亲多次改嫁、“我”努力挣扎也无力逃脱男性的魔爪,女同学们深陷男性的浪漫陷阱却欲罢不能。《阳光》主人公想尽千方百计试图抓住一个男人……正是女性对男性的重度依赖,使“缺席”的男性一样能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地左右女性的命运。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构形成了明显的情景反讽,即男性的“缺席式在场”。女性甚至不知道何为理想男性,只是不断盲目重复“依附”这个机械化动作,使得“缺席”的男人同样能将女性的命运戏弄于无形之中,女性解放因此成为一轮无法触及的“水中月”。可以看到,老舍在给予男性严厉的批判时,也对女性刻入骨髓的依赖心态进行了有力的反讽。
二、男性中心道德秩序的质疑视角
在《阳光》和《月牙儿》中,老舍通过各类男性“前后不一的言行、表象和实际行为不符”[3]45的情境反讽,结合言语反讽,以女性的视角对男性社会所谓的道德秩序进行攻讦。
《阳光》的主人公成长在一个封建威严的父权家族,她的父兄利用她的“纯洁”来给家族“争脸面”,伪造清白的家世,私下里却肆意糟蹋别人家的女儿,荒淫无度、胡作非为。老舍通过言语反讽,揭露了男性的伪道德:他“是个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的人……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他的婚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要给胡闹的青年们立个好榜样,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有道德”“新思想”,属于正话反说,他的“道德”是升官发财,他的“新思想”是不择手段,虚伪丑陋的嘴脸就藏在“道德”的面具下。面对这样的父兄和丈夫,老舍赋予了主人公反讽的眼光:“一个讲道德的人可以娶姨太太,嫖窑子;只要不自由恋爱与离婚就不违反道德。”“讲道德”与“娶姨太太”“嫖窑子”共存,“自由恋爱”“离婚”和“反道德”划等号,这种相反意义的词同时出现的悖论式的反讽[2]157,有力地抨击了道德秩序的混乱与虚伪。
《月牙儿》也通过反讽诸位男性前后不一的言行,暴露了男性中心道德秩序的丑陋的一面。“我”的新爸懂得让继女上学,从这点上看,新爸的确不是封建保守的旧式父亲形象。反讽的是,这个看似道德高尚、作风新派的“新爸”,不久后还是抛妻弃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新爸为什么会离开,文中没有交代,但从当初新爸愿意娶母亲这样一个寡妇就能推测出来,曾经的母亲“也是不难看的”,因此,母亲被抛弃的原因无非是男人的喜新厌旧。新爸前后行为的错位,形成一种情理的悖谬,制造出反讽结构,老舍借这一形象对始乱终弃的男性道德准则进行了批判。
除了这位打着“文明”幌子的新爸之外,嫖娼的男人中有不少同样是“有身份”“讲道德”的“文明人”。这些男性一边指责暗娼的行为,一边对“我”作“义务的宣传”。他们表面“卫道者”的形象与其本性的淫乱背道而驰,形成了反讽的利剑,剑锋直指男性的丑态。“义务的宣传”更是褒词贬用,嫖客们私下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自身的荒淫无度。道德准则是由他们制定,且为他们服务,因而“逛窑子”可以光明正大,纳捐的正式妓女也能名正言顺。所谓的“道德”,在男性的公然改变与肆意解释下,早已化为虚无。
老舍还设置了“感化院”这样一个社会话语环境的缩影,对男权社会道德秩序进行多重反讽。《月牙儿》中,暗娼们被抓进了代表着男性社会最高道德的“感化院”里。“感化院”为妓女“谋划”了两条出路:第一条路是教妓女做工,第二条路是嫁人。然而社会现存的秩序并没有为女性创造一定的经济条件,妓女“从良”后不能真正自食其力,女性“从良”别无他路,唯一办法只有嫁人。《阳光》中的“离婚”情节在当时的社会话语中只是无法实现的“闹剧”。因此,“感化院”本是拯救“失德”妇女肉体和精神的地方,却打着“道德”的旗号,迫使女子跳入另一个未知的地狱,还以此为“功绩”,这是对“挂羊头卖狗肉”的“感化院”的第一重反讽。另外,男人只须花两块钱的手续费和找一个妥实的铺保,就能来“感化院”领走女人,这是对“感化院”企图美化自身“功绩”的第二重反讽。“只须花两块钱的手续费”一句使用的是克制陈述的反讽手法,“故意把话说轻,但使听者知其重”[2]154,将妇女从良异化为简单廉价的商品,实际上,感化院和前来“救赎”女性的男人,从事着最无耻的买卖性交和最残忍的灵魂虐杀。显然,“感化院”的感化是无效的,乃至是起反作用的,女性终逃不过被男性消费的命运。披着道德袈裟的“感化院”与其“无良”行径之间的对立,具有可笑的反讽意味。因此,“女儿们”看透了这个貌似道德的男权社会: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誰坏谁就占便宜。主人公“我”宁愿进监狱、自甘堕落也不愿在感化寺接受“改造”,落入其他男人的魔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月牙儿》中的“我”,既是被反讽者,也是反讽者,对男权社会的道德秩序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在男性话语中“失德”的“我”对“感化”的不屑,恰好是对虚伪的旧社会道德和“卫道者”的第三重反讽。
三、启蒙话语的失效与颠覆
受到西方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出走——获得解放”成为有识之士大力推崇的价值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乐观地设想,对女性而言,只要接受新思想,追求个性解放,就可以摆脱传统和家庭的束缚[4]。而老舍却对当时宣扬的“个性解放”“新式教育”心存怀疑,在启蒙失效的现实语境里,他不得不拿起反讽的利器,击破文化价值观念的虚假幻象,以此达到批判和质疑的目的。
《阳光》中的“我”是典型的“启蒙失败”的产物,有着豪门女性的“通病”: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傲慢无礼,举止行为与贤良淑德的传统大相径庭。同时,“我”自诩为启蒙教育下的“新”式女子,甚至还要出洋留学。“五四”的启蒙观体现在这位富家女身上,仅仅表现为对“旧”文化的弃如敝履,对爱情小说、电影及穿时髦衣服等新事物的盲目追捧。她向往自由的恋爱,却对需要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更不曾考虑走出家庭后如何自力更生。其缺乏内省的“个性主义”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追求,透露出其精致人偶外表下精神的空虚与荒芜。虽然在启蒙的大环境下,“我”也曾幻想过理想的男性和自由的恋爱,甚至不惜与奉行“旧道德”的家人对抗,但启蒙的光芒只是短暂地投射在“我”的身上,很快被骨子里的拜金主义所遮蔽。“新式”的“我”向旧道德妥协的结果便是堕入下层,在无爱的婚姻生活里点燃了“我”情欲的火苗,对情欲的渴望使得正当合理的人性的要求发展失控到非理性的地步。在老舍的理想信念里,这个骄傲地自述其“个性主义”与“爱情追求”的富家女,成为对立于作者立场的“不可信”的叙述者,二者的道德距离构成了反讽,意在批判女性启蒙教育的偏颇与不彻底[5]。
《月牙儿》中的“我”在经历了丧父、母亲改嫁、被新爸抛弃、母亲做暗娼、被青年诱骗等种种遭遇后,作为一个受启蒙话语烛照的现代知识女性,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我”不愿意成为母亲的复制品,于是不可避免地想要逃离底层女性既定的人生轨迹,寻找自我的位置和价值。当“我”沉溺在男青年的温柔乡中醉生梦死之时,“小磁人”的遭遇点醒了我,使“我”清醒地看到在周围环绕着的那群男性的自私滑稽的嘴脸,也意识到了身边众多女性身上难以根除的依附心理。无论是做女招待、暗娼,抑或是在“感化院”,女性永远处于进退两难的生存境地,这使“我”产生了对男权中心世界无所适从的陌生与疏离感,并逐渐对于这个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产生了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所以,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惊醒后,走投无路的“我”终于明白,“我”的挣扎与母亲从一开始就先验般的顺从不过是殊途同归。而“我”为了避免成为像母亲一样的暗娼而采取的对母亲的逃离,被证明恰恰是将我推向母亲的手段[3]98。从“众人皆醉我独醒”到理解母亲、成为暗娼,这其中的前后反转与最终妥协所造成的无力感,正是对失效了的启蒙话语的反讽表达。
“我”的复仇则是更进一步地公然挣脱和颠覆了启蒙话语。带着被启蒙者的幻灭感,“我”如一颗恶瘤对这个黑暗的社会进行报复,向整个男性中心的文明社会发起攻击与破坏。既然“启蒙”不能为底层女性带来独立与解放,“我”被关进感化院之后,便拒绝一切从良的可能,对所谓的感化不屑一顾,甘愿沉沦。“启蒙”的真正内涵亟待明确,灵魂却在“反启蒙”的思想下趋于腐烂,“我”放弃希望,因为“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沒有起色”。老舍从女性视角表达了对启蒙话语的悲观态度,反讽的语气更蕴含着老舍对知识分子和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担忧。
“学校里教的本事与道德”曾作为启蒙神话影响着“女儿们”的行动,然而无论怎样努力挣扎,底层女性都无法摆脱生活的贫困,富家女在社会中同样不具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只能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男性身上重演着“家庭天使”的命运。“女儿”们实际越来越悲惨的境地,与其想要“吃饭”、向往“自由”的愿望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落差和反讽,现代社会并没有为妇女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即解决“吃饭”问题。经济权利的丧失成为导致女性悲剧的真正原因,“对于男权的过分渴望和父系家族的期盼甚至重置了启蒙的意义”[6]。
总而言之,老舍《月牙儿》和《阳光》在反讽的视阈下互为补充与参照,透过女性的命运悲剧看到了“娜拉出走”的困境。老舍批判妇女自身的痼疾以及在主体意识匮乏之下的女性解放的徒劳。在控诉虚伪透顶的社会道德秩序时,暗示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的重要性。在对社会的实际改良落后于日益更新的思想的现实境况中,提醒转型时期的启蒙者们,女性的解放需要一定社会经济环境的支撑, 唯有如此,“娜拉”们在启蒙话语指导下诉求的主体意识、恋爱自由、个性解放才不会是纸上谈兵。
参考文献:
[1]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5):106-111.
[2]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3]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4]蔡洞峰.“娜拉”的彷徨与女性启蒙叙事——以鲁迅女性解放思想为视角[J].东岳论丛,2018(7):85-93.
[5]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167.
[6]刘馨丹.市民世界的另类现代性——试论《月牙儿》中的自反性叙事[J].中华文化论坛,2017(2):160-166.
作者简介:唐超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