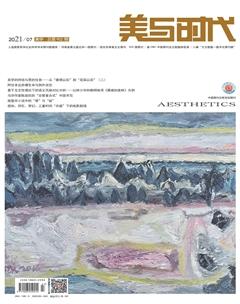论图像时代下舞蹈与话语的狂欢
李磊 楚金波
摘 要:《舞蹈风暴》(下文简称《舞蹈》)作为一档现象级网综,内含了丰富的语图关系网。《舞蹈》与文学话语的异性相吸作用既凸显了二者在形式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又在各自艺术魅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容与情感互补的双效收益。此外,《舞蹈》也是图像时代下融合了文学、音乐、绘画和现代科技元素的产物,其艺术呈现中也包含了不同社会权力话语体系,而每一体系背后都有特定的情感诉求。因此,有必要对《舞蹈》中潜藏的图文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
关键词:舞蹈风暴;图像时代;圖文关系;语图关系;对话;狂欢
科技不仅影响了人的生活,也极大地改变了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当代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是电子媒介的广泛应用,随之而来是“图像时代”的来临及图像学研究的兴起。在图像学研究领域,图文关系是重要分支,主要包括图文互文、图文互斥以及图文缝隙等研究模式。但学者们大多集中在经典文本、影像领域的图文或语图研究,而忽视了《舞蹈》这类网综所蕴藏的图文研究价值。W·J·T·米歇尔曾说:“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所控制的文化中……”[1]“形象”与当代人的生活紧密相连,而图像以其直观性赢得人们的青睐,并与文字、语词一同构成人们认识世界、表达情感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图像、文字及语词本身有媒介特性,它们彼此或正向或反向地有一定缝隙的合作关系,而这合作的背后则蕴含着时代的价值观念,最终构成人类特定时期的精神文化。《舞蹈》中的舞者将其所要表达的话语内容转化为肢体动作,为人们呈现出丰富的视觉图景的同时,也将特定情感传递给观者,进而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一、《舞蹈》与文学话语的异性相吸
《舞蹈》是舞者进行限时创演的全舞种竞技类网综,与时下流行的网综不同,它的创作者(包括舞者和节目制作者,下文同)对灯光(场景氛围)、镜头和“360°时空凝结”技术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与作家在环境书写、情节描绘及零聚焦叙事手法的使用方面具有同构性,因此,舞蹈与文学话语在人物塑造及情感表达上呈现出异性相吸的特质。
(一)《舞蹈》的场景与文学话语中的环境相对应。在《舞蹈》中,创作者以不同颜色的灯光营造了不同的场景氛围。正如阿恩海姆对色彩的研究,“色彩的一般表现力及其特定的温度不仅是由色彩本身决定,还要受到亮度和饱和度的影响”[2]。《舞蹈》的创作者很好地运用了灯光色彩,在《看见什么吃什么》中,舞者向观众展示的是处于热恋期的恋人形象,而舞台的灯光以明亮的暖色调——粉色为主,并配以舞者热情而欢快的舞蹈,这就与人物所处的浪漫和甜蜜的场景氛围相吻合。同样,文学话语也在以色彩进行人物塑造及情绪表达。在巴金的《家》中,有一段描述鸣凤投湖前的景象,“她的前面却横着一片黑暗,那一片、一片接连着一直到无穷的黑暗,在那里是没有明天的”[3]218。这里的“黑暗”显然有多重含义:一是指鸣凤所处的自然环境黑暗;二是女性所处的社会坏境黑暗;三是黑色有助于将人物的绝望、悲凉之情烘托出来。可见,舞蹈和文学话语在场景和环境氛围的设置上有相似性。场景和环境的设置不仅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也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从而使观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物的情绪状态。
(二)《舞蹈》的镜头语汇与话语文本的情节发展相对应。在《舞蹈》中,创作者通过切换镜头,将故事情节紧凑灵活地展现出来。在《繁华声》中,舞者塑造了一位处于人生低谷的年轻人形象。舞蹈之初,镜头下的舞者,双手抱膝,额头朝着膝盖的方向微低,坐在灯光昏暗的舞台中央,给人以孤独之感。舞蹈的中段,镜头聚焦在舞者的一个转身动作和随之而来的开门声上,这是舞者的情绪由低沉走向高昂的转折点。舞蹈的后期,镜头中的舞者与一股无形的力量展开了对抗式的“拉锯战”,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以及灯光变亮,舞者以一记右勾拳击碎了钳制他的力量,冲破了消极情绪的牢笼,迎来了新生。可见,镜头语汇是舞蹈叙事和情节推进的重要媒介,反观文学则以话语文本为媒介进行叙事。在巴金的《家》中,鸣凤投湖前有这样的景象,“她一路上摸索着,费了很大的力,才走到她的目的地——湖畔。湖水在黑暗中发光,水面上时时有鱼的唼喋声。她茫然地立在那里,回想着许许多多的往事”[3]218。其中“摸索”一词表现出了鸣凤对前路未知的小心姿态,“费了好大的力,才走到目的地”一句,表现出了路程的艰辛,也寓意着鸣凤人生路途的不易,而“茫然”一词则将鸣凤的绝望和无助展示的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镜头语汇和文学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性,创作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中进行叙事和情感表达。
(三)《舞蹈》的“360°时空凝结”技术与话语文本的零聚焦叙事手法有相似的作用。“360°时空凝结”是在定格画面的基础上以画面中的人或物为中心全方位展示人或物姿态的录影技术。在《不易》中,舞者通过借助外部物体,完成了由消极情绪向积极情绪的转变,而情绪转变的时刻是整个舞蹈的最高潮部分,需靠“360°时空凝结”技术来完美实现的。在舞蹈的结尾,舞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发光的小物件并将其放进了装满此类物件的盒子里。随着舞台灯光变暗,年轻人将这盒小物件笔直抛向空中,犹如一个个飘渺的梦想,可望而不可即,紧接着,在舞蹈画面定格结束后,随着这些小物件降落至舞台,寓意着梦想落地,一改之前无根之状而成有本之木,有了厚实、良好的成长环境。在文学创作方面,不论是莫言的《蛙》、鲁迅的《阿Q正传》,还是托尔斯泰的《巴黎圣母院》、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都通过零聚焦叙事手法将特定情境下的人物情感展示了出来,使得人物心理与外部环境相契合,达到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效果。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于某一时刻引起读者的共鸣。《舞蹈》中“360°时空凝结”技术和文学话语中零聚焦叙事手法的使用在故事情节、人物情感以及读者接受方面都起到同样的作用,显示出二者的相似性。
尽管《舞蹈》和文学话语在艺术呈现手法和形态上有所区别,但二者在最终的艺术呈现效果上具有相向性,即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这也说明了图像与文学话语的共通性。
二、文学话语与《舞蹈》的双效收益
在视图时代,《舞蹈》与文学话语不仅停留在创作形式的相似上,二者在题材和主题方面的相互借鉴也加强了彼此的联系。
(一)文学文本为《舞蹈》提供题材和主题的同时,《舞蹈》也丰富了其母题设置。在《花木兰》中,创作者在《木兰诗》故事原型的基础上,融入了新时代女性的情感诉求。舞者通过表现木兰自信、果敢和勇担大任的一面,展现了当代女性不服输和勇担当的精神品质。木兰的故事流传至今,“自然离不开木兰叙事母题(即情节单元)在时代变迁中所作出的改变,尤其是其在题材和体裁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4]。题材和体裁的转变与其主题内容密不可分。在故事主题上,近代之前的木兰形象偏向于政治教化功用,显示了其一定的局限性;而近代以来则更强调其形象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即已由政治教化向个体价值取向和社会话语上转变。同样,在《舞蹈》中,不仅仅是《木兰诗》中的花木兰,还有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九儿以及《哪吒闹海》中哪吒都被创作者重新演绎。创作者在经典形象的重塑上既做到了尊重传统,又做到了将舞蹈的魅力与经典形象中独有的精神品质、当代人的情感及价值诉求紧密结合。在艺术形式上,木兰的形象已在音乐、绘画和影视等艺术领域大放异彩,这也丰富了其文本母题的表现形式。此外,近年来大热的《朗读者》《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节目,以朗诵、咏唱、情境再现等形式将经典文本片段呈现,将蕴藏在话语中的精神文化以直观形象传递,实现了文学话语与图像的双效收益。
(二)文本故事为《舞蹈》提供素材,《舞蹈》也对文本故事中的空白进行了填补和延展。二者在“意象”的相互触发中还原了特定情境中的人物及情感。在《儿时》中,舞者仅以一个掌心朝内、五指向外轻轻一挥的动作就再现了母亲送别游子的情境,而这一动作变成了回忆的“触发物”,成为众多游子思念亲人与怀乡的意象。贾平凹的《纺车声声》将“纺车”作为忆起母亲的“触发物”。作者一开篇就写到:“如今,我一听见‘嗡儿,嗡儿的声音,脑子里便显出一弯残月来……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车……”[5]“送行手势”和“纺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母亲形象的情感载体,而这载体与国内外学者所述的“意象”大体一致。关于意象,“从时间上看,中西方意象理论都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其中,中国的意象论从先秦延续至今;而西方的意象论从古希腊延续到后现代;从‘意象本质上看,中西方的理论都认识到意象是‘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两大因素的完满结合物”[6]。只不过舞蹈将其“意”诉诸于肢体动作,而文学话语则借助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舞蹈偏向于直观的“象”,文学话语偏重于抽象的“象”,但当二者在素材上出现交集,是能够出现相互成就的效果的,即舞蹈将形象直观化,更容易被观众体验到。最终,人的情感状态在某个情境中被凸显出来。正如伊泽尔所说:“情境以及所有伴随着它的细节就是这样呈现出一种确定的形式,这种确定形式同样制约随之而来的表述,这些表述只有和那个情境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读者(观者)适当的理解。”[7]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舞蹈、绘画等偏重于空间表现的艺术,还是小说、散文等侧重了时间表达的文学体裁,都离不开“意象”所带来的情境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将创作者、人物形象和欣赏者联系在了一起,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所以,《舞蹈》与文学话语在“意象”选取、情境构造和情感表达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之下加强了彼此的联系,这也说明图像与文学话语有共通性。
舞蹈与文学话语的双效收益是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的:文学话语为舞蹈提供了叙事母题框架,舞蹈则为抽象的母题提供了直观的视觉感受,从而实现舞蹈与话语的跨媒介沟通,这也表现了图像与文学话语的相关性。
三、社会话语与《舞蹈》的联袂狂欢
“狂欢”原指人们庆祝酒神的活动,主要指人们狂欢式地感受世界的状态,后来被巴赫金运用到诗学研究领域。巴赫金认为理想的世界是一个非等级的、倡导自由与平等的世界。巴赫金在分析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亦探讨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基于其“对话理论”展开的,即“‘他人与‘我都具有自我的平等性。构成对话关系的必要条件,是各种声音之间的相互交织和论争,而对话的基本特征则是不同观念之间的相互理解”[8]。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对话理论从诗学领域延展到社会领域,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对图像时代的舞蹈与社会话语的认知有指导作用。
《舞蹈》将文学和舞蹈放置在图像的空间中,并处处彰显着人与“器”的关系。人与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人与科技、人与艺术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首先是人与科技的关系。机械技术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着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还改变着文艺生产、创作、传播以及接受的方式。其次,艺术是实现人与人思想、情感交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各种艺术之间在保持自身独特性之时,应相互借鉴和融合,以寻求创新和突破,而同一艺术内部的不断分化也有助于激发其生命力和活力。最后,艺术仍要回归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纵观整季《舞蹈》,舞者们主要塑造了追梦者、恋人、女性、家人、孩子等形象,并通过不同情境和场所展示人物的生存状态,以此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正如龙迪勇所说:“场所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它也收集事件、经历、历史甚至语言和思维……”[9]舞者们正是在特定“场所”中理清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诠释人与人的关系。
《舞蹈》不仅仅诠释了人与器的关系,它对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具有重要作用。舞者们主要呈现了三类人物状态,一是以自我为中心,并总是呈现出“我以为”和“我觉得”的人物状态;二是自我认同感缺失的人物状态;三是相对平衡的人物状态。过度状态中的人,他们试图将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标准绝对化和唯一化,这势必导致他们对外界的判断标准具有更多的主观成分,从而形成“话语霸权”。于缺乏状态的群体而言,强势话语对其有极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流行”就是最有力的说辞,而流行则以点击率、收视率和利润率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伴随事物被商品化,审美的趋同导致艺术灵韵的丧失,进而导致美的消失。于平衡状态中的人,注重对话,相互理解是其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态度和准则。舞者们从个体出发,尝试用舞蹈的力量引起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实现不同国度、文化、阶级、年龄和性别的相互理解。
参考文献:
[1]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2]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65.
[3]巴金.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
[4]胡玲.性别视角下木兰形象及其叙事的流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5]贾平凹.自在独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1.
[6]江英.中西意象理论比较初论[D].南昌:南昌大学,2010.
[7]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霍桂恒,李宝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84.
[8]吕君芳.创造普遍和谐的理想世界——关于巴赫金时空观、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的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252-255.
[9]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88.
作者简介:李磊,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批评、图文研究。
通讯作者:楚金波,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