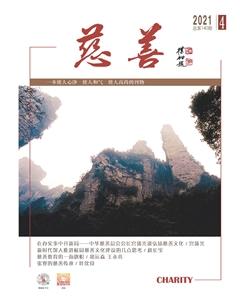我的船籍港
光阴荏苒,悠然就是一辈子。而今老了,回忆大半辈子与文学的交往,那不禁的兴奋又跃然笔头,自然又是对当年《新港》将我引进文坛的回忆。
回想起来,我对《新港》的认知亦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但与《新港》接触却已是走南闯北的考察队员了。一次,我到西藏考察并参加了平息西藏叛乱的战斗。
在冰天雪地的无人区,我开始了文学的创作。先是写了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寄给《中国青年》还收到返回的小样。然后,又写了个叫《101次》的独幕剧,还参加了北京朝阳区的职工会演。再后来,就雄心勃勃地写一部叫《屋脊阳光》的长篇小说并计划作《新港》的敲门砖。却只写了几章,就知难而退了。虽时隔半世纪,那未成之稿仍被我珍藏着。
但尽管如此,我与《新港》的缘分仍未曾断绝过。尤其到1960年因响应干部下放的号召回天津上船成了一名漂洋过海的“海狼”,并准备写一部以我那海狼世家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大破船的船籍港》,与《新港》的关系就更近了。
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却记得船刚回港,靠上码头就往编辑部跑。可是,又因不知具体的地址,在黄家花园一带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那深藏在新华路一座花园洋房的《新港》杂志社。更可笑的是,与两位编辑谈了一下午,走后才想起还不知对方的尊姓与大名。但尽管如此,那热情的鼓励与点拨却是永远难忘的。如,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在中国除上海的陆俊超还没有谁能写大海。如果我能完成此长篇,则肯定会引人注目的。但由于我还处于初学写作的阶段,开始最好别写长篇。写什么呢?短篇,特写,不仅成稿快,刊物也欢迎。另外,他们还给我开了一个20部世界名著的读书目录并让我填了一张表,说这就像船在其船籍港的注册。从此,我也是在《新港》挂了号的作者了。
回去的路上,我先去图书馆借了一堆书。然后就动手开始写短篇,而且每有所成就往《新港》跑。虽无一被采用,却得到更多编辑、作家的关注。这当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新港》的主编万力和作协的副秘书长周骥良。另外,通过《新港》编辑部还结识了《天津日报》的编辑。于是,随着我的第一篇小说《手上的茧子》终于在1963年9月的《新港》和读者见面,《在风浪中前进》《高高的冰桥》《扎网场上》《两个新船员》《打地基》等亦相继在《天津日报》《河北日报》得以刊登。
就这样,我的创作追求亦水涨船高。到1965年创作出《油驳风浪》时竟舍《新港》而投向了《人民文学》。但坦率地说,亦懊悔自己的冒失。却未想到,不仅未被退稿还收到一封中国作家协会调我去北京参加青年作家读书会的公函。等到了北京,才得知此读书会亦前文学讲习所的变身。我之所以能有幸被选中,也是《人民文学》想利用这一机会帮我提高创作水平并修改《油驳风浪》。
于是,就有了发表于1965年7月号《人民文学》头条并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小说《聚鲸洋》。对此,《新港》编辑的朋友们也为我欢呼与庆贺。却未料到,我的厄运也开始了。
若没记错,一天的上午我正陪天津广播电台《聚鲸洋》广播剧的导演在码头录音。公司党委宣传科的科长突然叫我去《新港》接任务。到编辑部,有人又将我领到同一个楼的作协办公室。并由一位负责人通知说中国作协和团中央将联合召开第二届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经市委批准我不仅将作为正式的代表,还在会上介绍自己的业绩。发言的时间为30分钟。讲稿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因为还要报送市委宣传部去审查。开始,我还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早在由周扬亲自主持的筹备会召开时,我就以列席的身份旁听并得知周扬的讲话还提到我。但我的讲稿还没完成,就风云突变了。
那是又一天的上午,《新港》编辑部的人突然来电话:“你最近怎么样?”似乎也不须回答电话就撂了。跟着,公司的党委书记就找我谈话:“北京那个会,如果让你去,你怎么想?如果不让你去,你又怎么想?”开始,我还真给问蒙了。清醒过来,才悟透那后边的潜台词。于是,就边走边说:“我根本也没想去!”
似乎,这一莫名其妙糊涂的事情也就过去了,却又不然。谁能料到,转天宣传科长又找我谈话。说北京的会可不去,但天津也有个这样的会就必须去。而且,还不是代表的身份,你又如何想?
牛不喝水强按头。最后,也只能在宣传科长的“陪同”下老老实实去第一工人文化宫,坐在最后一排列席天津市的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想,这恐怕是我文学生涯中最晦暗也最凶险的一段了。而我之所以如此说,则因受此事的影响,与我交往多年的女朋友也离我而去了。不久,又莫名其妙的偏头疼。想下船治病,不仅未获准,还被那个海军转业的船队政治指导员说是闹情绪。于是编辑部又来电话,说作协的代秘书长王曼恬要找我谈话。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到作协时,见王曼恬正在楼下领着几个工作人员洗沙发套。还没容我开口,她就冲我嚷:“写了个《聚鲸洋》就翘尾巴啦?还目无组织,装病离船搞对象。没出息、不争气。再有,为什么就不能争取入党啊。你呀你!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什么能没你的?”说到入党,我也不能不作申辩。我说,鉴于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复杂的港台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事。结果又惹她更大的不高兴。
等她走了,从编辑部朋友的口中才得知因为我她已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如,当时天津所属的河北省委的一位领导得知我所在单位党委不同意我当代表时就不高兴地说:“捕捞公司怎么搞的?这个王家斌也太不像话了。”又如,王曼恬去北京汇报时,周扬也指示:“不许王家斌离开船离开海,更不能让他烂掉了。”
还有,就是同行间对我种种的谣传。如,有人说我犯了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将给我以处分;有位所谓的工人作家甚至在一次聚会时说《聚鲸洋》是我用对虾换来的。当然,我能做的,也只能是以无奈的沉默来应对。但虽然如此,那更大的厄运随着党委书记的再次召见终于降临了。
那天,书记的神态亦格外严峻。我进屋时,他坐在写字台后边头也沒抬。默然相对了足有三分钟,他才开口说:出于对我的爱护,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经公司党委研究,决定让我立即到山东省的石岛港去上船。因为那船是为我而从渔场调回来的,所以要立马就动身。见我无语,就找出本毛选让我看某卷某篇某段。即:下级要服从上级,全党要服从中央。我就更闷口了。而且,动身时才知“陪”我去石岛的还有位海军政治部转业来的教导员。
行前,我分别给《新港》《人民文学》编辑部和全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写信申诉了我的情况,希望能帮我摆脱目前的困境。却未想到,此次的石岛行走竟差点走上九死一生的不归路。
我记得,船离石岛港时大海本是光滑如镜的。但眨眼间,整个渤海湾就开了锅。然后,又沧海倒竖,那排山倒海的巨浪把铸钢的锚链绠缆网具乃至舱盖皆一扫而光。最可怕的是一些渔民的机帆船,只见沉没,不见其再漂浮上来。到天黑时,我们也堕入深不可测的大漩涡,那虽是钢筋铁骨的船壳亦随时会解体。而全船的人,除船长乃死守在舵楼里,余者皆藏身于小餐厅。而此刻的船舱,又因发电机的中断,则变成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全船的人,除了绝望地喊叫,谁也拿不出脫离险境的好办法。而我,虽然此一经历亦成为后来长篇《百年海狼》中“沧海万世劫”难得的素材,但当时也只能暗暗诅咒那使我遭此厄运的周扬。就这样,排山倒海的惊涛骇浪终于过去了。天亮时,竟然以看到险些被风暴潮摧毀的大沽灯船。而且,直到老炊事员问船长想吃点什么,那晃晃悠悠的老海狼说:“我我,我想杀个人吃吃!”时,才知是他一天一夜把自己捆在舵轮上,才使我们冲出绝境的。
船终于进港了。靠码头时,见一熟悉的人影向我走来。到跟前,才发现是《人民文学》的崔道怡。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呵!老崔,想不到还能见到你。”
下地后才得知,老崔是为处理我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和刘白羽写信的事而专程来津的。但直到我们见面的第三天,才从华北局发布的公告得知我所经历的竟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海啸。
为此,老崔当即就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约我写一部战海啸的小说。跟着,《新港》和《天津日报》也纷纷约稿,但心有余悸,拿起笔,那可怕的巨浪又迎面扑来。结果,除了发在《天津日报》那篇《身置海啸无惧色》的小特写外,不仅一篇小说也未成,还病了将近一个月。而说到病,开始还以为仍是“偏头痛”。后发展成见了船和海就想吐,才知是心灵的创伤。再后来,甚至对文学也产生了厌恶的心理。到“文革”被抄家、批判,甚至把一支极珍贵的金帽派克笔也掰断了。据说,此一情节,后来还被崔道怡笔会讲课时引以为笑谈。
虽然如此,我与文学的情缘亦不可能被了断。而之所以如此,皆因文学从未放弃我。即便最严酷的“文革”中《人民文学》仍派人来看我或邀我参加学习班并发表《环节》等小说。《新港》关系就更近了。我不仅经常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还曾在改名的《天津文艺》上发表过《船检站长》和《活海图》两个短篇小说。
另外,因为我家与万力家仅一街之隔,经常见面,他对我的安抚与鼓励也是感人至深的。所以,到“文革”结束,得知我又想重写《大破船的船籍港》并在主持全国作协工作的诗人李季支持下,向交通部联系随远洋船去国外和更远的大海拓展视野时,他不仅大加鼓励,还为解决我出国政审和所需的外汇,曾以《新港》编辑部的名义给市委宣传部写报告,对我的出行计划则尤为关注,如开始我还想走外派的路子,他怕不安全给否定了。
交通部同意我办国际海员证,并批准我随中国远洋船出海体验生活的文件,终于由中国作家协会转来了。去天津远洋运输公司报到时,万力还给塘沽文联去电话,让他们安排车送我去码头。然后,我就以小服务员的身份随船去了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国家。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对如我这个所谓的海洋文学作家,就更如鱼得水了。
将近一年的航程,我不仅饱览了现代的异国风土与人情,还终于体验到深海大洋的神韵。尤其在太平洋和南中国海,更感觉到我其实还只是半个海洋文学的作家。如我的《聚鲸洋》,充其量亦只是大海边缘的一个湾。那曾使我心惊胆颤的大海啸,也无法与南中国海的风暴相比较。而且,若由此引申,甚至觉得我最崇敬的海明威和《老人与海》也是名实不符的。至于那些从未出过海,只能在海滩礁石缝扎猛子就自封为海洋文学作家的,就更不屑一顾了。
当然,要想写出一部真正的海洋文学,仅靠一次蜻蜓点水的远航是决然不够的。更何况,随着更深入的体验与探索,我发现对文学创作来说,那博大精深的海洋知识就更必不可缺。为此,便想起行前李季曾与我的一次谈话。他说:“现在我们作家的知识面太窄了。一个作家,还不如读者知道得多,谁还读你的书。比如你,首先该是个海的专家。”虽然,此言亦有其偏颇。但从日本归来我提前终结远航回家去研读与海有关的书,这也是深思熟虑的。
好景不长,就在做足前期准备要开始《大破船》的创作时后院又着火了。而所谓的后院,即我的原单位。事由是,因我常年在外早已不适合原来的工作。另外该单位又要搬迁,就更没条件搞创作了。为此,我也只能往天津作家协会调。但作协虽同意调入,却因专业作家的编制有限,被市委宣部的部长办公会否决了。最后,经万力亲自出马去力争,这才准我先调入,等《大破船的船籍港》完成时再解决专业作家的编制。
其间,万力同志有意让我到《新港》,一边当编辑,一边搞创作,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拒绝了他这一好意,错过了到编辑部工作的机会。
虽然,万力离我而去了,但他苦心营构的《新港》和他培养的如我这代作家仍在。
而且,虽然后来《新港》又几易其名,但《新港》的神韵却始终如影随形,且经久不散。尤其是,每当有新作品问世时,我又总会想到当年的老《新港》。至于外出笔会,每见人谈曾给《新港》投稿时,那内心中的自豪就更难形容了。再就是每有进取也会想到《新港》的老朋友。尤其当《大破船的船籍港》终于以《百年海狼》的新命题问世并在国内外引起反响时,万力的影子又必然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