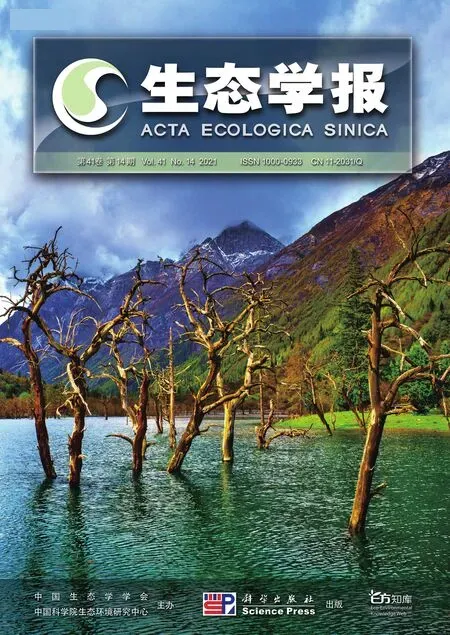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及驱动机制
金校名,李 博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大连 116029 2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大连 116029 3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6
海洋渔业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其较大的产业生产总值比重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依托。近年来,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2001年的17.95攀升至 2015年的21.51呈现波动性趋高走势[1],海洋渔业对海洋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来自渔民、鱼群内外部生存坏境及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水平对海洋经济作用程度。其演化往往是非线性的、无确定的,厘清其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是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谋求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需把握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各个演化阶段,寻找该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规律。所谓适应性循环是反映复合系统在遭受外界干扰后进行自组织学习并构建恢复力能力的演化模式[2- 4]。目前,国内外对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研究已较为成熟,主要用来探求在复合系统下时序上各研究领域的演变规律。国内适应性循环理论研究在基于社会—生态系统下,将旅游地发展演进和地域间生态系统评估作为主要研究层面。王群,陆林[5]等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利用适应性循环理论来判定千岛湖旅游地发展过程并揭示引发该旅游地循环运转的内外部驱动力;陈娅玲[6]将山西秦岭地区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适应性循环理论相结合提出该地可持续发展对策;王俊[7]在基于黄土高原地区农业社会—生态系统关键变量下分析导致该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演进机制;刘焱序[8]等以深圳市区为例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将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指数扩展为“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准则,为权衡空间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国外研究主要将适应性循环理论应用到把握系统动力模型的规律和对系统关键变量识别中。Wiese F K[9]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视角从时空方面阐明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变化规律。 Rogers J D[10]将适应性循环系统运用到人类社会系统研究中,揭示了社会变革中连续性和机会的重要性。Joanne[11]利用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圈来表征圣罗莎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旅游特征。Gronenborn D[12]通过适应性循环概念来解释导致欧洲人口规模大幅波动原因;Allcock S L[13]采用适应性循环框架来探讨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土耳其卡帕多西亚的社会文化变迁影响。适应性循环理论以其非线性逻辑构建,通过动态把握各研究对象发展走向的节点事件以捕捉适应性循环的驱动因素,进而明晰在复杂条件下所研对象的内部发展规律。
本文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以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把握系统关键要素,明晰该系统下海洋渔业发展脉络,揭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为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概况
国际性学术组织“恢复力联盟”为理解耦合系统下各单位子系统相互关系的动态演化规律而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14]。适应性循环是基于生态系统演替的传统观点之上,增加了更新和释放两个时间阶段,使适应性循环构成动态三维框架。Holling在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以时间为序列提出系统每构成一个周期的适应性循环需经历开发(γ)、保护(κ)、释放(Ω)、和重组(α)4个阶段,且每个周期循环的转换取决于3个维度,即潜力、连通度、恢复力[14- 17],而这3个维度也分别对应了地理学时空分析中所强调的“静态格局—空间交互—动态趋势”的组合模式[8]。目前,在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呈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与当地产业经济系统的发展过程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为整体把握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动态演化模式,将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框架延伸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中。在时间序列上,系统一方面来自于内部因子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压力的扰动,导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轨迹的周期也相应发生变化,同时系统内部动态及外部压力成为促成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周期转变的主要动力。由此,将该系统下的适应性循环圈(图1)划分为两个循环阶段:由γ指向κ和由Ω指向α,即系统适应性演变轨迹是在资源不断积累和转变的长周期与创新重组的短周期间运行,且不能同时发生只能按照纵向时序进行。

图1 适应性循环嵌套模型[17]Fig.1 Aadaptitive cycle modleγ 表示开发阶段、κ 表示保护阶段、Ω表示释放阶段、α表示重组阶段
循环阶段Ⅰ(γ→κ):在开发初期阶段,系统以生长积累为主,发展较为迟缓,恢复力作用不明显,同时受内外部扰动因素影响较小,脆弱性较低。当资源积累、技术手段、经济发展到达到一定高度,系统不断扩张,到了开发阶段末期,系统敏感不稳定状态逐渐暴露使得脆弱性、恢复力随之抬升。在保护阶段,受开发阶段大量积累作用影响,系统内各组成要素均达到了稳定且迅速的发展,表现在系统当面对扰动而显现的恢复力持续攀升,连通度逐渐发达,潜力不断提升。然而系统在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复杂性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脆弱性却持续走高,对应的恢复力上升到最高点后不能与逐渐趋高的脆弱性达到动态平衡后开始下滑,由此逐渐向释放阶段过渡。对于海洋渔业而言,初期往往是沿海地区渔民为满足生计需求进行海洋渔业资源开发而表现出的过度关注海洋渔业产量而导致的海洋渔业资源大量流失、环境恶化、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调等问题。同时,随着开发速度加快,一些隐形的负向因素逐渐暴露,为促进产业继续发展,由此转向保护阶段以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
循环阶段Ⅱ(Ω→α):在释放阶段,系统开始僵化,潜力迅速下降,恢复力回落,在遇到扰动因素无法迅速做出判断排除干扰,但受前一阶段该系统与各要素紧密联系的惯性作用,其连通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该阶段的海洋渔业发展状态一般表现为资源积累、产业推进面临瓶颈,在遇风暴潮、赤潮等自然灾害侵袭后,微薄的海洋渔业资源储存量以及极具脆弱的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状况在无法抵抗外界因素迅猛冲击会突然释放,速度较快。原本紧密而有机的系统开始崩溃,恢复力直线下降直至最低,由此进入第四环节,更新阶段。在此阶段,系统内部表现出较高的潜力,不断寻求创新及新的发展动力从而提高恢复力效能,并根据自身现有条件进行调整、重构、再适应。与此同时,系统会避免复制前阶段恶性因素,从而降低系统脆弱性。对于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而言,近岸海域污染,海洋灾害的扰动及不当的海捕行为等将导致海洋渔业资源质量低且数量少,阻碍海洋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只有将现存问题完全暴露并进行不断调整、更新,才有可能进入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新阶段或为新阶段的产生奠定基础[18- 19]。
根据适应性循环三个属性变化的标准值组合,表明系统并非依次按照开发、保护、释放、更新4个阶段发展,也存在病态状态:贫穷陷阱,僵化陷阱,锁定陷阱,未知陷阱。以贫穷陷阱为例,在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过程中,若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于海洋生物资源而导致超负荷海洋捕捞,从而引发海洋生物资源承载力急剧下降,同时又无法改变现有发展模式,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将无法还原,成为一个不可持续的枯竭系统,最终因陷入贫穷困境而使整个系统分裂,表现为低潜能、低连通度、低恢复力。而僵化陷阱,锁定陷阱,未知陷阱则分别呈现为高潜能、高连通度、高恢复力;低潜能、高连通度、高恢复力及高潜能、低连通度、低恢复力的病态组合结构。
2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分别从环境态势变化、经济发展高低走向及社会生产制度变革三大方面,参考以往专家学者研究成果[20- 22],依据适应性循环理论并结合重大转折事件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划分为三个适应性循环圈及若干个循环阶段(图2、图3)。

图2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圈 Fig.2 Adaptive cycle of marine fishery industry ecosystem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图3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历史时期和事件Fig.3 Historical periods and events of marine fishery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2.1 第一个适应性循环(1949—1965年):海洋捕捞业为主的恢复型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1937年至1949年,受抗战影响,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百废待兴。直至1949年,全国政协将“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海洋渔业发展逐渐从无到有。1949—1956年,为了大力恢复海洋渔业生产力来带动海洋渔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开始实施合作社运动,逐步完成由互助合作组到初级合作社最终向高级合作社的进阶。1956年底,已有占海洋渔业总体的72.53%的渔户参加了合作社运动,1957年底海洋渔业捕捞量达到近180万t,相比于1950年增长约2.4倍[23]。这种高强度,突增性海洋渔业捕捞使海洋生态环境无法迅速适应,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水产局由此制定了《水产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首次提出海洋资源保护实施方案:利用资源,保护资源,计划指挥生产,但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一直贯穿于该时期整个产业进程。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错误提出在1958年一年之内海洋捕捞量比1957年增加37%—50%,这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严重侵害了海洋近岸渔业生物资源,直致该时期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下降至最低点。同时受非科学化方针指导,违背海洋渔业生产作业规律,渔民打破休渔期、禁渔区,多采用机船拖网高耗能捕鱼方式,渔获物出现小型化、低龄化,迫使海洋渔业资源严重退减,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加之受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大批渔民受自然因素干扰失去海洋作业能力,遭受严重破坏的海洋渔业产业再次搁置,导致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崩溃进入释放阶段。1961年,中国沿海海域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总产量约为140万t。但此后,“养捕并重”方针的提出并未使脆弱的系统得到有效恢复进而进入释放阶段后的修复阶段。
总体来看,1965年之前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范围狭小,海洋渔业产业人才、资本等积累较弱且处于以海洋捕捞业为主的恢复型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以及缺乏海洋渔业科技等外向力刺激由此经历了由开发、保护、释放所形成的适应性循环前、中环阶段。
2.2 贫穷陷阱(1966—1976年):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危机期
1966—1976年,“文革”动乱期间,左倾错误思想误导海洋渔业产业政策,是触发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进入贫穷陷阱的关键节点。其间,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在近海海域出现大批围海造田运动,破坏近海海域滩涂资源,侵犯近岸水生生物栖息地,部分海洋生物资源濒临灭绝,极大破坏了海洋渔业生物多样性,使得原本未有恢复完全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再次受创。同时,为了扩大海洋渔业单产,大量引进网拖船,导致幼鱼、鱼苗被一网打尽,切断了海洋渔业资源再生。在产业分配上,否定“按劳分配”,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渔民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在海洋渔业科技层面,“三下乡”运动使大量从事水产科研团队、机构被迫叫停,致使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检测与防护工作受阻。这种混乱局面直至19世纪70年代初由于实施灯光围网渔业,城郊养渔业以及连家船的改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压力[24]。
2.3 第二个适应性循环(1977—1985年):海洋渔业养捕并重的过渡型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1977—1985年,在经历“文革”后,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海洋渔业产业重新谋划发展。在“政策放宽”,“市场经济”,“承包制户”等一系列丰惠方针的指导下极大调动了相关从业者对海洋渔业生产作业的积极性与信心[25],由此开启新一轮的海洋渔业适应性循环。
1978年全国海洋渔业捕捞业与养殖业之比为71∶29[26],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高密度海洋捕捞引发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再次受损。1979年海洋渔业捕捞量达307.79万t[27],捕捞强度与资源矛盾开始加大。为防止由于过度捕捞所致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失衡,1979年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以“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养殖,调整近海作业,开辟外海渔场,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市场供应”为工作方针进行深入贯彻,进而使适应性循环圈由开发向保护阶段过渡。
1980年,全年大功率机动渔船新增近7000艘,总功率高达2.72×105kW[27],使原本未得到有效缓和的海洋渔业再次受到海洋捕捞压力扰动,阻碍了海洋渔业产业调整进程。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沿海海域渔汛难以形成,导致中国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逐渐消失,由此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圈呈现出较大范围的释放。
1983年中国海洋渔业从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依据本时期中国海域现有资源环境状况,进行更新、重塑。通过调整拖、围、刺、钓作业结构比例,极力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开发中上层鱼类资源,着重提出“以养为主,养捕并举”的方针,且在养殖业中进一步提出发展“两高一优”政策举措,并以此作为今后中国海洋渔业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1988年全国海水养殖产量与捕捞产量之比为50.1∶49.9[27],产业结构趋于平衡,海洋渔业资源得以恢复调整,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向下一阶段转变奠定基础。
本阶段受政策因素导向,大力优化海洋渔业养捕比,使系统处于捕捞业与养殖业平衡发展阶段,经历了由开发、保护、释放、更新所构成的完整适应性循环。
2.4 第三个适应性循环(1986年至今)向现代化转型期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经过第二个适应性循环,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开始缓慢恢复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正向发展态势并逐步向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现代化方向迈进。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注入,海洋渔业产业多元化组合、产业发展政策定位及生态环境治理与预防等需长时间协调、博弈。同时,海洋渔业逐渐由以捕捞为主向养捕结合过渡,积极开拓远洋渔业,成为该系统适应性循环在海洋渔业产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化方向转变过程中的助推器,构成了以开发与开发保护交互促进阶段。
2.4.1初级开发阶段(1986—1990年)
自1985年起,中国第一支远洋渔船队在西非海域开展捕捞作业为中国远洋渔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打开了远洋渔业发展的新局面,弥补了中国海洋渔获物只靠近海海域为主作业的技术缺憾。1986年《渔业法》的正式颁布,从法律层面制约了因机动渔船大量增加,捕捞强度过大等而产生的系列问题。并对海洋渔业进行整体区域布局,将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根据各海域资源波动情况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相应调整。直至1990年,坚持“以养为主,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提出,转变了海洋渔业生产作业方式,同时中国远洋渔业五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点及面,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进入新一轮开发阶段。
2.4.2过渡开发阶段(1991—2000年)
为避免海洋渔业由以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和自给自足型的小规模单一海洋产业为主而进行的海洋渔业经济创收,经初级开发阶段的养捕并举及远洋渔业的探索实施,缓解了由此带来的海洋渔业产量、质量低下和海域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负增长”计划,进一步缩减海洋渔业捕捞量[28],侧面拉动了海洋养殖业并开拓了远洋渔业的发展。但在过渡开发阶段,初具改变的海洋渔业生产作业方式,使得海洋渔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运作机制产生对抗性,潜在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显现,病害滋生、缺乏培育经验是制约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因素。1994—1997年,政府集结一切力量提升科技推广力度,采用高技术设备集中化养殖,改善了以往放养模式,并进一步将水产技术推广体系进行规模化扩张,将“养护和合理利用近海资源”作为该时期海洋渔业发展重要内容。1998年,沿海地区加紧调整近海作业,以捕捞中上层鱼类资源作为主体,使资源利用更趋于合理[29]。
2.4.3开发与保护交互阶段(2001年至今)
此阶段,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将关注焦点由追求产量提升落到了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渔民利益维护上,即从产业环境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转变。中国渔业“十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保护,积极发展水产养殖和远洋渔业”成为该阶段系统的发展重点。2001年,全面展开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的渔船清理工作并取得阶段性进展。为进一步推行海洋渔业捕捞量由“零增长”向“负增长”的目标过渡从而相继实施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计划,鼓励渔民退出捕捞行业,切断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为海洋渔业向集约型现代化产业转变奠定基础。“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渔业增长方式,从提质角度,加强鱼苗新品种培育,继续压低海域捕捞强度,进而加快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使得养捕比例继续扩大,海洋渔业产业加工能力提升,海洋休闲渔业等快速扩张。其间,纳入“双控”管理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完成比率达到162.8%。随后,在“十二五”规划中,坚持生产发展与生态养护并重,积极探索“蓝色农业”发展理念,将海洋牧场建设和增值放流相结合恢复海底植被,深层次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并将渔民保障纳入系统向现代化进阶的范围,实现渔民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30]。进入“十三五”阶段,进一步拉长海洋渔业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条,拓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维度,进行优质化、高效能鱼类种质培育,剔除结构性过剩品种。形成有序、有度、有限的海洋渔业产业区域布局,深入夯实各海区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实现了海洋资源养护和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进阶式发展。
此阶段主要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开发和保护的前环阶段。
3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问题
中国海洋渔业受其产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双重影响,使该复合系统在分别解决各子系统内外部矛盾中寻求平衡从而完成一个适应性循环演化,并最终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若任意子系统在海洋渔业经济增长中出现崩溃,会迫使整个系统进入适应性死循环,形成海洋渔业不可持续增长或陷入海洋渔业发展危机。
3.1 海洋渔业产业子系统问题
自将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后,大批渔民开始从事海洋水产作业。1985年,从事海洋渔业人口数达161.31万人,年均收入2294元,超出同期农民年均收入的59.8%,一定程度上促成低收入农民跻身于临时性海洋捕捞行业,这种非规范化培训的从业人员的临时性加入阻碍了海洋渔业产业的合理化经营与管理[21]。20世纪50年代,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在水产业的普及与应用及片面追求“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盲目乐观海洋渔业开发方式,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主要集中于传统型海洋渔业第一产业,而在海洋渔业第一产业中则以对海域生态环境破坏力强的海洋捕捞业为主。这种不平衡的产业结构模式间接影响了渔民转产转业的观念及行为导向,阻碍了海洋渔业由一产向二、三产转型的速率,造成海洋渔业长期处于低值化,停滞化态势。同时,受早年间时代背景的约束和不科学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政策,错误将只关注提高产量,维持生计的渔民引入违背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律的道路上。直至改革开放后,“养捕并举”方针的实施有效改善了海洋渔业产业结构(图4),其中,我国海洋渔业养捕比由1978年的26∶74到1985年的45∶55再到2018年的77∶23,其产业结构逐渐优化。但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仍面临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经营格局过于分散、缺乏科技创新、风险保障机制落后,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无法支撑海洋渔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囿于在海洋渔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如(种苗、饲料、补给)等方面的有机构成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但缺乏合理化经营使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在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海洋渔业产业的边际效益开始下降,进而造成海洋渔业经济整体发展不平衡。

图4 1979—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捕捞、养殖及劳动力变化趋势Fig.4 Trend of marine catches, marine fishery aquaculture and labor force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from 1979—2015
3.2 海洋渔业生态子系统问题
建国以来,在经历战争浩劫之后,为大力恢复生产力发展和重整经济建设,将目光聚焦到开发一切可开发资源上。海洋渔业作为“资源无限量供给”型产业,理所当然充当起食物供给主要来源之一。在海洋渔业发展初期,突增性捕捞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如海洋捕捞量由1950年的54万t上升至1999年的1497万t,已经超出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科学评估中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捕量的66.3%,其捕捞作业方式以捕捞效率大、捕捞强度大的拖网和刺网为主,约占同时期内捕捞作业方式的40%和26%。同时,沿海渔民将维持生计作为无节制海捕的先决条件,导致该时期海洋渔业生态资源保护政策相对稀少。加之低水平的水产技术无法提升海洋渔业资源生态恢复力并伴随因外界不可抗力因素如海洋风暴潮、赤潮等灾害的扰动致使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承载力直线下降。而后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大量挤占沿岸海域滩涂资源,一些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各种污染物被携带入海,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2015年,沿海海域共发生船舶溢油事件3200起,溢油量高达42936t,水体表面污染严重侵害海洋渔业资源多样性。同时,随着生产力恢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迅速抬升,内陆人口大量涌向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快近海海域水质恶化速率,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阻碍海洋渔业种质资源修护。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国家从制度、科技等方面入手,逐步加强对海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使海洋污染有所遏制,但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依旧维持较低水平。
4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驱动机制
4.1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关键要素
从适应性角度出发,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既包括海洋渔业产业对于海洋鱼类资源退减、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的适应,也包含海洋渔业产业对政策体制及渔民生活状况的适应。由此构成该系统适应性循环圈的关键要素为海洋渔业产业、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社会环境。
首先,海洋渔业产业作为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构成因素之一,理应成为该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关键要素。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的良性化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其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目前,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正由“一、二、三”向“一、三、二”转变[1],逐步从粗放式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模式向集约化产业发展模式过渡,进而带动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向可持续化发展方向推进。
其次,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是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并贯穿于整个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始终。海洋渔业资源存量的增减,鱼类生存栖息环境的优劣,各海域海洋灾害的扰动等生态环境变化已成为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向前推进的巨大推动力或阻碍力。
最后,海洋渔业社会环境中政策体制和渔民生活状况是推动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把控者和利益相关者。自1949年全国政协将“保护沿海渔业,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到2013年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1],再到2017年农业部制定的《全国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中国海洋渔业发展从政策体制上进行调控,扭转违背海洋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路线。渔民作为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开拓者和维护者,是海洋渔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能力、生活质量、幸福感指数对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4.2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驱动机制
纵观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各个阶段,推动该系统运转主要受资源限制的内部驱动力和市场需求、政策制度响应的外部扰沌力的共同作用(图5)。

图5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与驱动机制结构图Fig.5 Adaptive cycl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marine fishery industry ecosystem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4.2.1资源限制
海洋渔业资源是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得以发展的基础要素,也是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海洋渔业资源并非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均可再生资源,具有特殊性,使得中国海洋渔业开发不能以过分攫取资源为代价,从而造成海洋渔业资源负向变动。在海洋渔业发展过程中,由人为因素导致海域生态环境恶化或外在自然灾害所致的不可抗力使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如2015年,我国沿海海域共发生赤潮灾害35次,累计面积约近2809 km2,直接限制了海洋渔业经济产业链条发展,阻碍了系统的正常运行。20世纪50、60年代,在对海洋渔业资源无节制大包大揽后破坏了海洋渔业自身承载力,资源严重匮乏,致使该时期海洋渔业经济停滞不前[32]。缺乏资源供给的海洋渔业无法进行产业转型和重构并长期徘徊于资源开发过程中,加速系统陷入适应性循环圈中的释放阶段。由此海洋渔业产业开发必须保持适量开采,使其维持在一定存量的水平上,遵守海洋渔业资源休栖规律,形成一种稳定的可持续循环发展。
4.2.2市场需求推动
海洋渔业经济在得到市场需求满足后方可向前推进。市场需求包含两方面,其一为内在经济发展刺激,其二为人口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洋渔业初入正轨,前阶段战争因素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物质需求造成极大困难。在市场需求驱动机制下,海洋渔业产业进入开发阶段以满足人们的食物供给需求和营养摄入,及通过提升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从而间接促进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后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经济环境背景下,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于鱼类蛋白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必然要求海水产品大量供给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营养需求[33]。其次,囿于市场需求多元化发展,开始依据市场发展导向而改变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模式,近70年内海洋渔业实现由单一传统型海洋捕捞业发展到养捕并举的海洋渔业产业,待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基本稳定后逐渐开发出休闲渔业、远洋渔业等新型海洋渔业产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洋渔业经济转型。
4.2.3政策制度响应
国家政策制度变革是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外部扰沌力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从政策制度层面将海洋渔业产业开发合法化、系统化。1949年自将“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后,海洋渔业产业开发得到政策支持,由此激发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大批涌向沿海进行海洋渔业生产作业,使得海洋渔业产业得到有效恢复,渔民家庭财富得到积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随后,为进一步扩大海洋渔业生产力,中央提出冒进,急于求成等口号方针,错误将海洋渔业发展目标集中到过量捕捞方向;以及在文革期间过度强调“以粮为纲”、围海造田,导致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受挫、资源承载力下降、产业生态系统恢复力较低,系统跌入贫困陷阱。面对因生态环境因素而制约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等问题,政府部门做出适时的调整,相应提出“养捕并重”、“大力保护资源”、“加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保护,积极发展水产养殖和远洋渔业”等方针,分散海洋渔业产业开发模式,解决了因过渡捕捞造成的海域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海洋渔业发展困境,使得系统潜能得以进一步恢复,系统变量间联系也更加紧密,协调组织能力增强,由此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逐渐走出困境从而开始新一轮适应性循环。总体来看,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演变受政策制度制约突出,系统在政策制度的驱动下,由开发阶段(γ)→保护阶段(κ)→释放阶段(Ω)→更新阶段(α)循环演进。其中多数海洋渔业产业政策的提出均属于事后补救性质而非事前预防性质[16],但在经历贫穷陷阱后,政策制度的提出与实施使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朝着可持续方向健康发展。
5 讨论与结论
为丰富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有利于梳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在长时序上的演化过程,通过把握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对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所经历的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行划分,进而得到在该系统下中国海洋渔业发展规律。
(1)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先后经历了以海洋捕捞业为主的恢复型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到海洋渔业养捕并重的过渡型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最终到向现代化转型期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过程。适应性各阶段循环运转往往是在经历崩溃释放之后在更新阶段中形成新一轮开发,从而再次构成一个新的适应性循环。其中,海洋渔业产业、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社会环境是触发整个系统由开发→保护→释放→更新的关键要素,同时支撑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动力主要来自于海洋渔业资源限制的内部驱动力和市场需求、政策制度响应的外部扰沌力的共同作用。
(2)就目前来看,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整体上正以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进发,但分时期分阶段仍会存在崩溃释放阶段阻碍系统向前推进的速度,甚至会再次跌入贫穷陷阱。由此,宏观上亟需加强海洋渔业在生态环境保护、种质资源修复、生产方式优化、公共政策调控等统筹布局;微观上,首先通过采取农牧化方式(人工育苗放流、引种移植、改善渔场环境等)参与鱼类资源再生,加大海域自然保护区建设;其次发挥不同海域的比较优势,开发不同水产种类,实现区域空间资源优势互补,提升产品质量,改善海洋渔业生产消费结构,将开发焦点由近海转向远海;最后,创新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建立以ITQ制度为主体,其他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完善监管制度,同时及时调整制度设计价值取向以符合当前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需求。
(3)采用适应性循环圈以定性的方式来判定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演化阶段,在划分标准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为力求精确划分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演进阶段并把握其驱动机制,未来将结合定量分析,通过筛选关键变量进行对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恢复力、连通度、潜力进行测度,进一步阐释不同尺度下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演化过程,以期为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指导。
——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