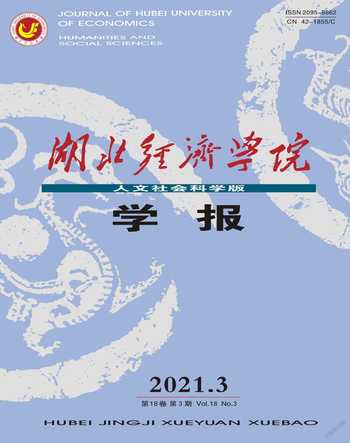《乔·特纳来过又走了》中黑人母亲的家园想象与身份困境
梁会莹
摘 要: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戏剧《乔·特纳来过又走了》中记录了美国黑人大迁徙时代黑人民族的身份焦虑和文化危机,其中的黑人母亲往往承担起凝聚、传承和修正文化信仰的民族使命。从守护传统家园的“他母”形象、在异质文化中的矛盾女性以及回归家园的自我救赎者等不同角色代表的黑人母亲身上能够透析整个黑人民族在社会转型期的家园想象和身份困境。威尔逊认为家园建设在于“自守”而非“求外”,要以民族自省审视内外部文化环境建立文化归属感,以民族能动性建构新家园模式。
关键词:威尔逊;《乔·特纳来过又走了》;黑人母亲;家园;身份
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1945—2005)聚焦非裔美国人的身份焦虑和文化危机,书写黑人群体自20世纪初的家园重建至20世纪九十年代的黑人发展史,从黑人民族自身反思非裔美国人身陷精神囹圄的心理机制,坚持将“能够凸显非裔美国人文化身份却又流散在外的元素重新找回并加以传承”[1]27,提升黑人民族的家园意识和文化情怀。《乔·特纳来过又走了》(以下简称为《乔》)以1911年的匹兹堡为背景,记录了美国黑人大迁徙时代黑人民族寻根的社会主题。南方种植园主变本加厉的剥削、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以及南北工业化差距刺激着数以万计的黑人踏上向北的迁徙之路,以期建构全新的家园。虽然威尔逊承认他自身的男性身份和视角有助于他刻画剧本中的黑人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忽视和贬低黑人女性地位。事实上,《乔》中威尔逊笔下以他母亲为原型的非裔美国女性往往承担起传承黑人文化、弥补文化断层、凝聚家庭和整个黑人民族灵魂的重担,但也存在“迫于个人意志的萎靡”或是由于“外界社会压力”而走不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以及历史预期”的女性人物[2]165。剧中赛斯(Seth)和贝莎(Bertha)的小旅馆临时搭建起离散黑人的“家园”,但它不是黑人社区的乌托邦式的避难所,重建家园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白人压迫,也有黑人内部的矛盾。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以《乔》中离散年代下黑人母亲的精神挣扎和家园追求为导向,深入探求不同年龄层、不同角色象征的黑人母亲在大迁徙时代对于黑人文化和家园建设的态度转向,并以此透析整个黑人民族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选择和迷惘乱象,进而挖掘威尔逊在黑人民族家园建设方面的政治思想和坚定立场。
一、临时的安身之所:家园守护与“他母”身份
“家园”是当代黑人文学探讨的主题之一。普林斯(Valerie Sweeney Prince)将二十世纪非裔美国人对公平、机会和自由的不懈探求看作是对家园的追寻,“家园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3]1-2,这暴露了黑人地理大迁徙前后身份失语和精神流放的尴尬境地。威尔逊认为,“家园随着黑人流散而崩塌”[4]44,黑人远离及割舍南方的文化之根是与家园的决裂,在异质文化中求生存只会压抑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由此可见,地理位置的迁移并非平行于身份心理的转换,“家园意识不是地理上的家园,而是身份的寻根。”[5]78威尔逊的家园情结在“匹兹堡系列”中得以彰显,他运用戏剧技巧首要呈现“家园”主题,强调想象和重建家园、守护黑人文化身份、抵御白人文化的侵袭的重要性。
《乔》中的临时家园模型来自赛斯和贝莎坚守的小旅馆。贝莎在剧中扮演替养母亲(surrogate mother/other mother)与社区母亲(community mother)的角色,这种他母形象“以黑人文化所倡导的爱的文化履行母性指责,同样扩展了母亲身份的范围,扩大了母性内涵”[6]9。贝莎的黑人身份建立在这种母性担当之上,她对黑人仪式的尊崇、民族精神层面的引导以及群体矛盾的协调体现了黑人母亲对传统家园的守护。“女性不仅仅是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者,也是文化的再生产者”,作为文化的监护人,她们有责任“以特定的文化方式建构‘家园”[7]130。贝莎的文化监护首先表现在她强烈的生活仪式感,其本质是对黑人传统文化元素的尊崇。作为仪式的践行者,她日复一日、不辞劳苦地招待客人就是一种黑人文化仪式,该仪式“赋予那些短暂停留的客人家园和宗教团体仪式感,让他们割断对往事以及家人的念想,一心投入到当下(旅社的)大家庭中来”[8]583。如一剂凝合剂,贝莎将来来往往的人群汇聚到自我想象的家园模式里。同时,她将拜纳姆(Bynum)的作法仪式当作规律的日常生活的环节之一,当丈夫赛斯对拜纳姆的古怪行为表示鄙夷时,贝莎辩护道,“当他为这座房子祈福时你也没有说‘不吧”,“拜纳姆没有打扰到任何人”[9]8①。她对拜纳姆的崇拜在于其宗教仪式服务于整个黑人族群的精神生活,是非洲文化的精神遗产。“拜纳姆法术的获得与表现几乎都和回归历史、认同非洲文化根源紧密相关。”[10]171因此,贝莎将拜纳姆看作是民族大家庭中的精神领袖。然而,贝莎个人却信奉基督教,她这种对于白人宗教和黑人文化兼容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黑人群体精神层面的矛盾,也有无力抵御白人文化渗透的无奈。
贝莎对家园转型和社会动荡的焦虑表现在她固化的生活习惯。她的活动空间局限于厨房和餐桌,“城市、厨房和子宫的场所重现明确地告诉我们非裔美国人对家园概念的理解。”[3]3以厨房为代表的家庭内部空间的沉闷和狭隘一方面说明缺乏流动性的生活惯例限制了贝莎应对生活变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暗示她对家园想象的局限性。当赛斯对她提出制咖啡壶的要求不满时,她的话语透露了一丝焦灼和愤怒,“男人,闭上你的嘴,去把咖啡壶做好”[9]17。黑人日常生活物品的差错在她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会打破常规,造成生活仪式的混乱。咖啡壶背后的零容忍实际上放大了她内心对于黑人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做出不利于保护黑人文化传统、有悖于家园建设行为的恐慌感。然而,从城市的外部空间对家庭内部空间的渗透作用看,“厨房”不足以成为民族文化的保温瓶,贝莎的角色功效只作用于黑人内部。
即便如此,贝莎依然是黑人家园的精神母亲。她超越非生物性母亲的身份,成为黑人社区精神层面的提醒者和引路人,而非仅仅停留在物质哺育层面。在卢米斯(Loomis)对卢瑟福·塞利格(Rutherford Selig)寄予高期待时,贝莎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塞利格的丑陋面孔,她提醒卢米斯不要因寻妻心切而被白人塞利格的行为表象蒙蔽,因为塞利格只是利用黑人家庭成员间的真挚情感牟取暴利,而非真正的“寻人使者”。冒进的吉瑞姆(Jeremy)想前往塞福斯(Seefus)碰运气,贝莎提醒他勿要重蹈覆辙,“你可能会被突然逮捕,然后进监狱”。她不仅提醒在外闯荡的男性,也默默引导青年黑人女性定义自由个体身份,她鼓励玛蒂(Mattie)自己寻找爱与快乐的真谛,而不是把幸福寄托于男人身上。这既是“他母”对女儿辈的教誨,也是黑人女性间互相扶持而形成的战略联盟。
此外,贝莎以矛盾协调者的角色维护着家园和睦。为维护个人家族名声,丈夫赛斯常常苛责客人的行为,流露出对客人的不信任,正是贝莎的积极协调才得以让旅馆正常运转。在小旅馆上演的冲突实际上也在影射黑人移民过程中经历的挫败、内部矛盾、潜在性暴动和集体创伤,但威尔逊以贝莎的行为强调了民族内部团结和集体意识对于肯定集体文化身份、消弭种族创伤的意义。贝莎作为“他母”的母性关怀降至每一位黑人家族成员,当赛斯指责吉瑞姆被警察抓走破坏了自己家族的好名声,贝莎指出了黑人家园的外部威胁:“你知道警察是会这么做的……会把其中一些人抓走”[9]18;在赛斯和卢米斯为女儿佐尼亚(Zonia)的住房费用讨价还价时,她为孩子解围:“让她来帮我干活吧”[9]19,顺势将孩子留下来。她避免冲突的爆发和矛盾的升级实则是在维护黑人传统家园秩序,正如她驱逐旅馆中的悲伤,开展欢笑的洗礼,渴望众人能在家园的和谐氛围里沐浴自由与爱。相对而言,赛斯所维护的家族名声只是黑人家园中的一个小单位,而贝莎关注的才是命运共同体下的整个黑人民族的精神需求。
二、异质文化中的归属:家园变迁与身份焦虑
二十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反映了南方黑人迫切逃离压迫,寻求避风港以及重建家园的心理。在北方工业家的鼓吹下,“北方城市一跃成为未来家园的象征。移民纷纷北上寻梦”[3]14。但长期处于被奴役状态下的黑人尚未彻底消除心底的自卑与创伤,对新家园内部家庭结构和外部社会环境缺乏认知,加上黑人社区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黑人群体在白人社会中都处于漂浮状态。“‘家国这一术语本身就表示,作为存在主体,其必然是复杂相连的意识形态集合体,包涵归属感(belonging)的概念、拥有家园(a home)以及个人的安身之所(a place of ones own)。”[11]2虽然赛斯和贝莎的小旅馆确实为黑人提供了安身之所,但个人的归属感实则取决于行为个体对待本民族文化和外部文化的审视态度。《乔》中年轻黑人女性玛蒂·坎贝尔(Mattie Campbell)和莫莉·坎宁安(Molly Cunningham)的身上或多或少带有黑人母亲的影子,她们对新家园的消极想象实际上印证了离散时代黑人群体对黑人家园发展理解的局限性以及对文化身份的焦虑感,展现了她们在大迁徙时代前后归属感的摇摆。
玛蒂的家园想象割裂了個体成长和家园发展之间的联系。她对于家园的理解仅局限于家庭成员的完整性,忽视了新环境下个人价值体系以及社区归属感的建构。身份既是主观的个人选择,也是外部赋予的属性。“正是内外定义之间的辨证张力赋予了生命体验以活力。”[12]58玛蒂既是妻子和母亲,又是黑人社区中的一员,但她过于强调家庭身份而忽略了社会身份,两者身份间辨证张力的缺失也让她的生活停止流动。二十六岁的玛蒂脸上布满了“失意生活下的重担和忧虑”[9]25,丈夫杰克·卡珀(Jack Carper)认为孩子的屡屡夭折源于她遭受过诅咒,因此抛弃了这个残缺的家庭。玛蒂却始终认为丈夫的角色高于一切,“他比整个世界还要重要”[9]27。即使寻人之旅历经波折,她仍盼望丈夫的归来,并恳求拜纳姆将丈夫召回。其实,拜纳姆给玛蒂的神奇小布袋中两个东西——根和粉就在暗示玛蒂过分迷恋丈夫的同时早已遗忘了她个人角色的光芒。她将生活的重心给予狭小的家庭内部而看不到整个黑人家园给予她的精神养料。“旅社对客人来说是家外之家,贝莎的炸鸡和周日的朱巴舞,在某一瞬间,为相聚在一起的住户们营造一种黑人社区的氛围。”[13]101也正是在旅社和外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她慢慢走出过往观念中固守的家庭模型,寻求个人价值。如果说吉瑞姆企图骗取玛蒂的肉体,他也一定程度上攻破了玛蒂的心灵防线,解绑了她的精神枷锁。《乔》的结尾玛蒂追随卢米斯的主动行为表明她明确了情感的新追求,威尔逊以玛蒂的觉醒强调黑人女性个体解放是实现家园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时黑人社区的团结也能赋予个体归属感。
激进女性莫莉对家庭的内部想象是极度绝望下的空白。她身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仇视男性、怀念母亲。与玛蒂的出场描写相比,二十六岁的莫莉更显新时代下激进的风尘女子特征。“携带着一个小型纸制行李箱,身穿当下流行的彩色连衣裙”[9]46。她在与拜纳姆的交谈中控诉了父亲的暴力与对家庭的漠视,认为父亲一心把世界翻个底朝天。她对父亲的仇恨态度映射出男权压迫和种族歧视下黑人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尽管每个围绕性别分工建构起的家庭都充斥着内部矛盾”,黑人的家庭领域“因为贫穷、种族主义以及性别间不平衡的权力而显得更加凶险”[3]44。关于父亲的消极记忆让莫莉不再信任男性,她看透了年轻男人骗人的鬼把戏,决定不要孩子,因为孩子只会证明女人是为男人延续子嗣的生育机器,而家庭则成为男性暴力的宣泄口。莫莉对于黑人母亲命运的悲观解读不仅暗示莫莉亲身经历过的家庭悲剧和男权暴力,也暴露了长期以来黑人家庭中“女人——孩子——男人”之间的畸形关系。子女在家庭中本是男人和女人的情感纽带,但权力机制下的性别分工将女性束缚于家庭内部,滋养着男性暴力,引发家庭代际创伤。“就功能而言,正常的‘家或者说理想的‘家应该能促成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让人在平和中去爱、去接受、去感悟人生”[14]112。但处于非理想的家庭中,莫莉被无辜戕害,她对组建家庭早已心灰意冷,宁愿选择另一种畸形的生活方式与男性保持距离。
其次,莫莉对于新家园的外部想象更接近于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她拒绝黑人传统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继承了白人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因崇尚白人的自由主义,莫莉拒绝成为别人的“奴隶”。当看到玛蒂还在做熨衣服的活养活自己时,她嗤之以鼻,“我绝对不做那种活……尤其是别人的衣服。就是它把我的妈妈害死了”[9]60。在她看来,为别人干活永远摆脱不了低贱的奴隶命运。因此对于吉瑞姆的示爱,她明确了自己“不工作”“不去南方”的态度[9]63。深入骨髓的南方阴影证明“背井离乡的非裔美国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奴役”[15]475。所以莫莉的家园想象是寄希望于新环境——北方,而全盘否定南方黑人传统文化。但莫莉没有认识到独立自由女性的真正内涵,她拒绝劳动甘愿堕落为风尘女子,只能永远依靠男性存活,走不出男权压制的怪圈。黑人青年一代对白人文化中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崇拜揭示出黑人传统文化危机,而他们随波逐流的心态也暴露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和对未来家园的迷惘。虽然黑人女性与男性的矛盾在剧中演变为文化的冲突,即以男性拜纳姆为代表的黑人文化与女性莫莉为代表的白人文化,但莫莉在黑人文化取舍方面依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觉得拜纳姆的法力很可怕,另一方面又产生好奇,毕竟她母亲生前非常相信拜纳姆之类的变法。莫莉对黑人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导致她归属感的摇摆,即使她排斥南方的记忆,想立身于北方,归属感的匮乏让她无力想象一个完整且现实的家园。
三、矛盾中的救赎:母性回归与家园重建
新型黑人既渴望融入白人社会,接纳白人的主流思想,摆脱低劣卑微的边缘地位,又发现无法割裂黑人文化之根。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用“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的概念分析了黑人群体在异质文化中的心理机制:“他可以感受到自我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也是一个黑人;带着两种思维,两种无法和解的冲撞;黑皮肤下有两种对抗着的思想,彼此凭借顽强的力量抵御被对方撕碎”[16]8。《乔》中的黑人母亲玛莎(Martha)的内心有着两股冲撞的力量,她先后对女儿抚养责任的“割弃”和“追寻”体现了她走出家园而又回归家园的自我救赎心理,但不彻底的自我救赎也影响了下一代青年對黑人家园展开想象的能力。
玛莎为追求白人基督教而割弃对女儿的养育责任既是她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也是她对黑人文化无意识的背离。在得知卢米斯被乔特纳抓走后,“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就好像我把我的全部心血倾注在一个裂了缝的坛子里,最后一切付之东流”[9]82。之后她和女儿佐尼亚(Zonia)被白人房东赶出了家,流离失所,无奈寄宿在自己的母亲家。丈夫角色的缺失让玛莎对不再完满的家庭愈发绝望,这种沉痛成为一种心灵包袱阻碍玛莎投入新的生活。意识到她将自我和生死未卜的丈夫、残缺的家庭捆绑在一起而消耗了青春、斩断了未来,她决心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将生活控制权掌握在个人手中,追求个人自由。重逢卢米斯时,她向卢米斯坦白,“……我在心中将你杀死了。我埋葬了你”[9]82。然而,玛莎为追求个人发展而暂时搁置了对女儿的抚养责任,将女儿托付给自己的母亲。从几代人的母女关系可以看出女性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玛莎“既是女儿又是母亲,既是自我又是他者”[17]27。若将未出场的玛莎母亲和玛莎本人进行对比,更容易看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两代母亲的社会处境,千千万万个像玛莎母亲般的黑人女性一直以来驻守家庭,承担着养育重任,而像玛莎般的新女性已经可以踏出家园、寻求新生活,但无意识中割断了母女之间的传承纽带,打破了黑人文化的传承模式。这种有意识的“得”与无意识的“失”展现了黑人母亲在平衡个人自由和民族文化时的身份困境。
玛莎寻回女儿是玛莎家园意识的苏醒,但投身白人教义的行为暴露了黑人宗教文化的传承危机。威尔逊本人反对黑人信奉白人的“神”,认为这会一定程度上削弱非裔美国人的身份意识。“他不反对基督教,但反感那些强化‘白人性的基督教教义和基督徒形象”[8]595。玛莎给自己换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字——Pentecost,新身份的开启也意味着玛莎对家园的回归终究是不彻底的,即使与激进女性玛蒂不同,玛莎没有与家园决裂,但她没有意识到自我文化身份被白人文化逐渐吞噬的危机。在得知丈夫把女儿带走后,她开始寻找女儿,弥补母亲身份的过失。卢米斯在与玛莎重逢后指责玛莎让女儿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motherless)”[9]82,这种指责激起了玛莎的愧疚。“卢米斯将女儿交给妻子的根本原因是他对母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重视”[10]179。玛莎离家前无意识的“失”在卢米斯的提醒下似乎变成了黑人母亲的失职,这种评价与玛莎对于女儿的爱以及家园的初心是不对等的。女儿抚养权的失而复得是玛莎回归黑人家园的表现,但这种不彻底的回归暗示着玛莎自我的双重性并未得到有效平衡。
《乔》中佐尼亚的孩童形象揭露了黑人家园重建过程中的彷徨感。佐尼亚一直哼着的歌是她对未来的态度:“明天,明天,明天永远不会来临”[9]39。“这首歌的歌词也体现了佐妮娅与父亲的关系,她必须陪着父亲去寻找玛莎。但佐妮娅想永远做卢米斯的小女儿。”[15]474因此,她一直排斥长大。这种排斥和对未来的惧怕突出表现在她对自我生长的抑制,贝莎曾提醒她吃早餐,“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不肯吃饭的孩子。你干瘦的像豆架”[9]78。佐尼亚控制自我饮食的异常举动暗示她心理层面的畸形发展,也是成长过程中母亲缺位而父亲无力弥补的事实依据。她还极力否认外界的评价,邻家男孩鲁本·斯科特(Reuben Scott)将瘦弱的她称为“蜘蛛”“黑寡妇”,她却继续逃避现实。当卢米斯把她转交给她的母亲玛莎时,佐尼亚表现出无比的惊恐,“我不会长大!我的骨骼不会再长了!它们不会的!我保证!”[9]83。对她而言,成长意味着变化,变化会使未来的一切变得无法定义,捉摸不定,这带给佐尼亚的是无力和彷徨感。“威尔逊主张黑人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们悲伤的根源,从而化解悲痛,重新开启全新的健康生活”[18]33-34。沉溺于过去而畏惧未来则无法保证家园的发展,威尔逊用孩童鲁本颠覆了佐尼亚的“过去”思维,鲁本与佐尼亚的约定婚姻“意味着他们从童年到少年再到成年的行为准则的改变”[15]475。
由于从小缺乏母亲的引导,佐尼亚对未来家园的想象是狭隘的。“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19]213。因此,仅仅“根植于过去的纯粹的‘恢复”远远不够,还应该在传承过去文化的基础上,鼓励“流散者在建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agency)”[5]99。然而,不论是对黑人文化的传承还是对未来家园的建构,佐尼亚都未能呈现出积极的态度。在母亲玛莎出现之前,她对母亲的憧憬是美好的,当鲁本说他看见了赛斯的亡母梅布尔女士(Miss Mabel)的鬼魂,并将她描述成身穿“白色长裙”、手握鞭子的女鬼时,佐尼亚却认为她可能是“天使”[9]74。“天使”是正义、善良、圣洁的化身,这实际上也是佐尼亚对想象中母亲的期待。但与母亲相见后又被再次父亲抛弃,家庭团聚的想象画面被现实击碎,佐尼亚沦为父亲和母亲文化分歧的牺牲品。“这让人想起黑人家庭被拆散,家人被卖到不同农场的场景”[20]113。显然,奴隶制的结束并没有完全打破黑人家庭离散的模式,这场由黑人内部主动发起的迁徙反而在延续着民族创伤。“明天永远不会来临”,这是威尔逊对青年一代缺乏引导、难以投身于未来家园建设的担忧。
四、结语
威尔逊认为《乔》这部戏剧是他的代表作,因为这部剧囊括了其他戏剧中的大部分思想。以美国黑人大迁徙为创作背景,威尔逊表达了对黑人文化和民族家园建设的态度。家园承载着民族文化,是精神归属的支撑,而黑人母亲是家园建设中文化记忆和身份发展的影响者。她们对子女的哺育已经远远超越物质层面,“(她)教会你如何转变”,“如何审视你明天的出路……以及如何自我面对孤独”[9]29。因此,黑人母亲是连接民族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她们对待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民族家园的构建。从黑人母亲家园想象的心理图景来看,整个黑人群体在离散时代流露出对过去和将来,个体发展和家园共同体,文化认同和排斥的多元态度,这也是威尔逊对民族命运的担忧所在。“威尔逊清楚,自己在纸上和舞台上所纪念的社区充斥着犯罪与贫穷。但他的艺术视野提醒我们,在那个家园、那个社区、那个祖先的遗址中保留着一条珍贵的社区生命线。”[4]59他主张黑人群体从自身反思民族发展的困顿局面,在文化传承中定位家园建设依据,发挥集体能动性参与民族发展建设,既不可深陷在过去的种族创伤中忧郁萎靡,又不可因身份焦虑而迷失在白人文化中,要以黑人群体的家园意识凝聚传承力量,以文化传承修正民族信仰,追求身份的归属。
注 释:
① 本文中对《乔》的引用皆出自Wilson(2007),所有原文引用均为作者自译。
参考文献:
[1] SHANNON S G. Framing African 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The Bookends Plays in August Wilsons 10-Play Cycle[J].College Literature, 2009, 36(2): 26-39.
[2] ELAM Jr H J. August Wilsons Women[C]// NADEL A. May All Your Fences Have Gates: Essays on the Drama of August Wilson. U of Iowa P, 1993: 165-182.
[3] PRINCE V S. Burnin Down the House: Home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5.
[4] WARDI A J. From 1727 Bedford Street to 1839 Wylie Avenue: Home in August Wilsons Pittsburgh Cycle[J].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2013, 82(1):44-61.
[5] 郑海霞. 华裔身份的追索与建构:美国华裔文学流散叙事研究[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6] 毛艳华.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母性研究[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7] YUVAL-DAVIS N. Gender and Nation[M].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8] ELAM Jr H J. Teaching 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J]. Modern Drama, 2007, 50(4): 582-600.
[9] WILSON A. 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M].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 Group, 2007.
[10] 李尚宏. “你自己的歌召喚着你”——论《乔·特纳来过又走了》中的黑人身份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 (3):169-180.
[11] GEORGE R M.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M]. Cambridge UP, 1996.
[12] HECHT M L, JACKSON R L, RIBEAU S A.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M]. L.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13] GRANT S. Their Baggage a Long Line of Separation and Dispersement: Haunting and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in 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J]. College Literature, 2009: 96-116.
[14] 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3,34(01):111-119.
[15] BOGUMIL M L. Tomorrow Never Comes: Song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August Wilsons 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J]. Theatre Journal, 1994,46(4):463-476.
[16] DU 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 LILLVIS K. Posthuman blackness and the black female imagination[M]. U of Georgia P, 2017.
[18] GAYATHRI N, ALAGARASAN D T. Probing into the Psyche of Subalterns in August Wilsons 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Humanities, Literature and Science,2016:30-38.
[19]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C].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0] OTU O O, UDUMUKWU O. Racial Identity and Modern Day Slavery in August Wilsons Gem of the Ocean, 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 and Ma Raineys Black Bottom[J]. AFRREV LALIGE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Gender Studies, 2015, 4(1): 10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