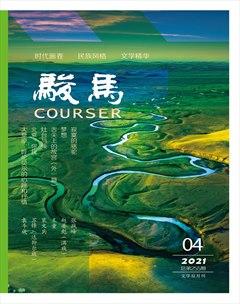石命
宋扬
1
泡桐崖下,那一整片天然裸露的石头抱得死死的。
墨斗。墨轮转动,墨线拉直,挑起,弹下,宣告一块石头将从此处分娩,与母体分离。石匠早已洞悉石头的硬度、质地和肌理。錾子中的某根被选作开路先锋,在墨线上等距离凿出一排石眼。插入石眼的钢楔子们有些迫不及待了,那些被铁匠千锤百炼锁住的能量需要喷发,钢楔子们等待着来自铁锤的召唤,只一击,铁锤就能点燃引线,引爆自己,就能撕裂巨石——那是钢楔子们的荣光与渴望,也是它们的使命。
锤杆是石匠延伸的手臂,碳钢锤头是拳头,石匠胃里消化着的麦子、高粱、番薯、玉米就是烈性炸药。一锤,一锤,炸药的刚猛之力从石匠紧握锤柄的双手沿锤柄向锤头突奔,在锤头与钢楔子冲撞的瞬间炸裂。
硬实木棍做不得锤柄——巨石弹向钢楔子弹向锤头的反击力沿锤柄向手掌反扑。冲撞,乱颤,虎口震裂将是必然。石匠有的是力气,但石匠懂得敬畏自然,敬畏巨石。只有那看似柔弱的新柏堪当大任,它们只有大拇指粗细,但已具体而微,厚实,柔性,绵劲,可最大限度缓解石头对手掌的震颤。石匠的双臂挥起来,重力与加速度叠加,大锤坠悬,锤柄在石匠头顶弯成蒙古可汗的弓。不!比弯弓射雕更磅礴野性!“嗨……哟……”石匠的呐喊由胸腔迸发,沉闷回旋。石匠的手臂猛地收住!回拉!手臂、胳膊、肩膀、腰身肌肉攒集凸起,脖颈上青红的血管像被刨了窝的蚯蚓,四下奔命。猛地,那张弯曲的大弓反方向回弹,锤头的加速度陡转方向,力道增成,“嘣!”山谷传音,裂雾穿云。铁锤撞击嵌入石眼的钢楔子,炸药与炸药合谋,石头裂开一道近乎直线的缝。这是一种刚对另一种刚的征服,是一种附加了智慧的力对另一种原始笨拙的力的攻克,像古代以刃斗兽的猛士。“嗨……哟……嘣……”“嗨……哟……嘣……”一声,两声,三声……一次次猎捕与征服。犹斗的困兽,在挣扎,在悲鸣。
大锤挥斥方遒,是大兵团作战的将军,身先士卒。大锤撂倒对手后,士兵錾子们潮水般涌了上去。
2
钢钎一撬,石头轰然倒下,可绝不俯首称臣,不屈之气鼓成六个切面上凸起不平的愤怒。尖錾子,扁錾子。錾子的使命就是要一点点消磨石头,直到它们臣服为薄薄的洗衣板、滚圆的石磨、装猪食的石槽或横平竖直的墙基石。
屈人之兵,收人之心,石匠不懂打仗,但攻心为上的道理无师自通。石匠知道,刚败给勇猛大锤的石头需慢慢收复,使狠,石头将以粉身碎骨的决绝让石匠徒得一堆废料。石匠的动作变得温柔缓慢,空出左手小指,四根手指轻轻扶住尖錾子,錾子以四十五度的斜角轻抵石头愤怒的凸起。石匠右手握斧,小心敲击錾子。“当”,錾尖迸出了第一点火星,石匠密切关注着石头的反应,它只是微微抖动了一下身体,没有激烈抗争,更没有以断裂明志。石匠安了心。“当,当,当……”石屑四下飞溅。扁錾子接力,一点点磨平尖錾子留在石头上沟沟壑壑的伤痕。慢慢地,石头的面平了,石头的背光了,石头的四四方方水豆腐一般滑了。不知不觉间,石头对撂倒自己的石匠不那么咬牙切齿了。它惊讶,石匠温柔地抚摸,让自己又有了生命。某一天,石头被砌作墙基,挺起了一座房子;石头变成石磨,磨出了白嫩的豆浆;石头磨成洗衣板,穿上了浣衣女铺开的衣裳……石头这才明白,自己成全了一个好石匠的名声,一个好石匠也成全了原本待在泡桐崖籍籍无名的自己。
有的石头,会遇到更手巧的石匠和更纤细的錾子。
女人的舞台在绣花细针,在柔软锦缎。石匠分粗细,细匠以精雕细刻著称。细匠的舞台在天地间至刚至硬的石头上,他们的工具,只是一把更细更小的錾子。
与所有錾子一样,雕刻文字、图案的錾子迎接的依然是温柔而单调的轻轻撞击,那些錾尖儿却在石头上开了花,成了树,变了鱼鸟兽人。以錾为笔,以石作纸,手随心走,錾会手意,全看细匠胸中有丘壑,才能把粗粝化为精致,把单调繁复成永恒的经典图文。细匠知道石头的诗意,如同画家知道一张徽宣的素雅和宁静。只要让石头开花,就装饰了人间烟火,丰富了艺术庙宇。细匠算得上雕塑家,也配称画师和书法高人。
石匠打下的那些粗粗细细的石头有了不同归宿。无论被做成受人高香供奉的神仙菩萨,还是遮风避雨的房子,抑或藏污纳垢的猪圈茅厕,石头都认了命,就像石匠,认定自己的一生,就是石命。
3
粗匠并不知晓自己抡大锤的身姿张扬着力与美,甚至连那些细匠也不认为自己日复一日敲击錾子可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他们只有把打好的石板石条、刻好的石碑石兽抬到买主家,才能换回让一家人活命的粮食和孩子的学杂费。石匠也知道生活的艰辛,如同知道一块石头棱角的尖锐和纹理的曲折。石匠用倔强打磨岁月的坚硬,用意志融化生活的冰冷。
抬石头是每一个石匠的必修课。
见过抬着石头行走的石匠,你才能理解弱小的蚁群何以能迸发出那么奇伟磅礴的凝聚力。愚公移山般的莽勇中,你能看见智慧的闪光——粗实的麻绳套牢石头,杠套杠,力均分,4人、6人、8人、16人……我见过家乡的石匠抬着家乡一历史名人的巨型石像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128人的石匠队伍,千钧重担分到每个石匠身上,已飘若轻云。
石匠号子也是每一个石匠的必修课。
石匠把一首首俚俗的号子,扛在肩头,让沉重的石头在歌声中变轻。你听,石匠号子唱起来了,即物起兴,合辙押韵。领唱的石匠唱前半段,众石匠跟后半段,此起彼伏,山谷合鸣。号子在随意间暗合着节奏,在高亢中放纵着悠扬,在粗犷里浸透着柔情。石匠以朴素的歌喉,唱地方风物,唱人文美景,唱爱恨情仇……石匠的歌洋溢着浓烈质朴又坦坦荡荡的天地神韵。
他们唱农事,“九月小春要点下,田边土坎要挑沙;落雨要把胡豆点,天晴要把红苕挖;十月阳春暖和啦,乡间活路乱如麻……”将节气与农业生产巧妙结合,寓教于号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二十四节气歌》;他们唱地方建设,“大桥修得真正好,修桥之人有功劳……桥墩稳来铁索牢,钢板水泥路面浇……轮船开来桥下过,汽车桥上乐逍遥。”一歌三赞,一赞修桥的劳动人民,二赞桥本身坚固耐用,三赞桥带来了交通便利;他们劝人行善,“正月里来是新年,弟兄邀约去赌钱;上场就赢几十万,请起挑夫把家还……腊月赌钱又一年,双脚跪在爹面前;三百棍子随你打,后悔当初去赌钱。”从正月唱到腊月,将赌钱人一步步走向深渊终悬崖勒马浪子回头的过程细细数来,让人警醒;他们赞家乡风物,“下了陡滩行得慢,不知不觉到乐山;嘉定过河大佛寺,大佛脚踏乌尤滩;大佛乌尤两边站,中间显出闪弯弯……”“乐山”“大佛寺”“乌尤寺”,家乡美景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满满的自豪感全在闪弯闪弯的旋律中;他们也唱爱情,“观音寺出了灯和尚,深沟子还有幺姨孃……”生拉活扯,硬把清規戒律中的僧人与女人一块儿说,话里话外,暧昧人间烟火。曲高,难免和寡,内容“荤素”搭配,才是生活本真,也才更动人迷人;他们还学《诗经》借物起兴,“一看船拐石礅子,二看青山白鹤林……八看渡口闹腾腾,九看花伞一长串,十看有无意中人”绕了一大圈儿,到“九”到“十”才唱出真正目的,“叫一声那个幺妹妹,快来喝茶看美景;叫一声那个石匠哥,快来喝茶看美景;满山白鹤成双对,鸳鸯凼儿比海深……”石匠们也勇敢追求爱情,石匠号子乐而不淫……
石匠号子与打石头、抬石头相伴相生,是繁重劳动中以苦为乐的生命之歌,像大山一样巍峨起伏,波涛一样汹涌澎湃,小溪一样潺潺缓缓。有人说,人类的生产生活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文化因子。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写到,“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吕氏春秋·淫辞》记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抬木队伍中,有人喊出了第一声“舆謣”舒缓劳累,引得众人仿效而纷纷唱和——“舆謣、舆謣”。人类抬着石头从石器时代走进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石匠是所有匠人中最古老的种类之一。我常常为石匠号子叫屈,《诗经》中为何不记一记石匠号子?
石匠号子中的每个词都如石头一样质朴,每句话都像石匠一样坦诚,每句韵都有来自泥土却往云端走的力量。也许,石匠曾惊讶地发现——“石怕唠”。石匠在周而复始的“唠”(号子)中忘记了肩上石头的轻重,石头也在石匠周而复始的“唠”(号子)中被一块块抬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石匠们在号子的节奏中协调成一群举起数倍于自己体重的重物集体行走的蚂蚁,他们哼唱着石匠号子,稳稳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一个不再需要石匠的时代。
石匠眼睁睁看着古朴浑玉般的农业文明渐渐被新兴工业文明所取代。洗衣机替代了洗衣石板,抽水马桶替代了石砌茅厕,钢筋混凝土替代了石头地基,石头已几乎很少有用武之地。偶有石料需求,机械化作业的石场里,切割机分离,起重机吊装,大卡车运输,石匠的铁锤、錾子被遗落在老宅不起眼的角落,早已锈迹斑斑。石匠的工作范围一日小比一日。终于,只有少数尚允许土葬的偏远山区才能见到石匠的身影了。
泡桐崖下,一个老石匠死了。送丧队伍中,石匠们走在最前头,他们要用最隆重的八抬送老石匠上泡桐崖。石匠们都已经很老了,他们走得缓慢,要沿一条历史的河回溯;他们的每一步都颤颤巍巍,像抬着一块他们多年前打下的石头。石匠们的双脚从那一整片天然裸露的石头上踩过。石匠们用弯曲的脊背和最后一曲石匠号子送着老石匠——
“太阳落崖就四山阴嘞,高山凉水它冷冰冰,劝郎莫吃那冷凉水嘞,吃了凉水就冷了心。太阳落崖就红彤彤嘞,泡桐树上它挂灯笼,风吹灯笼它团团转嘞,火烧灯笼就红了天……”
责任编辑 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