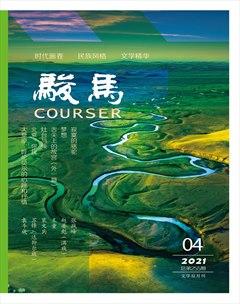辉腾高勒
吕阳明
一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辉腾高勒是个普通的林区小镇。辉腾高勒这个名字,给人一种辉煌的、腾飞的美好感觉,实际上辉腾是“极寒”的意思,高勒是河的意思,用一句略有诗意的语言概括,一条即便是三伏天也冰凉刺骨的河,从林区小镇旁奔腾流过。
顾名思义,小镇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那年冬天,霍思源的爸爸说,收音机里说了,我们辉腾高勒创下了同期最低温记录,零下48度。小镇上的人们沸腾了,那可是中央台的新闻啊,人们激动得两眼放光,几乎是奔走相告了。小镇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向大兴安岭森林的过渡地带,最美丽的季节是夏季,就那么两个多月。多年以后小镇开发旅游,街道两边的路灯杆上到处挂着“小镇不大,美丽如画”的宣传画,我觉得真是再贴切不過了。
霍思源的爸爸霍远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学校里没多少学生,我和霍思源是同桌。霍远老师的西部口音总是听得我们昏昏欲睡,而他却总是以自己的口音为傲,他说,你们晓得吗?我这个口音才是标准的古汉语口音,你们读诗词,是不是有很多不押韵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哦,不是古人不押韵,是你们的读音不标准了。你就说这李清照的“独自怎生得黑”,你们读“黑”,其实宋朝时这个字读“褐”,他讲得摇头晃脑,可是我们还是读“黑”。
我爸妈是逃荒来的河北人的后代,他们没有文化,但是勤勉劳作。我曾经试图了解先辈们是怎么从河北来到草原的,没有定论。父亲总是说,你爷爷奶奶在世时没说过。母亲会说,问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做啥,就算是皇宫里来的,咋的,你还能回去啊。我想了想,的确回不去,就不再问了。我妈总是这样说起霍思源,那个臭小子,长着和他爹一模一样的酱块子脑袋。这么一说,还真形象。我妈每年都要做大酱,黄豆煮熟捣碎,做成一个个长方体的大酱块,在热炕头上捂出绿毛,再洗刷干净,掰成小块儿装缸。霍思源和他爹的脑袋还真跟酱块子形状挺像。我妈愿意让我去霍老师家玩,理由很简单,霍老师是读书人。我妈是邮电所的临时工,她说,霍老师的信最多,一个月所有的信件里差不多有一半写着“霍远”的大名,都是一些大学啊,编辑部寄来的,真是太有学问了。
我妈说得对,霍思源家整个一屋子都是书,一张小长条木桌摆在屋子中间,被一直堆到顶棚上去的书围得水泄不通。霍思源的母亲又高又壮,是林业局的伐木工,说起话来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抡起长柄大斧子一会儿工夫就能砍倒一棵大树,年年是劳模、三八红旗手、铁姑娘队队长,年轻时脾气暴得跟男人打架,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家公认没人敢要的老姑娘竟然嫁了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两口子每天争吵,天大的事要吵,屁大的事也要吵,人们都说这两口子过不长远,不定哪天一拍两散了,哪知道转过年生了个小酱块脑袋,日子就吵吵巴火地接着往下过。
那时我学习成绩好,除了作文成绩比不过霍思源,每科都是第一名。霍老师也很喜欢我,我望着那些书说,老师,这些书就是你讲的文学?霍老师说,这只是文学的一小部分,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吧。我接着问,老师,文学有什么用呢?霍老师说,什么用也没有,百无一用。这个回答让我吃了一惊。我说,那,我们学它干嘛呀?霍老师说,总得有人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也不翻开,说,“呼兰河小城里以前住着我祖父,现在埋着我祖父,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难去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本小说的开头,我崇拜地望着他,发现他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他不再看我,眼睛望向糊着报纸的天棚了。
那一年的那一刻,算是我的文学启蒙吧。霍思源那时沉迷其中,他是把上数学课的时间都用来写诗的。他写东西从来不让人看,不过,他也不是所有的课都没有兴趣,比如历史课,他听得兴致勃勃。那位小陶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在学校代课,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她讲课从不用教案,把教案往讲台上轻轻一放,伴随着优雅的手势,娓娓道来。
二
初中毕业,霍思源和我一起考到海拉尔去念高中了,我是重点班,他是普通班。那一年,小镇里传言小陶老师和霍老师好上了。那时我们对“好上了”是什么意思还不甚了解,可随后发生的事让我们大吃一惊。一天上历史课,小陶老师正讲那首失传了的《广陵散》时,一阵吵闹声从窗外传来,我们纷纷向窗外张望,猛然看见霍思源妈妈凶神恶煞地从校长室里冲出来,直奔教室而来,霍老师随后追了出来,在后面紧紧追赶,教室的门被一脚踢开了,一声叫骂,“你个狐狸精,勾引别人家汉子,看老娘活撕了你。”小陶老师哪见过如此阵势,吓得花容失色,嘴唇哆嗦着喊,哎,你干什么……这是课堂,你怎么骂人呢。女人说,骂人?俺还想打人呢。冲上去,伸出大手一把揪住小陶老师的衣服就往外拽。只听“刺啦”一声,小陶老师的上衣被撕裂了,露出了粉红色的胸罩。一对雪白挺拔的乳房像受惊的小兽一般跳动着,几乎要从胸衣里跳出来了。人们瞬间惊呆了。小陶老师惊叫了一声,一手掩着衣服一手捂着脸,跑出教室去了。
从那以后,小陶老师再没有在课堂上出现过。后来听说,小陶老师在宿舍哭得双眼红肿,把教导主任吓得够呛,唯恐她一时想不开出什么意外,守在身边不停地安慰她。小陶老师后来不哭了,爬起来煮了碗面条,吃了。把宿舍里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对教导主任说,大姐,我走了,反正也转不了正,这个课我不代了。小陶老师走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微笑着和同事告别,最后径直走到霍远老师办公桌前站住了,眼睛热辣辣地盯住他,轻声说,霍远,你跟我一起走吗?声音不大,却如平地一声惊雷,办公室里的老师们呼啦啦各找借口如鸟兽散。
小陶老师说,你要是真心的,现在跟我一起去长途客运站,敢不敢?霍远慌作一团,嚅嗫了半晌,说,我还能去哪里。小陶老师说,世界那么大,哪里不能去?霍远老师沉默不语。小陶老师仿佛等了有几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眼睛里的亮光终于慢慢熄灭了,拎起提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我们读高中的四年里,霍远老师成了小镇上的新闻人物,可惜不是因为文学,他忽然之间成了一个放荡公子,三天两头地闹出绯闻来,并迅速扩大到周边县市。写信讨论文学的女青年,文联开笔会时结识的女文友,小镇政府的女打字员,甚至外地来的女鱼贩子,接二连三地成为他故事里的主人公,他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不问出身、老少皆宜的悲悯情怀。思源妈忙得像福尔摩斯一般,跟踪,盯梢,破案。虽然她长得人高马大,却很怕狗,偏偏小镇上家家都养狗,所以走到哪里都拎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棍子。小镇上的人看见思源妈拎着木棒在街上大步流星地走,都禁不住坏笑起来,故意逗她,大嫂子,你这急三火四地干啥去呀?思源妈妈也不含糊,大嗓门喊,俺家公牛跑丢了,正找呢,看我不骟了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骚。
三
高中时,霍思源是有名的校园诗人,他甚至还办了份校园文学小报。一学期出一期或两期,手工写的娟秀的字迹,一看就是出自孟晓之手。即便是高三时,也没有间断过,粘贴在教学楼门厅的黑板上,每期都有霍思源指点江山般的诗歌和孟晓细腻缠绵的小散文。霍思源极力鼓动我也写,可我那时对写作唯一的兴趣是怎样在考试中得高分,怎样凤头猪肚豹尾。那个时代男生女生很少交流接触,还处于上世纪最后的纯真年代。霍思源、孟晓和我三个人虽是同乡,经常坐一趟长途客车回家,可是基本上不说话,在车站遇见远远看一眼,也不打招呼,各自买票上车,到了站各回各家。冬天,到辉腾高勒时天已经黑了,我们俩会送孟晓回家,她在前面十多米的距离,我俩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胡侃海聊,一直聊到了孟晓家院门口。
看得出来,霍思源喜欢孟晓,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可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学校的小树林里抽烟,没日没夜地写诗。当然了,这些诗他不会在那个小报上发表,这些诗歌都是写给孟晓的。那年高考之后,我们都落榜了。再开学时,我们三人都回到学校重读,成了同班同学。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能考上大学的真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文科,就更难了。那一年,时光过得飞快,如今回想起来,除了学习的辛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再次高考之后,我幸运地考到了首府的师范大学,霍思源和孟晓再次落榜了,霍思源自己对父母说不再重读了。据说霍老师认真地和儿子谈了一次,问,你真的不复读了?儿子说,真的。霍老师叹了口气说,你可想好了,不是我不供你读书。
录取通知书下来后的一天,孟晓来找我,她站在我家院外不进来,在那里喊,杨小明、杨小明在家吗?我从屋里出来,来到院子外面,看见孟晓站在夏日明媚的阳光里,鼻尖上有一层细腻的汗水在闪亮,一身漂亮的裙子,墨绿色带白点,高跟鞋显得她高挑挺拔。我拘谨地问,有什么事吗?她笑了,说,没什么事就不能来看看同学了?祝贺你啊,大学生,还是本科,前途无量。我说,谢谢。她把一个纸兜递到我手上,说,我买了你爱吃的糖,大白兔奶糖,我自己的钱买的,我上班了,在粮食局,开票员,接我爸的班了,我爸说,错过这次今年就没机会接班了。她说得有些语无伦次,她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停下不说了。我说,真好,祝贺你有工作了。她望着我说,你大学毕业,还能回来吗?我说,应该不能吧,我爸说了,考上大学就不让我回来了,去大地方。孟晓笑了,说,是啊,好男儿志在四方。她把一个硬皮笔记本递到我手上,说,这个笔记本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打开看了看,娟秀的字迹写了大半本子,都是在文学小报上发表过的散文和诗歌。
那个暑假,小镇上多了一个长着酱块儿脑袋的小男孩。大约在四五年前,在辉腾河边放羊的小媳妇塔娜生了一个小男孩儿,成了那年小镇上的新闻。因为她的丈夫几年前喝多了酒,掉进辉腾河里淹死了。塔娜生了个男孩儿,满脸幸福的笑容,肉嘟嘟的胖了一圈,胸前胀鼓鼓的,衣襟都被奶水浸湿了。有好事的女人问塔娜,孩子他爸是谁啊,啥时候办喜事啊,塔娜说,当然是我丈夫啊,他看我可怜托梦给我的。
这事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过去了,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小男孩的脑袋像一件慢慢成型的雕塑品一般,日渐显露出了酱块子的轮廓。人们恍然大悟,沉寂了四五年的话题又重新捡起,添油加醋演绎一番,终于传到了思源妈的耳朵里。
思源妈拎着根棍子去河边,远远看见那个小酱块子脑袋,就喊,那小孩儿,你过来。那孩子戒备地望着思源妈手里的木棍子,思源妈就把棍子扔在地上,从衣兜里掏出两块糖。孩子就过来了,思源妈睁大了眼睛左右端详,摸摸鼻子,揪揪耳朵,小男孩被鼓捣烦了,“呸”的一口唾沫吐在思源妈的脸上,一溜烟跑了。思源妈气得大骂,抓起地上的木棍子,一口气追到辉腾河边,正遇见拎着奶桶的塔娜,思源妈说,你说,这孩子谁的?塔娜说,我的!怎么了?思源妈说,你和谁的?塔娜说,我丈夫托梦给我的。思源妈说,你糊弄傻子啊?塔娜放下奶桶,腰一叉,说,你管得着吗?你拎着棍子撵我家孩子想干啥,你动我儿子一根汗毛试试。
四
霍思源高考落榜回到辉腾高勒后,他妈在临街租了个门市房,开了一家小饭馆,让霍思源经营。早晨是奶茶包子,中午和晚上家常炒菜。可是霍思源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小饭馆都是他妈在忙乎,他每天还是不停地写诗,写小说,人在饭馆里,心思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他的诗歌都是写给孟晓的。孟晓犹豫不决,把这事跟父母说了,她说,爸妈,有男生给我写信。孟晓妈妈说,好事啊,你现在工作了,该考虑这事了,一定要找个有工作的。孟晓问,要是没工作呢?孟晓妈说,没工作有本事也行,只要不像霍思源那样就行。孟晓苦笑着说,妈,就是霍思源在追我。她爸妈惊得饭碗差点掉在地上,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行,绝对不行。她爸说,你没听镇上人说啊,姑娘们都离那小子远点,那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家伙。她妈说,就是啊,庄稼不成买卖不是,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荡,你给我趁早离他远点。哦,对了,听说派出所新来一个小伙子,我得赶紧托人问问。孟晓垂头丧气地说,我年龄还小,不想找。她妈说,那怎么行,这巴掌大的地方,好小伙子没几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霍思源的小饭店勉强开了有一年,就关门大吉了。据他妈说,把老本都搭进去了。辉腾高勒地方不大,人们都认识,有来喝酒的,喝着喝着就对霍思源说,一起喝两盅呗。霍思源真就上桌了。客人夸奖他有才华,霍思源一高兴,就又拿一瓶酒来,说,今儿敞开了喝,我请客。我怀疑他后来嗜酒如命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打下的基础。思源妈发现后,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你要是再上桌陪客人喝酒,我就整死你。
霍思源一直惧他妈三分,不敢再上桌了,可是客人们有招,喝着喝着就背起诗词来了,断断续续背不全,霍思源站在吧台后面就又热血沸腾了,跟着哇啦哇啦地朗诵,最后手一挥,豪迈地高喊一声,今儿这桌我请了……
那年大学暑假,霍思源跑来找我,拎着个脏兮兮的破面袋子,他说找我借二十元钱。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投稿。原来半面袋子都是手稿,有诗歌有小说,我望着那半袋子稿件目瞪口呆,我说你这是向文学高地发起疯狂的冲锋啊。他说,我肯定能成个大作家,你信不信。我说,我信,能不能先拿给我一两篇先睹为快啊,好歹我也是个学中文的。他冷了脸,说,你不借给我钱就算了,不能要求我违反了做人的原则。我说,我没说不借啊,扯得上做人的原则吗,写东西不就是给人家看的吗?他忽然就酸了脸,拽起破面袋子就走。
我寒假回家时,霍思源又来找我借钱了。我问他,发表几篇了?他憋了半晌,脸红脖子粗地说,哪个大作家没经历过退稿啊,不用在意。他那样说,好像被退了稿的是我一般。我跟我妈说起这事。我妈笑了,说,他那个破面袋子包裹已经被退回来好几次了,兜兜转转地把全国都跑遍了。紧接着担忧地望了望我,说,儿子你不会像他那样吧。我说,妈你放心吧,学中文的都成不了作家,都是方仲永了。我妈问,方仲永谁啊?我说,妈你快去邻居家打麻将吧,人家三缺一等你呢。
一天上午,霍思源风风火火地跑来了,眼睛里放射着狂热的光,他手里举着一张报纸,像挥舞着一面冲锋的旗帜。对我喊着,我的诗发表了。我接过那张报纸,那是一份日报的文艺副刊,我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找了半天,才看到他那首短诗,不多的几行,如今只记得“晨光爬上我的窗子,我望见窗外一群两条腿的动物”一句,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看见霍思源的作品发表。我问他得了多少稿费。他撇了撇嘴说,你可真俗,这是钱的问题吗?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坚定地自问自答。
那时小镇上刚出现出租车,不是汽车,是那种“三马子”。饭店关张后,思源妈一咬牙又给他买了一个三马子。与开小饭店时不同,这回霍思源乐颠颠地上街载客去了,其实,他主要是想去“偶遇”孟晓。孟晓那时坐在粮食局窗口后面开票,买粮的人把粮本从那小小的窗口里塞进去,孟晓就给开票,收款,在粮本上记录好,到了下班时间“啪”一声小窗口一关,真是潇洒极了。几次偶遇之后,孟晓的父母看出了端倪,就不让孟晓“搭”同学的车了。
半年后,派出所那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开始与孟晓频频约会。他骑着一辆嘉陵125摩托车,一身警服帅气极了,据说还是军官转业,腰身挺直,像一棵钻天杨。终于,孟晓小水葱一般的胳膊搂在人家的腰上了。俩人成了小镇上让人羡慕的一对儿。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读书,没有能够见证霍思源的痛苦,而且那时我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作家,处了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正是幸福浪漫的时刻。人在自己幸福的时候,是很少能关注到他人的苦痛的。大一大二时,我还和霍思源通通信,他的字还是那样像蜘蛛爬,后来就不写信了。
大四那年假期,我回辉腾高勒,我们在小镇的一家小酒馆里喝酒,很巧就是他曾经租下开小饭馆的那家,如今红火得不得了,招牌菜小笨鸡炖花脸蘑、油炸小柳根儿鱼,远近闻名。我们不咸不淡地喝酒,说着不咸不淡的话,他总是习惯地咧咧嘴,唇齿之间发出一种奇怪的咝咝声,像被烫到了一般。他说,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我激动地问,在哪儿看到的?他说,在你妈家。我说,哦。他说,上了四年大学,还是写得那么臭。我笑笑,说,本来我也不是当作家的料,写着玩。这时,老板娘热情地端来一盘酱牛肉,说,哥俩好好喝啊,这是本店敬菜。我扭头望了望老板娘充满张力的浑圆的屁股,说,你说,这同一个小饭店,换了人开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他愣了一下,脸红了,气冲冲地说,你这是报复。我说,我这是跟你学,说实话。他把酱块子脑袋往后一仰,说,我天生当不了生意人。我揶揄他说,那你天生当得了什么?他认真地看了看我,眼睛里的怒气忽然消退下去,代之茫然的水雾。他似乎是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我他妈什么也干不成。我说,别那么自轻自贱,喝酒吧。我端起酒杯,说,走一个。我们就干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他说,咱再走一个,我们就又干了一杯,没一会儿两瓶白酒见底了。霍思源摇晃着酱块子脑袋喊,老板娘,再给上瓶酒来。老板娘躲在里间不出来了。我说,咱不能再喝了,走吧。他没做声,沉默了几秒钟,忽然对我说,她……嫁人了。我愣了那么一刹那,才明白他说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跟我提起孟晓。我说,天要下雨,她要嫁人,随她去吧,这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我以为他还会说些什么,可是他开始背诵一段诗,“爱情消逝了如一江流逝的春水,爱情消逝了生命多么迂回,希望又是多么雄伟……”他朗诵得那样深情,嗓音略带沙哑,充满磁性。我说,好诗,你写的?他不屑地说,亏你还是学中文的,这是阿波利奈尔的《米拉波桥》啊。他又朗诵“爱情一去不回头,去了像是流水一样,爱情已经去了人生是多么漫长,而希望又是多么刚强……”我说,这又是谁的诗啊,意思差不多啊。他醉眼迷离地说,还是《米拉波桥》,翻译的人不一样,还有一个版本……我打断他的话,说,行了,别拽了,你这是孔乙己“茴”字的三种写法啊,哈哈哈……我一笑往后一靠,忘了小镇饭店的凳子都是没有靠背的,直接摔到了地上,后面的事就记不住了,喝断片了。
五
霍远老师是在临近退休那一年病倒的,脑梗,抢救过来后就不行了,换了一个人一般。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里,他再没有发表过什么文学作品,对女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公牛一般奔忙在各个隐秘的角落。
那年暑假我去霍思源家,发现那个在我印象中美轮美奂的书房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还是当初的那些书,一排排灰头土脸地歪在书架上,散发着霉腐的气味。我正面对着书架心生感慨,霍远老师踉踉跄跄地回来了。思源妈气乎乎地说,喝了多少猫尿啊,又上哪儿跑骚去了。大概感觉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脸上无光,霍远老师气乎乎地说,闭上你的嘴,说话要有证据,不要凭空污人清白。思源妈说,嘁,你还有清白?霍远老师进了书房,打了个酒嗝,对我和霍思源说,还是古人说得好啊,十年一觉扬州梦,青楼梦好,楚馆情深啊。思源妈说,瞅你那德行,哪像个当老师的样子。
霍远老师笑嘻嘻胡乱拽出来几本书放在我面前,说,这些……送你了。我一看,有拉丁美洲小说选之类的,《百年孤独》两三个版本的,还真是好书,那时国内加入了版权之约,已经买不到了。我还没等说什么,霍思源冲过来一把抢了回去,瞪着眼睛喊,爸你又喝多了。就是那一刻,我发现父子俩站在一起真是太像了,就像一个人在照镜子。我连打了几个喷嚏,大概是书上飞舞起的灰尘让我过敏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霍远老师时,他已经病了有大半年了。进了他家的房门,一股尿骚味儿扑面而来,地中央放一个大塑料浴盆,思源妈正像给小鸡儿褪毛似的把赤条条的霍远老师摁到浴盆里,看我們进来也毫不回避,嘴里叨咕着,快过年了,给你这老东西洗巴洗巴。霍远老师头发稀疏凌乱,肋骨瘦得像搓衣板,他眼神空洞迷茫,望着我,说,吃了吗?思源妈冲着他大吼,又犯糊涂了是不是,这不是你的学生杨小明吗?他咧开嘴,说起话来呜噜呜噜地直漏风,听不清说了什么。思源妈粗壮的大手拎起他胯下那截烂草绳一般的物件,用肥皂胡乱抹了两下,再丢回去,那截烂草绳有气无力地漂浮在浴盆里。我一阵心酸,说,我走了。他瞅了瞅我,说,哦,吃了吗?
霍远老师去世后,霍思源那辆三马子也在他一次喝大之后,撞到树上报废了,好在人没什么事。从那以后,他就再没做过什么营生,每天宿醉不醒,抽烟写诗,他投出的稿子永远都是两个结果,退稿,或者泥牛入海。那两年他在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后来报社副刊部开了一次笔会,从外地请来作家搞讲座,邀请他去参加,结果笔会的第一天晚上他就喝得酩酊大醉,举着酒杯骂那个外地来的诗人,让人家滚,说,我们呼伦贝尔没有诗人了?让你来充大尾巴鹰?以后再开笔会,没人敢请他这尊神了。
思源妈那几年天天忙着给儿子介绍对象,他连面也不见。那天,他对母亲说要去海拉尔参加一个笔会,他妈信以为真,给他带上钱,提包里装上换洗衣服,还没忘了叮嘱他“有相中的姑娘可别放过”。往回听见他妈这么说,霍思源会冷着脸不说话,而这次霍思源说,放心吧,这回不会放过,就拎着提包出门了。
中午时分,霍思源出现在了孟晓的商店里。那时粮食企业改革,孟晓买断工龄开了一家副食品商店,生意做得一年比一年好。孟晓看见霍思源,十分惊喜,哟,老同学,你可真是稀客啊,我这商店开了快两年了,也没见你来过。霍思源红着脸不作声。孟晓问,买点什么,烟还是酒,对了,你少喝点酒吧。霍思源憋了半晌,说了一句,来两桶方便面,两袋面包和火腿肠。孟晓说,哦,这是要出门啊。转身装在塑料袋里说,拿走就行,不用给钱……一回身看见霍思源瞪着一双血红的牛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呼吸又粗又重像在拉风箱。孟晓吃惊地问,你怎么了……话还没说完,霍思源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从裤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长途汽车票,低沉地吼着,你跟我走吧,跟我走吧,票都买好了。孟晓彻底蒙了,没明白啥意思。霍思源拉着孟晓的胳膊就往门外拽,孟晓挣扎着喊,你疯了……霍思源说,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流浪,去天涯海角。孟晓脸涨得通红,说,你又喝多了,醒醒吧,哎……哎,你弄疼我了,放手啊,哎——快来人啊。商店后面就是孟晓的家,已经提拔派出所副所长的孟晓丈夫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呢,听见孟晓喊,冲出来就是一顿老拳,两个人一直打到大街上,像两只顶架的公牛扭做一团,方便面、火腿肠和面包在脚下踩得稀烂。
这次广为流传的打架事件之后,霍思源就很少出门了,除了买酒之外。思源妈快要气疯了,每天在家里先是叨叨咕咕,后来就开骂,谁都骂,想起谁骂谁。有一天骂到了孟晓,骂她是修行了几百年的狐狸精……刚骂了这一句,就看见儿子从房间里蹿出来了,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条大短裤,瞪着一双红红的牛眼,冲进厨房把菜刀抄起来,思源妈吓得“妈呀”一声坐在了地上,霍思源大步流星冲出房门。他家黑白花大奶牛归来进了院子,霍思源抡起菜刀在牛脖子上咔咔连砍两刀,大奶牛疼得“哞”一声惨叫跑出了院子。
整个小镇都在传说老霍家那个酒鬼儿子中邪了,思源妈找来镇里有名的张大仙,大仙说是被老霍家祖上一个不得志的秀才给附体了,还给画了像,拖条辫子,据说也是酱块子脑袋,说你不信可以问问家族里的老人。思源妈晚上就在路口摆了供品,烧了一大堆纸钱,边烧边念叨,老祖宗啊,你怀才不遇心里憋屈,俺懂,可你找俺家思源干啥呀,霍远那个死鬼不是去陪你们了吗,赶紧走吧,别再来了。
六
那年我妈生病住院,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后,说什么也不在城里住,说是在楼房里要憋出病来,我就送她回辉腾高勒休养。听说我妈回来,思源妈拎着两大盒补品来看望,还给我拿来一袋子干蘑菇。她和我妈没说几句话,就哭了,对我妈说,她婶子啊,看你养了多好一个儿子,有出息又听话,听说都成作家了。我妈不知说什么好,思源妈哭得更厉害了,对我说,杨小明啊,你和思源打小一起长大,替我劝劝他吧,他也就听你的。你快劝劝他别写了,他也不是那块料啊,你路子广,帮他找个女人,随便啥样的,都成。
还没等我腾出时间去找霍思源,他自己来了。一年多没见面,他已经活脱脱是一个酒鬼了,大中午的还醉醺醺的,嘴里喷出难闻的酒臭味儿。他的脸色青里发灰,根本不是一个中年人正常的肤色,一双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我生气地说,大早晨就开始喝酒?他说,昨天晚上喝的。我说,你骗鬼啊。他讪讪地笑了,说,就喝了一点点。我冷着脸不理他。他说,听说你出书了,给我看看。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递给他,说,很多都是参加征文凑数的。他看了几页,明显一脸的不屑,又往后翻了翻,就把书随手往桌子上一丢,说,现在真是出书的人比读书的人还多啊,是个人就能出书。我尴尬地笑了笑,有人夸我出书时,我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谦虚一番,可是听别人说出来还真是刺耳。我说,我不是说了吗,瞎写,单位重视文化,就给出了,出之前还真想找你给看看来着,后来一忙没顾上。没想到他不为所动,依旧不依不饶地问我,你写这些有什么用啊,别人嚼过一千遍的馍,这样的书出多少都是文字垃圾。我终于忍不住了,冲着他吼了起来,你倒是出本书给我看看啊,别在这儿说风凉话了,就你写的那些文学,早就过时了,都什么年代了,你那酱块子脑袋里想什么呢,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霍思源被我整蒙了,怔怔地望着我,脸涨得通红,鼻梁上的伤疤都红得发紫了,那是一次打架后留下的印记。他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了。我母亲埋怨我说,你刺激他干啥,犯了病咋整,你给他治啊?让母亲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担心,推门出去,远远看见他往家走,酱块子脑袋一晃一晃的。
我回海拉尔后,还真通过关系,给霍思源找了个活儿。在建筑公司当材料员,名字好听,实际上就是打更护院。我兴冲冲地打电话到霍思源家,正好是他接的电话,没等我说完,他就说,这事再说吧。我说,你啥意思啊,给个痛快话。他慢悠悠地说,你这是让我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啊。我说,你他媽的爱干不干,你以为你是陶渊明啊。说完就挂了电话。
从那以后,我们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海拉尔和我一起住。这样,除了春节、清明上坟之类的,我就很少回辉腾高勒了。故乡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地方,是个出来了就回不去的地方,也是即便能回去也不再愿意回去的地方。偶尔见到辉腾高勒的人打听一下霍思源的情况,说法惊人的一致:还那样,完犊子了,天天喝,早晚得喝死。
夏天的某一天,我在百货大楼门前遇见孟晓,十分惊喜,她来上货,很忙,下午就要回去。我拉上她去吃午饭,她喝了一杯啤酒脸就红了。她说,咱们班同学就出息了你一个。我说,有啥出息不出息的,各自谋生罢了。她说,同学聚会你也不来参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啊。我说,哪有的事,总是去外地培训,赶不回去。我随口问,霍思源参加同学聚会吗?孟晓说,没有。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当初霍思源写给你的那些诗稿……还在吗?她想了想,说,早就不在了,当时还真留着,后来就不见了。孟晓忽然笑着问我,高中毕业时我给你的那个笔记本,也早就不在了吧?我说,怎么可能呢,一直在我的书箱子里保存着呢。她很感动的样子,眼圈有些发红,说,都过去了,一转眼我们都四十岁了,上学时霍远老师教咱们语文,也就咱们现在这岁数吧,那时候觉得四十岁好老啊,简直老到地老天荒了……
那天回到家,我问我妈,我那个装书的大木头箱子还在辉腾高勒老房子里吗?我妈说,早就不在了,忘了跟你说,那一箱子书让耗子嗑得稀碎,仓房又漏雨,长了一箱子蘑菇。我愣了愣神,心中一阵失落。好吧,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会永存的,晚上还要去参加一个饭局,顾不上想那么多了。
一个星期日,有人在单元门外按了门铃,我给开了门。不一会儿气喘吁吁上来一个人,手里还拎着一兜子水果,竟然是霍思源。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惊讶之余还很亲切。我说,你怎么来了。他的气色似乎好了许多,说,想你啦,来找你喝酒。我问,你怎么来的?他说,我打出租车来的。我问,来海拉尔有事?他说,我不是说了吗,找你喝酒。我有些迷糊了,从辉腾高勒到海拉尔两百多里地,打车要几百元,就为来找我喝酒?看他的样子又不像在开玩笑。我说,中午不行啊,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约了别人吃饭,你别走,晚上咱们好好喝一顿。
那天中午我约了当地一位著名的作家吃饭,请他给我的小说集写个序言,怕说了刺激他,就没详细说。他很失望地垂下了头,说,唉,是我来得不是时候,下午我要回去,晚上还有事呢。我说,那你中午跟我一起去,大家认识一下。他说,我跟你的朋友不认识喝什么酒啊,我走了。说完就腾腾地下楼了。我追出去送他,他情绪很低落地往客运站方向走。我说,这样吧,还有时间,咱们先找个地方喝几瓶啤酒。他说,不喝了。我说,那好吧,等我下次回辉腾高勒,找你喝酒。他站住了,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我看见他眼圈发红了。我叹了口气,说,兄弟,我们都四十岁的人了,说这些还有啥用。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吧。伸出一只微微颤抖的手和我握了握,转身走了。
七
清明后没几天,下班回家。我妈对我说,你霍大娘来电话了。我说,哦。我妈接着说,霍思源死了。我惊跳起来,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我妈倒是面色平静,上周吧,喝酒喝死的呗,从春节到现在,一直没命地喝,说到了中午还不见起来,你霍大娘喊他不應,推门进去一看,已经硬了。我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我妈还在念叨,你霍大娘这糟心的命啊,当初可是抡大斧子采伐的铁姑娘啊……
那年中元节,我开车回辉腾高勒给父亲上坟。我是在中元节的前一天傍晚时分进的小镇,准备第二天上坟后直接返回海拉尔。日暮时分,落日的余晖给小镇镀上了一层静谧忧伤的色彩。我开车沿着小镇唯一的一条水泥路慢慢地开,外面的世界一日千里,辉腾高勒小镇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一处熟悉的街角,一家小商店和饭馆,一棵道旁长得高了一些的松树,都能勾起少年时的记忆。中元节的傍晚,十字路口街角都跳动着摇曳的火光,那是人们在给亡人烧化纸钱,这让整条街道看起来像一条在火光中飘动的河,充满了海市蜃楼般的诡异色彩。
忽然,路旁一个熟悉的身影让我停了下来,仔细一看,正是思源妈,她几乎是跌坐在路边的道板上,林业工人的职业病让她的腿僵直得像两根粗硬的木头,黑红的脸上老泪纵横。我心中一阵难受,下了车,慢慢走到她的身边,她不看我,兀自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哭着叨咕,霍远你个老王八犊子啊,你可把我坑苦了,非得要写这写那的,有个屁用啊,没长那个弯弯嘴非得吃那个镰刀头啊,我肠子都悔青了,下辈子可不找读书的了,放牛的种地的做小买卖的,人家哪个不是活得展油活水啊……啊嗬嗬……
我鼻子一酸,说,大娘,别哭了,起来吧,当心着凉,我替你烧吧。我就把那一捆子纸钱从她手里拿过来,一张张投入火中。我说,思源啊,要知道这样,那天我就陪你好好喝一顿了,唉,你在那边好好的吧,要是有下辈子,可别去写什么诗歌小说的了,没用,都是屁用不顶的东西……
就在这时,我猛然看见一个长着酱块子脑袋的人正沿着火光晃动的街道慢慢向我走来,和霍思源长得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鼻子上没有那道伤疤。他轻轻挥舞着一根长长的柳树枝条,赶着几头牛兴致勃勃地走着,他的脸上闪烁着满足的、欢乐的、圣洁的光芒。他慢慢从我身边走过,走向远处的街道,最后拐下路面,往辉腾河边去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熊熊的火苗烧着了我手里的纸钱,烧疼了我的手,我才猛然清醒过来,赶紧把纸钱扔进火堆里。风卷起黑色的纸灰,在暮色阑珊的天空中飞旋飘动,像是在跳一支含义不明的舞蹈……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