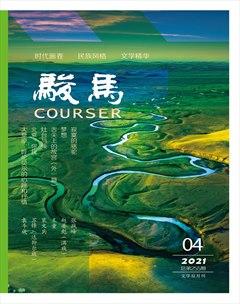寂寞的骆驼

从省城回“哈拉其盖”,要驱车三百多公里。我们已经在沙海里行驶了将近一小时。一路向西,这是唯一的公路,见不到四季变化,时光静止,朔风凛冽,逐沙而来,蓝天和黄沙分享着空旷与辽远,幽静的沙海埋藏着无数过往者的青春,荒凉的沙丘下是逆风者的足迹与灵魂。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很多年,曾经的壮志凌云,变成了豪饮风沙、汗洒戈壁的旋律,经年累月伴随着苍茫与孤独,缓缓沉寂。
回去之前,我去相了一次亲,其实我并不喜欢相亲。以前自以为长得很帅,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那种帅。可是拜“哈拉其盖”的盐碱水所赐,这几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发际线至少上移了两厘米,已经变成鸟见鸟散、花见花谢的那种帅了。现在家里对结婚这事催得很急,但是哈拉其盖的女人就像沙漠里的树,少得可怜,所以被逼无奈走上了相亲这条路。
姑娘叫马丽,城里人,比我大一岁半,老秦介绍的。老秦说:“这姑娘很善良。”在老秦的催促下,我主动和马丽联系起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仅限于微信联系,看过照片,还没有真正见过面。
今天,正好到城里出差,就鼓起勇气约了马丽。马丽选了一家俄罗斯餐厅。城里的阳光真好,照到哪里都是五颜六色的。暖暖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粉里透红,她浅浅一笑,那双含笑似语的杏眼放出了强烈电波,让我有些亢奋。而我的气质摆脱不了哈拉其盖的沙土味儿,跟马丽坐在一起,不像是相亲,更像是父女重逢。我脑子里冒出两个词“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她吃黑面包配鱼子酱的样子很优雅,此时,我突然很邪恶地想到,如果和她接吻时,她的嘴里会不会还残留着鱼子呢?我想倒一杯水,她也伸手过来倒水,我碰到了她的手,白嫩细滑富有弹性。我们同时把手缩回去,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担心她猜到了我邪恶的想法,赶紧低下了头。
马丽主动给我讲了,大三时与朋友徒步穿越沙漠遇险,被老秦救命的事。她说:“永远忘不了秦叔叔的救命之恩,永遠忘不了那身绿军装。”她觉得军人是最安全可靠的,动情之处,眼含热泪。
“秦叔叔?老秦是我的同事,那你也得管我叫叔叔!哈哈哈!”我想开个玩笑。
“你想占便宜!我比你大一岁呢,你得叫我姐!”她并没有生气。
分别的时候,她头发上的香味随风而来,慢慢地沁入我的胸腔,我可能对她有感觉了。而她赶时间,挥了挥手,匆匆而去。我明白,这与我以前的相亲一样,聊得很好,那是出于礼貌,再见之后就再也不见了。
打着补丁的公路无限延伸到天的尽头,过了前面那道沙梁,就可以看到562号界碑,界碑上的国徽和“中国”两个字特别醒目。每次路过,我们心中都充满自豪,会下车庄严致敬,这是习惯,也是仪式。
其实,这里没有大漠孤烟,也没有长河落日,公路上除了我们,看不到移动的东西。我们像赛车手一样躲避着公路上的坑洼,车身随着路面起伏,车轮摩擦地面发出震耳响声,感觉整个身体都要颠散架了。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海外面的戈壁滩,此时我们已经看到距哈拉其盖38公里的路牌,那是一个标志,过了那里就穿过沙海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起。“喂,快到了吧?吃点汤面啊!”
“老秦打来的?我还真有点饿了。你说,没有老秦,咱们是不是都得饿死?”青格乐点了支烟,边说边抽。
“老秦要是转业走了,我肯定得饿死!但你不会饿死,你是有老婆的人!”
“滚蛋!你就是忌妒我!有老婆就是好,气死你!哈哈哈!”青格乐故意逗我。
“你有老婆又咋样,还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你就是半条光棍!”
“半条光棍也比你那条烧火棍强!对了,你跟那姑娘见面聊得怎么样?”青格乐主动问起我相亲的事。八字还没一撇,我不想说太多,就随便应付了几句。跟马丽见面时的一些非分之想,更不敢跟青格乐说,如果他知道了,就相当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看来有戏!”他一脸坏笑地说。
“应该没戏。那姑娘各方面都很优秀,长得又好看,不可能嫁给一个沙漠里的边防警察,除非脑子进水了。”
“边防警察怎么了?没有边防警察,哪有国家安宁?如果能嫁给边防警察,那是一种荣耀,她应该骄傲自豪。”青格乐还挺把自己当回事。
以前,我看别人穿军装觉得特别帅,自己真正穿上以后,才知道背后的苦和累。天真地认为,大学生来基层锻炼几年,很快就可以回到城里,可撞进来就出不去了。孤独和寂寞常常让我恐惧,我太想回到城里了,我不想一辈子都陷在这堆沙子里拔不出来。我可没有老秦的觉悟,如果让我一辈子待在这里,我会憋死的,我只想早点离开哈拉其盖,找个老婆,平平淡淡地生孩子,过日子,照顾父母,可是想离开这里谈何容易。
哈拉其盖生产寂寞,也盛产艰苦。我们刚分到哈拉其盖派出所不久,青格乐的未婚妻就追到了哈拉其盖,生米煮成熟饭的那天夜里,我搬到了老秦的屋里。我几次偷偷地掀开窗帘看对面的房间,他们居然整晚都不关灯,我脑海里出现了他俩战斗的场面,内心有点失落。
我经常跑到沙梁上吼几声,排解心里的压抑,我给这种吼起了一个名字——“吼沙”。说来也怪,好几次竟然把巴特儿的骆驼吼来了。它的眼睛似乎有魔力,跟它对视不了多久,心里就平静下来,不自觉得放慢节奏、放平心态。这种情绪是阶段性的,如果能多办几个大案,再立个功,那种压抑就会变成愉悦。
这几个月,追逃围堵越境人员的任务特别重,每个星期都是连轴转,现在浑身没劲儿,身体像被抽空了,经常感觉脚下踩着棉花。我开着车,突然困意泛活,我的眼皮像两片磁铁,拼命地往一起粘。这时,一辆货车出现在公路上,突然在不远处停下来,片刻之后加足马力仿佛要起飞,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那一瞬间,我的脑袋是空白的,甚至是麻木的。那夺命的会车,形成一股强劲的风,把我的脸都吹变形了。我猛打方向盘,来不及回转,直接扎进了路边的沙子里。
车停下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困意全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青格乐被我的急刹车惊到了,粗鲁地把我从车里拽出来,自己坐到驾驶位上。青格乐个子不高,很敦实,明显上身长而下身短,别看他腿短,但他跑得很快,而且劲儿特别大,他刚才差点把我胳膊拽脱臼。
“妈的,怎么开车的!这是要命呢!”我快被气炸了。
“不对劲儿!这车有问题!我好像看到羚羊角了!”青格乐警觉地说。
还没有回过神的我和青格乐对视了一下。“是吗?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警车才跑的?”
“追!”青格乐把油门踩到了底,他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我赶紧跟所里报告情况。
“喂?老秦啊,是你值班吗?有个情况跟所里报一下。我们现在在38公里这儿,遇到一辆可疑的货车,现在我和青格乐要追上去看看。具体情况一会儿再说。”
“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他们有武器。保持距离,不要追得太紧。如果察觉有危险,立即申请支援。实在不行先放过去,让其他卡点堵他们。”老秦交待得很细。
货车开得飞快,我们一直在追,眼前尘土飞扬,荡起一层层沙砾。货车突然冲下公路,朝无路的戈壁奔去。青格乐毫不犹豫地跟上去。我们的车剧烈颠簸,如同在海上飞驰的快艇,我能感觉到脸上的肉在猛烈抖动,五脏六腑都在移位,我紧紧地拉着车门上的把手,有好几次我都要吐出来了。眼看就要追上货车了,结果它又停下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下车盘问了。
突然,青格乐说:“别动!”
话音未落,货车加速倒车,直接向我们冲过来。青格乐极速转向,货车如恶狼般紧逼不放,转着圈撞向我们,四周尘土漫天翻滚,我们都看不到路了。货车趁机撞向我们,一阵剧烈的撞击,我整个人都晕了。货车又转到青格乐那一侧,继续撞过来,尽管气囊弹出来,青格乐的额头还是被划开一道口子,血瞬间流出,我们的车停下了。货车以胜利的姿态,扬长而去。
我们眼睁睁看着货车逃走,肺都气炸了,真是胆大妄为,居然连警车都敢撞,简直就是亡命徒。青格乐两眼冒火,挣扎着要继续追,可是车已经走不了,还怎么追。
“老秦,那辆货车把我们的车撞坏了,往巴音浩勒方向跑了。青格乐受了点伤,我们现在追不上了,你把情况通报给那边的派出所吧。”
没能追上那辆车,真是窝囊。我和青格乐一路上都不说话。俩人的情绪如同这辆车一样,引擎盖向上翘起,“哒哒哒”拍打着,水箱一直冒着气,心情真是坏透了。就这样,我们开着这辆破烂的警车颠簸向前,离哈拉其盖越来越近,我看见远处的沙丘上,一个身形佝偻的男人,牵着一头骆驼,从一棵胡杨树旁走过,斜阳孤影,融入沙海深处。这个男人是个退伍兵,叫巴特儿,不太会说汉语,现在是一名义务巡边员,巡了半辈子边境线,无妻、无后、无家,与骆驼和马相依为命。那背影仿佛是父亲接儿子放学的一幕,让我想起了孤独生活的父亲,有一年多没见他了,心里涌起一些酸楚。
我和青格乐回到派出所时,已经接近傍晚。我们刚停好车,老秦从蔬菜大棚里出来,一只手端着三个拳头大的西红柿,另一只手抓着两根黄瓜、一把小葱。他个子很高很挺拔,皮肤黝黑,膀厚肩宽,头小脸方,脑门上的褶皱一层一层盘旋到发际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云贵高原的梯田。他的衣袖卷得很高,露出粗壮的手臂,青色的血管野蛮地爬行在干涩的皮肤下面。裤腿卷到了膝盖,露出突兀的小腿肌肉。他头顶快秃了,还留着几根稀疏的头发,孤单地被风吹起。看见我们平安回来,他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原本他的眼睛就很小,常年被风沙侵蚀,被烈日暴晒,一笑连眼珠子都看不到了。
“安全回来就好!别垂头巴拉的,今天逮不住,明天他们也跑不了,我已经通报给巴音浩勒了。今晚给你们吃西红柿鸡蛋面,我刚炒了点肉酱,可以蘸着酱吃黄瓜和葱。”老秦是宁夏人,他的口音,一听就有黄河水的味道,浑厚沙哑,像牛在沉吟。
老秦做的面真好吃,好吃到在整个哈拉其盖没有对手。饭桌上,大家聊起了转业的事。老秦是所里最老的干部,他已经超龄,实际上最有资格、最有把握转业的就是他了,按政策他早就该转业了。今年老秦也确实想转业。我们都很矛盾,如果按资历排队,老秦肯定排第一,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小九九,都想争取先走。
老秦是个好人,本事很多,不仅抓偷越境的人有一套方法,他还会做饭,能给人看病,我们都很依赖他。关于转业的名额,他已经让了好几年了,大家嘴上不说,心想都希望他再让一次,可是看样子他今年是不准备让了。上个月,他已经偷偷地收拾东西了。去年,老秦被评为“全国戍边模范”,这是上级对他的肯定,他激动得老泪纵横,那泪水里说不清是自豪,还是委屈,只能说甘苦自知。
吃完晚饭,我和老秦坐在台阶上抽烟。老秦一直没说话。
“怎么,有什么心事吗?”我能感觉到老秦情绪的波动。
“没什么!今年不转业了。明年再说吧。”老秦深吸了一口烟,语气里有些无奈。
“为什么?”
“副所长的母亲得了癌症,他想转业回去照顾。”老秦沉默了一会儿,小声说。
“哦,你想把名额让出来?有没有跟嫂子商量一下?”我知道就算老秦让出来,也不会轮到我,只是替他可惜。
“不用商量,我说了算。大不了晚一年回家,二十几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一年。”他说得很牵强。
说实话,派出所的条件太艰苦了,没人愿意留下来,很多人待不了一年就申请调回城里,调动不成就想办法转业。有的年轻人转业不成就复员,连干部身份都不要了。老秦是老典型,人们并不在意的“奉献精神”,在他看来似乎特别重要。
夜里,老秦睡不着,在屋外抽了很多烟。外面的温度很低,他裹紧棉大衣,踱来踱去,在地上走出了两行挣扎。第二天,他找教导员把转业申请撤了回来。今年的转业办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副所长的转业命令就到了。
副所长走的那天,我们喝了一次大酒,算是给他饯行。老秦酒量大,一直很清醒。副所长喝得连哭带笑的,抱住老秦整整哭了一晚上。其实,我也哭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心情很复杂,是羡慕副所长获得自由,还是感慨老秦的無私,终究还是说不清楚。
上面的机构改革说来就来,推进速度太快了。我们都始料未及。所有的人事关系全部冻结,这也就意味着老秦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转业了。老秦表面上很平静,可他却反复地说:“看来得干到退休了!”
“你是不是后悔了?”我知道老秦心里不好受,但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没什么后悔的。我十五岁就成了孤儿,最早在云南当兵,缉过毒,受过伤,立了一等功,破格提干,后来又被送到军医院学习,我的一切都是组织给的。说小点是哈拉其盖需要我,说大点是国家需要我,人得懂得感恩,不能说走就走!反正部队工资高,钱全寄回去了,家里娃娃也大了,婆姨也好着呢,还在村里盖起了小楼房,没什么要操心的。主要是,我从小没爹没娘,真羡慕别人能侍奉老娘!咱们这些人亏欠家人的太多了,副所长还有机会照顾老娘,就赶紧照顾吧,别等人没了再后悔。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老秦的眼泪在打转。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脱口而出。
“对对对,还是你有文化!”
在老秦面前,我觉得很惭愧。他就像巴特儿的那头骆驼,一直守着这片沙漠。他每天走着相同的路,做着雷同的事,在枯燥和寂寞中咀嚼着生命的韵味,柔情中蕴含着韧性,知足而平静,平凡而渺小,仿佛夜空中的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无法照亮整个夜空,却努力照亮他的四周。望其项背,我永远也达不到他的境界。
凌晨的时候,我们正睡得酣畅。巴特儿火急火燎地冲进来,汉语说得本来就很生硬,一着急夹了一大堆蒙语,青格乐赶紧给翻译。原来,巴特儿家的马生不出小马驹,快憋死了。巴特儿无助地望着老秦,不停地给老秦双手作揖。老秦说:“好多年没干这营生了,手生了,试试吧!”于是,老秦赶紧穿戴好,从柜子里包了几件手术工具,跳上巴特儿的摩托,就冲进了夜的深处。
正是春寒的时候,冰冷的风在夜的裹挟中,将路边的一株株骆驼刺吹得“嗖嗖”响。飞驰的摩托车,激怒了暴戾的风,无情地切割着老秦的脸,刺入他的身体。天空中一道流星划过,点亮了浩瀚的黑暗,伴着满天的星辰陨落。
巴特儿说:“流星是好兆头!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老秦说:“放心,肯定能给你带来好运!”
中午的时候,巴特儿骑摩托送老秦回来了,还带来半只羊。老秦说,巴特儿请大伙吃羊肉。晚上,老秦给大伙炖了一大锅肉,香味飘得很远,隔着好几间屋都能闻到。我已经忍不住了,偷偷站在灶台边,口水在嘴角酝酿着,但我控制住了,没让口水流出来。老秦揭开锅盖,夹了一小块给我。
“尝一下,咬得动吗?”
“烫!烫!烫!”我赶紧用手从嘴边掏出那块肉,吹了又吹,又放进嘴里。这是一个很知足的晚上,大家吃得很过瘾。
吃完肉,我和老秦坐着抽烟。青格乐躲到角落里跟老婆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戏精”上身,立刻从公牛变成羊羔子,好像要找奶吃一样,哼哼唧唧,肥腻得很,真没想到一个膀大腰圆的爷们儿居然会撒娇。隔着门都能听到,肉麻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此时,我心中也泛起了涟漪,不由地拿起手机,拨通了马丽的电话,本来我是想问她上次见面后,对我的印象如何,可实在开不了口。只好没话找话说:“我们今天吃羊肉了,老秦做的,可香了,我都吃得走不动了!”
马丽问:“有什么事吗?”
她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难道她就不能问一下,我对她的印象怎么样吗?如果她问了,我就好顺着她的话往下说了。比如,我对你印象挺好的,如果你没什么意见,咱们可以先处一处。可是,她现在似乎看出了我的套路,假装听不懂我的意思,吊着我的胃口,真让人挠心挠肺。
“嗯……嗯……嗯,咱俩上次见面,不知道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主动说出想说的话。
马丽说:“挺好的,我挺喜欢跟你聊天的。不过相隔太远,见不到面是个很大的问题。”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清不楚的,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和我聊天?这两个意思可不一样。如果是“喜欢我”,那就是说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是“喜欢和我聊天”,那就是在敷衍我。
“如果你没什么事,我先挂了,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下。”她的语速很慢,但每个字都像提前准备好的钉子,一枚枚钉到了我的心脏上。
挂了马丽的电话,这一晚上,我辗转反侧,真想知道马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小样儿,一个大龄剩女,还故意拿捏我!后半夜,我想通了,老子不尿她,看她什么时候能嫁出去!
戈壁滩的早上,静美如画。刮了一夜的风,沙丘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阳光洒在沙丘上,金光灿灿。几株孤独的骆驼刺,根及深处滋养着顽强的生命。我盯着派出所院墙上那句话,默读了好几遍:“缺水不缺精神!”可什么是精神呢?我一直没明白。
我们正吃着早点,巴特儿就来报警。他看到了562号界碑处,有很多陌生人的脚印。这段日子,越境者确实特别多。所长带着我、青格乐、老秦、巴特儿,一起赶到562号界碑。越境者跟“狐狸”一样狡猾,白天不动,晚上才出来。我们得先潜伏下来,晚上出击。春天的风沙很猛,能将地上的小石子吹上天,打在脸上特别疼。我们躲在几株沙柳后边,青格乐像糖炒栗子一样翻来翻去,真烦人。
这帮“狐狸”反侦察能力很强,我们伏了一天,结果他们更换了越境地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重新部署了战术,开始悄悄移动设伏,不能让他们发现。第二天晚上,我们把设伏点移到了界碑西端,等待的过程特别漫长。青格乐要抽烟,老秦一把抓住他的手,小声说:“千万可不敢抽,这是晚上,你一抽就暴露了,那咱们今天白等了!你又不是新人,这点规矩都忘了!”老秦的话还没说完,我们的前方突然闪起一道白光。所长小声说:“是手电筒!”大家一下就激动起来,大鱼终于出现了,我已经开始预热了。
可是我们等了很久,也没有人出现。所长带我们猫着腰,悄悄移动过去,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几行脚印和吃剩的东西。
巴特儿说:“我敢肯定是越境的。”
所长说:“这些家伙去哪儿了?”
老秦说:“黑天半夜,他们不熟悉路,肯定会用手电,还是要找光。”
我们再一次潜伏下来,等待光的出现。果然,还是老秦有经验,没过多久,我们的四点钟方向出现了晃动的光。我跃跃欲试地要奔过去立头功。所长一把拉住我,让我先别乱动,他指挥我们分两路包抄。于是我们寻着光的方向去找,還真找到了几串脚印,顺着脚印一直找到了凌晨,终于找到了那几只狡猾的“狐狸”,不过有一个已经渴死了,还是个年轻的姑娘,那么小,真可怜。这几个人大概已经走不动了,根本没有反抗,束手就擒。押回所里后,给他们吃饱喝足了,就准备移交到支队去。
所长派我和青格乐、老秦,一起去支队移交。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天黑前我们要赶到城里,一刻也没敢耽搁。不成想,我们在半路上遇到沙尘暴。眨眼的工夫,一面黑幕从天到地,慢慢地移动过来,眼见天越来越昏暗,如同张开口的袋子,把天地都装了进去。车的四周就变成灰蒙蒙的,风像打嗝似的一阵阵翻滚。黑幕一点点逼近,瞬间如同夜晚。我感到越来越局促气紧,越来越不能呼吸。地上的碎砂石被狂风吹起,密集时如倾盆大雨落下,胡乱地拍打在车窗玻璃上。这么大的沙尘,也许我们会死在这里,我眼睛都不敢睁,赶紧弯下腰,把头缩进衣服里,死死地握住安全带,车身剧烈地摇摆着,车慢慢偏移,滑到了路基下面,幸好没被掀翻。谢天谢地,我还活着!回头看看,车上那四个越境者都在车上,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这场风沙太大了,把路都盖住了。此时,我们躲在汽车里不敢动,很快就被弥散的土腥味盖住了。我觉得鼻子干痒,毛细血管正一点一点地裂开,嘴里都是沙子,嘴唇也裂開了,难受得要命。青格乐将大衣的领子立起来,把脖子缩进军大衣里,挡着嘴和鼻孔,只露一双眼睛,像一只乌龟,看着他滑稽的样子,我却笑不出来,其实我比他还紧张。
“怎么没有发布气象预报呢?早知道有沙尘,就应该再早点出发了。”老秦嘀咕着。
这沙尘暴像个坏脾气的孩子,脾气说来就来,带着飞沙走石,没完没了地哭,你能看到它的存在,却没办法形容它的样子。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只能判断亮的地方是天,暗的地方是地。我实在憋得慌,只是把车窗打开了一指宽的缝隙,听得见漫天沙尘游走的声音。
青格乐说:“兄弟,快关上,沙子都进来了!”
的确,这个时候开窗就等于吃沙子。关了窗,闭上眼,等着这场沙尘暴的尾巴过去。这风沙的声音好像孤狼的哀嚎,真够吓人的。漫长的等待真是一种煎熬,好在沙尘暴越来越小,透过落满浮尘的挡风玻璃,终于看到天色亮了起来。沙尘暴慢慢过去了,天地恢复了平静,空气依然是浑浊的。车还陷在沙子里,我们拼命地挖,车还是开不出来。
青格乐说:“看来,得把车上那四个人叫下来,搭把手!”
老秦说:“算了,万一他们跑了,那麻烦可大了!”
我说:“没事,他们往哪跑?再跑也跑不出这戈壁沙海。”
老秦没有再反对。青格乐用蒙语跟那四个人说,要老实点。
人多就是力量大,一下就把车从沙窝子里抬出来了。
青格乐刚上车,准备打火。一只最小的“狐狸”趁我们不注意,居然戴着手铐跑了。这小子跑得真快,在沙地里都能跑起来,一转眼已经上了沙梁,马上就翻下沙梁了,如果让他翻过梁,就看不见了。青格乐一直用蒙语喊:“别跑,再跑开枪了!”青格乐的枪已经掏出来了。
老秦赶紧按住了青格乐:“千万别开枪,还是小孩子呢,我去追!”
我还没反应过来,老秦已经追出去了。我和青格乐赶紧把剩下的三个关进车里。青格乐想跟老秦去追那小子。我不敢让他去追,我一个人可看不住三个人。
“放心,老秦肯定能把那小子逮回来!”我心想,别看老秦平时是个厨子,那可是抓过毒犯的英雄,抓个小孩子,易如反掌。
青格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两头为难。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老秦押着那个小孩出现在沙梁上了。
“快看,我就说了老秦宝刀不老哇!缉毒英雄抓个偷越境的小孩,还不是跟抓小鸡似的。”我远远地向老秦挥着手。青格乐的表情这才放松下来。
虽然沙尘暴停了,但风还是有点大,老秦押着那小孩低头迎风往回走,衣服被风吹开了,像两面旗子在招展。从老秦手中接过小孩,我赶紧把他关进车里。
一阵风把老秦的帽子吹走了,他的头发像火苗一样直往上蹿,他赶紧去追,眼看要抓到了,不知道怎么停住了,不再追了,帽子越吹越远。
“老秦,怎么不追了!”我大声喊。老秦不应,慢慢地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
“看把老秦累的,还宝刀不老呢,我去扶一下!”青格乐赶紧跑过去,刚走到老秦跟前,他就声嘶力竭地喊:“快过来,老秦不行了!”
我分明清清楚楚听到“老秦不行了”,可是我不敢相信,我拼命冲过去,我边喊边哭,声音都在颤抖:“老秦,老秦,醒醒,这里太冷,我带你回去睡!”老秦不应我。“快帮我扶上来!我要背他回去!”我向青格乐大声喊到。
青格乐说:“不能背,快把衣服脱下来,兜住他的身体抬到车上,直接去县医院!”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青格乐说什么我就照做。真是辆破车,我拼命加油,车速还是那么慢,二十来公里的路仿佛是一条天路,走得很艰难。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求求老天爷,快点给让出一条路,这是在救命啊!”
“老秦!老秦!”青格乐不停地呼唤。
“老秦,快醒醒,马上就要发警服了,你可是第一代移民警察啊!”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哭声穿透了阴云。车上那四个“狐狸”吓得不敢吱声,那个小孩突然嚎啕大哭。
老秦走了,没能穿上曾经渴望的新警服,当然也看不到新警服上面的三个字“移民局”。
老秦并不老,再过一个月才满四十三岁,人生短暂,他竟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留下。他救过那么多人,但我们却拼尽全力也没能把他救回来。他啰啰嗦嗦开导我安心工作的话,言犹在耳,此时回想起来,每一句都是那么真诚而温暖。他总是把好的东西留给战友,我们每个人都欠他的,是谁这么狠心非要把他带走!都怪我,车开得太慢!如果我开得再快点,老秦就有救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已经不属于我了。
我帮老秦整理遗物的时候,打开了他的笔记本,里面的字写得很大,虽然不好看,但很工整。其中一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荣誉却给了我一个人,我要更加努力工作。”这让我很羞愧。老秦虽然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却越来越伟岸。哈拉其盖来来往往换了这么多人,我没办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直留在哈拉其盖,是靠什么熬过来的。
合上了笔记本,我发了一条短信给马丽,告诉她老秦牺牲的事。马丽回过电话来,哭得泣不成声,她说一定要来送送老秦。
老秦是烈士,他的追悼会很隆重,北京的领导都专程来送他。这片平凡寂寞的戈壁沙海,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很多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送他上路。当嫂子见到冷冰冰的老秦时,突然给了老秦一巴掌,眼泪瞬间倾泻下来,只有眼泪没有哭声。过了好久,她才哭出声:“哎呀呀,老东西,你是咋狠下心的,丢下我和孩子这么多年不管,说走就走了,等你等了二十几年,你就连句话也不留,你可真狠心呀……”嫂子哭得晕过去了,人们掐了人中,她才醒过来,醒过来继续哭。
马丽来了,她给静静躺在那里的恩人磕了三个头,眼睛红肿,泪如泉涌。门口,突然有人撕声裂肺地喊了句:“老秦一路走好!”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副所长回来了。哀乐低回,哭声悲泣,安静的灵堂被副所长的喊声震醒,大家一起喊:“老秦走好!”哭喊声此起彼伏。如果有一天,我像老秦一样留在了哈拉其盖,能做到老秦的一半,我觉得这辈子也值了。
送走了老秦,我的心情始终无法平复,有一种错觉,老秦还在身边。回到派出所,院子静得令人窒息,门口的木凳拉长了时间的流动,厨房里没有一点烟火气,宿舍门口挂着一件衬衣随风摇曳。推开房门,再也听不到老秦的声音,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我真不愿意走进去。
身后有脚步声,我回头一看,马丽站在院子中间。
她说:“回省城前,我想看看秦叔叔工作过的地方。”
我迎马丽进屋,阳光照进来,窗帘很薄,像她的皮肤一样,透着光。白色书桌上的油漆已经脱落,烟灰缸里还存着陈旧的烟蒂,裹满茶渍的杯子仿佛腾起氤氲。马丽坐在书桌前,翻阅着老秦看过的书。我们彼此都不说话。我想打破尴尬,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她没有接,而是把手放到了我的手背上,温暖而柔软。我们相视微笑。
我望着窗外,白墙、蓝顶、黄沙,红色的大理石旗台,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我眼中充满了色彩。我看到不远处的沙梁上,巴特儿的骆驼正望着我。
责任编辑 乌尼德
张战峰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全国移民管理文联文学专委会理事,广东省小小说学会理事,佛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发表《寻找光明》《等风来》《坡上开满油菜花》等多部短篇小说,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