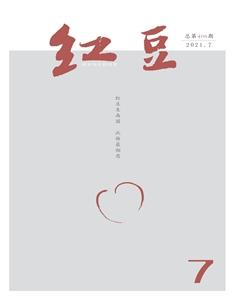李方微篇小说二题
李方
空酒瓶
石头是朋友但不是酒友,他是博物馆下属石刻馆的负责人。不喝酒的石头,就把博物馆的老闫介绍给我,以便我们在街头小馆闲坐的时候,有个人陪我喝酒。老闫当时也就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虽然做着副馆长,却一点架子也没有。大夏天的坐在博物馆隔壁的马师羊羔肉馆,老闫在油渍麻花的桌子前解开衬衫的扣子,露出贴身的破了两个小洞的背心,直嚷着热。
一大盘子热气腾腾的羊羔肉端上来,老闫直接上手,烫得嘴里呼噜噜的,手不停地把几块羊羔肉悉数撕开:“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吃,趁热吃!”一大口肉,一片洋葱头,吃得三个人满头都是热汗,两手、满嘴都油腻湿滑。
喝酒,老闫是用碗来喝的,当然也不是多么大的碗,还没到梁山好汉那样豪迈的地步。倒满酒,端起来一扬脖子,喝干了,赞叹一声:“好酒!”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作家,你随意啊。”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闫。
李白斗酒诗百篇,那只是个传说,但我怎么着也不能丢作家的脸呐,仰脖子一碗下肚。
老闫欢喜地用油手拍我的大腿:“痛快!你这个兄弟我认了,以后喝酒,没谁都行,没有你,不中!石头,你记好,以后就找李作家喝酒。”
自那以后,我隔三岔五就要和老闫大喝一回。赌博是越赌越穷,喝酒倒是越喝越有。
春节后上班,打电话老闫不接,联系石头让他约老闫。石头说:“喝什么呀。老闫喝出了心脏病,连年都没过成,到西安‘搭桥去了。”
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喝酒如果有谁出了问题,在场的人都有连带责任。所以老闫心脏搭桥手术回来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探望,对着老闫瘦小愁苦的老婆说:“以后再也不约老闫喝酒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老嫂子这里也交代不过去。”
没想到老嫂子端过来一杯茶,说:“你们不约老闫,老闫约你们啊!”
老闫哈哈大笑:“谁了解我?老婆。老婆一辈子没工作,全靠我养活,但是她大权在握,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唯独喝酒给我自由。”
好容易熬过去三个月,老闫喊着叫着要喝酒。一上桌我们还没有说一句劝诫的话,老闫掏出几张纸,一人一份,拍到我们手里:“你们看看,这是生死状。上面都写清楚了,喝酒是我自愿的,就是喝死也与在场的兄弟们无关。老婆子都签了字的。”
我说:“闫老兄,你这是何苦?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老婆、孩子好好活着呀。”
老闫倒满酒,依然是一碗,说:“兄弟,你是不是不高兴?”
“我是不高兴,而且是相当不高兴。”
老闫放下酒碗,脸色凝重地说:“兄弟,这么跟你说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爱好,各自的命运。有人爱钱,为了金钱啥事都能干出来。我就好这一口酒,你不让我喝酒,就是成心不让我快乐。老婆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这个道理她是特别明白。儿子都上大学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不可能照应得了他一辈子。不偷不抢,用自己的工资喝两口小酒,这是最大的快乐。我常说宁叫袜子脱了底也别端个空酒杯。我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也还是有责任、有担当,但命运……”老闫直接将酒灌了下去,“我抗争过了,也妥协过了,所以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也静养了三个多月,现在我还想抗争一下。你如果还有啥想法,今天喝过,咱们的兄弟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中不中?”
我端起酒碗,站起来和老闫碰了,脖子一仰成了俩空碗。
秋风渐起,黄叶满地的时候,石头打电话说:“老闫走了,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吧。”
也没有准备什么丧仪,提了两瓶珍藏多年的茅台。其实很快,老闫就到了七尺二寸深的黄土里,再也看不到了。众人走后,我和石头留下来,将一瓶酒打开,绕着老闫的坟堆洒了一圈。然后坐在墓碑前,打开另一瓶,你一口,我一口,轮换着喝,直到喝干。第一次喝酒的石头,竟然没醉。
两个空酒瓶,端直地立在墓碑前。
吴裕泰里的刘小姐
旧城区通向新市区的路是康宁路。原来没有路,是把凤凰岭拦腰挖断新辟的。在路的上方架设了一条灯火辉煌的彩虹桥,在彩虹桥靠近旧城的一侧路南,是太阳城的房产,沿路的商业旺铺中,吴裕泰连锁店特别显眼。
百年老店吴裕泰是经营茶叶的,现在的连锁店,却是吃饭、喝茶混搭。
我惨淡经营文字多年,浪得虚名已久。今天是足浴城老板的同学刘祥生请客,要我给各个包间起名以招揽顧客。在等人时,有个不年轻的服务员,两次来清理茶桌。第一次我觉得眼熟,第二次我认真看了确定是她,就装做去上洗手间,在雅间外面轻轻唤了她一声。她果然是三十年前蔬菜店里的小刘。
蔬菜店是商业系统开的,门面很小。蔬菜都是一些大路菜,品种单一,里面有好几个营业员,大都是一副对顾客爱理不理的样子。
“这小白菜蔫得连一点水分都没有了,还跟早上一个价?”
“嫩得出水的那是小刘,你买得起?”营业员说。
顾客朝店里伸头一看,小刘竟然没有在。
小刘在,那当然一切都好说。谁都愿意在小刘面前多待一会儿,但谁也不愿意被小刘挖苦一顿,或者让小刘瞪一眼。
蔬菜店窗户外并不全都是等着买菜的顾客。比如我们这些中专学校将要毕业的三年级学生,更多的是一些在家里等待就业的青年,只要有时间就会跑到蔬菜店里去看小刘。
我们去蔬菜店的路上,打赌是必须的。一方说今天小刘肯定在,另一方就说她肯定没上班。如果小刘没上班,大家就会觉得很遗憾、很伤感。更怪的是打赌内容:今天小刘肯定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衣外面,或者衬衣的领子肯定在外衣里面。输的一方要出钱为赢的一方每人买一个西红柿,有时候是一根黄瓜。
小刘有两件的确良衬衣,一件白色的,纽扣是黑色的;另一件是粉红色的,却钉着形状很别致的蓝色纽扣。小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的情况多一些。
那时候刘祥生就是个比较新潮的人,戴着一顶解放帽。他也常去蔬菜店里看小刘,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蔬菜店里的小刘对别人不买菜而专看她已经显得很平静了,所以低声对刘祥生说:“你是不是该上课了?”
刘祥生才脸红脖子粗地喘着气跑到教室门外喊报告。老师语调沉稳地问:“干啥到现在才来?”刘祥生擦着汗说:“睡着了。”老师情绪激动地说:“你别再装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到蔬菜店里看小刘去了?”一下子笑得满教室的桌椅板凳都跳了起来。
我与吴裕泰里的刘小姐并没有谈论很久。我心情和语调都很激动地说了她当年在蔬菜店里的情形。她只是隐约地记得我而已,平静地拧着手里的毛巾,说后来商业系统散了,她买断了工龄,曾经在商城摆了很长时间的地摊,再后来丈夫卷了钱跟另一个女人跑了。
那天的饭吃得并不愉快。刘祥生晃动着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光芒刺射着我脑海里的刘小姐。他要我选古今中外二十四位美女来命名二十四间包厢,我斜着眼睛对他说:“你就不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你为什么不按二十四节气来命名呢?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自然的规律,也对应着人体上的诸多穴位。在每个节气里按摩不同的穴位,人的身体才会和自然相和谐。美女和你的生意有什么关系?”他恍然大悟,说:“高,实在是高!必须敬酒。”
我没喝酒,也没告诉刘祥生那个搞保洁的就是当初他“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的小刘。
从吴裕泰走出来后,我感觉我走过了自己的三十年,也走过了蔬菜店里小刘的三十年,但没有再看见吴裕泰里的刘小姐。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