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康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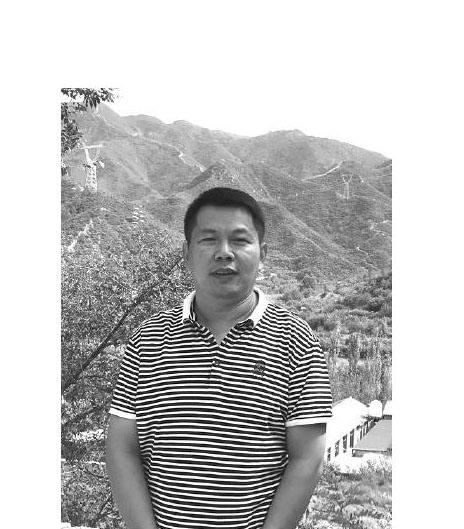

刘勇,安徽省作家协会、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见《阳光》《小说月刊》等。多次荣获省“金穗文学奖”“政府文艺奖”。出版小说集《折子戏》《能不能陪我跳支舞》等8部。
一
消杀车终于改好了。傍晚,在水池旁,谭梦奎一边用粗肥皂加洗衣粉恨着劲搓手上黑黑的油污,一边兴奋地抹了抹嘴和我说。就见他手上油污变成黑水卷着泡沫欢快地向下水口奔去。他嘴唇上的灰块儿,在毛茸茸的小胡子上,欢快地蹦跶。
我白了他一眼。心想,改好了就改好了呗,至于兴奋成这样吗?又不是第一次干这活。你不知道,明天我们上午去试车。谭梦奎两眼冒出春暖花开的样子,咧着嘴说。试车有必要这样激动吗?我脱下工作服后,也把手伸到水龙头下。
早上的起床号还没响,谭梦奎就起来了,他蹑手蹑脚地想不发出声,尽管小心翼翼的,还是冷不丁地发出声响。整得我困劲全无,躺在床上想昨晚上看的小说《红高粱》,文中采用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倒是很新鲜。在军营里读小说纯属一个乐趣,消磨时间占大多数,其他别无旁念。
谭梦奎小声说,起来吧。我先去车间看看,捯饬捯饬。饭后,我们就能出发了。
一直以来,没见谭梦奎这样兴奋过。他来修理班之前,是在汽车班,不知啥原因,用管钳把一个老兵给搂住院了。差点儿被开除,小轿车自然开不上了,背个处分,就到修理班了。来到班里,压根没见他笑过,每天都是阴沉着脸耷拉着眼皮,一幅苦大仇深的表情,谁也不愿搭理他。因为在宿舍他和我临床,时不时唠上几句。人就这样,你敞开大门,自然会有客人来。我们就熟了,话自然要多些。
谭梦奎是四川人,初中刚毕业,就报名参军入伍,到部队后就对解放车着了迷,新兵连还没结束呢,他就递交申请书,要求到汽车连学习。不知啥原因,没去成,分到勤务队站岗去了。他不灰心,接着写申请,还买来汽车维修的书像模像样地看。读得有些痴迷,政委好几次查岗,都站在他身边好半天了,他竟然不知道身边有人。这警惕性咋行,来了敌人自己都不知咋死的。团长逮着队长训,队长逮着班长熊,熊也熊了,训也训了,他照旧沉在书里,不肯出来。晚上说梦话全是汽车理论,一套一套的。队里也没啥好招,就安排他去后勤喂猪,人家喂猪都是憋足劲去干,年底保准获个嘉奖啥的。他倒好,一门心思研究发动机,就差没拽着猪耳朵当方向盘了,哪得闲“伺候”它们。就见猪饿得嗷嗷直叫,日渐消瘦。几头个大的猪带头抗议,把猪圈门给拱开了,上演一出“胜利大逃亡”。就见一个军营里,都是“二师兄”,乱哄哄一片。排队的,不排队的,它们哼着歌,扭着超肥的大屁股,小尾巴扑棱得像发报机上的小天线,完全都是自由活动的节奏,遛弯的,钻菜地的,爬山的,还有几个俊俏一点儿的小花猪直接拐向机关首府,这如拯救大兵瑞恩一样火爆的场景,顿时炸了营。气得政委手发抖,张着大嘴咋呼:谁干的,谁干的,我非处分他不可。多亏了队长、指导员一个劲地说情,他才少背一个处分。
谭梦奎那几天跟“贵宾”接待日一样,先是政委找谈话,然后是团长,接着指导员,他也不记得谈的啥了,就感觉脑子昏昏荡荡的,谈话似乎还没结束,他就病了,卧床不起,三天三夜滴水未进。队长慌了神,连夜和指导员商议,上报政委。政委说,这个瓜娃子就是有韧性,可塑之才啊!就这样谭梦奎如愿进了司机班。半年培训过后,东风141、北京吉普、上海轿都开得贼顺溜,况且拐弯都不带减速的。每个车的火花塞,发动机转速啥的也是耳熟能详。回来后,他缠着班长干了一件你想都想不到的事,他们司机班五个兵,利用一个冬季,组装了一台解放车。好家伙,轰动整个军区,还上了《战友报》。年底,司机班得个集体三等功。
傍晚,我站在空旷的山脚下,顺着夕阳的光,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看着车间里身穿油渍模糊工作服的谭梦奎,像爱护枪一样地哈口气,细致地擦着机床,真令我感动。
而此时的我,一脚踏在岩石上,嘴里咂着草梗,草的青甜顺着味蕾走进心间,像胜曰寻芳泗水滨,又像天街小雨润如酥,心里翻腾着旧时唐诗宋词元曲。打死也不会向谭梦奎一样,守着冷冰冰的车床。
试车是改装车中的一道程序,我们负责工序,将传统的卧式锅炉消杀车改装成立式锅炉消杀装备车,也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本来可以不急着干的,班里本身就没几个人,一个战友外出培训,班长请探亲假,还有一个泡病号的。那阵子,班里只剩下我和谭梦奎了,这家伙看到车来后,就主动请缨,要独自完成改装任务。队长哪放心,让我协助他,毕竟锅炉的各种管道我比他熟得多。就这样,他拿着焊枪,我拎着管钳,开始干起来。期间邓工程师去看多好多次,每次都是很满意地点点头,背着手走了。在班长探亲假休满返回的当天,车子改装顺利完成。望着崭新的装置,班长消瘦的脸颊上挂了一天的笑,还不停地夸:不错,不错,进步都快。
试车是班长提出来的,主要是考验锅炉在车上的适应度,通过一段路程颠簸颠簸,看看可有其他的毛病。
车出军营大门后,站在车厢里打晃的谭梦奎就低声和我说,今天路程有点儿长,你站稳了。我问:会不会找个好地方看看。谭梦奎眨了眨眼,点点头。
二
军都山里的春天,多少有点儿恋旧。羞羞答答,就是千呼万唤,不随心愿她也不出来。都四月份了,深山里的桃花、杏花、海棠花才刚想姹紫,嫣红期呢?还要等几天。迎着风,暖暖的,山开始泛绿了。
譚梦奎像第一次逛王府井大街一样,显然有点儿小激动,一会儿理了理军装,一会儿扶了扶帽子,一会儿眼神不知往哪看了。我看到他眼神中包含着很多东西,有期盼、惊喜、忙碌,略带点儿慌张。他搓着手嘿嘿地笑着,说,要是能来瓶北冰洋汽水多美啊,一定会爽翻了!
车刚拐进昌平境内,就被交警拦着了,一番询问后,车又原路返回了。这,这,咋回事,咋又回来了?车厢里的谭梦奎有些焦躁。
临近中午时,车子到康庄。康庄是北京延庆县的一个小镇,有着“聚八方之风物,集万古之重载”的区位优势。班长说过,是古镇,年代久远着呢。
带车陈干事说,下车,下车吧!我请你们吃个饭。
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木须肉、葱花炒蛋、京酱牛肉、糖醋鲤鱼,外带一盆榨菜肉丝挂面汤。陈干事说,来瓶八达岭特曲。班长忙说,酒就别喝了,你们还得赶路,保定离这怪远的。陈干事觉得有道理,就对服务员喊:拿点儿汽水、可乐过来。
陈干事说,今个不顺,咋会想到与景区大维修碰上了。害得我们十三陵没看上,真遗憾。来,来,别搁筷子,接着吃。
就见谭梦奎闷着头,逮着北冰洋汽水咚咚地直喝。然后,胃里咕咕泛着气往外冒,时不时打个嗝,像怨气,也像叹息。
走在康庄街上,我问谭梦奎咋了,上午兴奋劲儿哪去了。谭梦奎重重叹口气,说,去看十三陵,等一年了,没去成,特晦气。其实,也不是非看不可,主要是为了爷爷的心愿。我爷爷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看看皇帝老儿的陵园,念叨了大半辈子。就是咽气前,还想着这事呢。爷爷把遗愿交给我爸,家里太穷,出不来。看到我来北京当兵,爸就把爷爷心愿托付给了我。
望着中午的阳光,我特想流泪。正如昨天在电视里看到故事一样,一个黄河边的老汉,一辈子没去过县城。我拍了拍谭梦奎的肩膀,说,我以为啥大事呢,瞅机会吧,有机会,我还陪你去。
我看到谭梦奎眼中冒出点儿阳光,一会儿又乌云密布,脸色暗了下来。
春天,预示着忙的开始,车床班接到任务,无线电班接到任务,维修班自然不会闲着,这次任务有难度,军区下达30套高端防护密码门。邓工程师也来了,亲自坐镇指挥。八十年代初高端密码听起来多少有点儿新鲜,谭梦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丢下汽车维修书,盯着图纸不停歇。俺天爷,我这高中毕业的,看图纸都晕菜,他倒好,黏在图纸上缠着邓工问这问那。晚上,跟打了鸡血样,打着手电在被窝里抱着《机械制图》的书“啃”,成宿成宿的不睡。就见一本书被他用笔画得比八卦图还八卦,奇门遁甲啊!邓工看着书,苦笑不得,只好说,送你了,好好学,好好学。
这就是谭梦奎的韧性,起初看着好笑。后来,我发觉这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优点。
谭梦奎体单瘦弱,一个大脑袋显然与身体不太般配,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是他感知社会的窗口,也是他窥知人间的冷暖之门。他的多愁、正义、好学、悲悯等无时无刻都在他灵敏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游刃有余。班长吸着烟,噘着嘴说过,这家伙不成功,便成仁。我就不明白地问,干一件事,非要“成仁”吗?班长挥挥手说,拉倒吧,你小子,不要跟我瞎掰,我没你肚里墨水多。我嘿嘿地笑着,拿着密码锁的说明书进车间琢磨去了。
密码门是有标准的,钢板、压条、焊缝等都有要求,马虎不得。这远不比上次做行军帐篷,有点儿误差不算啥,就好比方,固定杆长个三五厘米,是好事,在地下更牢固。在用铆钉固定帐篷支撑杆挂件环节时,谭梦奎一直没能把铝钉头铆圆。邓工看他方式不对,手把手教他如何用锤拍打。他倒好,人小锤大,气力还跟不上,下锤也没准头,三锤不到就夯手上了。第二天左手肿得跟发面馍一样,休息了俩礼拜,才消。等他手恢复好,帐篷也装车发货了。他懊悔得不行,整天逮着红萝卜啃,说是增长气力的。谁知那玩意行气更厉害,一个寝室里迷漫着萝卜屁味儿,无法安睡。就是天天开着窗户通风也不管,谁能管住他无时无刻地放。班长实在没辙了,就跑到炊事班借个炉子拿瓶白醋在寝室里熏了三天,才算好些。
三
2018年,我在战友经营的“庄道轩”茶舍品茶时,岳宏峰说,要说现在建材商厦展示的各种高档豪华门,除了指纹,扫脸系统高端些。门的质量确实没法与我们当年生产的门相提并论,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当年我们生产的门,你就是拿着冲锋枪,“嘟嘟嘟”打上一梭子子弹,压根就找不到枪眼,充其量有几个小白点儿,瞧瞧钢板多厚。现在的倒好,雍容富贵,高端华丽色调的烤漆里裹着单薄的铁皮,拿个改锥不费大劲一捅一个洞。
我听了哧哧哧直笑,岳宏峰以为我不信。就接着说,你不要笑,我说的都是真的。上次我一个亲戚买辆小轿车,也不是啥名牌,在车下拧螺丝来,手一滑,底盘戳个窟窿,这质量真不敢恭维。想当年,部队里老解放,光一个保险杠,俩人抬着都费劲,你瞧瞧现在的保险杠,能管保险吗?
说得也是,我们的高端密码防护门是全军首创。谭梦奎看不懂图纸,但他有钻劲,从第一块儿钢板开始,他瞪着那双小牛眼,没落下一个环节,哪怕是一次焊接,一个打孔,他都亲力亲为。邓工有时会说,你们的认真劲儿要有谭梦奎十分之一,我们的任务就能轻松一半。军营的日子,也是下雨了天晴了,天晴不忘戴草帽,下雨不忘穿棉袄。八成战友的心思真没放在啥行军帐篷、密码门上,有兴趣的是枪啊,炮啊,导弹啊!更喜欢听两伊战争,伊朗放火箭了没有,伊拉克咋还击的,要是有这样的讲座,听三月都津津有味。队里一张《参考消息》,指导员是从来没看上,到年底还问通讯员,报纸咋回事,一期没见到?那两成战友呢,兴趣就不好说了,有想花花世界鸳鸯蝴蝶的,有想趁着培训畅游神州的等等。心思也就多了去了,难以统计,因为心思那玩意太活泛。谭梦奎仍斗志不衰,兴趣不减。周五时,一个门的外边框焊好后,下一步要打孔,上来六个年轻小伙愣没把门架起来,班长喊着我和谭梦奎。就见战友们都使出全身气力,个个脸憋得跟紫茄子一样,门才晃悠悠地架起来,很艰难地放在打孔机上。孔打好后,架门时两个战友偷懒,还没喊放下,就提前抽手了。就听譚梦奎一声惨叫,他的左脚被压住了,千金重的门啊。大家慌忙架起门,谭梦奎抽出脚来,鲜血已渗湿了解放鞋。他很懊恼,逮着门,用拳头砰砰砰砸了三下,手上也跟着冒出血来。
炊事班给谭梦奎开了小灶,我把炖好鸡汤给他送去。就见他左脚和右手都缠着绷带,对称性极好。就调侃一下说,你这跟老山前线下来一样,功臣啊!谭梦奎有点儿着急地问:今天,邓工去安密码锁了吗?我说,你看你,自己伤不关心,想轻伤不下火线可是,你自己去车间看看啊!
谭梦奎见我嘟囔他,有点儿不好意思,挠着头,嘴里吸溜着,真痛,痛得一夜没睡着。
上午开班会,责令两个偷懒的战友写检查。邓工要求: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暂停生产。班长对岳宏峰说,你上午负责调漆,把比例都记下来。其他人,继续排查。等邓工开会回来,再定下一步工作。
阳光真好,班长接到通知去机关开会去了。我和小饶能偷偷懒,他去无线电班找啥三极管去了。我抱着《解放軍文艺》陶醉起来,看到小说里有句话:“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我读后有点儿惆怅,望着窗外梧桐树叶,哗哗地随风舒展着,山峰上的明长城一直安详着,像一条苍龙。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这样赞过长城:“因残破而展示了生命的力量,因蜿蜒而影射着古老国度。”或许正是这种秦时楼堞汉家营,出塞山川作势雄的风雅,才使我们的青春有了眷恋之处。
我随手捡起一块儿小石子,往正在低头调漆的岳宏峰扔去。先听到梆的一声,接着是岳宏峰的惨叫,惨叫声尚未落音,他就捂着眼在地上打滚,哇哇地嚎啕大哭。我心一颤,坏菜了,小石子也能闯祸。
恰巧班长回来,他和小饶一起,用自来水逮着岳宏峰的左眼直刺,不大会儿哭声停了。
我跑过去,紧张地问,咋弄得。
啥,咋弄得,你扔的石子砸在喷漆的塑料壶上,壶里的松香水溅到岳宏峰眼里去了。他要是瞎了,我非处分你。班长恨着劲说。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岳宏峰捂着眼回宿舍去了。我盯着自己的脚尖,心想,这就是生活吗,一个小石子的波澜。
回到宿舍,谭梦奎偎上来,一脸坏笑地说,没想到你也会“干坏事”。
我没好气地怼他:你能打八环,我还打不了十环了。
谭梦奎搓着手说,这哪跟哪,闯祸跟打靶有啥关系。等饭后,帮我看首诗,我写的。
这谭梦奎又整啥幺蛾子,还嫌不闹腾吗?竟然写诗了。我感到天昏地暗,头晕目眩,闷得喘不过气来。
四
列队去食堂时,岳宏峰小声地说,眼睛没事了,当时蛰得疼,没忍住就哭了。我跟班长求过情了,不让你写检讨了。
我很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向他竖起大拇指。
你是一株小草,我就是一颗参天大树。
你是一滴晨露,我就是长城的胸膛。
把你紧紧抱在怀里,地老天荒。
我读过诗,就问,你这是喜欢上谁了,想跟谁表白呢?谭梦奎红着脸,挠头速度比往常快多了。就问:诗咋样,可管?
我说,啥可管,我问你话你还没回答呢?
谭梦奎支支吾吾地说,你就说诗咋样吧!
我故意哈哈哈冷笑三声。谭梦奎白着脸,你啥意思,不照直接说吗?看你笑得,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我把信纸嗖一声,用力往天上一扔。扭过身,不再搭理他。
谭梦奎牙一咬,心一横,好,我说,我说可照来。先声明,替我保密。
夜色苍茫下,看着排除万难,下定决心,大义凛然的谭梦奎,我点点头。
晚风,卷着长城的呓语
将我的梦拉长
孤单的月影下
听到你亲切地喊我乳名
当我读到谭梦奎第6首诗时,我就明显感到,他诗歌天赋,远远超过我。我就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好了,军区报能发个八九篇,保准给你申请个嘉奖。他嘎嘎嘎地笑着说,压根没想发表的事,我想干啥,你最清楚。
看着一脸嬉笑的谭梦奎,我突然惆怅起来,一直以来,雄心万丈,信誓旦旦要发表作品的我,特茫然。虽然接到一家文学杂志的通知,要发表一组散文的,可就是不见样刊的到来。望着被夜晚笼罩的军都山,心中愁肠万千。我就跑到无人处,对着大山喊:军都山啊!你如此博大的胸怀,咋就容纳不了一个小作者的心愿呢?
上午,谭梦奎拄着棍跛着脚去车间看邓工装密码门,手里拿着小本子,不停地记着,下午就一个人闷在宿舍里写诗。我和他说过多次,诗歌是需要灵性的,不是在房间里闷出来的。他嘿嘿地笑,说,有效果,有进度。弄得一进门的班长一愣,问,啥效果?我急忙帮他掩饰,说,脚上的伤用药效果好,恢复得快。谭梦奎听我一说,红着脸,低着头,一瘸一拐拄着棍留给我们一个弱小单薄的背影。
晚上,谭梦奎吞着烟,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我计划好了,秋季时间一到,就复员回家。回家后先开个汽车修理厂,看发展情况吧,弄好了,就成立公司,我不弄啥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吹恁大弄啥,莫得用。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叫“广善”怎样?
能解释一下啥意思吗?我问。
你不晓得,山里娃娃苦啊,我想扎根后,帮帮他们,能帮一点儿算一点儿。把我的善心用广一些,我文化浅,琢磨不出好名字,也是这阵子看书,闲琢磨的。谭梦奎弹了弹手中的烟灰说。
望着黑夜,浓得有点儿化不开。为何人生过几年都要整个总结,想想未来的路。能永久呆在一个地方,寂静,安然。闲看云卷云舒,静品花开花落,该多好啊!我对谭梦奎说,此时,真想喝酒。
谭梦奎递来北京牌香烟,说,抽一根,这也解忧。是吗?我疑惑地点着,吸了一口,就像掉进山区老农家的熏肉房里,咳喘着,在浓烟弥漫中,找不到门的方向。
一个老太太来找指导员。老太太走后,就见指导员表情凝重。看这表情,八成出事了。往常指导员都是一脸微笑,让战士感到最和蔼可亲。特别是听他讲伊拉克打伊朗时,肢体语言特生动,眉飞色舞不说,说得嘴唇上泛着白沫,都不嫌累,笑容还会一直有。口讲干了,他会拽一根狗尾巴草梗,伸出大舌头用草杆子刮几下,然后让舌头在嘴里掂量几下,试试灵活度,不大会儿,他嘴里的两伊战争就开始硝烟弥漫了。今天,他这种表情比剃胡子时绷着脸还冷100多度,准没好事。
班长把我喊到办公室,严肃地问,说说吧,咋回事?
我一头迷雾。忙问,啥,啥,咋回事?
你小子就跟我装,谭梦奎的事你不知道?我装着很无辜的样子,露着很冤枉的表情说,我知道啥啊!
这小子就没消停过,才休息几天啊,竟戳事。他把隔壁食堂里做饭的梁小娥给搞了,女孩妈妈都找上门来了,这会儿估计政委难保他了。还有你,前阵子教谭梦奎写歪诗,我就琢磨不是啥好事,你也不是啥好鸟,回去反思反思。去,去,把谭梦奎给我喊来。班长拍着桌子,嗓门大起来,焦急地嚷着。
我走出辦公室,心想,这可咋办?
10分钟不到,就听到谭梦奎和班长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小饶说,不会打起来吧!我一想有道理,就冲进办公室,看见谭梦奎和班长扭在一起,各自拽着对方衣领不松手。
指导员指着班长说,我让你核实情况,就这水平,去,去,一边去。转身又训谭梦奎说,你啥态度,吃了雄心豹子胆了,顶撞班长,还想打人不是。
谭梦奎不服气地说,班长说我搞人家,哪有的事。不是毁人名声吗?
熄灯号都好久,也不见谭梦奎回来,班长开始慌了,就让我和小饶分头去找。我是在大食堂的房顶上找到谭梦奎的,平日里他喜欢坐在房顶上晒晒太阳,想想家乡。
看到房瓦上一堆烟头子。我就说,晚饭也找不到你。来,咱整点儿。我从怀里拿出午餐肉,醉山楂,二锅头。打开酒瓶,递给他。
诗人哥,作家哥,你说,梁小娥喜欢我咋了,有错吗?你知道的,我不就送给她几首诗吗?班长那啥态度,不是你们进屋快,我非拍死他。搁司机班时,一老兵,说我爷爷坏话,我一管钳给他拍晕了。
送诗我知道,真其他的啥都没干吗?小娥妈来找指导员干啥?我反问。
谭梦奎低着头声音很小地说,我亲了她。你知道下午闲着没事,我看小娥也闲着,我们就聊到一块儿了。那天,我念着诗,她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看着我,一直望着我,像伸出俩小爪一样向我摆手,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于是,我控制,控制,没能控制住,就抱着她的小嘴亲了起来。
就恁简单,往下没发展。我接着问。
没,真没。我知道部队纪律。不过我和她说了,10月份,退伍后,带她回四川。
指导员当着我的面对班长说,梁小娥妈也没说啥不好的,就是问问这小伙可本分。梁小娥爸爸走得早,家里就她一个娃。她妈听说去四川,有点儿舍不得。还剩不到两月,你给我看紧他。
五
我接到一个军区培训通知,时间半年。按说这机会是该谭梦奎去的。此时,他正关在办公室写检查呢。我连个招呼都没打上,就坐着车去军区报到了。
回来后,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季。我问了几次班长谭梦奎退伍时,说啥了没。班长回答得特干脆,没说啥。梁小娥带没带走我也不晓得。我时常望着大山,脑子一片茫然,有感叹号,问号,一直找不到句号,更不知道何时能把问号拉直。阳光在军都山上一季又一季地晒着,也一季又一季被遗忘,像明清时期没被记录在案而沉入海底的航船。
2008年5月,汶川地震,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个叫“广善物流的公司”捐赠救灾款300万。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公司电话。我拨通了电话:你那个,啥子事!我说,我是部队的小刘,维修班的。谭梦奎说,你个瓜娃子,从哪冒出来的。
谭梦奎9月份就递交退伍申请,政委是舍不得放他走的。找他谈了几次话,一直挽留。
退伍时,发的一点儿安家费,谭梦奎一把手都交给梁小娥。让她在康庄街上租了间门面,挂个汽车维修部的牌子。梁小娥在门店接活,谭梦奎在后院修。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你想,80年代,一个北京的郊区小镇,没你想象的车水马龙,没你想象的繁华如梦。过年前,他带着梁小娥,把十三陵看了一遍,开放的长岭、定陵,没开放的景陵、泰陵、昭陵,一圈儿下来,耗了半个月。梁小娥也不明白他为啥对皇家陵园感兴趣,整日没事就围着陵瞎转悠,以至于看门的老头认为他是盗墓贼,差点儿送到被派出所去问话。
因手里钱和时间都不宽裕,谭梦奎就放弃了去河北看东陵、西陵的念头。返回四川过年去了。
到了四川,梁小娥就不愿意回来了。不说是天府之国哪哪的好,虽然吃得辣点儿,可气候湿润啊,梁小娥的习惯性鼻子出血,一下就好了。没办法,谭梦奎把汽车维修部的牌子又挂在了家乡。梁小娥也是上心,憋足了劲,给谭梦奎生了三个娃,两男一女。可谭梦奎的娃娃远不止这些,多年来他资助的孩子应该是他娃娃总数的20倍,光大凉州就有30个编外娃娃。
我一直纳闷的是,他为何对皇家陵园那么上心,仅仅是简单完成爷爷的遗愿吗?我把疑问提出几次,谭梦奎总是在话筒里打哈哈。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看电视纪录片《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明清陵篇”介绍中说:自永乐七年即1409年6月20日修建“长陵”始,到清顺治初年完成“思陵”止,时间长达200余年。这200余年间或许跟谭梦奎家人有啥关联?我把电视截屏用微信发给了谭梦奎。
谭梦奎回,我哥,真佩服你的韧劲,盖了帽了。得空来广元耍耍,搞点儿地方小吃打打牙祭。我晓得,此事,仍是他不愿说的话题。就转着问,梁小娥管你管得严吗?
他回,这还用说,严的莫得一点儿想法。
夜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聊深了。我再想当初,谭梦奎要是不认识了梁小娥,会不会还整出啥幺蛾子。会不会仍设想着把山上的野长城租出去,把山挖空,搞几个“凉宫”,让外地游客都来避暑。会不会把康庄大街取直了,拓宽了,旁边再建一个飞机场。当年,我俩骑着马在康西草原上飞奔时,他撇着嘴说,这算啥,要是我搞,非得让内蒙古大草原的牛啊、马啊,羊啊都迁来,不说遍地牛羊了,也得天苍苍野茫茫啊!有时听他胡咧也是一种乐趣,最少他往着一个方向奔!而我的日子呢,虽波澜不惊,总缺云卷云舒。用笔记录的日子,总会显得孤单,像汪洋里的一条扁舟,有风和无风时,都不能汪洋恣肆,仪态万方。
谭梦奎说,小娥对你还有印象。问我可是班里的那个大个,一脸忧国忧民的表情。
看着手机,我有点儿哭笑不得。站在阳台上,瞭望夜空,月亮此时不在,星星们都静置在各自的岗位上眨着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生活如白驹过隙。
六
二胎放开后,谭梦奎问我,要不要再领一个了?我没明白他啥意思,就回,已经过龄了,下辈子吧!
谭梦奎发来,我是问我能再领一个吗?
你都有三个娃了,罚款交了不少吧,还想领,没累够啊!
是小娥,不知犯了哪门子神经,非要领一个。我咋办啊,我的哥。
这样的事,我没法拿意见。毕竟是谭梦奎的家事。为了缓和一下,我说,娃多了也好。可以去北京开分公司,顺便把你的康庄街捯饬捯饬。
你真是我哥啊,我都忘了说了,康庄正在扩街。我把当年的维修部买下来了,还有一个院子。想留点儿回忆,你不知道,当年梁小娥第一次就是在院子里给我的,那天晚上的月光真甜啊。回想起来,特有激情。
我质问他:这么说,在部队时候,你们就那个了,你个家伙瞒我快三十年。
语音通话里,我听到谭梦奎嘿嘿嘿嘎嘎地傻笑。
2018年10月底,休年假的我正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放飞心情。岳宏峰刚从滑草坝上出溜下来,脸煞白,嘴里叨叨着,玩得就是心跳,有点儿小紧张。比当年我们爬野长城刺激多了。我还想坐坐滑翔机,你坐吗?
我骑在马上,正准备和导游一起穿越草原湿地呢,手机响起来了。
谭梦奎哽咽着说,金庸,金庸大师走了。我的偶像啊,昙花如梦,倚天屠龙,雪山飞狐,笑傲江湖。我今天特悲伤,想找你叙叙。
我只好下马,找个阳光充足的长条椅,眯着眼,聆听谭梦奎的武侠之梦。
谭梦奎说,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喜欢习武,说是清末的武探花,当地志书上也有记载。当年,他在县里教拳,后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义和团一败,说要禁武,那日子就吃紧了,习武者都纷纷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了。我高祖爷也就从北京城跟着逃荒者一路盲走,路上碰到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他非说自己是紫禁城里的御林军护院。路上,逃命的逃命,逃荒的逃荒,谁会顾得一个疯老头子啊!我高祖爷就一路上照顾他,给他买酒买肉,要吃黄瓜不买番茄,要喝小烧,不买大曲。那时跑荒,很多人是顺着驿站的线跑,刚过了河北鸡鸣驿站,疯老头就病了。我高祖爷就找家客栈租间房伺候他,疯老头病得不轻,卧床不起,三天三夜滴水不进。一天傍晚天刚擦黑,疯老头坐起来说,你以为我真疯啊,疯是为了保命。我是皇家陵园的总监工……那晚月高风舞,疯老头清醒地说着往昔,从皇帝小时候,讲到进陵墓,嘟嘟噜噜说了快一夜。凌晨5点不到,疯老头从贴身内衣里拿出一本拳谱、一张图递给我高祖爷,说句,图里有大秘密。头一歪,就咽气了。
我高祖爷把疯老头埋在鸡鸣驿村的东乡,就一路奔张家口方向了。为啥去张家口他没说,我估计是给疯老头家里送东西。当到了宣化,发现整条大街没人,他一打听才知道闹瘟疫。于是转身,往西走。来到四川,走到广元这地,实在是走不动了,看着山清水秀的,也背静,就留下来了。
谭梦奎接着说,拳谱倒是没咋听祖上提过,倒是那张图神秘了。一代传给一代,一代代人琢磨着到底啥秘密。赶我看到这张图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图烂得捧不上手,估计是爷爷用面糊糊打浆糊粘的,摸着图上疙疙瘩瘩的都硌手,图画得像一座迷宫。我只看了一眼爷爷就收起来了,比他的命还珍贵。
草原上的俊马低着头寻找嫩草,鼻子还不时发出噗噗响声。这样的低缓,安详都是岁月的赐予吗?我终于明白,谭梦奎一家,或许就生活在赐予之中,冥冥之中有个宝藏或惊天秘密,正是这个“宝藏”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岳宏峰说,切,谭梦奎就是找到陵墓了,他敢去挖宝吗?这都啥年月了,他有孙殿英厉害吗,把东陵炸了,把慈禧太后剥得就剩一个小裤衩。谭梦奎他这只是一个念想,念想。都说人生是一场修行,不过,我认为谭梦奎倾情皇家陵园,比你钟爱万里长城厚实得多,人家大把大把精力撒進去了,你那充其量算幼儿园小蚂蚁班。
我突然有了骑马射箭的冲动。导游很为难地说,单射箭可以,骑马射箭,没,没这个项目。岳宏峰拿出几张钞票塞进他口袋里,导游高兴地喊,上马,上马。
驰骋在马背上,我问岳宏峰,要是莫言笔下的余占鳌生在草原,是不是也会成为草莽英雄呢?岳宏峰嘿嘿直笑,哥啊,你咋不问是九儿可能打过黄蓉呢?让金庸和莫言两个大师论坛论坛,或许能整出一部现代版的“九阴真经”来。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该有自己的故事。谭梦奎曾多次说过,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的眼中始终闪现着,食堂的饭桌上,谭梦奎一一捡起我们吃饭时撒掉的饭米粒、剩馍头、菜根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他的这个动作,让在座的战友们大为吃惊。不到一周时间,我们都改掉了撒饭、掉米粒的毛病。至今,碗里不剩饭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着,当看到女儿扔下不可口的馒头时,捏在手里,放在嘴边,真难以进口,别说下咽了。
回望康庄,是回望我们的青春岁月。谭梦奎的青春是加了满满的血的,像电脑游戏里的侠客,又像机械战神,在我们苍白青春的布幕上画满了激情、张扬和勤奋。我在电脑上正敲下这些文字时,谭梦奎打来电话,说,有个知名门业的老总,要买我当年记高端密码门的笔记,出价200万。我卖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你缺钱吗?
谭梦奎在电话里嘎嘎地笑着,笑声如他当年第一次牵着梁小娥的手,迎着朝霞,走在康庄的大街上。
责任编辑 婧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