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门驿
张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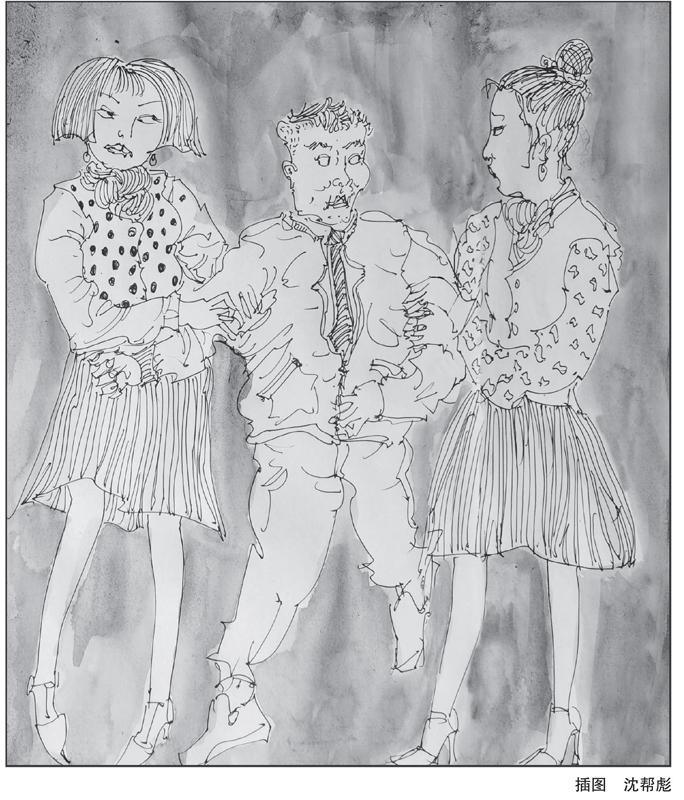
1. 小先生奔前程去了
对于龙门,有的鲤鱼跳过去了,有的鲤鱼没有;对于龙门,有的鲤鱼去跳了,有的鲤鱼没有;对于龙门,有的鲤鱼听说过,有的鲤鱼不知道。跳龙门的,除了鲤鱼,还有别的鱼;除了鱼,还有其他。跳过了龙门的鲤鱼,有的变成了龙,画在画上;有的变成了年纪更大一点的鲤鱼,后来,它们或者在海里,或者在网里。
它们呢?有金盔银甲,是水中飞翔的鸟儿,或为盘中餐,或是砧上肉,或有五德之才,或在五脏六腑中埋,或处惊涛骇浪之中,或遨游河清海晏之所。它们据说是美人,西方童话中的公主,东方神话中的鲛人。它们不远万里来到鱼门驿,做特产。
小先生第一次来到鱼门驿,好奇地看着特产们。特产是干巴巴的,明码标价的。特产放在驿站的商店橱窗里,是商品,也是饰品。不讳言其美,不讳言其丑。
驿站有诗情画意吗?有桥吗?有寂寞的梅吗?望不见了。小先生看到这里有停车场、男厕、女厕、鱼蛋粉、烧鸡翅以及茶叶蛋。而驿外,有高速路、高速车,有寂寞和不寂寞的人。
咖啡要热,方便面也是。冷了,方便面和咖啡都酸。咖啡三块五毛钱,方便面也是。小先生要了方便面,吃了一半,猛停下来,把背上的双肩包抱在胸前。小先生念完高三,要过鱼门驿,去更遠的地方读书。小先生的行李中除了书,什么都带了。
地上的树叶和塑料袋绕着咖啡的利乐纸盒打转转,像两个追逐的孩子。那天晚上,当年1号台风登陆鱼门。在鱼门驿建成之前,从小先生家到大学要坐五天的车。小先生没受过那个罪。
咖啡冰了,有冰的滋味。驿站的商店今天卖了七瓶咖啡,纸盒三瓶,铁罐四瓶。今天,有七个人在匆匆赶路的时候还喝了咖啡吗?小先生奔前程去了。
2. 真实的虚荣,你我皆有
鱼门驿的地形我熟悉,两山夹一道,北边叫作故乡,南边叫作他乡。每年,小先生都要在鱼门驿来回蹦跶,或是过年、清明、中秋,或是五一、国庆,也可能因着某个兄弟结婚。每次回老家,亲朋好友聚会,有的谈收入,有的谈买房买车,有的比一比对象,也有的含蓄表明自己升职了,更有的直接告诉大家,孩子考上名校了。无论哪一种,总会被另一个亲朋好友,或者亲朋好友口中的某个不认识的人生赢家所打败。
你想着大家会祝福你年入80万,在座的虽然不敢说自己挣得比你多,但永远有人会提及一个某某某。这位某某某跟他本人很熟、关系很铁,这位某某某则是年入100万呢。这时,摆龙门阵的人,不管出一张什么样的牌,总是会被后来者打倒,占不到上风。
往往在这种场合,小先生是脱俗的。他总是脱颖而出,他永远不用语言表达自己跟什么人熟,他只用图像,也就是照片。
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过年回家小先生带回来四张跟名人的合影,那气场就压住了大家。他觉得自己赢了。此后,每年他带回来的名人合影都在增加。许多年过去了,他竟然攒了两千多张与名人的合影。许多年过去了,他只攒了两千多张跟名人的合影,没攒别的,比如钱,比如所谓的事业跟爱情。
鱼门驿像一个水电大坝,用落差演绎能量。小先生在这个落差之间,贪婪地收集着能量。
大四那年,小先生在一家境外媒体的内地记者站实习,受派采访自己所在那所名牌大学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那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名专家、院长、教授,头衔多得能填满整条采访稿的字数。在平时,本城本省的记者约这位经济学家做专访,他总是要拒绝一番的,因为没有档期,最近也真的很忙。
但是,这位经济学家也看重国际影响力这个他涉及未深的领域。他没有怀疑小先生那瘦弱的外表,也没有介意小先生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谈吐。
他欢迎小先生,亲自为他倒水。在采访的过程中,作为大忙人,身兼多职的教授接了三个电话。每个电话他都说一遍,我很忙,我正在接受外媒的采访。
采访结束时,教授热络地拉着小先生合影,发到朋友圈上,告诉大家,今天他接受了某外媒的专访。他感谢小先生。小先生不会告诉教授,此时他只是本校大四未毕业的普通学生。如何普通?就是四年来没有拿过奖学金,努力要进社团,但是没有进得了学生会,也没有进得去校团委的一个普通学生。
院长发在朋友圈的那张合影,震惊了认识小先生的同学和其他普通老师。这是真的吗?至少这也不算假的。
从那之后,小先生发觉与名人合影,别有滋味。那种真实的虚荣,你我皆有。那种你我皆有的心态,让人不必分清理想、雄心壮志,或者是炫耀、显摆等等。
3. 猜猜我是谁
从鱼门驿的北边来了一个名人,小先生和他合影时,称他为刘主。
入行的时候,一位不受各路主办方待见的同行大哥告诉他,做记者虽然穷,但是可以“调戏”名人。跟刘主合影的时候,他践行了这句话。
小先生没有受到邀请,但那天他西装革履地走进了这个国际性的商帮会场。他没有任何身份,包括记者身份,他只是像一只液体小动物一样流淌着进了门。
会议规格很高,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听说了这个会。会上有大商人,也有政要。告诉他有这种会存在的老乡,虽然博闻,但也不敢奢望到会议现场去。小先生却默默地出现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也许他看起来像一个工作人员,来自主办方,或者来自承办会务的酒店。也许他看起来像一个底气十足的受邀嘉宾,因为他面对这样的场合,总是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
长条形的主席台上就座的是头一等的嘉宾,大厅里散开的小圆桌则坐着不分大小的各色人等。圆桌堆里有一个老年人,被小先生认出来了。是了,这个人就是鱼门驿北面大名鼎鼎的刘市长。
大名鼎鼎,并不是因为他的行政级别,而是因为老家民间流传着诸多关于他的励志故事——如何起于卑微,最后电视新闻里天天有他;如何经历曲折,奋斗不息,最终倾倒众生。
小先生读初中时,老师就在课堂上讲起过这位刘市长,是本中学校友,也是县里第一个考上某知名大学的人。然而,在外地,在这样高规格的一个盛会上,刘市长也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托着腮看着人来人往。
远远望去,他像极了一个普通的人。
应该叫他什么?刘市长?刘主!小先生剛听了一耳朵旁边的年轻人这样称呼他,于是也学着这样叫。小先生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称他为刘主?刘主是什么意思?刘主又是什么官儿?刘主属于什么级别?是这两个字吗?小先生不明白,不过,发音是这个发音没错了。
刘市长听到这家乡话,微微笑着转过头来,应了一声,看着小先生,那目光不是看陌生人的目光,而是看熟人的。
看来,叫刘主是对的。
小先生忙自我介绍:“刘主,我是阿影。我现在在这边工作。”刘市长并不知道“这边”指的是什么,或许是某个机构,或许是指这座他乡之城,他只是笑着点着头:“好,好,好。后生人,在这边好好工作。”
“刘主,我们合个影吧!”小先生已经不是新手,他眼疾手快,快得比快门还快。于是又一张与名人的合影出炉了,后来被贴在了出租屋那面并不体面的墙上。
在平凡人的认知中,这样的场合也许是个资源池。混进其中的弱者,大概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分杯羹,或是谈事情,或是谋名利,也有可能是来消灾免祸的。谁也没想到,像一只液体小动物一样流淌进这个严密场合的小先生,竟然是为了合影。他没有采访任务,只是为了合影。
合完影之后,他就走了。也许他怕露馅,也许他真的尿急。
从厕所出来后,他被两个一米七几的女服务员一左一右架走了。由于没有证件,他受到了最恶意的质问。好在他是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被架走的,最后人们相信他只是来上厕所的不懂规矩的人。
4. 拥有姓名
小先生并不拥有姓名,许多人一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叫小先生。因为没有留下名字,有一天他可能要重新跨过鱼门驿,从漂一族变为逃离北上广深一族。
其实,有那么两三回,小先生差点儿就留下了名字。
第一回是在海边。在一个灯火辉煌的厅堂,霸满整面墙的落地窗沁入幽幽寒气,远处有渔火和海的光。在这样的“乡下地方”,没人知道小先生是谁,于是他竟然拥有了一个水牌。
尽管整个会场近一半的座位都摆着水牌,但小先生还是感到特殊,觉得高兴。他找到自己的专属座位。尽管这个座位在最左侧偏中后的地方,但他还是感到特殊,觉得高兴。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姓名被放得这么大。
有水牌了,就意味着在这个圈子拥有姓名。
小先生仔细聆听主持人有没有介绍他,并没有。但他还是很高兴,乃至不关心今天来是干什么的,以及此刻的会场是什么主题。
小先生只知道有人在台上讲话,以及过了一会儿换了一个人讲话。这个夜晚有几次捧场式的哈哈大笑,有人在说很幽默,也有几番掌声。笑声响起来的时候,小先生正对着落地窗外辽阔而深蓝的天色出神;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小先生慌张地放下手机,也鼓起掌来。此时他正拿着手机拍自己的水牌呢。
鼓完掌了,小先生咬了咬嘴唇,把水牌照片发到群里了——只有图,没有配文字。许久了,并没有人回复。他看了两三回手机,静悄悄的。他尴尬地撤回消息,可是已经超过两分钟,撤不回了。他赶紧把群聊天记录删除,自己看不见,就当没这回事儿。仅仅只是没人回复,但他的心里已经上演了一场大戏,比如,被人看出来他平时是没有水牌的。
在这次兴奋夹杂着失落的海滨之行中,小先生最大的收获就是十余张跟名人的合影。
第二回是在街边。大清早的,一个首发式在街边举行。公共汽车站牌就愣愣地立在会场边沿上。早晨的太阳照下光线来,给公共汽车站牌拉下一道长条状的影子,这影子几乎是横切会场而过的。小先生从本趟公共汽车上下来。作为全车最拉风的乘客,下车之后,他径直走向会场,并且坐在了第一排。是的,这一次,他的水牌在第一排,并且不是靠边边的位置。他的左侧还有三位,他的右侧还有七八位。
有水牌了,就意味着他在这座城市拥有姓名。
这是一个露天公开会场,围观的路人不少。摄像机、照相机和麦克风们来来回回地走动。小先生觉得,这来来回回的走动也就是装模作样罢了,真播出来也就十几秒,有十几秒都不错了。虽如此,这却是极严肃的。他默默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着,把手机往回放,注意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公众形象。
愉快的首发式结束了,小先生快、狠、准地找到了全场最有名气的名人合影。他再三确认照片保存好了,才回到自己座位上。一群人开始过来收拾会场了。
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跟他说,把这个水牌带回去留念。女人把小先生的水牌拿起来,递给了他。他顺手接着,就往自己的袋子里放。放到一半,他发现自己被侮辱了,又连忙拿出来。是呀,哪有人参加完活动把水牌带走留念的?这得是多没见过世面的人哪?他再寻觅那个女人的身影,已经不见了。会场上只有走动着的稀稀落落的人。他不知道她是谁,以及人在哪里。
大家都走了,他也该走了吧?临走,小先生悄悄伸出手机,拍下那个水牌,若无其事地向公交车站走去。
5. 这显然不是P图
小先生在鱼门驿吹牛的时候,我认识了他,大鸿途公关公司的傅总也是。大鸿途公关公司原本把小先生作为公关对象,后来却成了他的东家。傅总带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青姐自驾车路过鱼门驿。小先生从长途大巴上下来的时候,青姐认出他来,叫了他一声。
青姐和他打过许多回交道,因为小先生是一名小报记者,帮大鸿途公关公司的项目做过好几回宣传。傅总则是第一次认真看到小先生。
这是清明时节,春寒料峭。傅总回乡祭祖,小先生也是。能在鱼门驿这个关隘相遇的,从大范围来说都是老乡。傅总和小先生都兴奋起来,小先生开始介绍自己和多少名人合过影。他从手提电脑中调出一张重量级的照片,上面和小先生合影的,是另一个大国的知名政要罗先生。
从肉眼来看,这显然不是P图。
小先生想从道理上说服傅总,这张图不是P的。说起来,自己虽然是个小报记者,可是那次也有幸约到了罗先生的专访。虽然说这一开始不太可能,不过,领事馆的新闻官在未成为新闻官时,曾是他的老师。他做实习生时,这位新闻官带过他。老师经常关照他,因为老师很看好他。小先生说,自己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略懂五门外语。学生时代在老家打暑假工,就是帮小厂翻译外贸单。
小先生说的也在情在理。不过,后来他又说过那次见罗先生的另一个版本。
罗先生的出访并不是一个秘密。在向公众公布的四个行程点中,每两个点都间隔着十几站地铁、七八站公交或三四次换乘。尽管距离如此不紧凑,但每个点都拥满了小先生的同行。当看到这帮娘儿们追新闻的时候,小先生才知道优雅且紧身的一步裙,以及八厘米的尖高跟鞋都是可以跑马拉松的。
第一个站点在蓝天会议中心,活动安排在早晨,小先生提前到了。他精神饱满,连平时不怎么吃的早餐今天也吃了。他一直在想办法进门,想了一个小时之后,罗先生的车从另一个门离开了。小先生没有看到离开时的罗先生,只看到离开时的罗先生的车。又或许那不是罗先生的车,只是他车队中的一辆。总之,小先生从同行们那印着LOGO的公务车着急忙慌的动向,感觉到最前面那些车里,总有一辆载着罗先生。
片刻之后,第一个站点的人空掉了,只剩下些许收拾场地的工作人员,就像一个灌满水的气球,被针扎了一下,水瞬间就漏光了。
第二个站点在一家超市,比较好进,因为这里原本就是市民百姓来来往往的公众场所。小先生相信自己在第二个站点不会失手。但是,他迟到了。当他从地铁站跑步进场时,刚好看到驱车离开的同行们。他果断放弃了第三个站点,打车直奔第四个站点。
第四个站点是小先生的母校,大门是进得去的,但是罗先生即将发表演讲的学院大楼已经被围成铁桶一个。小先生百无聊赖地走进学院大楼相邻的那栋楼。这里有一条他熟悉的防火通道,宽敞、干净。这通道最优秀之处就是安静、孤独,不被任何人打扰,连幽会的年轻情侣也不会来这里。读书的时候,每次小先生的自闭情结犯了,就会一个人跑到通道这里,闷坐、发呆。
这一次,他照例是闷坐、发呆。忽然,楼上下来七八个穿西装打领带,高高瘦瘦,身板笔直的黑人和一个穿白色套裙的白人。白人女士领着走近前的竟是罗先生?小先生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一边说了句“我们合个影吧”,一边已经按下连续快门。
路过的人群迅速通过,往通道的另一端去了。小先生只顾低头检查他的照片,无论是七八个黑人,还是那位白人女士,没有人说了什么跟小先生有关的话,或者做一个跟小先生有关的动作。
主要的人群已经路过,次要的人群正在变得稀疏。一个人迅速地揪住小先生,训斥着:“你干什么?找死吗?你刚才有多危险知不知道?好玩吗?”揪住小先生的是另一家媒体的一个老记者,平日,他被小先生称为大哥。他年长,他平时说话都挺有道理的。
今天,他也来了。不过,找死?不至于吧?这里是小先生读书和初恋的地方,他熟悉着呢。找死?不至于吧?如果可以用生命来合影,也没有关系。小先生回过头,看到老记者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6. 公关达人
在鱼门驿,小先生像一匹千里马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他告诉傅总,不仅外国政要,本国的大领导,他也有合影。他举了个例子:安部长,您知道吗?小先生看着傅总,他估计傅总最多也就是个混省城的,安部长这种级别的,估计能镇得住他。果然,傅总被镇住了。
傅总和小先生坐在鱼门驿公厕对门的餐饮桌上吹牛聊天,傅总请他喝啤酒。奇怪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鱼门驿这种专供过路客歇脚排泄的地方,却有啤酒卖。尽管,可供选择的啤酒只有一种。
傅总找来一个一次性软塑料杯,给小先生满上啤酒。小先生喝上一杯,更加兴奋了,除了吹牛,他还开始讲段子。比如有个鬼故事,讲凶杀案的。凶手试图洗掉衣服上的血迹,却怎么也洗不掉。最后死者看不下去了,为凶手推荐了某品牌的洗衣皂。这个段子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次,但经他讲出来的版本,是最好笑的。
傅总对青姐说,把小先生挖到咱们公司去。青姐说,您看不出来他就胡吹啊?其实他能有什么人脉?您别信以为真。傅总说,我管他真的假的,我想要这个人。这也是个人才啊,两千好几个名人的合影呢。傅总又说,我试过他的酒量了,一杯啤酒的量就开始讲段子。傅总迟疑了一下,稱赞说,讲得很好,尺度、分寸恰到好处,有氛围。
傅总还没跟青姐说完这话,小先生已经在公厕门口吐了。他不确定哪边是男厕,怕进错了,只好在门口就吐了。就这酒量去公关公司?但是小先生解释说,他晕车,正因为晕车,所以才不敢开车。
大鸿途公关公司的薪水比报社高,小先生毅然投到傅总麾下。傅总亲自挖来的人才,又是傅总的老乡,初来乍到的他得到不少女同事的青睐。但是,他很快办砸了两件事,不得不离开公关公司。
第一件事,小先生把大鸿途一个重要客户的真实收视率泄露给媒体。第二件事,他把大鸿途另一个更重要的客户的真实投资金额泄露给媒体。办砸第一件事的时候,傅总骂了他一顿。办砸第二件事的时候,傅总直接让他走人了。
小先生抱着小纸箱,收拾自己办公桌的时候,委屈巴巴地看着青姐:“青姐,傅总不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泄露商业机密。”青姐有点同情他了:“你没有泄密,媒体怎么知道呢?唉,我知道你和他们关系好,肯定是他们看你老实,套路你了。”青姐觉得可惜:“傅总挖你过来,就是看中你有媒体资源,结果你把这个优势反着用?”
小先生张了张嘴,没说什么。办第一件事的时候,他正和众媒体觥筹交错,一个男记者突然指着新闻通稿上的数据说:“不是吧?你这个收视率鬼才信。”一个女记者笑道:“你这夸大了一倍吧?”又一个男记者比画着手指:“八倍。”而另一个男记者喊:“十倍!”
他们喊数的时候,像极了拍卖会上的买家,口气坚定,声音响亮。小先生忙说,通稿上都是真实数据,大家又哈哈一笑。一屋子曾在同一跑道上的兄弟姐妹,此时有说有笑。这毕竟是酒桌,大概也只是说笑吧?
但惊悚的是,当天网媒出来的数据,就是通稿上的数据缩小了十倍,第二天的传统媒体,数据也惊人地一致。
办第二件事的时候,“拍卖会”再次上演。小先生冒着冷汗,找出了所有相关的新闻、通讯、评论文章,没有一条稿提到的信息源跟大鸿途有关。小先生没法找记者们要什么说法,因为稿件可以有其他信息源。
7. 东安里684号的门票
做不成记者,也做不成公关了,暂时待业的小先生找到了我。他说,去年清明节在鱼门驿见过我,当时和傅总是一起的。他问我有无印象。
小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策展人。他说,他是一名行为艺术家,现住在东安里684号。他想在那里办一场展览,而他那两千多张与名人的合影一展出,足以用来收门票。
小先生想成名,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想,但无论正道歪道,他都没有成名的资本。后来,追寻名人成了他的癖好。为了这个癖好,他不停地与名人合影。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跟名人的合影已经达数千张之多。他发觉,这是一场行为艺术!
我看着小先生,他有着谜一样的自信和神一样的思路。我决定先看看他的展品再回答他。
我去看过几次现场,东安里684号是一栋很老的别墅了。也许当年它曾经像一栋别墅,但如今却更像闹市中被租客们瓜分的一具残骸。
老别墅的门窗和黑漆栏杆对着巷子里的书店,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人来书店里买鲜花、面包和冰淇淋,也可以看到夹着手提电脑的年轻人来书店里喝咖啡。当然了,偶尔也会有人来买书。
老别墅的身后是一处安着健身路径的小院子。晴天,健身路径上遮满了老妇人们抱过来晒的被单和枕头胎。雨天,小院子里虽然没有被单和枕头胎,但大概也不会有人来健身了吧?
夜里,巷子里多数店面都齐门拉闸了。烧烤摊飘着烟,麻辣烫档冒着水汽,偶有酒瓶子破碎的声音在夜风中转瞬即逝。这里是小先生这位行为艺术家的深夜食堂。
进入小先生那间三十来平方米的出租屋之前,需要越过许多奇形怪状的木楼梯和窄通道,这可能会使参观者不满。小先生把拎着的外卖打包盒搁在楼梯扶手上,顾不上吃,就忙着替我打开房间门。
在房间,哦不,在展厅里,阳光从窗户外照射进来的路途并不平坦。它需要穿越梧桐树叶的层层障碍。它需要被削得支离破碎,然后斑斑驳驳地映在那面墙上。天花板上,某年新刷上去的白粉已经掉出一块“地图”来,边界上还有掀开了的、摇摇欲坠的墙皮。这也许会危害参观者的人身安全。墙上是密密麻麻的照片,照片与照片中间,是上一任租客以及上上任租客留下来的铁钉和挂钩。
尽管如此,房间里有香气,有隐隐的音乐以及迎面而来的和煦的风。有名的马拉松冠军在电台楼下等车,伸手一挥,似乎在跟远处的人说再见。著名的美食节目主持人在新酒楼开业剪完彩的空地上,颔首看着一个阿姨搬椅子。知名歌星的御用词人从人来人往的文体中心走出,后面跟着背吉他的年轻人。富甲一方的商人躺在椅子上献血,不远处是停在广场上的献血车。一名妇孺皆知的官员调整着自己的麦克风,他的背后是足球场和红横幅,横幅上写着“面向基层就业”几个大字。学术大师走下讲台,面向观众挥舞着双手。当红的女明星在背景布前摆着专业的姿势,双眼望着斜上方,神情忧郁而模式化。德高望重的心理学专家穿着与相声演员同款的长褂,正运用传统文化教人看淡一切。诲人不倦的成功学教父穿着齐整的黑白套装,营销着他的时不我待成王败寇……
在这些偶然与非偶然的画面中,小先生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他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背景物。
小先生倚在房间门口,手里端着麻辣烫外卖泡沫盒,吸溜着盒里的面条,以及整扎整扎的香菜,咸咸的酱油味儿飘满了整个屋子。
空有一个民国时期老别墅的文艺外壳,但这个现场真是十分不理想。
“可以,但是办展要经费,你得给我钱。”我说。小先生问:“经费都用在哪些方面?”
“包括做水牌什么的……”我漫不经心地说着,却被他打断了,“水牌?水牌有什么费用?不就一张纸?”我告诉他,我也要挣一点儿。
“挣我的?”小先生很惊讶。
“不然呢?”我波澜不惊。
小先生脸上浮起失落的神色,吸溜完最后一根面条,酱油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
8. 有一种艺术叫俯仰
我们的买卖谈成了。小先生終于成名了,他是一名行为艺术家。有一阵子,来看摄影展的人塞满了东安里684号。他们很快看完,很快便走了。他们没有购买门票。他们多是小先生的朋友或者朋友们的朋友。我看到,小先生的朋友还是不少的。
小先生向观展者讲述每一张合影背后的故事。故事或者励志,或者充满对人生的思考,总之,都饱含着关乎艺术或者哲学的意蕴。这些故事基本是真实的,但故事的意义则是我和他一起思索出来的。
在东安里684号热闹的日子里,也有来访者要求与小先生合影。是的,因为和许多名人合过影,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平台,一个概念平台。于是,便有了要和小先生合影的人。尽管我们在小先生和名人的合影中,看到他总是笑容满面,但在他与观展者的合影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笑容。这种笑容似乎在宣告,他把合影这件看似毫无意义的事做到极致了。
在不久之前的人生低潮期,小先生想证明自己的欲望强烈到了极点。他几乎逢人就说,他见过某某某,采访过哪个人,又和谁谁谁合过影……这种啰嗦重复、麻木无神使他像极了男版的祥林嫂。嘴里的璀璨过往和他低潮期的真实处境形成了刺目的对比色。也正因这种强烈的欲望,他没有犹豫太久就应下来我开的价钱。
不过,名气和其他气体略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流动不定。
作为一名行为艺术家,这个行为结束了,下一个行为是什么?想好了吗?作为一个尚未构建起盈利模式的行为,下一笔办展经费在哪里?想好了吗?小报记者出身的小先生,想必也懂得这些道理。作为一名行为艺术家,小先生紧握着左手中的“行为”、右手中的“艺术家”,它们却正从指缝间流走,像握不住的气体一样。
我给小先生提供了一些思路,并不新颖,甚至有点老套。我告诉他,有的艺术家拍了许多个不同的笑容,以展现不同处境中的明媚人生;有的拍了许多双不同的眼睛,以展现不同视角下的风景;也有的拍了许多双手,以展现辛劳与收获;或者拍了许多双脚,以展现跋涉与远方。你,仍是去拍许多不同的人吧。和名人相对应的,是留不下姓名的甲乙丙丁。你去和他们合影吧。
有一种艺术,叫俯仰。
这么一说,似乎很有道理,但并不准确。仰望是仰望了,大家对上都有仰望之心,倒也不必讳言,但是俯视呢?小先生能俯视什么?
我和小先生站在平坦的大地上,人群川流不息。夜,他睡在用书本砌起来的“榻榻米”上。由于有一些新书还没有开封,吸塑包装经常在他翻身的时候就滑掉了一角。日,阳光被风吹散,柔和地照在环保袋材质的衣柜上。睡的、用的、吃的,住所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临时,就像那不被提倡的一次性杯子。
从生理年龄来看,小先生不小了。许多比他小的男青年,都有着自己的成就。但从心理年龄来看,他似乎还是一位小先生。生活或工作,一切都显得那么临时。这种临时暴露出他的一无所成,但也透露着那种乾坤未定的萌动。
9. 这次没有摆拍
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小先生接受了我的思路。为了和货车司机合影,他先偷拍了一位五官很耐看、表情很亲和的司机师傅。在那个车来车往、人声喧哗的城乡接合部工业区,他表现得像个欠揍的路人甲。司机师傅把烟头一吐,紧起眉头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合张影。司机师傅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跟他说:“老板你如果有货就上平台下单。”
说完,货车响起了威严的倒车警示音。那倒车的声音告诉他,此时强行合影,比面对名人的八个警卫要危险。
车开走了,小先生向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货车司机“下手”,仍是没有“得手”。他有点意外,怎么跟货车司机合影,比跟名人合影还要不顺利一些?然而,对于名人来说,与仰慕者合影已经是不成文職责的一部分,他们习以为常了。与他们合影,看似有阻力,其实门是敞开的。但对于货车司机呢,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和小先生合影。
近黄昏了,工业区的美食街上袅袅升起人间烟火气。沙县小吃、隆江猪脚、原味汤粉、化州糖水们像雁阵一样,一字排开。市井之声飘浮在渐渐密集起来的灯火中。小先生有主意了,和快餐店的老板们合影,也一样很有意义的。然而,快餐店的老板并不觉得和小先生合影有什么意义。
汤粉店的老板忙得飞起,没听清楚小先生想干什么。每次小先生一开口,总有其他的顾客杂七杂八地喊着:“我要七块钱的”“我要十块钱的”“我不要放辣”“我的两个辣一个不辣”“我的是细粉”“我两个宽面一个细粉”“一个细粉大碗,一个细面中碗,一个宽面不要辣”……
小先生的声音被淹没了,然而记忆超群、天分过人的汤粉店老板仍然目无遗留地注意到他,并向老板娘说了声:“你问问他想干啥?”
脾气不好,也没有耐心的老板娘并没有问小先生想干什么,只是在一个小姑娘拼命喊着“我要的是小碗!小碗!”之后,把那份没人要的中碗端给了小先生。小先生有点莫名其妙,就像老板娘看小先生同样也是莫名其妙。老板娘用一句“这碗不用钱”加剧了这种莫名其妙,并意图结束小先生这一天的努力。
小先生一边吃着“中碗”,一边上货车平台下单。他没有货,但他打算为一次合影埋单。然而,当他看到数额并不算大的估价时,手指在手机上划了两划,退出了。从前,他为了和一位名人合影,曾经自掏腰包买下相当于半个月收入的门票。在他沾沾自喜说出这段经历时,友人给了他一个大拇指,而家人给了他两个白眼。如今,拉货估价远没有当初的门票高,但他退出了。毕竟,此时的他作为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小先生扫码付了“中碗”的款,就走了。他没有再纠缠汤粉店的老板,但是老板那句“你问问他想干啥?”却留在了他的脑海里,成了一句禅语。他品,他细品。
小先生接触过许多名人。名人谈人生,谈经验,基本都是专业的。名人的许多“成功经”,都很有道理,但小先生却找不到使用说明书。他又打开了那个拉货的手机APP平台,像玩游戏一样,玩了许久。
由于经费没到位,我们的合作黄了,后来就没联系了。最近一次路经鱼门驿,我又遇到了小先生。他从一辆货车上下来,由北往南走。我从省城回老家,由南往北走。我们在驿站休息,他递给我一支矿泉水,自己也咕咚咕咚地仰着脖子喝水。
我问小先生:“我记得你是晕车的?你说因为晕车所以才不敢开……”他把瓶盖拧上,接着我的话说:“自己开就不晕了。”
我问小先生:“以后我们还合作吗?”他说:“以后有机会吧!”他接着解释,那个我曾经提议的“俯仰系列艺术展”,现在“俯”的部分,他只攒了20张不到的合影。这些合影从他和他的同行货车司机开始,然后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小先生又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矿泉水,把空瓶子往垃圾箱里一丢,从手机里翻出照片给我看了。那20张不到的合影,却几乎覆盖了一条产业链的代表性符号。
不同的是,小先生和与他合影的人不仅在照片中存在联系,现实生活中他们也是打着交道、不离彼此的。这些照片,都是有小先生参与其中的真实“活场景”。它们的优秀之处在于,看起来没有一张是摆拍的。
小先生继续解释,他还是很希望“俯仰系列艺术展”能够出来的,不过,要等一等,等他的照片攒得再多一些。这在短时间内是完成不了的,他希望我有耐心。我们聊得不多,便又分手。我上了车,从鱼门驿由南往北走;他也上了车,由北往南走。
我看了看后视镜,小先生奔前程去了。
责任编辑 张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