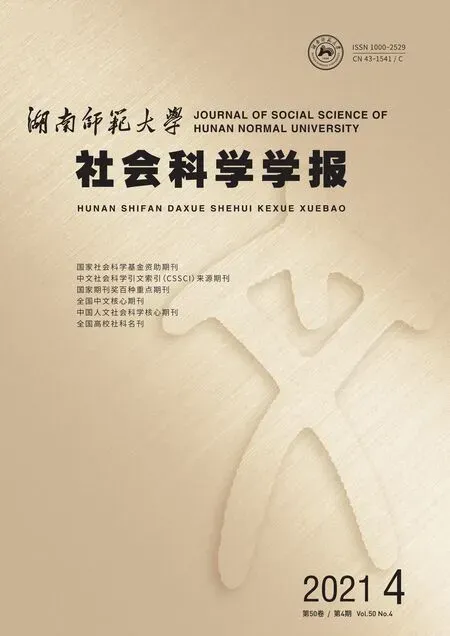互斥与流动:国内嘻哈歌手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
马中红,杨风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纽约布朗克斯孕育成型之后,嘻哈在诞生之后的头十年里几乎没有受到来自流行音乐工业的任何干扰,他经历了相对独立发展的一个年代,成为独特的文化艺术潮流运动。嘻哈包含了说唱(饶舌)、打碟(DJ)、街舞、涂鸦四大早期元素和beatbox、嘻哈服饰、街头篮球等新元素。20世纪80-90年代嘻哈传入国内之初,完全模仿美国黑人嘻哈的风格,歌词中充斥着滥交、吸毒、暴力、酗酒、歧视女性等主题,饱含着抵抗、愤怒和反叛情绪,因而,导致嘻哈文化在中国一度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于“地下”状态[1]。变革出现在2017年,随着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①的走红,部分嘻哈歌手在娱乐资本包装下,迅速从“地下”转向“地上”;嘻哈文化也借此“出圈”,进入公众视野。当嘻哈文化风头正劲时,夺得2017年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冠军的歌手PG One(王昊)“夜宿门”事件以及《圣诞夜》风波②将嘻哈歌手推向风口浪尖。《人民日报》发文批评PG One,认为其作品无筋骨、缺道德、没温度,无法获得大众认可,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2]。新华网也指责其“低俗当不了个性,恶名换不来资本……这样的歌手,不尊重行业和观众,传播不了和平与爱”。与此同时,其他嘻哈歌手生活混乱、思想偏激、高调猖狂等个人问题被相继曝出。在负面报道集聚所引发的“道德恐慌”下,公众逐渐从娱乐狂欢中回归理性,反思嘻哈文化可能潜在的社会危害及消极的示范效果[3]。政府管理部门在之后更是明确提出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要做到“四个坚决不用”,即品行不端、低俗媚俗、思想境界不高、有污点和绯闻的演员坚决不用,着重从道德层面对演艺人员提出了要求[4]。
由嘻哈文化在国内发展的简要勾勒来看,嘻哈歌手形象经由二次转译而生成。首先,嘻哈文化是美国青年亚文化的舶来品,从流入国内伊始就被标榜为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消极存在。其次,大众媒体遵循主流社会价值评判标准,有选择地对嘻哈文化加以报道,呈现出正反二元对立的媒介形象,而较少考虑嘻哈歌手作为主体的媒介实践。换言之,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为研究者所忽略。那么,嘻哈歌手有着怎样的媒介实践?他们如何想象和建构自身的媒介形象?嘻哈歌手的媒介实践与广阔的社会动因有何关联?这需要我们打破大众媒体“他建”形象的囹圄,从嘻哈歌手的日常媒介实践去考察他们自我媒介形象的塑造,这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路径。
二、文献与理论
媒介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媒介,人类可以认识自己和历史。“媒介把世界带给了我们并塑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依然存在一个外在于媒介的真实世界。区分真实世界和媒介世界变得越来越困难。”大量研究大众媒介建构的文献就是试图帮助人们认知媒介世界是如何经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而被制造出来并发挥作用的。对大众媒介建构社会的宗旨有“共识论”和“冲突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媒介世界促进社会共享某种意义,并创造或使文化增值和交换;后者则强调共识模式通常是在维护现有社会的不平等和生活方式。具体到媒介建构嘻哈歌手形象,可供参考的有效文献并不多。一项建立在国内新闻媒体对说唱文化再现的研究结论显示,大众媒介建构出一种理想化的公众人物形象,这与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嘻哈歌手的负面形象构成明显反差,与嘻哈文化原本反叛的亚文化精神不一致。另一项基于新闻报道、电视节目的海外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建构的嘻哈形象充满暴力倾向、仇视同性恋、厌恶女性[5]。而关于嘻哈歌手形象的媒介自我建构,国内文献尚未涉及,海外文献中有通过对嘻哈歌手社交媒体的定性分析,揭示出嘻哈歌手反对种族歧视、不满政党统治的叛逆形象及其寻求身份认同的自我表达[6]。无论如何,媒介建构世界,或特定对象的媒介建构议题几乎是媒介世界最主要的研究内容,覆盖了不同个人、群体、区域、城市和国家的形象建构与传播。与此相反,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研究付之阙如,此情形可简单明了地归因于个体媒介表达权的缺失。
数字媒介赋权给普通用户记录、传播和表达之后,个体自塑形象的媒介实践和“媒介形象自我建构”方破土而出。这里所谓的“媒介形象自我建构”指网络用户基于网络媒介的特性有意识地展开个人媒介实践以塑造个人形象,与大众媒介形象建构的差异在于:其一,自我建构的媒介实践基础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性、共享性的数字媒介,而非自上而下的中心主义的大众媒介。其二,以个体为中心的表达和表演,“媒体不再只是人们用来认识世界的一种渠道,也是用来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认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渠道。”[7]其三,自我建构的形象存在解构社会、媒介等“他者”形塑的社会刻板印象,有利于重新塑造新的媒介形象,或补充和修正原有媒介形象。网络用户自拍、晒图、表情包成为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实践者,自拍“其实是把自己变成客体进而进行审阅,然后得出对‘自我’的一种判断,进而‘主体性’被建构起来”[8]。而如此建构的自我形象被认为是重塑的理想化自我。彭兰的研究表明,网络自拍、晒图是自恋表现,也是个人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表达了理想自我的设计,另一方面,假想的‘他者’的眼光时时会干扰着个体”[7]。与此相仿,越来越多的“地下”青年亚文化,如滑板、涂鸦、嘻哈,越来越不愿意身处“地下”,任由大众媒体涂抹他们的形象,如今,他们更热衷于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发声”,不只如麦克罗比和桑纳特所说的那样,亚文化只想通过媒介在大众面前为自己“正名”或“自卫”,媒介对亚文化的影响也不只停留在表面,相反,现有青年亚文化实践与媒介关系越来越紧密,亚文化实践就是媒介自我建构的实践。
在福柯看来,自我建构是支配技术和自我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社会已经将个人置入了惩戒性的、规范化的、全景监控的权力牢笼之中,支配性权力技术通过运用规训手段来对个体行为进行定义与控制,使其服从并达到特定目的,从而使个体进行温顺的实践活动[9]。而自我技术是个体以目的为导向,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对个体身份进行确定、保持或改变的手段[10],是个人依凭自己或别人帮助,通过诸如书写、通信、直言等自我技术,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以及存在方式施加某些特别的操作,从而完成创造理想自我的技术。比如,福柯对“个人笔记本”作为自我书写形式加以讨论,认为“个人笔记本”能够使个人的灵魂摆脱担忧未来,转而朝向沉思过去,“在福柯看来,个人笔记本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的折中表达方式,因此它隐含着个人的选择取向,从而可解释为自我建构/自我创造。”[11]深度媒介化时代,个人书写自我、建构自我的媒介前所未有的丰富,尼克·库尔德利称之为“媒介多元体”,我们使用的是越来越彼此连接的多元媒介,而不是单一媒介,甚至个人就是媒介的组成部分,并被嵌入了复杂的网络体系中,个体的自我媒介形象建构成为“跨媒介叙事”的文化实践。所谓“跨媒介叙事”,亨利·詹金斯认为“一个跨媒体的故事横跨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一个平台都有新的文本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的、有价值的贡献。每一种媒体都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媒介既可以独立叙事,也存在因果关系。个体的跨媒介叙事可以理解成参与者将故事文本通过多种媒介形式呈现,从而全方位地将自身展示/表演给受众,目的是立足于自我需求,借助媒介的差异性选择跨平台完成自我表达和整合媒介形象建构。
三、研究设计
本文以《中国有嘻哈》的参赛选手为研究群体,以内容分析的方法探究他们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考虑到代表性的问题,又将研究范围缩小到第一期至第四期(2017—2020年)的十二强选手,共48名。在考察了48名选手微博发文和抖音视频的数量、可查阅时间及原创歌曲数量后,最终将研究范围锁定在其中的22名选手(如表1所示)。之所以选择微博贴文、抖音视频和歌词这些跨媒介叙事文本作为考察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信息丰富,受众关注度高。微博发展至今成为国内娱乐业大本营,微博“弱关系”特性和平台技术鼓励陌生人连接以及信息发散性流动;抖音平台对音乐效果、视觉化传播、娱乐化的追逐吸引嘻哈歌手入驻,两者均以信息广泛和共享著称,主打全民传播,用户在平台有相对自由的表达权。其次,自我表达更加真实。歌词是嘻哈歌手所特有的“自我书写”方式,是其情感状态、生活处境和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故事化表达所流露的情感更为真切。在研究22名选手的微博、抖音和歌曲后,共搜集微博发文30 933条,抖音作品799条,歌曲393首,在剔除内容重复和无明确意义表达的文本后,最终选取样本数量如下:微博28 130条,抖音760条,歌曲377首,样本总量29 267条。

表1 研究对象及样本数量
本研究以AIO模型为类目建构基础,该模型由美国学者Wells和Tigert对生活方式的内涵做出规范后提出,主要从活动(Activity)、兴趣(Interests)和观点(Opinion)三个维度来测量消费者的个性、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并设有工作、业余爱好、社会活动、度假、娱乐、购物、运动、时尚服饰、环境、社会问题等36个子维度[12]。AIO模型综合了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生活型态研究,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型态来了解其生活方式的全貌[13]。AIO模型的内涵与英国文化社会学家费瑟斯通的生活方式理论不谋而合,费瑟斯通认为:“生活方式指特定的地位群体生活的突出风格,隐含个性、自我表现和风格的自我意识。个人的身体、衣服、言谈、业余消遣、饮食爱好、住房汽车、对度假的选择等都被认为是占有者/消费者的趣味的个人性和风格意识的指标。”[14]也就是说,随着消费主义社会的深入,个人的生活风格、活动形式、行为特征能够充分显示其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是个体自我形象建构和呈现的重要方式。此外,本研究还依据框架理论来进行类目建构。学者黄旦指出,框架理论的重点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了人们对之的理解。框架理论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怎样反映现实,如何构建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15]。因而,文本的建构、诠释或话语生产分析对于理解文本生产者的思想和主张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根据嘻哈歌手的跨媒介文本内容,可设置七大分析类目,分别是叙事主题、着装风格、装饰物品、背景呈现、休闲娱乐、身体展示、言谈举止,每个类目下又设有若干子类目。
(一)叙事主题
叙事是文本分析的核心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叙事者价值立场的最终呈现,能较好反映出嘻哈歌手的媒介形象。本文通过提取文本关键词作为叙事主题这一变量而建构了以下16个类目:(1)人生奋斗;(2)怀旧;(3)感恩;(4)文化传承;(5)家国大业;(6)社会公益;(7)黄赌毒、性爱、暴力;(8)拜金;(9)抵制商业化;(10)揭露社会问题;(11)反思嘻哈文化;(12)商业宣传;(13)为嘻哈正名;(14)吐槽;(15)自我展示;(16)弥补过错。叙事主题对应的情感表达、主张或目的可归纳为:讴歌奋斗、坚持梦想,感慨人生,感恩亲友和粉丝,热爱传统文化,爱国爱家,关爱弱势群体,回忆青春,反社会、反主流,歧视女性,崇尚暴力,热爱金钱,反对嘻哈音乐创作的商业化,抨击社会黑暗面,追求嘻哈自由、独立、叛逆的音乐本质,爱岗敬业,对舆论表示不满,炫耀自我的音乐才华,对过错表示歉意等。
(二)着装风格
根据微博和抖音的图文及视频,嘻哈歌手的服装风格特点共设置10个类目:(1)嬉皮;(2)嘻哈;(3)朋克;(4)街头;(5)中性;(6)简约;(7)优雅;(8)气质;(9)国风;(10)其他风格。
(三)装饰物品
嘻哈歌手的身体装饰物设置10个类目:(1)脏辫;(2)金链;(3)戒指;(4)墨镜;(5)耳钉;(6)嘴钉;(7)舌钉;(8)手表;(9)其他装饰;(10)无装饰。
(四)背景呈现
嘻哈歌手微博、抖音发文中的图片或视频背景选择通常是有意为之,虽然比较隐晦,但往往能够表达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价值主张,对于考量其媒介形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为背景变量设置了如下14个分析类目:(1)酒吧;(2)夜店;(3)健身房;(4)演唱会现场;(5)宾馆;(6)家;(7)工作室;(8)商场;(9)参赛现场;(10)车站、机场;(11)商业活动现场;(12)书店;(13)书画展;(14)歌剧院。
(五)休闲娱乐
本文为休闲娱乐设置了11个类目:(1)文体活动;(2)棋牌麻将;(3)喝酒、抽烟;(4)蹦迪、K歌;(5)飙车;(6)逛街;(7)旅游;(9)诗词歌赋创作;(10)古典音乐赏析;(11)观看歌剧。
(六)身体展示
本文为身体展示设置了4个类目:(1)文身;(2)肌肉;(3)胸部、臀部;(4)其他部位。
(七)言谈举止
本文将言谈举止拆分为言谈和举止两个方面进行类目构建,言谈即为嘻哈歌词文本中的用词特征。举止在这里特指嘻哈歌手的招牌手势,即惯用动作,招牌手势是嘻哈歌手身份认同和风格展示的标配,目的是用来展现个性、扮酷装帅,又或是有其他特殊意指,本文为言谈举止这一变量设置了6个类目:(1)讽刺;(2)侮辱;(3)耍酷;(4)鼓励;(5)助威;(6)其他。
嘻哈歌手的着装风格、装饰物品、背景呈现、休闲娱乐、身体展示和言谈举止所对应的情感表达、主张或目的可归纳为:彰显个性,对父辈或主流文化的抵抗,叛逆情绪的表达,自我调侃,炫耀财富,炫耀圈子、人脉,展示才华,重情重义,追求自由、纯真的生活状态,讽刺、侮辱对手,抒发无聊情绪,热爱生活,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等。
四、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特征
(一)嘻哈歌手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类型
正如戈夫曼所言,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行动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运用某种技巧,选择适当的言辞、表情或动作来表演自我、制造印象,使他人形成对自己的特定看法,并据此作出符合行动者愿望的反应[16]。表演过程有着清晰的前台和后台之分,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或社会所接受的刻意加工过的形象。后台,则往往是“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16]。在戈夫曼看来,前台和后台是相对的,是特定语境中作为参照物的存在。前台也并不是具体物理空间固定的场所,而是受到客观世界规训后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的产物,后台就是脱离规训后的一种非制度化的产物。这种在规训中形成的制度化产物,仍然对人们在网络中的角色扮演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17]。网络空间的崛起,颠覆了人际交往中面对面的互动方式,网络空间所具有的真实、虚拟、流动、隔离与连接等特性[18],延伸了人们的生活场景,前台与后台作为隔离观众的地理分界线被打破,因而网络空间中的前台展演和后台展演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反而多了几分混杂,使得真实性呈现与表演性呈现交织在一起。
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本质就是通过媒介进行的自我呈现,以控制他人对嘻哈歌手的反应,即“印象管理”。戈夫曼认为,印象管理的策略有四种,即理想化表演、神秘性表演、误导性表演和补救性表演[16],本文在借鉴戈夫曼印象管理策略的基础上,将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策略分为塑造崇拜、制造神秘、产生误导和真实流露四种类型,与之对应的四种媒介形象特征分别是理想型自我、神秘型自我、本真型自我、悖反型自我。
1.理想型自我
在嘻哈歌手的媒介自我建构中,理想型自我是最常见的一种表演模式,目的是通过“晒”各类图片、言行以及相应的场景来提升自我形象,拔高人设。嘻哈歌手理想型自我的媒介形象主要有两类:理想公众人物和理想个人形象,出现频率分别占38.38%和7.23%(见表2)。理想公众人物形象表现为爱国、热爱传统文化、热衷公益、奋勇拼搏、爱岗敬业。其中,尤以爱国形象最为典型,通常当国内发生重要意识形态事件或国际政经要事时,表现更为突出。以“抵制新疆棉花”事件为例,嘻哈歌手的叙事主题集中表现为“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支持新疆棉花”;着装风格以简约、国风为主;装饰品以印有国旗的手环为代表,图片或视频背景呈现为五星红旗、李宁专卖店、新疆棉花等;身体展示通常表现为印有国旗的脸,再加上紧握双拳的助威型手势。理想的个人形象则以才华出众为代表,这一媒介形象塑造的语境大多为演出和出席重大活动,叙事主题围绕嘻哈歌手的“专辑宣传”“才艺展示”“公益活动”等;着装风格以优雅、气质为主;装饰品中突出展示时尚手表;背景基本上是颁奖典礼现场、演唱会现场、公益演出现场;休闲娱乐通常是歌曲创作、演唱练习等;手势多为鼓励性的握拳。由此可见,在嘻哈歌手理想型自我形象塑造中,其建构的媒介形象展现出的是一种具有示范效应的正面形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效能。嘻哈歌手理想型自我塑造的是一种“超我”的存在,他们以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戒律和自我理想为标准,并在此框架内建构出理想的自我形象,以此获得公众认可。

表2 理想型自我的媒介形象
2.神秘型自我
不同于理想化自我形象所展示出的品行高洁、才华出众,嘻哈歌手神秘化呈现往往是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审美和趣味。主要有品位高雅和神秘莫测两类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出现频率分别为6.52%和2.81%(见表3)。品位高雅的媒介形象其叙事主题以参与书画展、出席音乐会、观赏戏剧表演为主;着装风格展现出气质、优雅、简约的特点;装饰物以手链和手表为主;背景以书店、书画展、剧院居多;而在身体展示和言行举止方面则没有明显表现,彰显出嘻哈歌手高雅品位或者技高一筹的能力,借此与普罗大众拉开距离。神秘莫测形象,主要通过制造猜疑,使受众产生猎奇心理。在微博发文和抖音视频中,嘻哈歌手往往以一反常态的服饰、背景以及诱导性的言辞制造神秘感,让受众“想入非非”。相比于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神秘化自我形象更具有戏剧性和艺术性。

表3 神秘型自我的媒介形象
3.本真型自我
本真型自我与嘻哈文化原初的文化精神相一致,也与嘻哈歌手的本真个性相关联。一方面,嘻哈歌手遵循享乐主义原则,展示自我欲望和情感需求,折射出唯乐至上、趋利避祸的人性本质;另一方面,嘻哈歌手展示出一种理性的、反思的社会批判者形象。嘻哈歌手本真型自我的媒介形象主要有反主流的生活方式、斗士、挣扎这三类(见表4),出现频率分别占到14.25%、5.38%和18.64%。反主流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嘻哈歌手对主流社会和主导文化怀有抵抗心理和不满情绪。

表4 本真型自我的媒介形象
其次是极为严重的“拜金主义”,如歌曲《市中心》唱出了嘻哈歌手对名利的疯狂追逐,对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的吹嘘,将歌词作者有钱就能获得权力和幸福生活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展现得一览无遗。
再者,表现出对女性的极端歧视和污辱。歌曲《圣诞夜》中的“晚上吼”“纯白色粉末”“酒吧”等词汇,建构出滥交、吸毒、下流的媒介形象。所作所为均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风尚相背离。此外,歌词作者还将女性视作男性附属品,或是可进行交易活动的商品,充斥着对女性的诋毁情绪。
嘻哈歌手反主流生活方式的媒介形象从叙事主题来看,可归纳为酗酒、吸毒、滥交、打架斗殴、炫富、享乐;着装风格以朋克、街头、嬉皮等个性化、夸张的服饰为主;装饰物多为脏辫、金链、墨镜、耳钉、嘴钉、舌钉;背景杂乱,有街头、夜店、赌场、宾馆、洗浴中心;休闲娱乐的方式则表现为抽烟、喝酒、蹦迪、闲逛、赌博、购物、飙车、旅游、K歌;身体展示通常为文身,以及胸臀等私密部位;言谈举止中频繁出现侮辱性的污言秽语和讽刺性手势。
与反主流生活方式的媒介形象相映成趣的是嘻哈歌手的“斗士形象”。这些自我建构的形象充分体现出嘻哈文化的原初精神,即叛逆性和批判性。首先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如歌曲《豫盖弥章》对南昌豫章书院以帮助网瘾少年戒网瘾为由,残害青少年身体健康为实的揭露和抨击。“铁棍”“没有光线”“凶光”“割手腕”等歌词将施暴者的凶相和受害者的绝望描述得淋漓尽致,透露出对豫章书院恶行的愤懑与痛斥,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父母失责的问罪。其次回击大众对嘻哈的污名化,力图为嘻哈音乐正名。嘻哈歌手拒绝承认嘻哈是堕落者释放负面情绪的传声筒,反而将其视为一种连接表达和经验的艺术,帮助年轻人直面困难,敢于逐梦,勇敢表达自我。嘻哈歌手斗士形象叙事主题集中体现在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问题、为弱者发声、为嘻哈正名;装饰品突出表现为脏辫、金链、墨镜和耳钉。
嘻哈歌手的挣扎形象通常在抵抗商业化和遭受不公待遇的语境中得以呈现,主要表现为嘻哈歌手对嘻哈文化本土化发展的反思和质疑。他们处于追求自由、独立、反叛的嘻哈精神和迎合商业化的夹缝中,不知道如何找到平衡点。正如嘻哈歌手在歌曲《阴暗面》中表达的那样,为了赚钱,歌曲需要迎合商业市场,但自己却不想一味迎合大众品味而将嘻哈变成纯粹娱乐化的消费品,想坚守嘻哈的精神内核,内心充满矛盾和纠结。嘻哈歌手这种挣扎形象的话语建构是从歌词的叙事主题、背景呈现和休闲娱乐三个方面进行的:叙事主题多为反思嘻哈本土化发展、对嘻哈的商业化表示不满、对嘻哈创作方向的困惑;图片或视频中的背景通常是工作室;休闲娱乐的方式则以抽烟为主。
4.悖反型自我
模块能够提供公司应急预案信息的录入、修改、删除等功能,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新增或修改将公司应急预案信息提交到后台数据库中,也可将不再需要的信息进行单独和批量删除。
如果说理想型自我、神秘型自我和本真型自我之间虽然建构出的媒介形象有矛盾、断裂和混乱之嫌,但自我建构者的前台表演却是言行一致的。与此相对,悖反型自我往往呈现出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展演,而这种展演通常是无意识的。悖反型自我的出现频率为6.79%。表演者在畏惧后台“自我”为人所知时,前后台呈现出悖反的极端表演。具体到嘻哈歌手的媒介自我形象建构,通常表现为微博、抖音中的图文不符,例如微博文字表达的是爱护环境、保持清洁的主题,但图片中出现的却是脏乱差的背景;又如抖音视频中文字表达的主题是勤俭节约的主题,但视频中呈现的背景却是超级购物中心、豪车和高档酒店。

表5 悖反型自我的媒介形象
(二)嘻哈歌手不同媒介自我形象建构的差异
嘻哈歌手在微博、抖音、歌词这三类媒介中塑造的形象类型有一定的趋同性,除了歌词中仅出现理想型自我和本真型自我两种形象外,微博发文和抖音视频所建构的媒介形象完整涵盖了理想型自我、神秘型自我、本真型自我和悖反型自我这四种类型。此外,差异性也同样存在,如图1所示,嘻哈歌手在微博上建构的形象以理想型自我为主,占到62.23%,神秘型自我、本真型自我和悖反型自我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理想型自我,说明微博被嘻哈歌手重点用于正面形象的塑造,因而在微博上倾向于展现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品行高洁的一面,具体形象表现为爱国、热爱传统文化、热衷公益、爱岗敬业、奋勇拼搏,旨在起到积极正面的示范效应。抖音建构的形象是以理想型自我和本真型自我为主,分别占到49.45%和35.64%,就理想自我而言,嘻哈歌手在抖音塑造的媒介形象偏向于理想化的个人形象,具体表现为才华出众、顾家、自律;本真型自我是以夸张的着装风格和装饰、豪华奢侈格调的背景呈现、抽烟喝酒等放荡不羁的休闲娱乐以及露骨的身体展示呈现出一种拜金、叛逆的媒介形象。由于歌词是以文字为存在形式,没有图片和视频作为考察对象,因此只能从中梳理出理想型自我和本真型自我这两种媒介形象,两者的占比分别为29.82%和70.18%。理想型自我的媒介形象具体表现为奋勇拼搏、热爱传统文化,本真型自我则表现为反主流的生活方式、斗士以及挣扎的媒介形象,是嘻哈歌手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

图1 各媒介自我形象建构差异
(三)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变化
理想型自我、神秘型自我、本真型自我和悖反型自我在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中出现的频率差异较大,其中以理想型自我和本真型自我的再现最为频繁(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嘻哈歌手在媒介形象自我建构中,更倾向于塑造理想型和本真型的自我,两者占比分别达到了45.61%和38.27%,神秘型自我和悖反型自我则分别占到9.33%和6.79%。与大众媒体新闻报道中建构的说唱文化形象正反二元对立的形象类型不同,嘻哈歌手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更为丰富多样,尤其是神秘型自我和本真型自我两大类型所包含的个人形象的品位高雅和神秘莫测,以及形塑反主流的另类生活方式、敢于直面和挑战社会不平、挣扎在追寻嘻哈本真和为生活所困的夹缝中,是大众媒体鲜有涉及的。

表6 嘻哈歌手自我呈现类型
为进一步了解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变化特点,我们引入时间变量进行考察,并对各类媒介形象重新编码(表7),依次为A、B、C、D、E、F、G。考虑到2017年是中国嘻哈文化首次登上综艺大舞台,在商业资本加持下成功“出圈”,那么,在“地下”到“地上”转变过程中嘻哈歌手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是否发生了变化?本研究以2017年为节点,分别往前、往后各推进3年,以2014—2020年嘻哈歌手的微博发文和歌词为分析对象③。
如图2所示,嘻哈歌手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表现出三类趋势:其一,积极正面的理想化形象和强调个人才华的形象与时俱进,显著增强;其二,反主流生活方式、拜金、歧视女性的媒介形象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其三,挣扎、纠结、矛盾的自我形象随着时间推移明显增多。

图2 嘻哈歌手自我形象建构时间纬度的差异
2017年以前,嘻哈歌手基本处于“地下”生存状态,圈子小,影响力弱,其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偏向于反主流、拜金、歧视女性。这与嘻哈歌手作为边缘群体被排斥在社会主体结构之外,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关,当他们无法抵达社会主流价值观崇尚的有关体面工作、财富自由以及成功人生的定位时便会产生“地位挫败感”以及紧张、不满、内疚、焦虑等情绪[19],因此,他们在歌词中常常通过类似支配女性、对抗社会、追求财富的越轨性表达,想象地满足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随着嘻哈文化登上大众舞台,跻身商业流量大潮中,嘻哈歌手在“地下”积攒的亚文化资本逐渐转化为经济资本,乃至社会资本,在初步完成财富自由和地位提升后,嘻哈歌手转向微博、抖音等平台,展现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重塑乐观、阳光、快乐的自我形象,力图摆脱大众媒体和社会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2017年以来,随着嘻哈文化走红,嘻哈歌手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对嘻哈文化的本土化发展感到困惑和迷茫,突出表现在嘻哈歌手挣扎、纠结、矛盾的媒介形象呈现上,这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
五、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权力关系
深度媒介化意味着深度社会化,自我的社会性越来越强,人们被要求不断地展示自我/表演自身,频繁地管理自己的日常形象。库尔德利探讨在线自我形象管理时,认为在数字化媒介世界和新的社会关联中,个体被强迫在平台上进行生产、展示、表演和互动,用不同的平台展现自我的不同层面。数据记录、挖掘技术使个体能依靠自己的数字足迹管理个人行为,调整自我形象的建构。自我的建构越来越依赖于外在媒介,即“社会化的自我建构”,任何个人、群体和文化都被卷入其中,必须学会对自己进行媒介化的展示,建立社交网络。展示成为我们管理自己“私密人格面具”和“公共人格面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用来解释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时的不同面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继续追问的可能性,即我们管理自身、展示自己、建构自我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我们是完全自由地想象和建构自我的媒介形象,还是受哪些社会化力量的左右?
(一)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力量
嘻哈歌手活跃在互联网各类社交媒体和平台中,本文重点分析的微博、抖音以及歌词文本是跨媒介叙事中比较典型的媒介类型。不同的媒介类型各自独立,又彼此勾连,成为形塑嘻哈歌手与“媒介多元体”[20]的总体关系,是嘻哈歌手的“连接性存在”,即需要为自我形象不断输入越来越多的、持续不断的信息,并向所有人永久性开放,维持潜在性回应的态度。微博的本质是开放的,既连接熟人,也容纳陌生人。抖音也是如此。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得益于开放性,也受之于开放性。微博和抖音的友好界面,创造了方便接收和转发的信息流,个人有创造和使用信息的较大自由度,为嘻哈歌手自我表演、展示身份、开发公共形象或准公共形象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使这两个平台中的自我形象倾向于理想化的公众形象和理想化的个人形象。与此同时,微博生态中的一级生产者④构成复杂,表现为文本生产者⑤中不仅有一般用户,还有众多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这意味着嘻哈歌手的微博叙事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的凝视。此外,微博作为媒介融合产物,具备多元化的媒介功能和传播手段,热搜、置顶、算法推送、@功能等技术因子强化了微博的曝光性,高话题度和高关注度,为嘻哈歌手摆脱边缘处境,走向公众视野提供了途径,因而在微博的媒介形象自我建构中,嘻哈歌手倾向于呈现一种理想化的公众人物形象。不过,“大规模的展示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互相监督立下了规矩,把日常的行为和表现转换为景观和观景。”[20]具有归档功能和记忆功能的互联网平台,不只成为自我形象建构时的“镜像”,内化“他者”的监督,同时,也成为可追踪的工具,对嘻哈歌手建构的自我形象形成威胁,PG One人设崩塌便可佐证。
与微博和抖音不同,歌词属于开放性和互动性较弱的媒介,更为注重文本生产者的自我表达,受众无法直接参互其中,因而是一种具有“私密人格面具”的媒介类型,能更好地传递嘻哈文化本真意义和嘻哈歌手的个体化情感。“嘻哈词曲分家的做法不是一种倒退,歌词和旋律的脱节恰恰为这两种音乐元素各自独立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21]嘻哈强烈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取向是通过歌词传递的,因而历来被视为嘻哈的灵魂,嘻哈的精神。同时,嘻哈旋律和说唱特点使歌词具有模糊性和隐蔽性,使那些与主流文化相区隔的内容得以“逃脱”公众视野,在小众群体中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嘻哈歌手真实自我的表达。
(二)商业资本的操纵力量
在商业资本和商业网络平台眼中,嘻哈是一种带有极强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新鲜事物,是网络综艺节目、大型音乐会现场,乃至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等商业化舞台的“新宠”。在商业逻辑的框架下,嘻哈歌手的自我形象建构必然是放大娱乐性、压抑反叛性。“嘻哈反叛精神的表达空间被压缩或隐藏,‘酷炫’‘动感’‘嗨翻全场’‘押韵’‘潮’等关键词建构了社会公众所认知的嘻哈文化形象。”[22]商业媒介建构的嘻哈歌手形象是如此,嘻哈歌手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也逃脱不了商业逻辑的宰制,比较明显的表现是为吸引流量,嘻哈歌手转向重娱乐、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演唱风格。过度商业化,也引起嘻哈歌手对自我形象的质疑和反思。在他们看来,国内嘻哈音乐在商业娱乐浸染下所形构的“形式化”浪潮已经背离了嘻哈精神所坚守的独立自由、追求个性化表达、持有批判态度的文化内核,嘻哈不应一味商业化,而要保持本真(keep it real)的底色,嘻哈歌手应该化身斗士,以批判者的姿态揭露社会问题,为弱者发声。但是,大型综艺节目的规则显然是为流量变现而设置的,即使允许嘻哈亚文化元素“登场”,允许嘻哈歌手个性化表达,其目的是“引流”,其限度是“不出事”。娱乐化和个性化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冲突,因为娱乐是以大众的喜好为导向,而个性恰恰意味的是卓尔不群[23]。嘻哈歌手在坚守嘻哈本真与谋取利益之间挣扎,一方面为了谋利而被迫迎合商业市场,另一方面又因商业化后嘻哈精神的缺失而耿耿于怀。处在生存与守真夹缝中的嘻哈歌手,在歌词中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撕裂的自我形象。正如嘻哈歌手杨和苏在歌曲《阴暗面》中所唱:“但现在我隐约觉得写歌像是被迫营业,是一个我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异教徒,看待问题的角度只属于极少数,又或许是这个世界得了富贵病……如果连镜子里的人都不认识我了,那曾经的我,他不得恨死我。”更深层的影响是,嘻哈的娱乐化倾向将直接导致保守派和开放派的断层与割裂,传统的嘻哈亚文化团体的稳定形态将由此趋向离散化[24]。保守派嘻哈歌手坚守的嘻哈音乐和价值立场在商业化浪潮下只能蛰居“地下”,很难再登上大众舞台,开放派嘻哈歌手则转而成为代表中国嘻哈文化的实际主体。但以后者为代表的嘻哈音乐,在本质和内核上却早已带上商业化的“复制品”色彩,嘻哈文化在商业娱乐化叙事下被重新定义,嘻哈歌手自我建构的整体形象也面临坍塌。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力量
随着曝光度的增强,嘻哈歌手更倾向于在微博和抖音中建构出积极正面的理想型自我,一改以往低俗、不良的负面形象。究其原因,除了商业收编的“洗白”外,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不可小觑的规训力量。主流意识形态对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规训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大众媒体经由塑造嘻哈歌手理想化媒介形象而变相收编,比如塑造“逆袭”形象,赋予嘻哈歌手“拼搏”“梦想”光环,使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个人奋斗成就自身的价值主张。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引导嘻哈文化朝向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而消解嘻哈文化的抵抗和偏离色彩。其二,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和法规规制嘻哈歌手等艺人的言行举止,达到震慑效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规制直接影响了嘻哈歌手媒介自我形象建构,道德化、理想化的媒介形象成为合法化存在的前提条件,理想型自我形象、品位高雅型自我形象便成为嘻哈歌手的“标配”。不过,嘻哈文化本真型形象时不时会渗透理想型形象,更为有意思的是,占比不高的悖反型自我形象也偶尔“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想型自我形象。比如有嘻哈歌手在微博发文宣扬传承美德、勤俭节约,可画面中的人物却一身名牌,极其奢侈。此外,为维持理想型自我形象,嘻哈歌手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无力抗争的弱势形象。嘻哈歌手王以太被男观众泼香槟、蓄意侮辱后,非但没有实施反抗,还故作镇定,继续演出。事后则发微博抒发内心感慨,“以前觉得你们开口饭挣得不容易,如今我算是明白了,这六块钱一张的戏票里边,三块钱买你们的艺,剩下的三块钱呢,买你们做个靶子,给他们天花乱坠糟蹋着玩。我们唱戏的呢,谁都不认识我们,我们谁都不认识,说理都没地儿说去,你说真的去讲理吧,人说你仗势欺人,一点名声都保不住。”⑥
结语
通过对国内嘻哈歌手形象的媒介自我建构的研究,可发现,嘻哈歌手自我媒介形象是在与大众媒介、商业资本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传递出撕裂与无奈的自我表达。首先,嘻哈歌手通过跨媒介叙事策略,辗转于微博、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和歌词写作,借助不同媒介的技术特征和跨媒介连接网络,有针对性建构起自我形象的不同面向,通过微博完成更偏向于公共理想型自我形象建构,而经由抖音则选择性地建构起更具个人色彩的理想型自我形象。嘻哈歌词文本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更接近于本真型自我形象。同时,在跨媒介叙事中,这些形象类型互为补充、互为增强,也互为解构,呈现出不同语境下“随机应变”,使嘻哈歌手的自我形象建构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其次,随着商业资本、大众媒体、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介入,嘻哈歌手开始对自己坚守的嘻哈精神产生怀疑,个体身份在“地上”与“地下”之间来回切换,一方面因为迫切想要摆脱边缘化境地,实现名利双收,而被迫追随商业资本,逐渐背离嘻哈文化的原初本真,徒留下嘻哈演唱形式与风格;另一方面又想坚守嘻哈精神内核,逃脱资本和意识形态操纵,却往往力不从心。身处夹缝和混杂无序的社会环境,极大影响了嘻哈歌手媒介自我形象建构的一致性,反倒呈现出断裂、矛盾、混沌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对国内嘻哈歌手媒介形象自我建构的探究,厘清了嘻哈歌手在媒介镜像中的自我表达以及大众媒介、商业资本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嘻哈文化本土化发展的影响。打破了大众媒体关于嘻哈歌手或积极正面,或消极负面的二元对立媒介形象的建构,从嘻哈歌手在互联网代表性媒介平台和嘻哈歌词的自我表达中发现他们建构了理想型自我、神秘型自我、本真型自我和悖反型自我的媒介形象,为大众了解嘻哈群体及其文化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同时也为全球性的嘻哈文化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和佐证。
注释:
① 《中国有嘻哈》在2018年改名为《中国新说唱》,并沿用至今。
② 《圣诞夜》是嘻哈歌手PG One的一首原创歌曲,歌词内容涉及吸毒、滥交、歧视女性等话题。
③ 考虑到抖音是2016年9月才推出,且嘻哈歌手入驻抖音的最早时间为2017年,所以本研究没有选取抖音作为研究对象。
④ 媒介系统中的一级生产者是传播的起点,通常是个人或组织作为传播活动发起人或者传播内容发出者,也可以称之为“内容生产者”或“内容生产种群”。
⑤ 这里所说的文本生产者同样扮演传播者的角色。
⑥ 该动态来自于嘻哈歌手王以太2020年4月21日的微博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