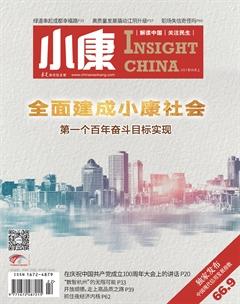我在浏阳写出了神话书
林小淼

我有本写神话的书,因疫情和插画等种种情况拖了很久,今年终于要出版了。前年出版社让我写一篇“为什么要写神话”的文章,那时我还没接“大城小事”专栏,那篇文章关于浏阳只字未提,但写了近一年关于浏阳的专栏后,如果出版社再让我修改,我恐怕得“声明”:如果不来湖南、不住浏阳,我可能不会动笔写神话。
写神话离不开浏阳这地方的加持。我刚来浏阳的那个冬天,连续下了八十三天的雨。八十三天,三个月,每天都是连绵不断的小雨,一刻都没有出过太阳。
有天早上刷牙,我看见洗手池边缝长出一株橙色小蘑菇。水水嫩嫩,看着美味又恐怖。我把它揪下来,凑近闻了闻它奇异的蘑菇味。我已经被这现实魔幻彻底吓蒙了,以为自己被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掌拍进了《百年孤独》的马孔多。
后来,我认了。哪怕雨一直下,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当毫无预兆地雨过天晴时,我人生第一回对太阳的出现激动不已,站在外面晒太阳,看每个经过的人喜气洋洋。灵魂像是伸出了无数敏感触角,四面八方死命圈住阳光拽进体内,我一会儿想大笑,一会儿想疯跑,一会儿想唱歌,一会儿想亲亲谁的脸,如果我会写诗,我早就写了。
从那天开始,我想明白了湖南这地方的神奇之处。想明白了为什么屈原能写出那样神秘迷人又超现实的《楚辞》,那就是湖南、楚地给他的滋养。其他地方要么敬神,要么畏神,只有楚文化是娱神。对神族的态度非常不严肃,即使是讨好,也属于一种“我想让你高兴高兴”的取悦型讨好。
我窗外的浏阳河,在雨天里,有时是蟹壳色,有时是幽幽的灰,有时是肤浅的褐……
別处那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生怕神族发脾气,一怒之下搞个三年大旱或者发洪水把大家淹死的状况,在楚地见不到。当然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里考据出来的。如果说别处是敬神畏神的话,楚地更多是活泼地媚神,《离骚》里有强烈的呈现。
除了闻先生考据的文化,我觉得地理环境对创作也有极大的刺激。延绵的山,数不清的河,阴雨连绵,鸽灰色的天看不见太阳。这些像用素描铅笔画出来弥漫在心上的风物,这块土地的神奇魔力,会很容易把你拖进另一个肉眼看不到的时空。
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让你想象力匮乏,怎么可能让你不想提起笔写点什么?相对应的就是热带地区很少出作家、诗人。热带岛屿就是用来享受阳光沙滩蓝天的,谁会在那样的好地方,闷在屋里写东西?
而我窗外的浏阳河,在雨天里,有时是蟹壳色,有时是幽幽的灰,有时是肤浅的褐……有一回夏天暴雨,河水暴涨,淹到路上,断了电,抽水车赶来连夜工作才不至于让我陷入极度恐慌。
我家挨着一座小小的天马山,自然传说又是山上住过一匹“天马”,或者还有一个骑着它的道人或者真人之类的。心血来潮时我就去爬天马山,跑上跑下恰好一个半小时,当锻炼身体。家人反对我独自爬那山,说人烟稀少。有个雨后周末我自己跑去爬天马山,到半山腰,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女人夹着嗓子唱歌——“小茉莉哦小茉莉”,毛骨悚然。赶紧转身看,没人。立即跑下山,一路下来,空无一人。我吓得越跑越快。
到山下,看见一对父女。小女儿坐在遥控车上,爸爸拿着遥控器操控她前后左右行动。我走过去想问那爸爸:“刚看到有人跟我后面上山吗?”小女孩的胖手突然猛地啪一下拍到车方向盘,车子高声大唱:“小茉莉哦小茉莉请不要把我忘记,太阳出来了我会来探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