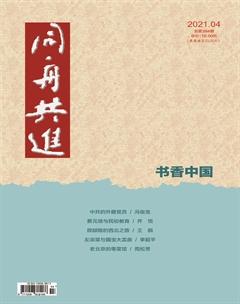陈平原谈读书
【多读“无用之书”】
李浴洋:陈老师,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很高兴可以就“读书”这个话题和您做一次访谈。
关于“读书”,您先后写过《书里书外》《书生意气》《漫卷诗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与《读书是件好玩的事》等。我注意到,从1990年代开始,差不多每年的“世界读书日”,您都会应邀撰文或发表演说来谈“读书”。能否首先请您谈一谈对于“读书节”的看法,以及您为何一再“劝学”?
陈平原:设立“读书节”,是有心之举。最好的状态是,“读书”已经成为再普遍不过的事,不需要你提醒,也不用敲锣打鼓地提倡或庆祝。
教了几十年书,很容易养成“好为人师”的毛病,这点我很警惕。本来嘛,大千世界,人各有志,很难说哪一种生活方式最好。在“劝学”这个问题上,我有时散文,有时随笔,有时讲座,说多了,自己都感觉不太好意思。
比起传授各种专业知识,劝人读书或教人怎么读书,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至于学有专精的教授们,普遍不太愿意涉足。前些年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就是想打破这个成规,让“劝学文”变得有趣且有学问。只不过,关于读书是否有用、有益、有趣,我希望论证的,其实是最后一点。假如有一天,“读书”这一行为真的风靡全球,我相信,“有趣”必定是最为关键的原动力。
李浴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和“开卷有益”相比,您更愿意告诉公众“读书是件好玩的事”?
陈平原:谈读书,我更愿意先问这“读书郎”的年龄、职业、心境、目标等,然后才“给个说法”。比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就只适合于专家学者,拿到广场上去对着大众宣讲,什么“独上高楼”,还有“灯火阑珊”,不合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体会,很少能“版权转让”。若“众所周知”,不用你来唠叨;若“独得之秘”,那么我听了也没有用。
谈起读书,我欣赏两句话。一是晚明文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说法:“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在校学生一般感觉不到这一点,还埋怨老师布置那么多“必读书目”,实在“不人道”。走出校门后,为谋生终日忙碌,那时你才意识到,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读书,确实是件很幸福的事。
二是1922年8月,梁启超应邀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有一讲题为《学问之趣味》。其中提及“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而最能引发趣味的,包括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等。我相信,人生百态,读书是比较容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最近这些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退休人士,因投资、旅游、收藏等缘故拼命读书,且很有心得。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想成为专家,就是喜欢,甚至成痴、成疵、成癖。用晚明张岱的话来说,有痴、有疵、有癖才可爱,因其“真性情”。读书也一样,不管你喜欢哪方面的书,只要能读出乐趣来,就是好事。在我看来,读书讲趣味,比讲方法重要得多。

李浴洋:不过,坊间关于读书的论述,更多还是旨在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像您这样特别推举“读书讲趣味”的,似乎不是很多。
陈平原:现在年轻一辈所面对的诱惑,比我当年多得多。那么多“有趣的玩意”在等着,为何选择相对比较辛苦的读书呢?这个时候,能否真切体会到“读书之乐”,就成了关键。
李浴洋:您认为,在今天倡导“有趣的读书”,最大的困难与最大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陈平原:在我看来,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过分功利化。时至今日,“黄金屋”与“颜如玉”的希望已相当渺茫,但依旧还是很多人刻苦读书的主要动力。寒门子弟若想凭借自家才华和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来,彻底改变命运,读书依旧是最值得期待的“正路”。
也正因此,功利化的閱读乃当下读书的主流。我以前就在访谈中说过,身处专业化时代,确实需要很多目标非常明确的阅读,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并非读书的全部意义。传统中国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在今天看来,或许过于高蹈;但将读书仅仅理解为拿学位、学本事、谋职业,还是过于狭隘了。这也是我再三提倡大学生应该养成阅读文史哲等“无用之书”习惯的缘故。不是说“有用之书”没价值,而是因其已经进入各大学的规定课程,有了制度性保证,且广受世人的推崇,根本用不着你提醒或提倡。
有感于当下的读书过于功利,我建议大家在业余时间,多凭自己的兴趣读一点“杂书”。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描述钱锺书的读书:“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汪曾祺撰《谈读杂书》,说此举的好处多多:第一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增长知识,第三学习语言,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这里所说的“读杂书”,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书”,而是指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且不含功利目标。
所有关于读书的论述,其实都该有的放矢——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读书当如“挖树兜”】
李浴洋:您刚才谈到,对于书籍的兴趣是您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养成的。通常来说,“读书”这一话题总是与学生时代难解难分,故“读书”一词本身,就有“求学”与“在学”的意思。在您的学生生涯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读书经历?
陈平原:我们77级入学时年纪普遍较大,学习很自觉。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时,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此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喜闻乐见》以及《论凤姐》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
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我买的是1980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翻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李浴洋:您那时摸索出什么读书的诀窍了吗?
陈平原:当年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去给80级的学弟学妹们介绍学习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应届毕业生,比我们年轻不少。还记得我当时的发言,主要是质疑“金字塔读书法”。胡适的“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常被老师们用来教育学生,要求好好打基础。我说,这方法对我们不适用,因为没有具体的工作目标及衡量标准。学海无涯,一味追求既“广”且“大”,到我们退休了,还没到长“高”的时候,岂不可惜?我自己的体会是,读书当如“挖树兜”。选择特定的树桩,顺着树根的走向往四面八方挖,挖着挖着,就连成了一个网络,你大学阶段的学习任务就完成了。
以我的观察,会读书的人,大多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知道自己为什么读书,从何入手,怎样展开,以及如何穿越千山万水。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基本训练或走出校门的人来说,我的“挖树兜”读书法不无可取之处。只有“带着问题学”,才能选准目标,集中精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你阅读的积极性,而且容易见成效,鼓励你不断往前走。
【人文学者的“博雅”与“专精”】
李浴洋:您成为职业学者之后的读书生活,我们可以从您的随笔集中得见,从中很能感受到您的“读书之乐”。马克斯?韦伯曾在1919年断言,“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以学术为业》)不知您是怎样理解“读书”与职业学者这一身份的关系的?
陈平原: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韦伯的断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专业化”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当然,过于强调这种“专业化”,也会有很大的弊病。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可能限制其学术视野,也可能影响其综合判断,更可能消解其本该承担的人文关怀。
关于学者如何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中国人有个绝妙的说法,叫“博雅”——与“专精”相对应。如果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不管是今天在校念书,还是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最大的困境,很可能就是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我希望大家关注那些有专业能力而又趣味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周氏兄弟,可以说就是近现代中国最为博学深思的“读书人”——我把“读书人”看得比“专门家”还高,除了学问,还有趣味。周作人《我的杂学》分20节,总结自己一生所学,从《诗经》、陶诗到中国旧小说,从希腊神话到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到性心理学,从医学、宗教学到妇女学,从日本俗曲到佛经文本,几乎每个领域他都有论述。周作人说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样的“常识”,可不容易具备。至于鲁迅的读书趣味及知识结构,可参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不仅周氏兄弟,清末民初的很多读书人,在古今中西之间奋斗、求索,大都眼界开阔,趣味广泛,志向高远,很值得今人追怀。

李浴洋:在如何处理“读书”与“治学”的关系问题上,的确存在古今之别。
陈平原:作为学者,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很容易会忘了读书是件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
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浴洋:过去这些年,您一直主张通过“必读书目”来校正学生们的眼界、趣味与心态。这是否也与您对于“专业化”与“业余性”的思考有关?
陈平原:大概30年前,我接手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钱理群教授给了我他们那一届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我一看实在太多了,刪节后发给了研究生。此书目使用了十几年,轮到我的学生辈吴晓东、王风他们来权衡,据说又大为删减。但到了学生手中,估计还会三折九扣。学科范围的拓展以及学术热点的转移,促使新一代学者需要读很多新书;但即便如此,若干本专业的基本书籍,我以为还是非读不可的。
现在很多学校不重视“必读书目”的作用,可我认为其可以伸缩,但不宜完全抛弃。社会阅历、生活体验、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巨大差异,导致学生们对不同的文学作品,有的极为痴迷,有的毫无兴趣。作为一般读者,“好看不如爱看”,你愿意读都什么都可以。但专业训练不一样,有些书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单从写论文的角度,选冷门、读僻书,是比较容易出成果的。可太在意发表,容易剑走偏锋,不去碰大家或难题。长此以往,很可能趣味偏狭且低下。读书的人都明白,长期跟一流人物、一流文章打交道,是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的。用老话说,这就叫“尚友古人”。
这就说到文学教育的目的,到底是培养有技艺、善操作、能吃苦的专门家,还是造就有眼界、有趣味、有才华的读书人。我常感叹,老一辈学者的见识远远超过其论著。围绕学位论文来阅读,从不走弯路,全都直奔主题,这不是“读书”,应该叫“查书”。多年前我说过,我喜欢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而不太欣赏眼下流行的“不读书,好求甚解”。

【人文学乃人类文明的压舱石】
李浴洋:今日,网络已经无孔不入。在为人们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网络也挑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阅读习惯。您是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读书的?
陈平原:对于习惯于阅读纸质书的我来说,电子图书或网络数据只是用来查阅与检索的;至于下一辈的学者,很可能走出另一条道路。我不反对研究生阅读校对精良的电子图书,甚至要求他们做学问时要善于使用各种数据库。我唯一担心的是,整天在网络上东游西荡,表面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收获甚微。还不仅是阅读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心情——面对网络上排山倒海、五花八门、激动人心、不读就过时的信息,你还能沉得住气潜心阅读思考吗?说句玩笑话,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可真是“五色令人目盲”。
过去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为什么?因为那种紧张的阅读,需要调动全部的精气神。如今则移动鼠标,一目十行,边听音乐,边品咖啡,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朋友聊天,这样的阅读习惯养成后,很难再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现在的大学生,很少能在课堂上记笔记的,說老师你把讲稿给我们不就得了吗?可我理解的记笔记,主要是迫使自己集中精力,否则你跟不上思路,抓不住重点,记不下来的。
更为严重的是,人生原本千姿百态,可如今信息的传播太猛、太烈,导致越是生活在大都市,越必须警惕自己的人生是否被“模式化”。今天你以为极为重要、众人都挂在嘴上、不知道就“出局”了的,过不了一年半载,很可能就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今人的目光,过于集中在“时尚话题”——从财经到八卦到琐闻,因而浪费了大量美好时光,实在可惜。
李浴洋:您曾说过:如果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不是说书本本身特了不起,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还有追求,还在奋斗,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对此,您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
陈平原:《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出版后,我曾接受采访,谈及当下部分中国人的“读书”:第一,知识面广,但缺乏深入探究的动力与能力;第二,擅长检索,但抵挡不住时髦的诱惑,难得深入思考;第三,喜欢表达,但主要是滔滔不绝的“独白”,而不是有理有据的“说服”,更不是包含倾听与自我反省的“对话”。
最近这二十年,网络力量狂飙突进,不要说城市面貌、生活方式,甚至连说话的腔调都“日新月异”。年轻人因此而志得意满,忽略了各种潜在的危险——包括读书、思考与表达。稍有航海知识的人都懂得,空船航行时,必须备有“压舱石”,因为此时船的重心在水面以上,极易翻船。在我看来,人文学(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乃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不随风飘荡,也不一定“与时俱进”,对于各种时尚、潮流起纠偏作用,保证这艘大船不会因某些特定的原因而颠覆。在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的时代,请记得对于“传统”保持几分敬意。这里所说的“传统”,也包括悠久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的读书习惯。
与此同时,必须学会“拒绝”与“遗忘”,从而建立自家的阅读立场。这其中,批判的功能格外重要。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话,读书人须不断地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不仅反省具体的结论,而且反省整个知识体系、时代潮流——包括教育机制与传播途径等。我在《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一文中称:“基于自家的立场,自觉地关闭某些频道,回绝某种信息,遗忘某些知识,抗拒某些潮流,这才可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来。”
【读书的策略】
李浴洋:您说的“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可谓至关重要。这不仅关涉读书姿态,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性格和自我意识的确立。
陈平原:书读得越多,越能深切感觉到,读书是自己的事,别人帮不了多少忙。身为教师,说这话,近乎自己拆自己的台。可这并非故作高论,而是认定读书一事讲求的是自得;世上有值得倾听的读书甘苦,但无可供传授的读书诀窍。我能讲清楚自家的经历与困惑,至于对听者有无帮助,说不准,那得看各人修行。你我都有关于读书的切身体会,但别人的体会只适应于别人,再好我也无法拷贝。听“成功人士”讲读书,唯一的作用在于引起读书的兴致、勾起见贤思齐的愿望,以及促进认真的自我反省。
读书是很个人的事情,趣味也因人而异。审美眼光确有高低雅俗之分,但就“阅读”而言,关键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趣味。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十年后才能读懂的,不妨暂时束之高阁。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偏食”是正常的。因为,有趣味就意味着有个性、有边界、有局限。第一次面对人人说好而你很不喜欢的书籍时,心里很惶惑,也很茫然。久而久之,明白自己的“阅读趣味”,你就坦然了。
李浴洋:以您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于“读书”的高度自觉,我想终归还是可以有若干策略让我们参考的。
陈平原:建议认认真真读几本好书,以此作为根基,作为标尺,作为精神支柱。过去总说“多读书,读好书”,以我的体会,若追求阅读的数量与速度,则很可能“读不好”。成长于网络的年轻一代,很容易养成浏览性的阅读习惯,就是朱熹说的“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因此,我主张读少一点,读慢一点,读精一点。世界这么大,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懂得,不欣赏,一点也不奇怪。不追求阅读的数量,是希望你我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欣赏路边的风景。表面上看在后退,实际上是求进取。
所谓“读好书”,我并不主张只读五百年或一千年的经典。若真的以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者“八部书外皆狗屁”,那很容易变迂腐的。新旧并置,长短结合,只要是经得起考验、略有些年纪的好书,都值得你我认真阅读。
李浴洋:说到“读好书”,除去书籍选择,在阅读思路上您有无推荐?
陈平原:抗战中当过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徐复观,抗战结束后以少将军衔退伍,专心做学问,日后成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43年,他到重庆的勉仁书院找熊十力先生求教,熊十力吩咐他先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这书我读过了。熊十力说,回去再好好读。几天后,徐复观来见熊十力,说那书我又读了,里面有好多错误,这里不对,那里不妥。话还没有说完,熊十力拍案而起,说你这笨蛋,你滚吧,这么读书,一辈子都没有出息。读书先要看它的好处,你整天挑毛病,这样读书,读一百部、一千部、一万部都没有用。徐复观日后追忆,说这件事让他“起死回生”,明白该如何读书了。
熊十力主张读透一部经典,养成好的眼光、趣味与能力,是经验之谈。你的主要任务是汲取好书中的精华,用来滋养自己,这是第一位的。至于高屋建瓴,火眼金睛,把古人批得体无完肤,那是做研究的时候才需要的。
李浴洋:熊十力与徐复观的例子非常生动。在古今中外的读书人中,还有没有您特别欣赏的?
陈平原:再举两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魯迅与章太炎是怎样读书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来做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有我独立的准备”。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之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却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他认真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地,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结硬寨,打呆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这是鲁迅的经验。

李浴洋:那章太炎呢?
陈平原:章太炎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有曰:“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其实就是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
俗语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要想读懂读通“圣贤书”,恰恰必须关心“窗外事”。不是放下书本只问“窗外事”,而是从书里读到书外,或者借书外解读书里。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中说:“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识得了字,不一定就读得好书。读死书,读书死,不是现代读书人应有的胸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算是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关心时世,洞察人心,是将死书变成活书,将苦读变成人生一大乐趣的关键。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术与人生完全可以合一。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二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这是我的理想。
李浴洋:听您谈了这么多读书的真知灼见,我收获良多。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请您推荐一到两本有趣的关于书籍的书给大家,您会推荐什么?感谢您接受访谈。
陈平原:谈论书籍,最好兼及“精神”与“物质”。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值得推荐。
另外一本则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安贝托·艾柯与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让—克洛德·卡里埃尔的对话,讨论书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以及网络时代纸本书的未来,书名为《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吴雅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