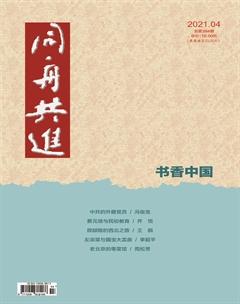书店:城市的文明之光
维舟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在物质繁荣之下,很多城市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却频频引起社会关注,当然不只是因为书店本身(录像租售行业的衰落就没引起这么大反响),而是因为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空间的象征。
在电商、电子出版物如此发达的时代,现代城市还需要书店吗?需要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书店、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没有了书店,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阅读的黄金年代】
国内的书店也曾有过辉煌时期。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人陷入全民的知识渴求,说书店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化殿堂,大概也不为过。当时像成都甚至出现过通宵排队购买中外文学名著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如今追星的狂热。
作家毛喻原在《再见冬妮娅》一书中曾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书店,心中感慨颇多。“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我们的书店拒绝武侠小说,也拒绝流行读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書店仍能盈利。比照今天的情况,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当时的书店还不需要迎合市场的压力,店面租金和人员成本都不高,买书的人也多——在那个年代,连电视机都还是奢侈品,书籍几乎是为数不多的文化消费选项之一,还未遭到电视、网络的强有力竞争。
1990年代初,中国的书店面貌发生巨变。此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一大批风格独具的民营书店开始密集涌现,后来各地最具代表性的书店,几乎都创建于这十年间。如北京的万圣书园、席殊书屋、风入松、国林风图书中心,上海的季风书园,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学而优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枫林晚书店,贵州的西西弗书店,长春的学人书店等。
但实际上,从大的文化发展趋势来看,书店的式微已在酝酿中。有在文化系统任职的领导回忆,许多一度大受欢迎的剧种,在1980年代就“都不行了”,“电视开始往家庭里走,报刊发行量大增,而报纸则是极其流行……后来流行歌曲、卡拉OK、舞厅、电视都来了,戏曲就哗啦啦地退了”。观众正在更新换代,其构成、趣味和选择今非昔比,流行文化的崛起势必会挤占阅读的时间。只不过电视一时尚难席卷全国(全国电视普及率2000年是86%),而对中国人来说,“读书”又具有特殊的意义,暂时还不像传统剧种那样受到全面的冲击。
如今回想起来,这是在互联网大潮涌来之前的一个阅读的黄金年代。1997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一次统计报告,全中国仅有62万上网用户;两年后,当当网问世,很快成长为威胁实体书店的一大巨头。
其实,在网络的威力显现之前,电视的影响力、全民“下海”赚钱的冲动和店铺租金上涨的压力,已开始让一些书店感到窘迫。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年,中国网民飙升至近3亿,当当、卓越(后来的亚马逊中国)、京东等电商平台凭借低折扣和送达到家的物流配送力量,影响力日渐扩大,而实体书店的困境也逐渐浮现。2013年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调查显示,在此前十年里,全国有一半的实体书店先后倒闭,总数多达一万多家。
这样的影响也波及世界各地。法国巴黎的文化地标、已有两百年历史的老店莎士比亚书店,受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下半年里,书店销量下跌了80%,不得不在亏本经营中苦苦支撑。
虽然这一现象,在这十多年里早已屡见不鲜,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却众说纷纭。新媒体阅读的分流、网上书店的冲击甚至“中国的年轻人不爱读书”都曾被列举出来作为“替罪羊”,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书店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它的生存最终也跟服装店、鞋店一样,是一个可持续经营的商业问题。
早在2012年春,上海季风书园的创始人严博非在被媒体问及新店经营状况时,就连说了三个“不好”,当时季风的营业额已锐减至全盛时的1/4,而门面租金、薪资支出却比开店时大幅上升。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商业机构对书店租金尽力减免,但薪资的压力仍是实实在在的,这意味着书店必须另辟收入来源才能活下去、活得好,仅靠扶持仍无法续命。
不仅如此,这也表露出国内书店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量的书店同质化竞争,既缺乏在选书、空间风格等方面的特色,卖的“商品”(书籍)又与别处无异,却又比电商平台贵。这是无法指望读者们出于“情怀”而一直无条件扶持的。
然而,很多书店经营者创业的初心,与其说是为了商业经营,倒不如说是出于文化使命感——1990年代那批有代表性的民营书店老板,在他们身上,大部分是“文化人”的气质压倒“商人”,他们常常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卖书”,倒是在对抗消费主义。
书店要摆脱困境,说到底需要脱胎换骨的转型,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仍试图“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的,相反,必须“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书店的确不应该只是“卖书的地方”,这就触达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书店?书店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书店存在的意义】
这个问题原本并不存在,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书店的存在,是为了让人能有地方买到自己想读的书。
虽然书店在中国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直到很晚近的民国时期,它才逐渐演变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它起初只是市场上的临时摊位,“书店”一词的出现,不早于清代中叶。这说明,其实书店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扮演重要角色。
晚明时的胡应麟就曾记述,在省城、府城这样的都市之外,书店是极少的,甚至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到近代也并无多大改观:1914年前后,30万人口的山东省会济南,就只有9家书店。当时真正像样又丰富的书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书店才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者金克木曾回忆,北京的旧书店和书摊子,对年轻时的自己而言,就像是一所非正式的“大学”,可以站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翻阅,“旧书店里的人是不管的,无论卖中文书的或卖西文书的都不来问你买不买。因为是旧书,也不怕你翻旧了”。
清末民初时,全国的书店都收拢在商务印书馆等三大出版巨头的庞大销售网络之下,尤其是通用的教科书,行销全国。叶圣陶在小说《倪焕之》中,曾借用甪直镇上小学教师之口抱怨,“大书店最关心的是自家的营业,余下来的注意力才轮到什么文化和教育”,商业利益的驱动多过文化使命感。
确实,当时的新书出版销售之所以吸引了众多怀着各种目的的文人、商人投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通俗文学新书具有资金周转快、利润高、更便于短线作业、面向顾客群体更广等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各种小书店在当时旋生旋灭、生生不息,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物质支撑。像鲁迅就经常以内山书店为据点,会客见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自视为社会的灵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此种观念的生成,与当时的小书店是分不开的。
书店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尽管有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但还是延续了下来,直到在市场化和新媒体的大浪之下受到猛烈冲击。2011年,《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标题说出了人们内心的感受:“实体书店纷纷倒闭,逛书店会不会成为历史?”不过,这与其说是在讨论实体书店的经营状况本身,倒不如说是聚焦我们社会的读书现状。
1992年,在第一届台北古书拍卖会上,著名的诚品书店曾这样解释:“台北自诩为国际性大都会,购买力早已让欧美各国称羡,唯独在古书业,并未随着经济起飞而发展,反而日趋没落,甚至不能跟它蓬勃的出版业相提并论,无疑是此地文化界的一大缺陷。”两岸同根生,这番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这边各大城市的现状——没有像样的书店,似乎对一座现代城市来说是不相称的。
倒不是说非要花大价钱来维持一个不赚钱的行当,而是说,这涉及现代城市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生活,书店又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精神需求的独立书店,是城市文化多元的体现,因此,容纳不同特色的书店,是一个城市精神生活的多元化的外在表征。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每一家独立书店的消亡,都是对公共文化多元性的一种打击。
当然,实体书店的危机并不只是在中国,欧美、日本也同样严重,很多人都在忧虑“年轻人不看书”的现象。在日本,2005年的全国实体书店总数为17153家,到2014年就减少为12793家,而日本的新书还不能打折,此举已经减少了网上书店对实体书店的冲击了。
这甚至还不止是阅读的危机,美国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中说:“并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在消失,博物馆、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艺术与音乐学校——这些让我感觉自在的地方都進入了濒临灭绝物种列表。”互联网的冲击加速了之前就已被很多学者关注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退回到私人的世界里自娱自乐,通过电视屏幕、网络和遥远的外界发生联系,用社会学家桑内特的话说,这是“公共人的衰落”。
就中国社会的现实来说,这还具有复杂的双重处境:一方面,知识生活未能触及日常生活的核心地带,对务实的大众来说,读书仿佛是“有文化的人”才关心的事,更乐于通过轻松的娱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另一面,电视、网络等媒体形式又使人们的文化消费极大地丰富了,阅读早已不再是唯一的文化生活。一如贫乏的年代里桌上没什么菜,只能多啃主食,但日子越是丰裕,主食就吃得越少,吸收营养的渠道也变了,要再回到以往那个主食当道的年代,似乎是不可能了。
在这一意义上,书店的处境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缩影,对此的关注与思考,其实远不止关乎书店本身,而涉及城市规划的理念,甚至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品质。就像城市中的绿地,它可以让人得以有一小块地方“诗意地栖居”。
【书店如何生存】
如果要保留实体书店,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如何让它在现代城市中生存下去?
在香港,像旺角这样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有不少书店,然而几乎都是“二楼书店”,因为底楼的铺面租金太高,书店根本租不起,只有像香港三联这样的出版集团,才能在底楼支撑一个较大的门面。相比起来,台湾的诚品书店则开辟了另一种模式:依托房地产综合开发和多样化经营,使书店变成一个文化品牌和人流聚集的枢纽节点。
出版人陈颖青曾说过,在市场的高度压力下,如今必须懂得如何应对市场,而“一本书能不能卖,总共就是两件事:一是书本身,二是社会的共振”。也就是说,书店就算只是卖书,需要考虑的也不只是把“货物”摆在哪儿就结束了,甚至还需要具备策展能力,推动这些书在社会上激起反响。
对于传统的书店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上海季风书园在店面设计上就可看出差异:早先的陕西南路总店几乎全是书,只在一个狭窄的过道里摆几张茶几作为休息区,一旦到了读书分享沙龙时,这儿就挤得水泄不通。2013年迁到上图新店,却专门辟出一块不小的咖啡馆区域,内间还有专设的报告厅作为聚会演讲的场所。其实,在这方面季风已经慢了一拍,像2006年创办的单向街书店,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文化活动;2011年创办的方所书店、2013年创办的钟书阁、2014年创办的言几又,无不着意于设计感和消费体验,并以文创活动等多样化经营来获得多元收入来源。
这顺应了后现代社会的关注重心从“消费”到“体验”的转换,以至于有些书店本身都变成了“景点”。2016年开业的上海大隐书局,坐落在充满古典气息的武康路,内部设计也十分典雅,很快成为许多文化人钟爱的聚会场所。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改建自原先的东正教堂,在2019年底开张时就引起轰动,几天里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他们与其说是读者,倒不如说是游客,目光都不是在看书,而是忙着拍照。近两年杭州、上海的茑屋书店也是同样的情形,以至于开张都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到处都能看到文艺青年去打卡后拍的照片、分享的感受,但这随即又引起了一种不满的声音,质疑这样的“网红书店”是否违背了书店的本意。
的确,之前就有人讥讽,这样的书店其实是“以书籍为装饰背景的咖啡馆”,但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无可厚非,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给书店带来更多元化的收入,实现可持续经营。日本今野书店的老板就曾说,为书店客人提供咖啡,“这种模式,一是能够让客人放松,二是附设咖啡馆会有双重效果,书店和咖啡馆的利润率都会提高”。
在网络的冲击下,书店创新只能是“背水一战”,它必须带给人们网上所没有的体验——特别是面对面的对谈、设计空间的感受、周到的服务等等。这样,一家书店其实已经变身成为文化综合体,它集书的销售、咖啡馆或茶馆、文化对谈空间、文创用品店、创意设计等诸多功能于一身,日本的有些书店甚至根据书的多样性兼营杂货,包括餐具和衣服,人们在那里可以获得整体性的体验,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网络书店仅凭低价售书的单一功能,很难取代它。
另一种出路则是个性化。国内的书店原先是高度同质化的,图书的品种和结构都差不多,但近年来也在不断借鉴别国书店营销的成功范例。比如在日本东京,每家书店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是专注于某一门类的书,特别是珍稀的二手书和古董书,有些是在特别的地点开设特色书店(如京都在动物园内新开书店),甚至还有森冈书店这样每周只卖一本书的书店——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策展能力辅助,配合以相应的主题活动。其共同的内核在于,必须注重读者的用户体验,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在特定空间下的感受。日本就曾有过测试,在专业人员改变选书、摆书方式后,平均单客购书额竟然涨了三四倍之多。
2015年,无印良品首次尝试附设书店,结果大获成功,卖书后客流量有明显增加。设计师清水洋平发现,书天生就是“长尾产品”,每一本书的世界观都很独特,能联系不同人,因而具有多样性和连接性,还能帮人打发时间,因而无印良品书店可以吸引一家人购物时无处可去的男性、男性上班族等各类人群。在此,它提供的其实是“有书的生活”——这个重点在于“生活”,而不是“书”。
这样,书店其实超越了书店自身,而融入了社会生活。在近代的西欧,咖啡馆无疑就是这样的公共空间,如果说人们去咖啡馆,并不只是去喝咖啡的,那么这道理对书店也一样,也只有真正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人们才会感觉离不开它、用它来满足自己的文化生活需求,同时支撑它的生存发展。
当然,也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书店和咖啡馆、茶馆的区别在哪里?在笔者看来,这既可以在功能上有所重叠(书店也可以卖咖啡、卖茶),但又要有所区隔——如果是一场新书分享活动、文化讲座,那么在书店无疑比咖啡馆合适得多了。说到底,就像《东京本屋》里说的,“书店就是让一个人和一本书偶然相遇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一个人,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是‘书店”。
这实际上对书店的经营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迫使它具备多元综合能力,并能调动多种文化资源,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相关的文化内容,并根据读者的反馈,不断加以调整改进。毫无疑问,这非常难,但也唯有如此,它才无法被轻易取代。
【书店的未来,城市的未来】
书店的生存并不只是书店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造成中国书店业今日的处境,除了租金涨幅大、书价上涨令一些人望而却步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电商平台相对于传统零售业特别发达,为争夺市场份额又能亏本经营,在图书销售上也能不断推出很低的折扣,这在十多年来一直使实体书店陷入苦战。书店往往变成了一种样本展示空间,不少人在书店翻翻书,转身去网上下单。而日本的实体书店则没有这样的苦恼,因为日本规定新书一律不得打折。由于新书的毛利几乎总是定价的22%左右,所以日本反倒是二手书店发达,因为二手书可以有自由定价权,能取得70%的利润率。
和其它行业不同,出版、书店是极少数恪守固定价格制度的行业,每本书的定价都标注清楚,不能改动,这不像服装,每家店都可以有自由定价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价格拉高或压低,但书的进货、卖价很难有调整空间,这原本旨在消除书店之间的价格竞争,确保不管在哪里,买到书的机会都一样,人们也都买得起书。
欧洲和日本一样,在固定价格制度的基础上,禁止电商平台降价出售新书。20世纪初,英国书商协会和出版社共同达成《图书净价协议》,明文规定:除教科书外一概不得打折出售。不过,由于几家大型连锁书店的挑战,英国法院在1997年裁决该协议失效,开始转向美国式的自由价格制度。中国的实体书店面临的则是:自己固守固定价格制度,但网络书店却可以自由定价来打价格战,以至于陷入难以摆脱的被动态势。
在政策制定和市场治理的问题上,这或许在短期内难以取得进展,但各地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上,预留文化空间,充分考虑像书店这样的文化设施,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因为这和图书馆、美术馆等一样,其实是给当地居民提供的公共福利。
不过,单纯的扶持事倍功半,更好的选择是如何取得各方共赢。在这方面,近些年来先锋书店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从2014年起,它避开大城市,而深入到各地乡村,已先后开设皖南碧山、浙江松阳陈家铺、福建厦地水田、云南沙溪等六家书店,几乎每到一地,都成为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像云南沙溪的先锋书店,在2020年5月疫情期间逆势而行,开业不到半年就实现了盈利,堪称奇迹。
它为何能成功?这大体可归结为它成功联结了各方需求,又契合了市场痛点。本来,在中国的实体书店版图上,乡村几乎是个空缺,长期缺乏高质量的书店布局,因此先锋书店的这一规划本身就找准了空白,“燃亮乡村阅读之灯”。与此同时,“先锋书店”的品牌和一流的设计理念,结合当地的景色,嵌入地方的文化脉络中,立刻成为当地的文化坐标,吸引了很多人不远千里前去观赏——他们当然不仅仅是去买书的,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像浙江桐庐的先锋云夕图书馆,在2015年开张时,当地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仅有1家民宿,但三年时间就增至24家。
在云南沙溪,当地政府几乎是把一座废弃的粮仓免费送给了先锋书店,这本身就免去了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高昂的地价和租金,只是需要一点书籍的配送成本、后续的员工薪资,而这些原本也都是需要的,鉴于它带动的巨大效应,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当然,尤为关键的是建筑设计。沙溪先锋书店落成后,被广泛誉为“全球最美书店”,很多人专程去沙溪古镇“朝圣”,特意在沙溪停留几日,这对当地政府而言,也绝对是一个双赢的项目,真正把“乡村振兴”落到了实处。
像这样的成功案例也提醒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需要书店,或不喜欢读书,关键在于能否提供不一樣的体验。这就像一个小县城里,平日电影院的两个厅都坐不满,但新开的一家大商场里,却七个厅都爆满——人们并不是没有看电影的文化消费需求,而是原来简陋的设施体验太差,越差越不想去,以至于恶性循环。
在此,一家书店其实已是文化综合开发项目,成为撬动当地文化生活、文化消费、创意产业、旅游景观乃至土地增值的支点,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很难被其它设施所替代。这既需要书店方面的资本和创造力,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眼光和决策,当然也离不开一流的建筑设计团队,且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最终将每一个项目都发展成为“文化IP”。
由此来看,国内实体书店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年轻人都不爱看书了”,而是“年轻人都变了”,如何顺应时势,挖掘新的需求,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不仅考验经营者的市场嗅觉,也考验各地政府能否转变思路,甚至勇于创造机会。如果能这样,那我们有望看到的,不仅是实体书店不一样的未来,也是城乡文化空间不一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