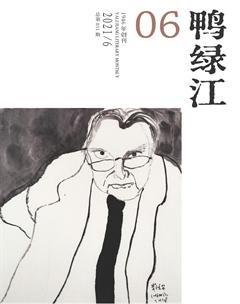柳沄的诗(十一首)(作品选读)
柳沄
两座山
两座山,面对面
站立了很久
中间是一条
叫作细河的河
汛期,河面宽阔
依然被叫作细河
两座山隔河而视
那姿态,说它们是在互相睥睨
就和说它们是在相互仰慕
一样有道理
此时的天色
已被一群一群登山的游人
一层一层地走暗
对面的山顶上,几位
同行的伙伴在不停地喊我
像喊着一个
丢了魂的人
两座山不为所动
在它们看来:恨够不着的
爱同样够不着
回去的路上
我忍不住再次回过头去
静谧的星空下,那两座山
一样高的同时也一样矮
当然,这跟我非要写这首诗
没有什么关系
天空
一只麻雀飞过的天空
与一群麻雀飞过的天空
是一样的
一群斑头雁飞过的天空
与一群丹顶鹤飞过的天空
是一样的
甚至乌鸦飞过的天空
与苍鹰飞过的天空
也是一样的
但我仰望的天空
与鸟儿飞过的天空
肯定不一样
就像一只麻雀和一群麻雀
那么不一样;就像
乌鸦和苍鹰那么不一样
就像一群好看的斑头雁
与一群更加好看的丹顶鹤
那么不一样
被一块石头瞧着
它在瞧我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
一直蹲在那儿瞧着我
像我瞧着它那样
瞧着我。我是想说
——像我瞧着一位
缩颈抱膝的男子那样
好奇地瞧着我
山里的落日
落得格外早
而透明的余晖
使我莫名地想到
透明的福尔马林
它蹲在那儿
继续瞧着我
像一位缩颈抱膝的男子
在瞧一块,从未
瞧过的石头那样
饶有兴致地瞧着我
瞧着我
于福尔马林似的余晖中
若有所悟地坐在
身体与遗体之间
瓷器
比生命更脆弱的事物
是那些精美的瓷器
我的任何一次失手
都会使它们遭到粉碎
在此之前
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
坠地时又将尖叫释放出来
这是一种过程,倏忽即逝
如此,千篇一律的瓷器
谁也挽救不了谁
黄昏的太阳雄心消沉
围绕着那些瓷器
日子鸟一样乱飞
瓷器过分完美,使我残缺
如果将它们埋入地下
那么我漫长的一生
就只能是瓷器的某个瞬间
但在另一种意义里,瓷器
坚硬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它们更喜欢待在高高的古玩架上
与哲人的面孔保持一致
许多时候,我不忍回首
那样它们会走动起来
而瓷器一经走动
举步便是深渊
因此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瓷器宁肯粉身碎骨
而拒绝腐烂
是的,瓷器太高贵了
反而不堪一击
在瓷器跌落的地方
遍地都是呻吟和牙齿
瓷器粉碎时
其愤怒是锋利的
它逼迫我的伤口
重新绽开
幸福的杨树
一只飞倦的鸟
落在了一棵
正在落叶的树上
那是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鸟
树则是每天都能碰到的杨树
周围的杨树远不止一棵
似乎只有它,让
漫长的等待站在了
最值得等待的地方
我是在赴約的途中
见到了这一切。我
再次相信:偶然
比必然肯定更有道理
我边走边对自己说
那棵杨树是幸福的
至少,它因一只
偶尔栖落的鸟
而比其他的杨树
更像是杨树
我也一样,几次
与那位就要见到的人
面对面地待在一起时
我都格外兴奋
格外像我自己
滋味
撂下电话
女儿急着往外走
将刚咬了一口的苹果
随手丢在茶几上
很红的苹果
很好看很好吃的苹果
无奈地摇晃那么几下
就再也不动了
我能猜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初恋远比任何一只苹果
都更有滋味
连招呼也不打
女儿推门就出去了
那跑下楼梯的脚步声
把我带出老远
女儿确实长大了
她已有太多的理由
在丢下一只苹果的同时
把我也丢在屋里
然而,无论我如何想
女儿的突然离开都好比一次停电
我很难一下子
摸到蜡烛和火柴
有好大一会儿
我跟那只发呆的苹果
一样静,一样
缓不过神来
不一样的是心里的滋味
我无法像被咬过的苹果那样
很甜很甜地对待着
所遭遇到的一切……
蠕动的小径
河对岸,蠕动着一条
时隐时现的小径
觉得没啥意思时到阳台上望望它
便成为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那里常常空无一人
常常是它自己,弯曲着
钻入一片晃动的林子
当它从另一端钻出来时
又弯曲了一些
极少有人走动的小径
极少有人知道它通往何处
但在我看来:既然
它和自己一样宽
那么肯定也会和自己一样长
现在是初春,不久
路边的草木就会用各自的枝叶
将它遮在浓荫里
那景象,就好比
不一样的孩子用一样的睫毛
把月亮掩在睡梦中
我对那条没有人走动的小径
渐渐地有了兴趣
比如此刻,它
好像刚刚从东边回来
又好像正朝着东边赶去
时间在它那儿
始终那么直接和简单
仅仅是一种往返
或者来回……
山里的石头
山里的石头真多啊
跟城里的人一样多
高的和矮的
坐着的和站着的
跟人一样多的石头
跟人根本不一样
它们沉默了那么久
却仍在沉默
此时,我和几位诗人
于石头的沉默中
说着唠着,偶尔
非常激烈地争辩着
这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得太多
而仅仅是说得太多
石头好像是在听着
更好像是在睡着
它们经常在一梦到底的酣睡中
把一年睡成一天
再把一天睡成一秒
所以,我们经历过的
石头早就经历过
比如时间,比如雨雪
比如阳光和月色
但与沉默的石头
根本不一样:我们
说着说着就把自己
从这个世界上说没了
空着的座位
列车驶离始发站
已经很久了。我身边的
九排三号,还空着
很安静地空着
除了安静,什么也没有那样空着
空得过道上每一个走动的乘客
都特别像它的主人
奔跑的列车
继续飞快地向前奔跑
一直空着的座位,使
两个本该在难挨的旅途中
肩并肩坐在一起的人
莫名其妙地少了一个
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仰靠在椅背上,想象着
Ta的性别、年龄以及模样
突然就想到了前天下午
为我拔牙的女牙医
她露在口罩外面的两只眼睛
非常漂亮
这一切
使空着的座位
更空
几只蝴蝶
在蝴蝶非常喜欢的地方
飞舞着几只
非常好看的蝴蝶
在一阵很轻的风中
它们忽高忽低地追逐着
比很轻的风
似乎还要轻
——几只蝴蝶
蝴蝶般美丽
其翩然的样子
很容易让人想到那支很著名的乐曲
想到两个为了爱情,而
不得不成为蝴蝶的人
这是一个,阳光
灿烂得有些过分的正午
几只蝴蝶使小区里的
假山、喷水池以及众多的花卉
突然就有了灵魂
我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只是在生活中遇到什么
就享受着什么,我
只是多少有些理解了
那两个可怜的人为啥非要变成蝴蝶
瞧啊:在相互追逐的过程中
蝴蝶那么轻易地就绕过了
人很难绕过的东西
也许变成蝴蝶之后
人才会有这样的快乐
哪怕今天傍晚
就是世界末日呢
一种过程
一只肥大的桃子
一只光芒四射的桃子
从枝头上宁静地落下来
就像凡·高割掉的耳朵,那么沉重
一只富贵的桃子
一只被风雨诅咒过的桃子
一只盛满水声的桃子
从那个高度上掉下来
并且像落日那样,弹了几下
一位美丽的少女匆匆走来
弯腰去拾那枚桃子
當她抬起头时
已成老妇
得意的事情大概都会这样
——这种念头在我心中一闪
那桃子和女人
就突然腐烂了
世界说:嘘
别出声……
【本栏责任编辑】 铁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