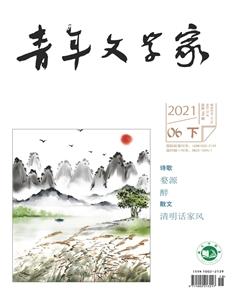路易斯·麦克尼斯诗歌的记忆书写
吴泽庆 杨纪平
路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是英国20世纪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反映了诗人的自身经历,揭示其复杂的精神生活,尤其唤起了诗人童年的酸甜苦辣。诗歌不断再现麦克尼斯对童年的模糊记忆,童年被“责任与魔法”掌控着,伴有“一切如新和一切如旧”的双重感觉。诗人在个人和公共的双重危机下,创作了很多半自传的作品,其中从《再访卡里克》《自传》和《开往都柏林的火车》中可以看到他早年在爱尔兰和英国的生活足迹。麦克尼斯作品主要描述每日生活,通过生活的点滴,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实现与他人的心灵沟通。
艾略特则认为,20世纪诗人应该让自己的作品复杂且含蓄。麦克尼斯眼中的诗人,不是一个被误解的局外人,也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代主义者,而是一个专业的艺人。麦克尼斯采取了一种自传体的方法来写作,以期用相同的经历和读者产生共鸣。麦克尼斯关注自身生活,这成了其诗歌的基本原则,在他整个诗歌生涯中,他一直都恪守这种原则。麦克尼斯的母亲在他七岁时去世。麦克尼斯骨子里是爱尔兰人,虽然出生于北爱尔兰,但有爱尔兰的南部血统。后来父亲再婚,年幼的麦克尼斯经常由家里的用人照看,麦克尼斯的童年是灰色的,他性格孤僻、敏感,不喜欢与人交往。他的诗作总是充斥着黑暗、孤独和死亡的意象,传达着对个人身份危机的苦闷与彷徨。
《再访卡里克》是一首描述作者回到他父亲工作的卡里克弗格斯镇的诗,他把当地视为一个隐喻,那里有自己潜意识中忘不了的经历。“出生前就离开祖辈的家/十岁开始学外国语/在西爱尔兰,还是在南英格兰……我的选择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不管我继承或获得了什么/遗留在我童年里的喜好/就像安特里黏土里迟来的岩石/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改变它的力度和名字—/出生时的山峰已经遥远”。十岁之前麦克尼思一直生活在卡里克弗格斯,他过着压抑且沉闷的生活,十岁之后麦克尼斯去了英格兰求学,从马尔伯勒到牛津大学。英格兰对麦克尼斯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爱尔兰才是他的祖国。童年的不幸经历和后来的异乡求学生涯让他内心有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陌生感。朗利认为,麦克尼斯早期诗歌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他在卡里克弗格斯度过的童年环境的一种自我反应。卡里克弗格斯镇,是一段充满画面感的记忆,并非一幅文化的想象的地图。西爱尔兰是他心中坚守的神话般的一份忠诚,尽管它意味着家庭羁绊。麦克尼斯的父母都是在康纳马拉的克莱登附近长大的,诗人认为自己和妹妹伊丽莎白是来自西部的流放者。西部是他的梦幻之地,是他诗歌中常常提及的乌托邦。如果说西爱尔兰代表一种梦幻,南英格兰则蕴含着现实和真实,那里有他熟悉的多塞特郡,当年在谢伯恩、马尔堡和牛津的生活足迹时常涌现在脑海中。在那里,麦克尼斯接受教育、从事工作和开始文学生涯,伯明翰大学、贝德福特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场所都见证着他的生活,在那里,他长大成人,建立了文学声望。
麦克尼斯经常反思诗歌和诗歌背景之间的关联,尽管他离开了爱尔兰多年,但是,越到后期,越激发起他去找寻童年的兴趣,哪怕有几分苦涩,并有意无意地与青年时期的现实进行对比,去扣动自己的内心深处。麦克尼斯在记忆中一直保留着过去,也许是出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或者说是他的艺术追求。这是一种痴迷的状态,童年在他的内心是复杂而矛盾的,诗歌中原始的经历和后来的生活体验在不断转化中。贝尔法斯特北岸的港湾一直在他的记忆里,那里是阴暗、潮湿的乡村。诗人记忆中童年的海,很久之后才去过,那是一种逃避,总能听到雾角的声音,儿时的他认为那是一种新奇的存在,有种冒险的愉悦。火车的噪音、海浪声和工厂的汽笛贯穿了他的童年,构成了诗人作品的早期经验,如同一个人持续存在的梦。诗人本能地去描写记忆中的童年影像,港湾、土地、工厂、花园深深地烙下北爱尔兰特有的印记,灰色港湾里满是污垢和旧桶,狭小的土地尽显绿色,小工厂点缀在农田之中,公墓和山楂树篱笆比邻而居。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原始的、一成不变的印象在增添着色彩,海洋在一次去安特里海岸的斯图尔特港的旅行中走进了他的世界:“突然,从一个角落或山顶吹来了一阵强烈的夹杂着鲱鱼味的咸风,我们下面是一片蔚蓝,依靠在渔民码头的墙上,洁白和海鸥交杂在一起。”诗人用了很长时间的积淀才在诗中再次展现出斯图尔特港口。诗人的“童年印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因为诗人后期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想象力不斷变化。事实上,他所有的社会记录显然是受北爱尔兰半工业环境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和机械相互衬托,栩栩如生,尤其体现在诗歌中对工厂的描写上。
麦克尼斯一直对自己的过去耿耿于怀,几乎达到一种痴迷。麦克尼斯发现,他的家庭环境中,很少有“欣喜的时刻”,在诗歌中,真实的黑暗与他哥哥的先天愚钝、母亲的抑郁症和死亡、父亲的再婚所投下的阴影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另一部作品《自传》的创作来源。《自传》创作于1940年,家庭发生的变故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影响,十岁时,他离开了北爱尔兰,开始了英格兰的学习生涯,以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自传》这样写道:“在我的童年,树是绿色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最初,麦克尼斯的生活还算幸福,那时的“童年”,树是绿的,充满健康活力,生机盎然。“有很多东西可以看”,诗人充满好奇,外面的世界美好而新奇,小孩子处于懵懂状态,好奇着世界上仍未被自己探索的许多美好。接着,诗人告诉我们,父母在他心中不一样的形象,“我父亲让墙壁发出回响,/他把衣领穿反了……/我妈妈穿着一件黄色的连衣裙/轻轻地,轻轻地,温柔。”这里,出现了父母平时的生活场面,父亲穿反的衣领和母亲的黄色连衣裙形成了对照:父亲的粗心大意和母亲的温婉亮丽;父亲的喧闹和母亲的安静。“我五岁的时候,噩梦来了/之后的一切都不一样”。麦克尼斯五岁时,他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住进了都柏林的一家养老院,直至最终去世,那几年小麦克尼斯寂寞孤苦,最终没能再见到自己的母亲。麦克尼斯十岁时父亲再婚,他惧怕父亲,觉得父亲非常冷漠,难以理解。
五岁成了一个分界点,此前是轻松、温暖,以后便成了孤寂、绝望,温馨、幸福的家庭成为过往,日常平实的场面不再呈现。“噩梦降临,从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作者描写了夜晚里孩童的孤寂、恐惧和绝望,“黑暗中在跟死人说话/我床边的灯暗了下来。”睡觉时,没有父母相伴;说话时,无人在身边,留下的只是无声的黑暗;半夜醒来,发现无人照看自己,“当我醒来时,他们并不在乎,没有人,没有人在那里”;噩梦时,自己“无言的恐惧高喊,无人回答”;早晨醒来,看到的是“冰冷的太阳”,自己独自离去。孩童的心理经历了从期盼到恐惧,最后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着失落与煎熬,忍受着孤寂与折磨,面对现实是他一种无奈的选择。复句“早点回来,不然就别来了”是诗人的期盼,期盼他们早点回到“我”身边,因为幼小的“我”需要你们。同时,这也是对父母不断发出的警告,如果你们再不回来,“我”就失望了,等“我”绝望了你们就不再被需要了。现实让诗人意识到,母亲的离世,母爱不再,父亲再婚,父爱也在渐渐逝去,孤独、无助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自传》反映了诗人个人的童年生活,描述了诗人离开了北爱尔兰后,去了英格兰的学校接受教育。“不然就别来了”真实地表达诗人与父亲关系的日渐疏远,英格兰让麦克尼斯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和父亲在观念上也开始产生分歧。他改了爱尔兰口音,放弃了弗雷德里克这个名字,放弃了继承父亲的信仰,情感上开始倾向于英格兰的世界。不过麦克尼斯从未迷失对自己的认知,从未丧失爱尔兰人的自我意识。尤其是“早点回来,不然就别来了”似乎也在不断地暗示着他内心中渴望回归爱尔兰、回归祖辈家乡的愿望。
麦克尼斯在英格兰生活、工作多年,回归爱尔兰是麦克尼斯诗歌不断展现的场景,《开往都柏林的火车》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歌写于1934年,麦克尼斯前往都柏林去见威廉·巴特勒·叶芝,这样的回归不是寻求童年的记忆,而是汲取诗歌的营养,从而让自己的诗歌事业走出低谷。麦克尼斯曾有一段时间,不再创作诗歌,重新写诗后,诗集未获出版,于是他回到了爱尔兰。不过,《开往都柏林的火车》更多的是描写火车一路穿行的风景。麦克尼斯笔下的阳光笼罩风景往往描写的是英格兰,而荒凉单调却成为爱尔兰的主色调。“我们一缕一缕地筛分不成熟的想法/来对抗不断重构的基本事实”,诗人把想法置于“事实”之上,这样的先验思想让他在随后的诗行中,加入了更为丰富的想象,想象是碎片化的、是梦幻般的,诗行中出现“反复敲响的钟声、咆哮的戈尔韦海、巨大的海鸥、金色的河流、黄铜般的阳光”,塑造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里的浪漫主义源自现实真实,而不是某种信念或信条。可见,离开爱尔兰的麦克尼斯,信仰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人类主观经验和思想构建起来的理想国度,他所信奉的只有思想外部的现实、具体存在的事物。诗人的想象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物象,而不是人们脑海中呆板、可笑的观念,“我给你那些自然发生的/原原本本穿过空间出来的事物”,诗行具体描绘了“桅杆、骨头、海鸥、利菲河、树篱、粉刷过的墙”,这里的想象是一种真实的显现,不是缥缈、虚无。“我数着座位上的扣子,我把贝壳/举到耳边倾听空灵之音,只听到/整数的重复,钟声/反复敲响,恐惧的乏味”。诗人思绪不定,内心深处的思绪随着火车的轨道声时远时近,他的想法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似乎想倾听贝壳声,钟声却掠过耳鼓,单调得令人恐惧。《开往都柏林的火车》从旅程写到信念,再到描绘自然,书写想象,诗行跳跃,意象缥缈。漂泊不定是诗人生活之常态,迷茫犹豫更是诗人挥之不去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来自诗人对自身身份的迷茫,他生于爱尔兰,长于英国,却一直称爱尔兰为“我的祖国”,这种个人身份的迷失造就了麦克尼斯诗歌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麦克尼斯的童年回忆是“感知的统一”,火车上所想象的一切是对童年的回忆,这种回忆不是分离的、疏远的和互不相关的,而是有序的、自然的和统一的。麦克尼斯笔下的景物有宁静美好的“安特里姆郡的山丘、暗金色河流、宁静的阳光”,还有“狂暴的大理石子、雷神的霹雳”,有淳朴的乡间农民,也有城市里的现代女孩。他的诗歌体现了很多想象的经历,这些见证着诗人的矛盾心理。这首诗对比了“将我的思想聚集在我的拳头里”和生命本身流动的“重塑”。这接近于麦克尼斯在哲学中对“两种方式”的描述:“我希望世界是一体的,是永恒的,是绝对理念的化身……与此同时,任何典型的一元论体系似乎无可救药地静止。”像麦克尼斯这样的诗人,会质疑社会习俗和社会权威,但他不会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而会依据社会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麦克尼斯的诗歌书写成了年后的复杂情感和对悠然往事的反应,他经历的这种痛苦和愉悦,对他的身心产生了影响。因此,他的诗歌敏锐地捕捉到成年与童年经历的双重叠加,这些联系断断续续、一直存在。麦克尼斯的情感处于一种徘徊的状态,表面上看,他远离了“自己的祖国”,被排除在爱尔兰之外,成了一种无根的状态,然而,他的内心却从未离去,从未忘记自己的童年。在麦克尼斯的爱尔兰视野中,“超越”和“乌托邦”仍然是难以捉摸的目标。他的西部是一种令人向往却无法实现的状态,是一种追求的方式。他的诗歌究竟是一种逃离的过程还是一个被劫持的过程?童年是饱含失望还是充满欢欣?还是两者皆有?答案未知。不过,可以断定的是,麦克尼斯的矛盾心理以及他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复杂性,其中有情感共鸣、有追寻彷徨,还有自我审视。因此,麦克尼斯对艾略特的“诗歌的非个人化”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只是避免说“我”。不过,他后来的诗歌中的“他”是戏剧化的自我,代表着人类。也许,考德威爾的理论恰恰解释了麦克尼斯的大部分作品采用自传体形式的原因:诗歌本质是主观的,通过诗歌,人可以回归本我,实现与外在世界的心灵沟通。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WW062)英国“左翼诗派”诗学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