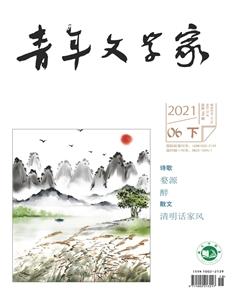浅谈韩少功作品中的乡土世界
唐语韩
韩少功2000年返回当年下乡的山村定居,2006年首度发表《山南水北》一书,韩少功写下中年再度下乡的生活体验,可看作是《马桥词典》的续篇。韩少功一头心牵着乡村,另一头又记挂着现代城市,他的创作便体现出一种他所独有的“乡土精神”,这种精神浸染在了他笔下的乡土世界的方方面面。
一、文学语言的乡土化
语言就是搭建乡土空间的砖和瓦,正如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提到的怀旧的“烟砖”一般,在构建房屋的时候,用料是十分讲究和难得的。这种带有乡土气息的语言,表现在《马桥词典》中,主要在词条的选取和阐释上,而在《山南水北》中则体现在人们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话语中。
方言词汇被大量选取进入了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诚然,最具“乡土性”特质的方言无疑是传达乡土情感的载体,但由于方言的地域性,仍需要借助普通话来解释,于是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张力。在这些方言与普通话或模糊或对立的关系背后,蕴含着马桥人独特的世界观:
第一,词义的相悖。马桥的方言义和普通义呈相反的状态。如在“醒”这一词条在马桥的解释就与大众认知相悖。在公众视野和大众认知里,“醒”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但在马桥世界里,词义恰好相反,“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就是指蠢货。公认的聪慧在马桥人这里变成愚蠢,表现出马桥方言特有的思维和认知。
第二,词义的蜕变。如“懒”这一词条中,“我”把兆青的小儿子魁元介绍到朋友的工程队谋生,他却嫌晒嫌累跑了回来,于是用了“懒”这个在“我”看来代表很重的批评词语来表达不满,但魁元却因此而自豪,夸张地列举自己诸多懒处。此时“懒”字已失掉所带有的消极语义色彩,被“我”所憎恶的耻辱在马桥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语,因而引起人们的向往。
第三,词义的重新定义。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前的《编撰者说明》中提示词的使用范围,有些词的流传和使用范围仅限于马桥,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对词的重新定义,具有严格的界定和界限。如《三月三》词条中马桥人要在农历三月三日吃黑饭和磨刀,这是仅限马桥的特有风俗,所以提到“三月三”就意味着黑污污的嘴和刀刃上颤动的春天。这些与普通话有别的方言的运用,使得马桥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发生在其间的故事也就着上了乡土的色彩。
在《山南水北》中,作者用各个独立的小标题串联成章,每个小标题下都有一个关于八溪峒或人或物的小故事,展现了八溪峒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待生活和生命的独特看法。口语化的乡言俚语贯穿在叙事语言中,有些词语不需要刻意的解释,根据上下文便能理解一二。乡土味儿还体现在村民对人物、事物的命名上,不呼其姓名,而以职业、长相特征取绰号:有根是船夫,便是“船老板”;战争留下来的战士叫“老逃”“逃夫子”“逃同志”;等等。这样的相处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反映出淳朴的民风。此外,村民的对话和言论更是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乡政府召开村组干部大会,宣布禁止“买码”,村民气得直拍桌子:“贺麻子,你不能做缺德的事!我们又没拿你的钱买码,你狗咬烂布巾啊?你蛮得屙牛屎呵……”这原汁原味的“语录”是农民生命状态和精神生活的本真流露。
二、文学形象的乡土特质
韩少功的乡土世界中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质,他笔下的人物并非大英雄,而是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又有些本事的“小人物”,甚至颇有些怪诞之处。作者用平淡的语调讲述着他在乡村的所见所闻,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人物的绝妙之处慢慢显现,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看得人津津有味。
(一)在质朴中见才智,在怪诞中见道义
《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中都有许多故事展现着在乡下生活的劳动人民如何在平凡质朴的生活中充分运用他们的才智。比如《马桥词典》中神秘的希大杆子不知姓名来历,却能拿出洋药洋布洋火换谷米吃,还可以给妇女诊病甚至接生……在《山南水北》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杀猪佬伢子同时也是兼营卫星安装的“卫星佬”,骑着摩托而来的两人确实将问题麻利地解决好了,这让“我”怀疑他们小小的摩托无所不能。
书中的山村人物常常貌似愚钝,却自有其智慧与道义。《山南水北》里的人物就默默地坚持着某种道义价值,往往感人至深。剃匠何老爹只用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就能使出数种精妙绝伦的“刀法”,而文中令人动容的不仅是何老爹的精彩剃头手法,更是何老爹与老顾客之间的深情厚谊。韩少功写道:“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青龙偃月刀》)何老爹为病重的三明爹最后一次剃头,让他带着笑意离开人世,体验了“人生最后的极乐”。还有未卜先知的笑大爷、垃圾户雨秋、神医塌鼻子、百蛇不侵的蛇贩子黑皮等,无不形象鲜明,滑稽可爱。韩少功对这些乡野奇人充满敬意与爱怜,他巧妙运用变形夸张的手法,集中地凸显某些人性特质,让我们在质朴中看到山乡人们的智慧。
(二)乡村中有人情,万物间蕴灵气
韩少功笔下的乡村总是上演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比如《马桥词典》中的半头人也能生活如常,村妇转世能认出前世的家人,找被称作梦婆的精神病人预测彩票然后真的一夜暴富,等等。《山南水北》中划船不用槳、不采药却能拿出黑药丸轻松治好各种疑难杂症的神医塌鼻子,更有夜晚突然出现无法解释的瞬间白日现象等,无不令人啧啧称奇,仿佛冥冥之中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与人共生,颇有巫楚文化之韵。
万物有灵,这是人类祖先最初的信仰,不仅人有灵魂,动物植物也都具有灵魂。《马桥词典》中那头只有煌宝能治住的牛“三毛”犁田的功夫极好,却因伤人事件死在当初说什么也不肯卖牛的志煌手中,死前还不停地流下眼泪。《山南水北》中讲述动物的故事则更为丰富:在抓蛤蟆的老五接近时就集体突然噤声的青蛙们,喜欢跟着人却不合鸡群的“小红点”……村里人也把狗称作“呵子”,这些山中异犬会不远千里为分离的奶狗送去口粮,会为主人挡煞,平常会充满戒备地发出吠叫守家,看见贼就咬,看见客人就以枝条封嘴,并且这样的习惯无人调教天生就会。不只是动物,植物也充满了灵性。《马桥词典》中引发“枫癣”的枫树,在《山南水北》中枫树更是会在有丧事的时候发出“树哭”,在人们想砍掉它的时候发出“树吼”,哪怕在枯死之后被人用作柴火也要报复人至死,令人发疯,所以被称为“疯树”。充满灵性的植物世界中,依赖农作物维持生计的村民,把瓜果蔬菜皆视为有情之物。除了这些奇妙如精怪的动植物,在作者笔下就连船只也有了生命,船主人胜夫子去世后,他的船总是无端脱锚,它像个活物一般寻找着它的老主人,最终被新主人一气之下一把火烧了,只剩下一把钉子。《山南水北》介于小说、随笔间的文体加重了这些场面的真实感。此类场面反复出现,倘若以理性和科学无法解释这些客观实在,那么至少可以保持尊重和敬畏。
三、现代化冲击下的乡土
神秘乡土常常被放置在现代物质文明与消费文化的价值对立面。韩少功的知青经历已然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块土地也为他的创作生发出不竭的灵感。面对都市和乡村、现代化与乡村生活方式的自主性,韩少功表现出了自己的价值倾向。
在《山南水北》中有农民无视衣服的剪裁妨碍劳动的灵活度,穿着西装挑粪、打柴、撒网、喂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山南水北》没有以往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没有坚守启蒙主义传统,而是作者对乡村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平实描述。作者从现代化的都市回到乡下后,一方面自己尽情享受着在乡间的质朴生活,另一方面又想尽办法将现代化的知识和技术带给乡村以求改善农民的生活现状。
四、结语
韩少功笔下的乡土世界更多关注的是乡村的抽象层面,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认同,并以此为基点结合整个人类的命运进行现代理性的思考。本文仅以《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两部作品为例,从语言、文学形象和现代化于乡村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韩少功笔下的乡土世界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其笔下的乡土空间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