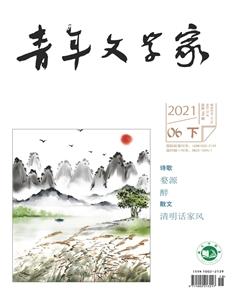以“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分析《故乡》《曼斯菲尔德庄园》叙事的相似性
倪金鑫
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即他不但关注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关注了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鲁迅创造小说的能力很强,而且他可以借助西方文学思想的启蒙方式来进行引用,他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专心致志于小说的研究和发展,终于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高峰。“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小说模式,也称归乡模式,常被鲁迅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作品如《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
简·奥斯汀是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她继承和发展了英国18世纪浪漫的现实主义传统。简·奥斯汀居住在英国的乡村小镇,过着祥和、安宁的生活,接触到的也都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因此作品中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代表作品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等。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的《故乡》与《曼斯菲尔德庄园》,在小说情节的展开中都运用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一、“离去”的被逼无奈
鲁迅的《故乡》以“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为开头,采取横截面的写法省去了“归乡”模式第一阶段“离去”的情节,而通过《故乡》中的某些提示、鲁迅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得知,黑暗混乱的社会中,中国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无疑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困窘,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毫无权利可言。而鲁迅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尝尽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他面对这日益被都市文化消解殆尽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村文化,面对黑暗的现实与生活的压力,鲁迅选择“寻异路、走异地”,他不得不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新的出路,鲁迅的离乡是被迫的。
简·奥斯汀以写英国的乡村风情著称,她曾说自己的作品无非是乡间村庄里三四户人家的故事,其中代表作品之一便是《曼斯菲尔德庄园》,这个作品是有关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爱的小说。作品中的女主角芬妮·普莱斯的“离去”也同样是被迫的。芬妮的母亲弗兰西斯小姐有两个姐姐,分别是大姐沃德小姐和二姐玛利亚小姐。大姐嫁给了牧师诺里斯先生,诺里斯先生在托马斯爵士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份教区牧师的俸禄,每年有将近一千英镑的收入,而二姐玛利亚小姐,她嫁给了托马斯·伯特伦爵士,一跃成为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以及男爵夫人,这门显贵的亲事得到了普遍的赞扬与家庭成员的一致认同。而芬妮的母亲弗兰西斯小姐却使她的家庭丢尽了脸面,她嫁给了一个海军中尉普莱斯,一无文化,二无财产,再加上她生育众多的孩子,丈夫又无所作为、整日喝酒取乐,她的家庭生活入不敷出,极其拮据。为了获取姐姐们的帮扶,普莱斯太太给多年未曾联系的亲戚写了一封求助信,伯特伦太太为了减轻妹妹生活的压力,在诺里斯太太的提议下,经过丈夫托马斯爵士的同意后,决定抚养普莱斯太太的长女芬妮。这对于普莱斯太太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这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减少与生活负担的减轻,而对于诺里斯太太来说则满足了她想要的仁慈的美好名声。此刻,没有人会询问九岁的芬妮是否同意前往曼斯菲尔德庄园生活,她没有选择,只能被迫与熟悉的环境分开,与自己最好的玩伴威廉分别,来到这个令她害怕与不自在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她在这里经受着诺里斯姨妈喋喋不休的“教导”,遭受着两位表姐的指指点点与嘲笑,时刻面对着托马斯爵士威严的面孔,过着寄人篱下、顺从听话的生活。
二、“归来”的事与愿违
鲁迅《故乡》中的“我”回乡名义上是为了处理卖老屋和搬家的事情,实则是为了找寻自己内心的精神故乡。鲁迅在外漂泊数载,为了生活东奔西走,尝尽人间冷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感到迷茫和困惑,回乡也是为了“寻梦”。在鲁迅的记忆里,故乡是美好的,色调是明快的,那里的人也都是淳朴有趣的。但当他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样的故乡的时候,他内心感到了一丝悲凉,不禁问道﹕“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下面又有说到他的故乡比这个好多了,但是却又没有影像。这是因为他内心的故乡是以小孩子的视角理想化了的精神故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没有言语,也没有影像。回鄉后,那个曾经被称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在生活的摧残下,也变得尖酸、丑陋、刻薄、爱占小便宜,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时广大底层农民生活的艰难与困苦。最令“我”震惊和失望的无疑是闰土的一声“老爷”,这让“我”感到悲哀,原来“我”与闰土之间已经隔了这么厚、这么高的壁垒,是绝不可能打破的。那个在金黄的月光下、海边的沙地上、在一望无垠碧绿的瓜田里刺猹的少年;那个在雪地里捕鸟的少年;那个与“我”以兄弟相称的承载着“我”对故乡的一切美好幻想的少年,已经消失不见了。在多子、苛捐杂税、官、绅、兵、匪的压力下,他已经变得麻木、沉默,如木偶人一般了。这无疑是对“我”的一种巨大打击,本想着回乡寻梦,结果无梦可寻、无路可走,不由得让人黯然神伤。
芬妮之所以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朴次茅斯,是在经过托马斯爵士的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当时亨利·克劳福德先生对芬妮表达内心的情意,为了获得芬妮的爱,还帮助了芬妮的哥哥威廉在海军中谋得了一个军衔。他所做的这一切让芬妮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她应该感谢克劳福德先生帮助了自己的哥哥;另一方面,在排练话剧《山盟海誓》的过程中,芬妮作为局外人清醒地看到了克劳福德与她的两位表姐之间的感情纠葛,认为他是一个玩弄情感、不负责任、生活不检点的人。因此,芬妮对他实在喜欢不起来。但出于上述的恩情,芬妮又很难做到对克劳福德先生恶语相向、断然拒绝,她唯一的做法就是逃避,以及等待着克劳福德兄妹的离开。托马斯爵士认为在克劳福德先生离开之后,芬妮肯定会意识到情人的奉承和爱意对自己的重要性。但当克劳福德真的离开后,托马斯爵士并没有如愿以偿,因此,他决定让芬妮回一趟自己的家,让她明白财产与地位对她未来的幸福生活有多么重要。因为托马斯爵士坚信,芬妮在丰衣足食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生活了八九年,已经丧失了比较和判断的能力,而她的父亲将会使她清醒。
对于芬妮来说,能回到那个年幼时以自己为中心的家庭,与长期分离的家人团聚,在路途中有威廉的陪伴并且能暂时逃离克劳福德兄妹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当芬妮的马车停在家门口的时候,她才能意识到现实中的家庭与她想象中的家是如此不同。她的家庭是如此的拥挤、破旧,家庭的秩序混乱不堪,环境与生活用品都是不洁净的,家庭里的吵闹声仿佛没有停止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除了刚下车母亲给了自己一个亲切的拥抱,好像没有人关注她。这与她想象中的充满爱意与欢乐的家庭是毫不相关的。芬妮在这里没有获得想要的幸福与满足,相反,她认为待在这里纯粹是一种煎熬。
三、“再离去”的毅然决然
鲁迅回到故乡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窒息的悲惨景象,面对着以杨二嫂为代表的被生活异化了的尖酸刻薄的村民,面对着以闰土为代表的老实干活谋生计的农民,却依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喘不过气来的境况,“我”才明白原来“我”心中的那个明亮的故乡只是“我”的一种想象而已,“我”彻底无家可归,俨然成了社会的过客与弃儿。“我”想要在故乡获取精神力量、追求归属感的梦破碎了,但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悲凉又涌入心头。但鲁迅并没有就此消沉与绝望,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坚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再离去,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身上,他不是一个虚无主義者,他坚信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美好的明天一定会来临的。
芬妮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方面都与自己所盼望的截然相反的家里,更是一刻都不想停留。因为她的家庭是一个粗俗、吵闹、混乱的场所,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以及怎样待人接物,尤其是她父亲的粗鄙和无礼更是让芬妮无法忍受。与乡村新鲜的空气隔绝,芬妮的身体也变得不如从前,她开始想念曼斯菲尔德庄园,想念那里的人与物,甚至她把曼斯菲尔德庄园称作她的家。当她收到埃德蒙的写着要带她回庄园的信时,她的兴奋是难以比拟的,因为“虽然曼斯菲尔德庄园可能有一些痛苦,朴次茅斯却没有快乐”。在芬妮自己家中,她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每天靠着用托马斯爵士给她的钱出去买面包充饥,家里的一切仿佛都与她格格不入;而在庄园,芬妮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伯特伦姨母需要她,那里的一切都秩序井然、美好安宁。因此,芬妮对于自己家庭的再离去是非常主动的,而且这种离开的意念非常强烈,毅然决然。
四、小结
综上所述,虽然鲁迅的《故乡》和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在内容上看起来毫无关联,但是在小说的情节叙述模式上都采用了“离去-归来-再离去”,对小说意义与主旨的建构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