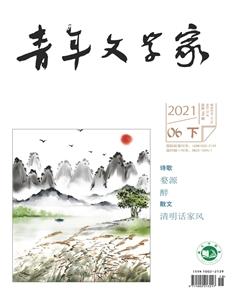唐五代词中“男子作闺音”词的底色
欧静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的出场通常而言是带有间接性的。女性作家的稀少以及社会中存在的男女地位不平等现象,无不在限制女性对于文学的介入,然而又可以说,女性从来没有缺席古代的文学创作,从《诗经》中的“佳人”“游女”形象,到后来诗词文学中的爱情篇章,女性作为社会中另一个与男性成员相对应的存在,总是会经常性地出席似乎是被男性所占领的文学领域。然而,这种作为描述的对象和情感付诸的另一方出席,或者是作为另有所指的意象存在,都是不够直接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出场的间接性,或许要到“男子作闺音”词的出现才有所改善。
一、词中“男子作闺音”现象的出现
曲子词作为配乐而歌唱的新体歌辞,最早是在酒筵歌席上创作与演唱的。《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乐府古题序》说:“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因之准度。”《花间集》欧阳炯的序里写:“则有绮筵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这样一种词的生发状况,可以说导致词直接诞生于一种女性化的氛围里。因此,文人在创作填词时自然会受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且考虑到由女性歌唱的需要,词的创作者会有意识地从词的主题、风格、语言等方面来迎合这种需求。词的“男子而作闺音”也正是这种创作迎合的体现,甚至后来的词人们也不得不部分地延续了这种风格。但这种现象持续出现在词的创作里,宋代以豪气词著称的辛弃疾也依然使用这种代言体,就与中国自古以来诗歌里“比兴寄托”的传统不无关系了。以恋爱中的男女关系来比拟君臣关系,早就存在于诗歌的创作中,如屈原的《离骚》就已经出现“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离骚经序》)的现象。这种“比兴寄托”传统和封建社会政治环境下文人对于创作言语的谨慎以及对于言志的委婉要求,使得词在脱离了早期的女性化创作环境之后,依然延续着“男子而作闺音”的创作方式,从而使得“男子而作闺音”成为词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男子作闺音”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则是由清代的词学家田同之完成的,他在《西圃词说》中说道:“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在他之前,清代文人朱彝尊也曾在《曝书亭集》(卷四十)中说:“词虽小技,昔者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所谓假闺房之语,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他们分别从抒情方式和“比兴寄托”的角度明确了词中“男子而作闺音”这一现象。
二、“男子作闺音”词在抒情中的倾诉感
男子作闺音这类词中,作者对于“闺音”主体身份的设立,使得词的抒情带有一种直接的倾诉感。以温庭筠的词作与和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的诗作来比较。温庭筠《菩萨蛮》:“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而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虽然同样写闺中愁思,所写对象同是女人,李商隐的《无题》用的是直笔描述,这种口吻,更像从第三者的视角来写这个女子从八岁到十五岁的生活,它的抒情藏匿在故事的背后,诗的视角和情感都带有一种间接性。而温庭筠《菩萨蛮》中所绘之景,从室内至室外的变动是从女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到的,这种主体感官视角的代入,使词在抒发脆弱的忧思闺怨时,不仅使人不至于跳出词所营造的氛围,也让这份情思有一种直面而来的倾诉感,它突破了作者与所写对象的身份限制,让情感的发出者直接与读者对话,这种直接性无疑让它的情感更大程度地被读者所感知。
三、“男子作闺音”词精于细节的画面感及绵软多情的意境
同样作为代言体格式,相比于之前诗中的“闺音”,词在遣词造句上更具有女性化特色,不管景物描写中的精致细微,还是情感表达上的细腻婉约,都营造了一份聚焦于细节的画面感和绵软多情的意境。诗作中虽然也不乏“闺音”,但由于“诗言志”的定位,其中又常蕴含着作者自身的期待和言指,因而它的用词和布局就不会拘于闺阁之内,而其所兴遥思,也往往不局限于两情之间,从而呈现出一种阔大的气韵和境界。而温庭筠的另一首《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作中选择的物象,从“玉炉”“红蜡”“画堂”,到“翠眉”“鬓云”“衾枕”“梧桐”,无不与女子的生活切切相关,这种细节性与其要抒发的女子的忧思是呼应的,抒情的场景局限于闺阁视线之内也正是出于对女子所处生活空间的模拟。“泪”“残”“寒”等,更是将这种雨夜的凄切情思,渗透在了这一方空间之中,浑然不知究竟是这香、这烛光、这梧桐树里的滴雨声因女主人公的情思而沾染上了愁怨,还是女子在这切切雨夜里因为这香、这烛光、这梧桐里的滴雨声才突然遭受了这相思的苦怨。唐圭璋先生评价它:“画堂之内,唯有炉香、蜡泪相对,何等凄寂。迨至夜长衾枕之时,更愁损矣。眉薄鬓残,可见辗转反侧、思极无眠之况。”这首词在抒情上的细腻深曲,也正是这种聚焦于细节的画面感和绵软多情的意境所共同营造出来的。
四、“男子作闺音”词在抒情上的片面性
“男子作闺音”的词作中以女人作为情感的发出者,这使其表达的情感,原是出于男性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女子的一种普遍性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女子的情感里自带着一种天真纯粹和痴怨的色彩。词作者在这种相当片面的设想里将感情的纯粹和痴怨赋予了词,同样也使得这种男子作闺音的词在抒情上整体上显现出一种片面性。词至韦庄,从为应制而作开始转向了自我情感的抒发,在他的词作里,既有拟作闺音的代言体,也有以自我为主体来表达真挚深情的词。前者如《思帝乡》两首:“云髻坠,凤钗垂。髻坠钗垂无力,枕函欹。翡翠屏深月落,漏依依。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其二:“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后者如《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同样写男女之情,在《菩萨蛮》里是男对女,“红楼”“香灯”“流苏帐”所构成的背景尽管也是温馨旖旎,但作品里主人公对于这个女子的感官来自别离时的眼泪和设想中的她对于远方之“我”的盼望,这种思念的情感固然真挚动人,然而在这里,这位男性主人公仍是在一个较大的广阔天地里以一个“出走”的身份来关怀这份恋恋不舍,这份情感可以说只是他羁旅中的一份慰藉,即使厚重,也不会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它只是一份混杂了少年情思的乡愁。张惠言评价这首词:“此词盖留蜀后寄意之作。”可以见这情思其实不纯,羁旅之怀、家国之思夹杂其中,使得这份情更为宏阔厚重,然而相应地,其中为男女之情留下的余地就显得薄弱了。相比较来看,两首《思帝乡》里写的女主人公的情感尤顯得纯粹而决绝,第一首里面“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这是一个深闺里的女子对这份情感的认知,它伴随她从日升到日落,从身体的感受到飘摇的思绪,视听言动中,无不是它。作者所写的女主人公,是在用生活的全部和心绪的所有来倾注于这份思念之中,这种唯一性所昭显的正是“情”的纯粹。而第二首中的“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是一位少女对一份感情的想象和期待,她的情的付与带有着不顾一切的决绝,尤其考虑到当时对女子的道德要求,这种不顾一切是直接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因此就显得格外真挚,并且自带一股“痴”性。这种纯粹和痴怨,由于“男子而作闺音”的这一现实,即词中这些女性的情感来自男性对于女性情感的设想,一种自作主张的设定,就反映出这情感的“真”和“痴”背后想象的局限性,从而见得“男子而作闺音”词在抒情方面有其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五、结语
“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虽然不由词首创,然而它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大规模结合,却使得“男子而作闺音”词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独特底色。这种词人以女性角色来发出情思之音的表达所形成的身份代入,使女性在其中获得了一种类似“主体”的角色,而身为男性的词人则反而成为这“主体”背后的影子,从而使这类词获得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视觉差异和审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