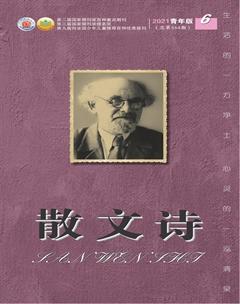咖啡苦不苦
黎落
我更喜欢一个人旅行。或许是因为我不擅长和人过分亲密。我所分享的植物都是长青的,花朵固然美,只是凋谢过于颓废,那就不如让它一年四季青着,有一种稠稠的茂盛。
最远的旅行是在欧洲,过安检时,我心生惶恐,没有熟悉的脸,乡音渐寂,身边每个人都是异乡,都是远,都是陌生的城市和街巷。仄逼的地下铁幽深,有压迫的事物如在眼前。当年读到陈丹燕的欧洲行,十分惊艳。选词从容泊淡,气质绵密疏致,尤其是路边那些咖啡馆。古老寂静,带着优雅疏离的欧洲人特质。
还是喜欢教堂和它们尖尖的顶。石板路圆圆的磨得发亮的光,在脚下延伸,会送人去往哪里呢?梵蒂冈城墙外摆出长长的两条人龙,国人很多,个个都那么美。世界越来越小,心越来越轻。
海水漫过脚踝,轻和重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旅行就是走一走,看一看,换一个地方遇见一群人,再换一个地方遇见另外的。敞开虽说不坏,固守也是好的选择。我愿意这样走下去,直到失望或者死亡。说到死亡,主题太庞大,不如藏进一粒果核,在更小的世界里做更小的自己。
有一家书店的世界地理杂志上有过交代,威尼斯细长的小巷,店铺一家一家开过去,漂亮的橱窗,漂亮的女人和男人。玩偶和手工。书店仄逼,书很随意地堆着,一直到天花板。后院靠近河水,一只贡多拉栓在门框的金属大把手上,一百欧元游一圈。你来,我就走;不来,我就等。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游河的不太多,更多人选择沿着水边细细地走。水在脚下,城在手边,心在心上。走得久了,会变得空。跨过河面的封闭长桥是一座监狱的组合部分,想象百多年前,有戴镣铐的犯人从这头走到那头,时间仿佛突然就长得看得见。生命顽强,生活卑微。很多故事都走不到终点。
“咖啡苦不苦”,这话不是我说的,陈丹燕说的。她在欧洲走了十几年,写下那么多旅行笔记。坐在露天咖啡馆的铁质椅子上,一只手端著咖啡,另一只手写着干净的文字。这个我喜欢的女人,有一种岁月静好的美。
走路走长了,我会随意坐在路边。抽烟的妙处就是和自己对话,我有一身的疲惫,你可有与之匹配的诗意?我们都活得太糟,太固有,太浪费。
还是选择写诗吧。咖啡的苦很契合诗歌的苦。黄昏的翡冷翠城刚刚落完雨,雨滴集合在地面,照出谁的影子?一只小小的流浪猫找不到过夜的家,跟着我走过长长的街。买了牛奶,可是我没法带它走。生命有很多不确定性,或者转过街角就能看见你。我愿意等你,愿意为你找一个过冬的地方。
终于有人愿意带它回家,我想笑一笑,更想哭一哭。终于还什么都没有做,那个弯腰捡起你的女人,才是你的有缘人。我只是路过,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在这个陌生国家的陌生的屋檐下。
有些地方本身就是一首诗,在等着你走进去。夏日的罗马,斗兽场的杀气早就不存在了,广场前美丽的女孩穿着雪白的连身裙,桀骜和优雅都是她们的,中世纪的暗影在哪里?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的恣意和任性,就没有相遇的魔咒和游弋。同样的,现在环形的长廊,历史是什么?是眼前所见,还是曾经血腥的生与死的角逐?
死亡有锋利的暗影,可以穿越,也可以被忘却。
不吃早餐已经很多年。
水在空荡荡的胃部行走,河流有向下的力量,山势耸立,两岸逶迤,冷暖不可说。
我对绘画有一种天然的亲切。那些线条。光影。色彩。明灭。胶着。画面中的宁静和纠葛,内外情绪的释放和包裹,属于一个人的自在。在笔端流淌的河和胃部流淌的河,都是有声音的,仿佛爱。
艺术的相通性,可以让爱它的人学着做更好的自己。当我在一条河中,我们的愉悦也是相通的。就像我在壁画前,在受难的基督面前。大教堂内到处都是色彩明亮的绘画,四面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走进去,坐下来,一颗心也沉入水下。你还是你,你又不是你。宗教思想的绘画都有宏大的主题,选择的题材来自《圣经》和历史,丰凝的饱和度很高的色彩,强烈的视觉传达,像置身河流。
我在一条河中走了多久?
那些年,我们都那么年轻,那么美。只是你转身的时间太长,壁画可以越过百年而不幻灭,我们却不行。生命线蜿蜒,彼此之间,早就是沧海桑田。
高高的台阶上,安妮公主和记者的爱情一点点铺开,剧情的走向有人性之美,这个逃出宫殿的女孩征服了罗马和她的臣民。美是全人类的,爱也是。那么,我也停下来坐一坐,不是为等待,我有哭泣的渴望,却没有一双流泪的眼睛。
悲伤对于我,已经是太过奢侈和矫情。不如去看山,山色如苹果树,开满苹果花。不如去看水,水色如泼墨。不如发呆。我是习惯酒醉的人,亲爱的,你有没有菊花酒?
一个倾斜太久的人,也是一座倾斜太久的斜塔。从高处下落的球体带着决绝的势,一路倾覆。伽利略的验证也是生命的验证,好像孤独,总是一路向下。这个年代,能抵达的多么危险。
可是,四月是极美的时光,天空有鸽子,水上有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