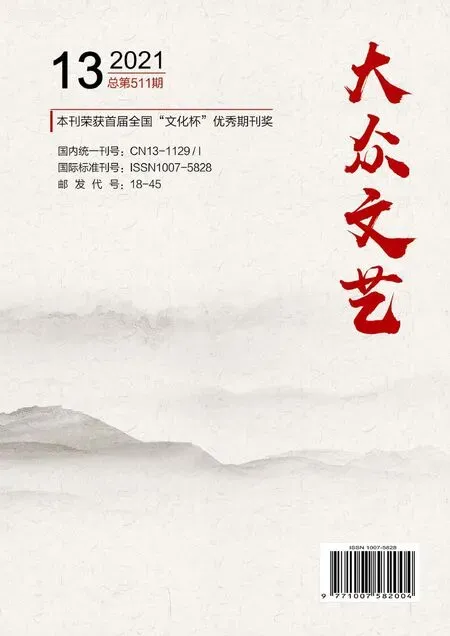从《山海情》看主旋律电视剧的突破与创新
王雪萍
(西安培华学院,陕西西安 710125)
2020年恰逢中国扶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这一关键节点,文艺界以“脱贫攻坚”为主题,创作了多种多样的“献礼剧”,带领观众多层次、全方位回顾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历程。《山海情》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一经播出就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山海情》从平民视角出发描绘闽宁两地深情,通过生活之中点点滴滴、桩桩件件的扶贫事迹,把中国智慧融入脱贫攻坚的壮丽历程之中,并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征程助力。
一、塑造人物群像,讲好百姓故事
自2011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出现了呈现明显的数量回落趋势,古装剧、偶像剧、都市剧占领了市场。农村题材电视剧收视惨淡、日益没落,其社会影响力应声而降,同时大量同质化的扶贫影视剧也呈现井喷化趋势,对于原本就缺乏农村生活经历的城市观众来说,很难被带入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剧情之中,如果以千篇一律的方式进行角色塑造,那么观众也就更加难以获得共鸣。
山东师范大学张新英副教授表示:“这类农村题材影视剧作品通过大众熟知的苦难苦情叙事模式,歌颂和彰显了农民高尚朴实的品德和人格魅力,然而过度夸张的剧情以及刻意的煽情,使得很多影视作品最终走向了虚假浮夸、千篇一律的刻板结局。”大量农村题材影视作品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过度苦情化,主人公在剧中孤苦无依,情感和事业都屡遭打击,但仍然奋不顾身地为别人(重病伤残的公婆和父母、身世悲惨的孤儿、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女)付出所有。农村题材电视剧如何将自然且真实的乡土人情和人性通过故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减少该题材的“说教”意味,是影视作品创作者们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山海情》中最能让观众产生共情的地方,正是剧中成功塑造的经典人物群像。
《山海情》作为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代表佳作之一,人物群像的塑造全面地展现了新时代农民集体的精神面貌,剧中的马得福、水花、马喊水、马得宝、麦苗等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真实而立体,生动而鲜活,感人至深。漫天铺陈、遮天蔽日的沙尘风暴,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剧中将当时的西北农村寸草难生、贫穷落后的真实面貌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还原,使观众更有代入感,更加能够身入其境地体会到脱贫攻坚的艰苦卓绝与不易之处。
在剧中扮演脱贫领头人马得福的黄轩,从第一天工作起就每天为村里农田灌溉用水和公共通电等问题而四处忙碌奔波,渐渐地他对于村里的发展之路感到无比沮丧又迷茫。正在这时,国家的对口扶贫相关政策出台,福建省担起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重任,并建立“闽宁村”,将其作为扶贫合作的样板。剧中马得福困难不断,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辛不易,但为了早日让村里的人脱贫过上好日子,他一直很坚定从未退缩甚至放弃。剧中展现的各种奔波不易,正是那时候扶贫基层领导干部们最真实的生活细节写照。主演黄轩感慨道“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基层农村干部们,我真的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值得尊敬,他们是火种、是光明,真诚地向他们送上最诚挚的敬意。”。
张嘉译饰演的马喊水,深刻了塑造了从西固走出去的老一辈们的形象,他们虽然几经挣扎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地方,但是他们始终铭记初心,没有切断和老一辈的根脉,反而是把根深深地扎入了更肥沃的土地中,用智慧和勤奋开拓新的疆土,互相扶持着走上了康庄大道。尤其在剧中,马喊水面对儿子马得福和村里老一辈之间矛盾爆发时的艰难抉择更让人动容。
李水花的扮演者演员热依扎用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样丰富立体,从反对婚姻包办离家出走到返回家乡听从父亲的安排嫁人,从搭建房屋到跟专家学习种菇,她塑造的水花不仅很好地诠释了女性如水般不断向上涌动的女性力量,轻柔且坚毅,内心永远坚定乐观,永远笑对生活的苦与乐,同时也蕴含了一种温暖美好的希冀,预示着未来闽宁镇将会一直朝着越来越繁荣的方向不断发展。
剧中同样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很多,比如白麦苗、马得宝,还有为了教育奉献青春的乡村教师白崇礼,共同组成了在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斗中,艰苦奋斗、团结一心的闽宁镇人民的群像。
二、灵活运用方言,呈现乡土人情
“土味”是许多观众对于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评价,当代的影视作品创作者们一直致力于更新该类作品带给观众们的刻板印象。在《山海情》中,不仅在视听语言的运用方面展现出电影质感,同样对于台词、音乐等细节表现也尽显真挚。剧中对于方言的灵活运用,使得乡土文化、乡土人情展现得更加有温度、有情感,同时也为农村题材电视剧更新大众的审美风向标与“土味”的刻板印象提供更多可能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方言是一个地区长期凝练而成的文化合集,是最能够直接体现人民原始真实的情感宣泄、交流沟通、心理活动的语言形式,与当地的历史传统、文化生态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我们能看到《乡村爱情》中的东北话、《什刹海》中的京腔、也看到《装台》中在地道的西京腔调,灵活巧妙地运用方言,也可以为影视作品的艺术感在适当的创作语境中增色。电视剧《山海情》主要运用了闽宁两种方言,其中,大量的西北籍演员使用方言演绎,突出了西北人淳朴的特质。例如,村民口中的“是达不是爸”充满喜剧效果,迅速拉近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同时,福建方言的运用也消减了因贫困而带来的沉重感,例如,“老教授研究自杀”“小偷要搞科研”等由于异地方言引发的冲突,让人啼笑皆非。又例如,闽宁两地语言不通所产生的现实场景在剧中重现,剧中福建扶贫干部与当地民众“鸡同鸭讲”的戏份,也直接反映了当地扶贫初期语言沟通困难的实际问题,剧中村民邻里、村民与村干间的“唇舌之斗”,也贡献了大量的看点和笑点。剧中除了人物台词运用方言之外,另一代表性的运用是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剧中几个重要的唱段如《唱花儿的花儿》,都起到了活跃剧情,塑造人物的重要作用。
从播出的效果来看,《山海情》方言版深刻地展现出地域方言运用于农村题材影视剧中独特而有趣的魅力和重要作用,展现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浓厚淳朴的乡土人情,丰富了在生存艰难的贫困地区依旧朴实真诚的乡村农民的形象。《山海情》扎根乡土,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原型,用原汁原味儿的方言作台词,方言版《山海情》的出现给予了乡土审美以正确的风向标。中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根源在农村。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村落也许会消失、乡土文化可能慢慢会离我们远去。通过影视作品留住乡土风情和一代代农民的背影,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根源。影视剧创作者们应当积极找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方向,振兴农村题材电视剧,保留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乡土人情和乡村韵味。
三、平民视角叙事,建构家国情怀
随着《山海情》《大江大河》《装台》等剧的热播,以平民化视角进行叙事的电视剧目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线,并且受到了观众的热捧。在影视剧的创作中,“平民视角”的创作理念是指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将观众意识带入创作过程的始终,创作出对观众有感染力的作品。[4]越来越多的优秀电视剧立足普通百姓平凡的日常生活,从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视角和审美趣味出发,贴近现实生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绘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哲理与人性,以平民化视角聚焦普通小人物,以小人物的命运展现时代变化,构建家国情怀,触及人的心灵深处,让人为之动容。
《山海情》导演孔笙介绍时说道,“这部剧的创作基点来自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对他们来说,脱贫致富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相辅相成,和他们每一个人复杂的个人情感都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平民化视角和国家叙事紧密结合,国家政策给人们给予了改变命运的转机,使得个体也能在群体的不断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没有雍容华贵的场景,没有夸张苦情的设计,有的只是老百姓为了生活奔波的日常,从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为观众讲述平凡又温暖的故事。例如,剧中的白崇礼老师,在剧中是一位为了乡村教育奉献青春的校长,他原本只是一个支教老师,但是因为心系山里的孩子,就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一辈子。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却在这个贫困山区的学校的三尺讲台奉献了一生,甚至一度不被女儿白麦苗所理解,但他仍然胸怀大爱、甘愿奉献、舍小家为大家,让人为之动容。这种将家国情怀构建放置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将诸多平凡个体的生活经历作为全剧的叙事基底,将他们的情感与生活理想融汇于国家发展进程的底色中,使得现实和历史巧妙交织,完成了平民化视角的灵活表达。
作为“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这部剧的剧名表达了福建和宁夏两地帮扶政策以来长久的深厚情谊。这部作品没有落入宏大叙事的窠臼,主创团队以平民视角的角度,为主旋律扶贫剧的创作找到了不煽情、不说教,贴近现实表达的方式,为观众建构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四、结语
《山海情》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电视剧,以扶贫为题材,是一部跨越世纪的“闽宁模式”扶贫故事记录,对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对于方言的灵活运用以及平民化的叙事对于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无疑是一次大胆且有影响力的尝试,释放了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潜力和活力,为我们深入探索创作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提供了有价值的创作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