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铺
林跖

1.路遇八仙
这是辛亥革命后,发生在鄂城的故事。
这天,刘老板起了个大早,他的布铺开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可近些日子的生意却一落千丈。好在前几天有介绍人联系他,说有人要买他的铺子,这不,他今天起了个大早,专门去城门口等买家。
不多时,道路尽头有两人骑马缓缓而来,刘老板一见两人都戴着白帽子,就知道约定好的买主到了。
可远远看去,刘老板的心跳漏了一拍,领头那人除了白帽子,还戴着一副青色鬼脸面具。这年月世道乱,群魔乱舞,该不会是什么江洋大盗吧?
等两匹马走近,刘老板仔细一看,心脏差点儿没从胸口跳出来,这哪是什么面具,分明是张真脸啊!
那马上骑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满脸铁青色不说,还歪嘴斜唇,皮肤僵硬如石头,乍一看还以为是人身上安了个青石雕塑。刘老板盯了半晌,也没见他有什么神态变化,简直像个……活死人。
刘老板心里害怕得很,只是想着要卖店铺,才没有扭头就跑。待两匹马踱到刘老板身边,另一匹马上的人翻身下来,说:“你就是布铺的刘老板吧?幸会幸会,鄙人马牧,之前跟你打过招呼的!”
眼前这人年纪四十左右,身材魁梧,一脸方正。刘老板镇静了些,招呼道:“马老板,幸会,这一路来得可顺利啊?”
“好说好说!”
两人这般寒暄了几句,马牧见刘老板时不时朝少年身上瞟,便贴心地解释道:“这是我的侄子,名叫小武。去年害了病,患上面瘫症,你别瞧他看着怪,但其实人机灵着呢!”
说着,那青色鬼脸的小武朝刘老板眨了眨眼,刘老板这才安心下来。他一边领着二人向城内走,一边询问二人的来历,听说二人是打上海来的,态度热络起来。
“上海好啊!富得流油,满地都是黄金!马老板怎么想着到鄂城来呀?”
马牧笑道:“还不是混不下去了!”
三人边聊边走,没几步路就进了鄂城。忽听一阵凄婉的丧乐传来,刘老板抬眼一看,暗骂一句“晦气”。原来迎面而来的,竟然是一队穿缟戴素,抬着薄皮黑棺的“八仙”,旁边还有鸣锣、放炮、吹乐的,很是“热闹”。
这“八仙”跟过海的八仙不同,指的是专做白事的抬棺匠,有的地方也叫八大金刚。
劉老板赶紧拉着马牧二人让到一边,躲进一条小巷子里:“马老板,对不住,刚进城就拉你给死人让路。”
马牧奇怪地问道:“让路倒是无妨,只是为何我们要躲进小巷子里?”
刘老板只说了一句:“这是黄六郎棺材铺的八仙!”
“黄六郎?”马牧追问,但刘老板却拉住他,让他不要多说。
八仙抬棺向前,正从巷口经过,马牧注意到,这伙八仙个个膀大腰圆、凶神恶煞,不似善类。那具又窄又薄的棺材顶在八人肩上,像根脆扁担似的,好似下一秒就要给掰成八截。
不只如此,八仙后头还跟着一队人,男女老少都有,哭哭啼啼,神情低落,显然是亡者家属。家属队伍里,还有个枯瘦的男子,满脸悲戚,双眼通红,攥着双拳时不时瞪向前方的八仙。
马牧问:“刘老板,这么薄的棺材,送葬的肯定不是富裕人家,为何还要请足八人抬棺,礼乐齐奏,摆这么大的排场呢?”
刘老板没回答,反倒拉拉马牧的衣袖,小声说:“马老板,我知道一条小路,咱们要不绕路走?这白事当头,万一冲撞了煞气,可就不祥了!”
马牧二人只能跟着刘老板绕进小路,很快,哀乐声听不见了,刘老板松了口气,彻底放松下来:“方才离得近,我不敢跟你多说。其实,这黄六郎乃是本地一个极可恶的恶霸!他在鄂城一连开了三间棺材铺,包揽了整个鄂城的丧葬生意,谁家死了人,都得去他家的棺材铺买棺材。关键是,买棺材必须从他家请八仙,一请就是八个,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马牧说道:“有这种事?人一辈子只死一次,就讲个入土为安,若是不孝子也就罢了,凡是孝顺一点儿的,谁敢让父母、家人曝尸荒野啊?”
“正是啊,所以鄂城的百姓不知叫这个黄六郎坑走了多少血汗钱!更可气的是,他还……”
“他还什么?”
刘老板却及时住口,摇摇头:“唉,一时也说不清,反正,这黄六郎是骨子里都坏得流脓了!”
马牧心中一叹,这世道坏成什么样了,竟连棺材生意都有人横加敛财!
2.店铺始末
不多时,刘老板引马牧二人来到一处三间大的店铺:“马老板,这就是我的铺子,你进来只管仔细瞧!”
店铺空间很大,格局也不错,是家好铺子,马牧问:“刘老板,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其他店的生意都不差,怎么就你的布铺开不下去了呢?”
刘老板脸色微微发白,眼神闪烁:“是我自己的本事不够……”
马牧也不再多问,在店铺里走来走去,看个不停。刘老板跟在马牧后头,一边殷勤地介绍,一边心里跟猫爪挠似的,这马老板到底要不要买啊?
足足看了半个时辰,马牧这才停下脚步,刘老板以为他终于要买了,马牧却说:“刘老板,不知道县里有什么便宜的地方可以住下的?”
刘老板忙道:“我铺子里面就有三个大房间,还带个大院子呢!”
马牧稍微退后一步,婉拒道:“抱歉啊,刘老板,我暂时不打算买。”
“为什么?如果是价格,我们可以再商量!”
“不是价格,我只是想再探探,这么好的店铺,生意为什么会差呢?”
刘老板脸色更加苍白,张张嘴回答不出来,眼看着马牧二人就要出门离开了,才咬咬牙,跑出去把他们拦了回来。
“唉,罢了罢了,我还是实话跟你说了吧,这店铺,的确有那么一点小问题!”
原来一个月前,有一个瞎眼的道人路过刘老板的布铺,忽然发狂一样地大叫,喊着什么“天煞汇聚,克死全家”之类耸人听闻的话,引来诸多路人围观,最后他竟呕出黑血一摊,倒地不起。刘老板吓了一大跳,赶紧叫伙计送那个瞎眼道人去医馆看病。
等到道人醒过来,才告诉刘老板,他的店铺乃是天煞阴魂汇聚之地,凭刘老板的命格,若不早日离开,怕是不日就要横死当场!
刘老板本来也不信这些话,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他一开门,门口竟然被一具棺材给堵住了!
“棺材?”马牧和小武对视一眼,“莫非……是黄六郎?”
刘老板神情阴郁,说道:“不错,正是黄六郎!这黄六郎说自己鬼命加身,身怀阴阳眼,能够预见一个人的死期,若是哪家有人要死,他就会在哪家门口放上一口棺材。除非找到他进行化解,否则必有血光之灾。”
马牧冷笑一声:“这是明着巧取豪夺!那你找过黄六郎吗?”
刘老板苦笑道:“自然,当天就去了!可是,这黄六郎竟想以十个大洋的价格买下我的店铺,这可是我祖上三代积攒下的家业,怎能便宜他!”
马牧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难怪刘老板这么急着脱手,原来是这样!”
刘老板忙说:“明人不说暗话,这摆明了是黄六郎看上我的店,派人设局,什么瞎眼道人、阴煞汇聚、棺材堵门,估计都是他搞的鬼,与我这铺子可毫无干系!”
“那刘老板为何不自己继续开店呢?”
刘老板一下子被噎住了,长叹一声:“就算我不怕鬼神之说,可周围的百姓却深信不疑,唯恐避我店铺不及啊!罢了,看来我只能去找黄六郎了!”说着,他垂头丧气,就要送客。
马牧反而笑了,从怀里掏出了三根金条,稳稳地放在桌上。
刘老板眼睛瞪得滚圆,吞了口唾沫:“马老板,你这是……”
“这家店,我买下了!”
刘老板笑得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像绽开的菊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三根金条塞进怀里,然后才反应过来,脸上一红,故作客气:“这个……马老板,你真的买了?可你该怎么开店呢?”
马牧摆摆手:“这你就不要管了,来,我们签契约吧!”
3.棺材堵门
店铺卖出去了,刘老板无事一身轻,当天晚上就请马牧二人去醉仙楼吃了一顿好的,酒桌上,不免又提到黄六郎。
原来,这黄六郎早年竟然也是干八仙出身,腌臜下九流的命,后来不知怎么的,开了一家棺材铺,竟从一个下九流的八仙发家致富,一连开了三家分店不说,还积攒下偌大的家业。
别人都说,他身具鬼命,煞气冲天,棺材铺就是他的发财符,所以,即使他已经发家致富,棺材铺仍然开了下去,还越开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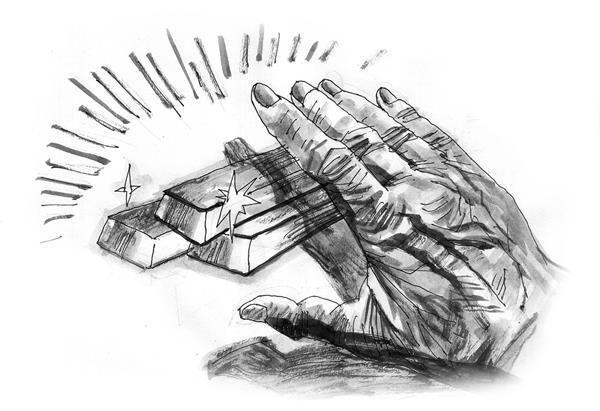
刘老板三人喝得正欢,忽然,酒馆的大门被人踹开了,三个彪形大汉神色不善地走了进来。
刘老板当即就变了脸色:“你们……是黄六郎的人?”
三人也不说话,让开身子,又走进来一个老板模样、五十来岁的男子,他个头极高,满脸横肉,壮得像头毛熊,一进门,就有一股盛气凌人的气势扑面而来。
来人正是黄六郎,黄六郎皮笑肉不笑地说:“刘老板,远远地就听你提起我,这时节,你怎么还有心情大吃大喝呢?”
劉老板一拍桌子站起来:“你不要欺人太甚!谁不知道是你设计害我?如今你的算盘可打空了,我的店铺,已经卖给别人了!”
“卖给别人?谁敢买你的店?”黄六郎刚问出口,眼睛就瞪向了马牧,“原来是个外乡人!”
马牧知道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了,端起酒杯:“黄老爷是吧?本该亲自登门拜访,不想在这里见面,敬你一杯薄酒!”
黄六郎根本不接,“哼”了一声,说:“吃了熊心豹子胆,连我的铺子也敢抢!”
马牧也放下酒杯,冷冷一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
黄六郎气得狞笑起来,手一挥,三个壮汉立刻逼了上来。
“砰”的一声脆响,一直没说话的小武忽地掏出一样东西拍在桌上——一支铁皮手枪!
三个壮汉当即慌了神,连连倒退,手足无措。黄六郎也倒吸了一口气,赶紧收起狰狞的表情,抱拳道:“原来是条过江龙!敢问尊姓大名?”
“马牧。”
“马兄弟,须知强龙不压地头蛇,你真要买这个店?”
马牧淡淡一笑:“世道艰难,有个栖身之地实属不易,七天后店铺开业,也请黄老爷大驾光临。”
“既然如此,祝马兄弟生意兴隆!”说罢,黄六郎转身就走。
等四人狼狈离开,刘老板眉头紧皱,忧虑道:“马老板,这下可糟糕了,黄六郎要是给你门口也摆一具棺材,你生意怎么做得下去啊!”
马牧浅笑道:“山人自有妙计!”
第二日,天蒙蒙亮,马牧就听到门口一阵刺耳的唢呐声,好像在吹丧乐。出门一看,吹唢呐的人撒腿就跑,但一具黑漆漆、已经封盖的棺材堵住了店门。马牧上前想挪棺材,没承想棺材被死死地钉在了地上,根本挪不动。
周围几个邻居也被惊动了,一看这场面,个个都变了脸色,指指点点。马牧却神色如常,干脆不搬了,他朝周围的邻居一拱手,大大方方地说道:“诸位,六日后我家新店开张,到时请一定要来捧场啊!”
周围人哪里敢搭话,扭头就走,唯恐避之不及。看这架势,别说六日后来光顾,就是经过这里,都得撒腿跑开。
很快到了第三日,这天下午,也许是良心上过意不去,刘老板又来了一趟,见着门口的棺材,他浑身一激灵,找到马牧就问:“马老板,怎么不把棺材挪走啊?”
马牧漫不经心地回道:“钉死在地面上了!”
“砸碎了挪走不成吗?”
马牧摇摇头,说道:“这黄老爷可不是省油的灯,你当这口棺材是空的吗?你靠近它的时候,没闻到一股臭味吗?”
刘老板一听,更是吓得头皮发麻:“里、里面……”
“别紧张,兴许不是人,只是野兽的尸体呢?”
刘老板一听差点儿没吐出来,破口大骂:“这黄六郎太恶毒了!”骂了一阵,他脸上露出一抹苦涩,咬咬牙,不经意地问道:“马老板,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马牧没有回答,转而问道:“刘老板,你来找我做什么?”
刘老板干咳两声:“这个,我是怕你人生地不熟,想告诉你更多黄六郎的事情!”

刘老板说自己收了马牧的钱,虽然解决了麻烦,良心上却有点儿过不去了,于是干脆出个人力,多方打听黄六郎的事情,正好有所收获,就赶紧来找马牧了。
“刘老板客气了,你我钱货两清,白纸黑字签了契约,不必觉得亏欠。”
“你别推辞,这些消息很重要!”刘老板说道,“我来是想告诉你,这黄六郎不是孤家寡人,他手下专门豢养了一帮八仙,就是之前我们在路边见过的那些,个个凶神恶煞。我之前以为他们都是正经招来的苦力,可这两天稍微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不清白!”
“怎么说?”
“我也是听在县里当差的亲戚说的,这些人里,有好些都是逃犯、土匪,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马牧来了兴趣,问道:“这黄六郎胆子这么大,敢收留这些人?”
“黄六郎可是比土匪更狠的恶霸啊,正好跟这些人臭味相投!倒是你,马老板,黄六郎现在不对付你,只是听说你几天后开业,想看你的笑话呢。等到后面,双拳难敌四手,你只有一杆枪,怎么敌得过黄六郎那么多人?”
马牧微微皱了皱眉:“刘老板,那你说该怎么办?”
刘老板叹息一声:“要我说,还不如跟黄六郎服个软,顶多损失些钱财,免得有生命危险。”
马牧冷哼一声:“刘老板,之前黄六郎谋夺你家产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情势不一样嘛!之前我不知黄六郎的底细……”
马牧冷笑一声:“那刘老板不妨把卖店铺所得的钱还给我,好自己找黄六郎和解?”
刘老板尴尬地笑了笑,说:“这个……已经签了契约的事,怎么能反悔呢?”说罢,他又苦口婆心道:“不如,我还你半根金条,咱们跟黄六郎和解如何?要不一根也行!”
马牧气得发笑:“要和解,你自己去!”
眼看马牧已经不高兴了,刘老板只能叹息一声,转移话题:“对了,你侄子小武呢?”
“他在里间准备我们将要卖的货物。”
刘老板侧耳去听,听到里头一阵敲敲打打的声响,说:“该不会是打制家具吧?唉,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这么十足的信心!”
“倒也算是家具吧!”马牧不置可否,打发了刘老板。
4.见招拆招
又过了几天,七天之约已到,马牧刚刚出门,就瞧见黄六郎带着一群人堵在了门口。
黄六郎朗声大笑:“马兄弟,黄某听说今天你开业大吉,怕没人光顾,特地带人来照顾你的生意!”说着,黄六郎身边的两个壮汉燃起一串鞭炮,丢在马牧的店铺门口,又有三人唢呐、锣鼓齐响,奏的却是送葬的哀乐。“噼里啪啦”的巨響,吸引了路人前来围观,但那口堵在门口的棺材已经掩盖不住里头的臭味了,人群只远远地围着,不敢靠近。
马牧冷静得不似常人:“黄老爷,只听说臭味能招苍蝇的,没想到还能招来你们。”
黄六郎冷冷一笑:“别扯这些没用的!你快开业吧,我倒要看看,除了我,谁敢买你的东西!”
马牧倒是饶有兴致:“你知道我要卖什么吗?”
黄六郎有恃无恐:“无非是些家具桌椅,不必担心,我做主,待会儿就买你一套!”
马牧盯着黄六郎看了半晌,直到把黄六郎看得浑身不自在,才转身推开大堂的门:“既然你想买,我当然不介意。”
门一开,在场围观的群众,还有黄六郎,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两间大堂里面,竟然摆了五六具棺材,看黑黝黝的木色,厚重至极。原来,马牧开的竟然也是棺材铺!这下,黄六郎的打算是彻底落空了,棺材堵门,反倒给马牧做了一次大大的宣传。
马牧不知从哪里掏出一罐火油,浇在门口那具棺材上,然后一把火点燃了棺材,他在火光中朗声道:“各位父老乡亲,今日借烧棺之机宣告,我家棺材铺正式开业,以后凡是有需要的,都可到我这里定做,我这里的棺材价格公道,用料十足,童叟无欺!当然,我还是恭祝大家长命百岁,永远也不要光顾我们才好!”
一席话说得后面围观的群众忍不住鼓起了掌,明明是棺材铺开业,可众人兴致却很高涨。
马牧扭头看向黄六郎:“黄老爷,不妨进门,我给你好好挑选一口心仪的棺材?”
黄六郎丢了大面子,脸上阴晴不定了一阵,忽然又大笑:“真是不知死活!你可知,为何整个鄂城只有我一人敢开棺材铺?”
“愿闻其详!”
“鄂城从前就是战场,在此地下,埋了成千上万的冤魂!所以整个鄂城煞气冲天,亏得我天生鬼眼,已经看到你眉间含煞,不日就有血光之灾!”
这话说得阴气森森,没吓住马牧,倒是把边上围观的群众又吓出去老远,生怕沾上一点儿煞气。
马牧不为所动:“真是巧了,算命的说我属猫,有九条命,最不怕的就是血光之灾。”
黄六郎恼羞成怒:“我们走着瞧!”
黄六郎一走,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很快,随着木棺烧成灰烬,马牧上前察看木棺余烬,意外发现木棺里还有一具薄皮棺的残骸,辨认之下,竟然正是初入鄂城时,那群八仙抬着的薄棺材!更别说,里头还能看到少量的人骨残骸。

显然,这棺材下葬之后,黄六郎又偷偷派人挖了出来,送到他这里!黄六郎打的主意,恐怕就是让马牧砸开棺材时打碎尸体,叫他落个狼狈的下场!
马牧神色越发冷峻,此等丧尽天良之人,简直天理不容!
等收敛好尸骨,已是傍晚。这时,刘老板又来了。他乍一看自己的布铺被改成了棺材铺,心中五味杂陈:“马老板,这可是临街的铺面,你竟然在这里开棺材铺?”
马牧摇头道:“不这样,怎么堵住黄六郎的嘴?”
“何必呢,何必呢?”
“刘老板又有什么高见?”
“不敢不敢,我来是想再给你带一点消息。”
马牧意味深长地说:“刘老板神通广大,消息灵通啊!”
刘老板愣了一下,勉强一笑:“这……我这不是在本地待得久了嘛!也不算是新消息,其实十年前,鄂城有三家棺材铺,除了黄六郎这一家,还有另外两家。”
“后来呢?”
刘老板咬咬牙:“听说都被克死了!有一家,每到半夜就会听到古怪的叫声,怕是闹鬼!另外一家更惨,儿子十几岁就撞了邪,半夜拖著一口棺材离家出走,离奇失踪,第二天,棺材铺老板也疯了,一把大火,把自己和老婆活生生烧死了!总而言之,他们的下场都很惨!也许这黄六郎说得对,鄂城真是百煞汇聚之地,不适合开棺材铺呀!”
马牧脸上平静如水,心中好像毫无波澜:“刘老板什么时候也相信这些了?”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刘老板“唉”了一声,“总而言之,你就一开棺材铺的,去哪里不行?何必跟黄六郎死磕?”
“开棺材铺怎么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刘老板无话可说,只能悻悻地离去。
当天夜里,马牧刚刚熄灯睡下,忽听黑暗中传来一阵怪诞的哭声,隐约有十几二十人,声调哀怨,此起彼伏,有女声,有男声,甚至还有婴孩的啼哭,听在耳里,真如鬼哭狼嚎般恐怖。
马牧立刻起身,刚想出去察看,忽听外面“砰”的一声枪响,紧接好几声乱枪,又有一阵“丁零当啷”的陶罐碎裂声,然后便悄无声息了。
马牧掏枪出门,见到小武一手提一陶罐,另一手握着手枪回来。马牧松了口气:“怎么回事?为什么开枪?”
小武把陶罐递给马牧,一张青色鬼脸更加狰狞:“黄六郎派人来了,我和他们对射了几枪,他们就跑了。”
马牧接过陶罐,里头传出一种怪异声响,似是哭声,又像猫爪子挠木头似的,刺耳无比。小武解释道:“这是一种名为哀虫的怪虫,专门生在尸体里,有时候在乱葬岗,我们听到的诡异声音,就是它们发出来的。把它们装在特制的陶罐里,就会发出类似人的哭声,甚是诡异。来人带了足足二三十罐,恐怕是用人的尸体专门豢养的。”
马牧冷笑道:“拿死者尸体养虫,竟有如此疯狂行径,我看他黄六郎真是离死期不远了!”
第二天一早,马牧刚刚出门,却发现门口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邻居。他扭头一看,只见侧边墙壁上血红一片,竟给人泼满了不知是狗血还是鸡血的东西!
不用想,又是黄六郎的手段!
忽然,人群中有人惊呼:“看啊!流血了!流血了!”
马牧低头去看,店铺门口不知何时被人放了一块青色的大石头,眼下这块石头竟跟泉涌似的朝外冒血。不多时,血色就打湿了整块石头,流成一摊,极为瘆人。
眼见众人怕得要命,马牧骂了一句:“装神弄鬼!”回头进门,很快,他就端着一个大锤子出来,“砰砰”两下把那石头锤烂了。
众人生怕马牧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可仔细一看,石头里面竟是空的!
马牧低头检查了一下,朗声道:“诸位,这是有人装神弄鬼,存心不让我的棺材铺开下去!请看,这块石头内部被凿空,再用鱼胶、铁钉重新固定,装上红色染料,等染料化开鱼胶,‘鲜血就从缝隙里涌出来。这分明是江湖骗子的把戏!”
马牧在石头残骸里面一掏,拣出好几根铁钉,众人一片哗然。
接下来两天,什么从天而降的鸟尸、爬成“死”字的蚂蚁、路过的道士和尚,各种各样的异象轮番上场,可马牧和小武对这些江湖手段了解极深,每每总是信手拈来就戳穿了骗局。
这般下来,谁还不知道其中猫腻?有些老人渐渐想起,这些年来,不少店铺、富户家里,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到底是谁装神弄鬼?大伙儿这下是心知肚明了!
5.阴谋算计
“废物!废物!”黄六郎在家中一连砸了三个花瓶,破口大骂,“都是废物!”
下首战战兢兢立着的,竟是刘老板!原来,刘老板为马牧打探消息,其实不是心里愧疚,实在是黄六郎专门派人找到了他,用他家人的安危对他威逼利诱,他才不得已去接近马牧。
黄六郎发完脾气,咬牙切齿地说:“绝不能让这家伙嚣张!既然软的不吃,那干脆直接办了他!”听出黄六郎的杀意,刘老板浑身冰凉。黄六郎道:“在城内杀人,有损我声誉……”他看一眼浑身颤抖的刘老板,狞笑道:“就看刘老板,能否想个法子骗马牧出城了!”
刘老板“啊”地叫了一声,软软地坐倒在地上。
接下来,一连三天,黄六郎都偃旗息鼓。
这天中午,刘老板又上门了:“恭喜马老板,你是一战成名,连黄六郎都不敢再招惹你了!”
马牧把刘老板迎进来:“刘老板此言差矣,这黄六郎还不知道憋什么坏呢!”
“你太谦虚了!我今天是专门请你吃酒,来贺一贺你的!”
马牧摇头道:“那黄六郎可是伺机而动,想要找我麻烦,我可不敢出门。”
刘老板在袖口一掏:“我早想到了,所以直接带酒过来了!”
马牧也不推辞,两人到了里间,就着一张桌子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聊开了。这一次,马牧醉得很快,话匣子也彻底打开了。
原来,马牧之前是当兵的,因为意外发了点横财,才带着小武到鄂城来。买这间铺子,也是为了好好安顿小武。
两人越喝越开心,马牧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大吐苦水,说自己生活也不容易,过得艰难,之前是觉得刘老板受了欺负义愤填膺,所以才不压价,出了三根金条,那已经是他全部的钱了。
马牧抓着刘老板的手,真是情真意切,句句真心,听得刘老板眼神闪烁,愧疚得很。
终于,见马牧睡过去,刘老板总算松了口气。他也喝了不少,扶马牧躺到床上,给马牧盖好被子,没有立刻离开,他内心是五味杂陈,恨不得现在就叫醒马牧,说出黄六郎的阴谋。可一想到违抗黄六郎的下场,他又长叹一声:“这年头,谁没有难处呢……”
刘老板转过身子,刚要离开,却听到身后传来马牧的声音:“刘老板,你何故叹息啊?”
刘老板一惊,扭头一看,马牧正襟危坐,双眼清明,炯炯有神,哪里还有半点醉态?
刘老板脸色“唰”地一白:“马、马老板,你是装醉的?”
马牧盯着刘老板,半晌不说话,突然双眼一眯,再次躺倒在床上,随即鼾声如雷。
“马老板,马老板……”刘老板连着叫了好几声,马牧都没答应。心中惴惴不安,刘老板撒腿就往外面跑,天色明明大亮,可這熟悉的铺子里,却遍布一股阴森寒意,尤其是走到厅堂的那堆棺材中间,刘老板当真觉得脚底板像踩在冰块上一样透心凉。
忽然“咯噔”一声,刘老板“啊”地叫出声来,好像有口棺材响了!扭头去看,整个厅堂哪里还有别人?刘老板心里有鬼,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

6.枪声大作
刘老板刚走不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小武,打开门,是个没见过的中年人。来人也不害怕怪脸的小武,急匆匆地问道:“马老板人呢?”
小武回道:“他醉过去了,你是——”
“我姓冯,是城外云庄的私塾先生。唉,庄里一个孤老死了,实在可怜,邻里筹了点钱,让我来这儿买一口棺材。”
小武点点头:“成,店里正好有几口成棺,你进来挑选吧。”
冯先生走进门内,瞅了一眼,随手点了一口棺材:“就这口吧!对了,小哥,我一路是走来的,棺材可搬不回去,得你帮我运回去。”
小武朝这人的鞋子看了一眼,点点头道:“那是自然。不过,你挑选的棺材……”
“怎么?”
小武为难道:“这口棺材是上好的木料所制,价格上,可能贵了些,我听你说是庄上人筹钱来买的……”
冯先生结结巴巴地说道:“是这样啊,这个,我太着急了,没想太多,太贵的棺材可不行。”
小武也不待他自己挑选,又说道:“我里间还有一口薄棺材,价格公道,用料也实在。”
冯先生忙不迭地点头:“可以,就要你说的那口了!”
小武收了钱,走到里间,不多时,拉着牛车从院门转到门口:“实在抱歉,马叔醉得不省人事,我一个人搬不动棺材,不如明早等马叔醒来……”
冯先生赶紧说道:“不必这么麻烦,我帮你一起搬!”
小武领着那人进了里间,阴森森的微光中,果然见到一口薄棺材,可冯先生刚一上手,顿时脸都涨红了:“这也太沉了!”
小武淡淡地说道:“我们铺中的棺材都是真材实料,自然沉。”
两人好不容易把棺材搬上了牛车,冯先生喘着粗气,道:“咱们快走吧!”
太阳渐渐西斜,根据冯先生的指点,牛车慢慢走上了一条小路,来到一片密林之中。这时,冯先生突然捂住了肚子,说闹肚子,然后一溜烟地朝密林跑。跑了几步,他朝后看了一眼,没发现小武跟来,当即左转右转,来到一个小山坳外,低声叫道:“黄老爷,黄老爷!”
随着叫声,三三两两的凌乱脚步声从山坳里传出,一会儿,竟走出十几个人来,都腰佩手枪,全副武装,不仅黄老爷赫然在列,连刘老板也跟在其中。
原来,马牧一直很警惕,没有特殊情况根本不会出城。黄六郎便让刘老板灌醉马牧,再让冯先生把小武给诳出来,接下来只要派个人去给马牧报信,他自然不得不出城!
黄六郎得意地对刘老板笑道:“做得好啊!不过,刘老板,还得请你帮个忙……”

刘老板心里一“咯噔”,只听黄六郎说道:“劳烦你再跑一趟,知会那姓马的一声,就说他侄子在我们手上!”刘老板顿时脸色煞白,马牧当兵出身,要是知道自己出卖了他,还把他侄子给害了,还不一枪崩了他!
刘老板正想着托词,黄六郎像看出了他的心思,怪里怪气地说:“刘老板不想去?听说你女儿今年十二了?生得倒也是不错,什么时候,让我手底下这帮兄弟见见?”
刘老板一听,顿时急了,骑上马就往鄂城赶去。
打发走了刘老板,黄六郎一行人也不耽搁,很快便从四面八方朝牛车包围而去。等他们稍稍走近,惊讶地发现,牛车、棺材都还在,但牛和小武却不见了,而且牛车上的棺材,棺盖不知何时已经掀开。
黄六郎眉头紧皱,难不成小武发现问题,骑牛跑了?忽听一声“哞”,众人扭头去看,原来牛被拴在二十米开外的树上,正悠闲地吃草,牛既然还在,那个少年郎去哪儿了?
忽然,黄六郎看向中间那口掀开了棺盖的棺材,惊得双眼直瞪:“该死!拔枪!拔枪快射!”
话音未落,两根黑乎乎的短棍忽然从棺材里头抛了出来,众人慌作一团:“手、手榴弹!”
“轰”的两声巨响过后,两双手四支枪同时从棺材里头伸了出来,借着手榴弹的掩护,火光喷涌而出。一时间,整个树林中爆炸声、枪声、尖叫声大作,硝烟四起。
7.恶鬼复仇
话分两头,刘老板骑着马,不多时就到了原本自家的布铺门口,看着物是人非的布铺,刘老板当真是百感交集。他上前敲门,可敲了半天,都没人来开,难道马老板现在还醉着?他干脆直接从墙上翻了进去,找遍整个店铺,却始终没有看到马牧。
没办法,只能等马牧回来了。就这般,刘老板胆战心惊地坐在院里,等了一个时辰,直等到天色黑了,门外才响起开门声。
终于回来了!
刘老板赶紧冲到门口,一看,惊呆了,只见马牧驾着一辆牛车停在门口,小武赫然就在他边上!牛车上还有一口棺材,如同历经了枪林弹雨,好多地方的木皮都剥落下来,却没有散架。
“刘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呢?”
刘老板嘴唇直打哆嗦:“我、我……”
没等刘老板说话,马牧说:“既然在这儿了,不如帮我们一个忙。”说着,马牧指了指身后那具棺材,又做了个铲土挖坑的动作。
“埋、埋棺?”刘老板忍不住“啊”地叫出了声。
牛车已经赶进院子,马牧“哐当”一声,把大门彻底关严实了。小武先点了四五支火把,把院子照得透亮,又进门拿了三把铲子。
刘老板注意到小武的鞋子边沿,血色一片,他一屁股就瘫坐在地上。马牧走到他身边,将一把铲子递给他,另一只手拿铲子指了指院子中央的空地:“刘老板,来,从这儿开始挖,越深越好!”
刘老板战战兢兢地接过铲子,却不敢说一个“不”字,甚至连问都不敢问,只得跟着那叔侄俩挖了起来。
忽然,“砰”的一声响,刘老板吓了一跳,那声音分明是从棺材里传出的!
“它、它、它……”刘老板语无伦次。马牧却将铲子一杵,不容置疑地命令道:“挖!”
不多时,三人便合力挖出一个大坑,马牧招呼刘老板跟他一起,将棺材抬进坑里。棺材极重,刘老板能感到里头有震动,有人!
马牧跳进坑里,一把推开了棺材板,火光中,里头果真有个被塞住嘴巴、绑住手脚、浑身是血的活人,刘老板定睛一看,不是黄六郎又是谁!
马牧扯开堵在黄六郎嘴里的布,只见黄六郎涕泗横流地喊道:“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马牧不为所动:“黄六郎,你作恶多端,可曾想过会有今天?”
黄六郎哭道:“我、我就是个棺材铺的老板,顶多赚些八仙的钱,何来作恶多端啊?”
“不敢承认?那我也不多费口舌了,一个字,埋!”
小武早就等不及了,双眼血红,提着铲子不停地朝黄六郎身上泼土。黄六郎吓得尖叫连连:“不要埋了!不要埋了!我说、我说!”
黄六郎将自己如何坑骗商家店铺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在一旁的刘老板听得像掉进冰窟窿似的,全身发麻,这黄六郎做的恶事,远不止强抢店铺这一件!侵占民田、逼人卖儿卖女、害人家破人亡……尤其是早些年,为了让棺材铺多些生意,他竟然偷偷给别人下毒,把人害死之后,再上门推销自己的棺材!一桩桩一件件,简直泯灭人性,令人发指!
黄六郎再次求饶道:“我已经全都说了,好汉,饶了我的性命吧!”
小武目中怒火喷涌:“还有一桩!十年前,鄂城有三家棺材铺,其中城南一家,有个姓武的十五岁少年,你可还记得?”
黄六郎当即一惊,仔细看了一眼小武,突然双目圆睁,似乎终于认出来了:“你、你是人是鬼?”
小武自顾自地说道:“他被你活埋在地下,你可还记得?如今,他来找你复仇了!”
“不、不可能!鬼,你是鬼!”黄六郎吓得魂飞魄散,小武一张青色脸孔,在他眼里忽然变得鬼气沉沉。
小武露出一个恶鬼一般的神情,用冷冷的声音说道:“当年,你派人假意来买棺材,就是用同样的手段将我骗到郊外,你们将我装进棺材,活埋在地下。我爹为此发了疯似的找我,后来因为找不到我,他和我娘真的疯了!可你还不肯放过他们,一把火,把他们都烧死了!可怜我的爹娘,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却被你害死!也许老天爷可怜我,也是我命不该绝,当时我随身带着一柄柴刀,我躺在棺材里,用尽浑身力气劈砍棺材盖,劈了三天三夜才破棺而出……从那天起,我的脸就彻底僵死,身体也出了状况,后来连骨头也不长了,可我毕竟是活下来了,上天让我活成恶鬼的模样,就是来找你复仇的!”
到最后,黄六郎还是逃过了被活埋的下场,在活埋之前的最后一刹那,他是硬生生被吓死的。
刘老板战战兢兢地瘫坐在地上,对面是马牧和小武。刘老板忍不住问道:“所以,小武其实不是你的侄子?”
马牧回答:“不错。”
“你们只有两个人,是怎么打死黄六郎那么多人的?”
马牧指了指院子里埋黄六郎的地方:“那口棺材运出去的时候,我人就在棺材里。这棺材是特制的,里头有厚厚的铁板,枪打不穿,还藏了好几颗手榴弹,我们早有准备,黄六郎人再多,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所以,你是运筹帷幄,早有打算,就等黄六郎出招了啊!”刘老板苦笑一声,“那你是怎么看出我有问题的?”
马牧淡淡一笑:“刘老板,你可不是唱戏的料啊,第一次见我,我就看出你欲言又止,像是心里有事。我也算见过不少世面,一个人到底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受人威胁来打探消息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刘老板听得十分惭愧,忍不住问道:“你到底是谁?”
马牧微微一笑,说起了当年。原来,他早年曾是辛亥革命中的一员干将,在革命战场上立下不小功劳,可后来局势动荡,使得他没了方向,终究心灰意冷,兜兜转转,最终决心退隐。

小武本是马牧的副官,也决定跟随他退隐。一日闲聊中,小武无意中透露了自己过去的仇恨,马牧才决定干脆就到鄂城归隐,顺便给小武报仇。
叙完旧事,马牧最终放了刘老板一马,看着他慌忙逃窜的身影,小武说道:“长官,真的放他走嗎?”
马牧轻轻叹道:“不过是个受人胁迫的可怜人罢了。”
小武像是听懂了马牧的意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僵硬的笑容:“如今黄六郎已死,我的大仇得报,接下来您可以安心隐居了。”
马牧沉吟片刻,说道:“鄂城的黄六郎已经死了,可人心里的黄老爷该怎么除呢?我以前读《狂人日记》,始终不解,可我现在忽然明白,枪杆子是杀不死人心里的黄老爷的!听说,那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就是专门杀死住在人心里的黄老爷,我决定好好看看!”
“《新青年》?”小武嘟囔道,“长官,您已经四十多岁了,怎么也称不上青年了吧?”
马牧“哈哈”一笑,意味深长道:“只要思想是新的,年龄又有何关系呢?”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杨宏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