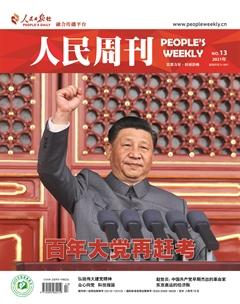在皱纹的地图里
朱成玉
老了,习惯性瞌睡,看一本书,看着看着就有了睡意。就如同此刻的你,读完《阿赫玛托娃诗选》的第十二首,睡着了。鼾声如小鹿,踢踏在诗行里。如果我把那杯咖啡递给你,并且把壁灯调得亮一點儿,你是会坚持着读完第十三首的。在那首诗里,你读出了谁的影子?
我凝神地望着一座老房子,朋友不解,这么个破房子,有啥好看的?我说,我在观望一段时光。没多久它就要被拆除,再来的时候或许就看不见了,所以,我把它记在心里,这房子就永远不会坍塌了,岁月也终将因此而不会老朽。
这老房子是我和爱人最艰苦又最温暖的岁月的见证。这让我想起安徒生的《茅屋》:在浪花冲打的海岸上,有间孤寂的小茅屋,一望辽阔无边无际,没有一棵树木。只有那天空和大海,只有那峭壁和悬崖,但里面有着最大的幸福,因为有爱人同在。
有爱人同住的茅屋,就是最美的天堂。
我愿意为我爱的人写诗,为我爱的世界写诗。而我的每一首诗,又都是一则寻人启事。在记忆之海里,用诗句打捞着走失的亲人。
亲爱的你,在第几行里?
我们渐渐老了下去,谁都躲不过时光的摧残。它看似温情款款,实则摧枯拉朽,任何人都不是它的对手。一道道皱纹,就是它的战利品。而我爱着你的皱纹,它们是游在岁月里的鱼。年轻时爱你的神采飞扬,老了爱你的苍老褶皱,这才是世上最好的爱的读本。
电影《奇迹男孩》里,朱莉娅·罗伯茨扮演的妈妈说:“我的皱纹,我的白发,它们就像一张张地图,告诉别人我去过哪儿,经历过什么。”那皱纹能告诉你,都去过哪里。这多好!在皱纹的地图里,我寻找我们一起经历的世界。在皱纹的地图里,我尝试着变回孩子,重新学习走路。把喉结隐藏,尝试着发出童声,用纯真的眼睛,重新把世界清洗干净。
身体日渐老去,思念故友却忘记了名字,老是怀疑忘记锁门,散步回来却没带钥匙,挤公交盼着有人让座,却又因为年轻人叫了一声“大爷”而心情不悦。所以尽管身体慢慢衰老,心灵却还在一刻不停地向童真靠拢。
大爷强势了一辈子,家务活从不染指,哪怕是妻子怀孕和带孩子的时候,也没见他帮过一次忙。老了,竟然像换了个人一样,把家务活全包了,还成天把大娘往外推,干吗?让大娘出去打麻将、扭秧歌,总之,爱干啥干啥,高兴就好。
这让所有人不解。大爷说,这辈子也没让她享啥福,给我生了这么多孩子,一辈子净吃苦受累了,老了,也让她享几天福吧。
这就是爱情。人世间,有多少走不通的地方,讲不清的道理,都可以让爱情去试试。
万宝湖的荷花凋落了,观赏的人渐渐少了,直到再无一人。人们喜欢绚烂,比如烟花。对于繁华趋之若鹜,对于凋零,无人问津。
在那一片凋零里,一朵晚开的荷花,异常耀眼。无人欣赏,它便开给阳光,开给风,开给这步步紧逼的秋天。
诗人雷平阳在一首诗里形象地把母亲和孩子结合起来——“母亲……坐在老式的电视机前,歪着头,睡着了,样子像我那九个月大的儿子,我祈盼这是一次轮回,让我也能用一生的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
看吧,在皱纹的地图里,爱,一直都是连接彼此的那条路,窄窄的,却在维系生命的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