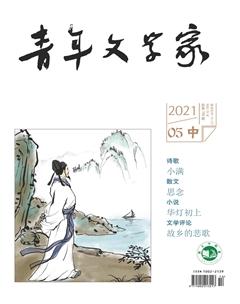试论夏目漱石《梦十夜》对鲁迅《野草》的影响
霍瑞欣
1924年到1926年鲁迅完成了作品集《野草》,《野草》由23篇散文诗构成,其中8篇都以 “我梦到……”开始,采取了梦的表现形式,除了这8篇之外也有不少描述梦的世界。《野草》中有不少作品受到了《梦十夜》的影响,《过客》就是其中一篇。
桧山久雄在《鲁迅与漱石》(昭和五十二年,第三文明社)中提到这两部作品中较多地使用了黑、暗等一系列的词汇,两篇作品描写的都是梦幻的世界,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多用到象征性的手法。由此可见《野草》或许是从《梦十夜》得到了某种刺激与影响。
《过客》是《野草》中唯一一篇以诗剧形式创作而成的散文诗。在这一点上,《野草》不同于散文形式的《第七夜》,除了黑暗之外,两部作品的表现和构思呈现不少相似之处。
一、《第七夜》中“西”的意象
《第七夜》与《过客》的共通之处之一就是主人公都是向着西方出发。《第七夜》由“我搭上一艘大船”开始。“西行”紧扣作品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将分析作品中与“西行”相关的表现和漱石其他作品中“西”的表现。
《第七夜》中与“西行”相关的表现中值得注意的是“异人”。主人公想与自己同乘船的大多数是“异人”,并有三个情节描写。
(一)我瞧见一个女子在倚栏低泣。更瞧见她擦拭眼泪时那条白色手帕。她身穿印花洋装……
(二)一天夜晚,我独自在甲板上眺望星空时,有个外国人走近问我懂不懂天文学。
(三)看见一个衣着入时的年轻女子,背对着沙龙入口正在弹钢琴。她身旁立着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正在引吭高歌。
“异人”一般指的就是西方人,而漱石在作品中特意使用了“异人”这个词。这三个场合中登场的人物都带有西方的氛围。(1)中的女性未必是西方人,但是穿着西式服装。(2)提及天文学和基督教。(3)男女弹着钢琴大声歌唱。即主人公周围的“异人”虽然可能有些并非西方人,但却带有西方的氛围。并且主人公和这些人之间无法对话。
笔者调查了漱石在其他作品中 “异人”的使用,发现漱石全集中共有9处用了“异人”一词。除了《第七夜》的两处之外,其他七处都指的是西方人。《第七夜》的“异人”指的是西方人或者西方化的人。载着这些人的船驶向的西方指的是近代文明。而这艘船象征的正是人们身处其中的近代社会。
漱石曾到英国留学。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漱石在《文学论》的序中写他的西行中一直伴随着不安。这种不安是出自对西方文学的疑问,也可说是对迅速文明开化的不安。漱石在英国第一次意识到了“自我本位”,并为此烦恼。
《第七夜》主人公坐着游轮向西航行。作品中的“自己”只是被动地向着西方的方向流浪。其中在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时写道:“变得非常不安。”“终于下定寻死的决心。”这种“西行”和不安让人联想到漱石所经历的不安的人生。笔者认为《第七夜》的向西航行并不单纯意味着漱石的留学,而是象征着抽象化的人生,这种人生是在经历了文明开化的社会变革的漱石的体验中得到的。
二、《过客》中的“西行”
《过客》描写的是某一个黄昏,一位经历了长途旅行、筋疲力尽的旅人向一位老翁与女孩讨水喝,并展开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中旅人前进的方面也是“西”。首先我们来看下场景设定。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
在这里,舞台设定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东和西两个方向。
和《第七夜》的主人公一样,《过客》中的旅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不过两人都向西方前行。但是《过客》的主人公却没有《第七夜》中主人公的不安。他的话中多次出现“要”这个字眼,表明了他虽孑然一身但决心坚定。此外《第七夜》中的“自己”是乘船被动流浪,而《过客》中的旅人则是徒步行走。从这些不同点出发,笔者认为两位主人公的“西行”具有不同的意义。
《第七夜》中的主人公和周围的人之间的对话并未成立,而过客中的旅人则和老翁及女儿开展了对话。老翁也曾经走过旅人的路,他和旅人为同类人。
旅人从老翁的口中得知等待自己的未来是坟。位于西方的坟显然意味着死亡和毁灭。《过客》中的死代表的并不是个人的死亡,而是更广义上旧中国的灭亡。鲁迅在作品集《坟》的跋文中寫道:“我确实知道一个终点。那就是坟。问题是去那里的道路,当然不止一条,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好。即便现在我依旧在寻找。”
鲁迅在不断寻找的终点不是个人的终结,而是旧中国的终结。鲁迅将改造国民精神当作自己的使命,埋葬旧思想。他将自己的生的灭亡当作代价。所以当老翁劝旅人最好折返时,旅人回答道:“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恨他们,我不回去。”
旅人憎恶的显然是旧中国的现状。并且不仅东方甚至南北皆是如此,所以旅人唯一的脱困之路只有西行。“过客”最后描写的旅人仰头毅然向西而行,表现了旅人的意志。
旅人三四十岁,困乏却倔强,眼光阴沉。鲁迅在写《过客》时45岁,可以说他刻画的旅人正是他本人的象征。
鲁迅在写《过客》不久前应报社的要求写了 “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二月)。其中有如下一句话:
我在读中国书的时候,总会感到沉静下去,远离真实人生。读外国书的时候,接触人生,经常会有想做什么工作的感觉。
鲁迅对中国和外国书籍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是否切合实际人生。他所主张的对国民精神的改造正是对现实人生的觉醒。可以说,“过客”向西的行进,是一次与充满欺骗的旧社会做斗争,寻求现代化中国的旅程。
虽然《第七夜》和《过客》设定都是西行,然而《第七夜》的西航是漱石接触并身陷其中的西方文化,《过客》的西行在鲁迅看来那是切断旧社会的唯一的道路和对近代化的追求。
三、悬空的恐惧
《第七夜》中主人公的不安来自对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浩瀚的海洋,从东向西移动的太阳,这些都显示了空间的无限性。在这种无限的空间里,“自己”乘着有一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陆地的船,不知去向何方。“自己”希望逃离这个无限的空间。于是主人公想到了用死亡来解脱。但是“只是船只似乎很高,我的身子虽已离开船只了,双脚却久久都不能着水。我才醒悟到,即使不知船只将驶往何方,我仍应该待在船上的。怀抱着无限悔恨与恐怖,静静地坠落于黑浪中”。
这里描写了另一个无限的空间,那是船和海之间。主人公从船上跳了下来,但一直到不了海里,处于悬空状态。主人公在悬空的状态下静静地坠落,不由得产生“无限的后悔和恐惧”。也就是说,即便是死也无法脱离无限的空间和不安。
对漱石来说,这个无法逃脱的空间就是文明开化的世界。可以说,《第七夜》的深度在于描绘生活在这个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的世界中的人类的苦恼、不安。对此情节的设定应该指出,无论多么苦恼的世界都不应该产生厌世的情绪。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应该在人生中解决对人生的疑问和不安,这反而是漱石的基本想法。
四、对绝望的反抗
鲁迅对《第七夜》最共鸣的东西,恐怕就是《第七夜》象征的无法逃脱的世界和生活及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的闷闷不乐。《过客》描绘出一个与《第七夜》相似的近乎绝望的世界。
“过客”来的路和去的路都是无限的。老翁也曾和旅人一样朝着西方走去,却被这无限的路程所挫败,停下了脚步。无论是老人的挫折,还是旅人路程的无限,这些都象征着旧社会黑暗和腐败。鲁迅给“过客”设定西行,无限扩展的向西的路程的空间,描绘出象征着自己化身的旅人。
《第七夜》中的“自己”因为对西航深感绝望进而投身大海,而《过客》中的旅人反而对过去的社会感到绝望。他只有向西行,既不能回头也不能休息。
鲁迅完成《过客》不久后,在3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函中写道:“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 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儿,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中略) 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鲁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显然想到了《过客》。可以说,这里呈现的鲁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不断前进的坚强性格,恰恰映射在《过客》的旅行者身上。
五、结论
经历了多次革命的失败,鲁迅看到了旧中国深不可测的黑暗,深切感受到國民精神改造的艰巨。对这样的鲁迅来说,《第七夜》的不可逃脱的世界和人类的苦闷引起了共鸣。《过客》不仅表现出人生的苦闷,还表现出了祈求食人社会灭亡的坚强意志。从这点可以看出鲁迅和夏目漱石在思想上具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的受容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