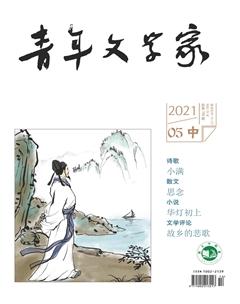日暮飞鸟起,相与归田园
韩美林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鼻祖”,曾经创作过诸多流传千古的佳作,为广大士人建立了一个永远的精神家园。本文将从陶诗中的“鸟”意象入手,探寻诗人的心态变迁与价值追求,并通过与诗人诗作对比探寻陶诗中对于“鸟”意象发展的文学史意义。
一、陶诗中“鸟”意象统计
陶渊明诗歌中所出现的“鸟”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带有具体名称的鸟,如仓庚、鸣鸥、云鹤等;二是典故中出现的神鸟,如三青鸟、鵕鹗、鸱鴸等;三是群鸟,如飞鸟、归鸟、失群鸟等。现将其诗中直接出现“鸟”字的二十二首作品依照系年做初步统计,并制作表格如下。
二、陶诗中“鸟”意象的三阶段分析
陶渊明的一生一直处于入仕—出仕—入仕—出仕此等循环,入仕之时常思归隐之趣,出仕之后仍念家国苍生,诗人的一生可谓是在不断纠结矛盾中度过。与之对应的,少年时代一腔报国热情的“飞鸟”,出仕后深谙官场险恶的“羁鸟”,以及最终决心归隐田园的“归鸟”都在反映着不同时期诗人的思想转变与价值选择。
(一)飞鸟志存高远的少年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陶渊明初次入仕为江州祭酒;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公又在荆州任刺史桓玄僚属;后又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旋入刘敬宣幕为建威参军。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陶公辗转四处官署,虽然四仕四隐显现的是陶公的纠结,但于其纠结中我们亦可以窥见其溢于言表的拳拳报国之心。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一句,陶公回忆自身青年时代,心怀九州四海的高远志向,愿做那只振翅苍穹的飞鸟,于字句间可见其意气风发之貌。
但经历了那段年少轻狂的岁月之后,官场的黑暗与无奈不断地逼迫着他游离逃避,心中的志向也开始在现实生活的黑暗下步步动摇。“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仰望远云,羞于面对高飞之鸟;临水而观,无奈愧对水中游鱼。曾经立志成为的那只飞鸟已然找到了其心之归处,但是陶公呢,仍在现实的泥潭里上下求索。这已经深刻地表现出作者内心对于年少时期的远大理想抱负的改观。又如:“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己酉岁九月九日》)通过哀蝉与丛雁的强烈对比,表现了诗人对自身生活经历的反思,更写出了其对高飞群雁的无尽羡慕之情。
由以上几例我们可以归纳出,陶渊明青年时代的诗歌中多以“飞鸟”意象为主,意象蕴意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代表了作者少年时期想兼济苍生的远大理想抱负;第二类则代表了作者真正出仕之后,看尽官场乱象后对自由象征的“飞鸟”的羡慕。此处之“飞鸟”,以其振翅高飞的昂扬姿态划过了诗人的青壮年,并于心中久久留下的年少的热血与志向,一直埋藏在作者灵魂的深处,象征着作者心中永远的自由的空间。
(二)羁鸟形迹拘役的仕途
陶公二十九岁因“亲老家贫”,怀着“济苍生,安天下”的志向踏上了心中那条前途一片宽广的求仕之路。几经波折辗转,来回反复,艰辛求仕路终于来到了尾声。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公出任彭泽令,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晋书·陶潜传》),最终决定辞官归里,为这一径长途画上句点。
而此段时间陶公的诗作中盡是对官场黑暗的讽刺批评与自身不断选择出仕的后悔厌倦,他常以“羁鸟”自比,困在茫茫宦海沉浮不定的陶公就宛如那囿于尺寸金笼中的飞鸟,不再拥有振翅高飞的力量。如其代表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鸟”与“鱼”原本都是自由的象征,恣意翱翔,随心畅游,但由于有了“罗”与“网”的困圈,“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诗人借二者自喻,表达了诗人对仕宦生活和官场的厌恶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又如:“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饮酒·其四》)陶公在诗歌中塑造了一只与鸟群失散,惴惴不安,徘徊不定,日暮之时独自飞翔,夜晚来临无处栖息的孤鸟形象。那一声声清悲的鸣啼叫出了作者的孤独苦闷,描摹出了乱世之中孤身一人的政治处境,既表现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厌倦,同时展示了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操守。再如“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杂诗·其十一》)等,都表现了陶公对心灵栖息之处的渴望与官场沉浮的厌倦。
通过上述例句我们可以看出,陶公这个阶段所描摹的鸟皆是“羁鸟”“孤鸟”“惊鸟”“失群鸟”一类,将“鸟”这一原本表示自由的意象,通过修辞加工,展现出完全相反的意境,从而以此种巨大反差表现了作者内心对仕途形迹拘役的控诉与厌倦。此段经历,既回应了前文“飞鸟”的振翅一飞,又为后文的“翼翼归鸟”进行铺垫,承上启下地刻画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将“鸟”这一意象的内涵不断丰富。
(三)归鸟恬淡田园的归隐
历经十余载的仕途坎坷,陶公终于决定回归内心的本真,归隐田园,过上了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隐居生活。在此后的诗歌创作中,除却对于宦海沉浮的回忆之作外,陶公颇为集中地使用了“归鸟”这一意象。日薄西山,归隐山林,经历了日出的翱翔、漫长的羁旅,才知道日暮之时的“归巢”尤为可贵。
此部分最重要的作品便是《归鸟》诗。全诗通过“归鸟”晨出晚归的行踪隐喻了作者从仕而隐的经历,表现了其从满腔热血一心家国的豪情到回归田园复杂矛盾的心情之间巨大的情感波动。诗歌首章表达了作者对“和风弗洽,翻翮求心”这一飞翔态度的认同,写出了他由于不满官场黑暗而选择归隐的心路历程以及希望自己永求初心的心境;第二章“见林情依”“性爱无遗”,都是借归鸟诉己志,由于“遇云颉颃,相鸣而归”于官场处处受限,只得“相与而归”回归田园;第三章“岂思天路,欣及旧栖”表现了作者对官场的厌倦,追求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仅想归隐一处“心远地偏”;第四章借写“已卷安劳”无须弋者表现了作者对宦海浮沉的失望与逃离的决心,也抒发了作者对田园的眷眷深情。全诗复沓回环,通过归鸟这一意象抒发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表达了其对恬淡自然的田园生活的无尽向往与对林间归鸟的歆羡之情。
此类归鸟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此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悠然自得之态,作者与鸟融为一体,寄身天地之间,悟出返璞归真的哲理。又如“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其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云鹤有奇翼, 八表须臾还”(《连雨独饮》)等,都是通过“归鸟”这一形象来表现作者对归隐的坚定执着与对恬淡田园生活的无尽向往。
陶渊明晚期创作中所用的“归鸟”意象,象征着作者对于隐居生活、自然境界与精神家园的回归。而这一整套“鸟”的意象体系,既写出了一只鸟由清晨高飞到日中羁困,再到日暮归巢的一天经历,又反映了作者一生从立志仕途到宦海沉浮,最终决定归隐田园的人生选择。如同那山林间日落归巢的飞鸟,陶渊明的回归,不仅仅象征着其自身回归精神家园,同时具有深刻的人格力量与深远的跨时代意义。经历了魏晋的玄学清谈、荒唐任诞,陶公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归隐道路,而其归隐的那片桃花源也成了此后所有羁旅仕途的文人墨客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