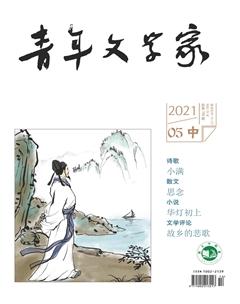以海德格尔视角解读陶渊明诗歌
何翼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兼民族矛盾错综交织、战争频发。权阀世代相沿,政治上则分裂割据,相互倾轧,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政治凋敝腐朽。在动辄得咎的社会环境下,面临政治和现实引发的巨大矛盾冲突,魏晋士人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或嗜酒服药以求自我麻痹,或隐逸山林,抑或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以种种放诞的行为表达忧愤和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其中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的陶渊明,年少时深受儒家影响,对政治尚存高志热忱,宦海浮沉长达13年之久,但终究囿于残酷政治现实,彻底摈弃仕途,把睿智的目光投向自在闲适的大自然,在田园劳作中找到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寄托,个人意识的觉醒推动其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高远的人格。而西方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海德格尔生活在由科技统领并推动社会深刻变革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他深切地关注着现代技术发展对人类生存产生的深刻影响,认识到作为思维的主体的人类,借由科学技术对除人以外的世间万物都加以认识,世间万物都成为人类研究、利用乃至占有的客体,并与认识对象之间是一种探究、利用和占有的关系。
海德格爾在作品《筑·居·思》中阐述了“就人的居住而言,人才存在”人与栖居地的关系,并在剖析荷尔德林的诗歌时强调诗意的栖居必然包含辛苦劳作。海德格尔对“此在与世界”的论述,强调世界使自身及万物出现,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互融合的,而此种贯通则来自诗人的创作。自然与“向死而生”的个体之间也并非是单纯的物料之利用的功利关系,人的存在是建立于 “在者的在之敞亮出来中”,意即自然中所呈现的各色景致,就是在者之敞亮,而其显现才成就了人之在,也就是“让……存在”。而个体栖居于自然,对自然的守护与欣羡,体现了亲密关系,人才能本真地“诗意栖居”。陶渊明的诗歌中也充分流露“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该文就以下方面论述从海氏的视角重新解读陶渊明的作品。
海德格尔把人称作此在,即“在此存在”,此在的展开方式,其一为情绪。情绪并不揭示这或者那存在者,而决定“此在存在且并不得不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表明生存是“此在”无法选择的,情绪也包括“烦”“畏”和“死”等。任何东西都存在,而这一普遍性又意味着“存在”的不可定义性,“此在”从而无法预知未来的生活,但是死亡却是唯一确定的,“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哲学观念中,“烦”意指人生在世过程中,个体面对无限繁杂选择的无所适从的状态。陶渊明从年少意气风发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期许“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但“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陶渊明虽然暂无死生之忧惧,但面对失控无序的社会发展,个人何去何从命运的渺茫,其文士自身价值观的危机频现,早年所接受的儒学思想的逐步瓦解,诗人就如同被抛向了茫无边际的宇宙,没有一点依托和把握,矛盾、焦灼、失意和孤独心态滋长。亦如陶渊明所著“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一开始即为被抛的状态,但此在必然领会其可能的发展来发现其现状。领会作为与情绪一样原始的展开方式,意即“会做某事能做某事”,陶诗中所言“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只有当个体从外界的屈从转向内心的自省,他才会认识到人的道德精神并非完美的, 如诗之“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诗人以全部热情与“天”或者“自然”进行心灵的对话,犹如“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
海德格尔说:“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畏使此在个别化为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此在的本质规定其只要生存于世,就会与其他存在者照面,意即共在。此在只要存在着,必然先领会到自身的存在,继而去领会到一切事物的存在。而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借由现身领会和话语来决定其展开状态,而这也能领悟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又能反思自身的存在。“此在”的展开状态可以通过操心的现象揭示自身,操心又是在两种方式上显现,即“操持”(Besorgen)与“操劳”(Fursorge)。在陶渊明笔下,“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忧烦比比皆是。此在亦包含有沉沦,当此在失落与其他的存在,譬如世界,而当畏剥夺了此在领悟其自身的可能性,此在就被抛回本真的能在世了。所以当诗人深感个人之力微小,流亡与死亡相偕,生命无常,从而选择“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诗人恰恰摆脱了囿于万事万物的沉沦,反而向着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片生命本真存在的澄明之境前进。
海德格尔说:“日常繁忙活动借以为自己把确知的死亡的不确定性确定下来的方法是:它把切近日常的放眼可见的诸种紧迫性与可能性推到死亡的不确定性的前面来。”众人借助日常的忙碌琐碎活动掩盖人必死这一确定的事实,来闪避死亡。但是不管常人怎样遮蔽死亡,“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陶渊明笔下直接涉及到死亡的就达50首之多。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也处处流露出人终有一死这一观点,“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诗人对死亡的本质认识来源于直观感受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陶渊明深受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乐于顺随自然,乐天知命,怡情养性,怀真守初。海德格尔认为,恰是畏清把加诸此在之死亡的一切掩蔽给清除了,此在对被抛入死亡的状态呈现得更原始,从而本真的向死存在。诗人钟情于大自然,不论是“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还是“贫居依稼穑”“弊庐交悲风”,在他眼中一切“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皆自在乐趣。诗人深谙自然、生命的运行规律,觑破生死,死亡达观旷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陶渊明的一生,从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到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再到终年的“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可谓是直面死亡。陶渊明所著《自祭文》和《拟挽歌辞》中,亦可见诗人正视死亡,并对死亡有所思,其不畏死的勇气澄明。清醒的畏赋予诗人 “此在”本真存在,并唤来此在的自由。
刘小枫说 “归隐生命的感觉有两个返回的对象,一是自然宇宙(山丘、田园、虚室);一是人的‘性本。这两个生命感觉对象统称为自然。”陶渊明诗曰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间,与自然相对的“樊笼”可以被理解为海德格尔所定义的“在之中”,因此,“返自然”则意味着去远。去远与定向也规定着此在的空间性,从而此在能操劳寻视其存在被揭示的世内空间。好比“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人的性本自然超越排除任何意向性的冲动,达到一种“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境界。海德格尔的觀点表示,作为此在的人,与其他的存在者是密切依存的。此在在世界中,而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也就是世内存在者,世内存在者本是通过此在在世才能呈现。因而,人和自然都借由在此在的在世生存中才呈现,“自然本身就需要一个世界才能来照面”。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也阐述 “人的本质基于在世”,但是在日常操持繁忙的生活中,此在其实被掩蔽在世内存在者之中,此在也并非以本真的方式生存。因此,人归返自然存在的一个前提,即取消人的生存性、在世性,可如此一来,人与自然就此融合,也就是人从在世的澄明又退返到自然的闭锁,但也就此沉入了原始的浑然。在《思的经验》一书中,海德格尔阐述道,“自然的自然性”是一种“由哥白尼的世界观所象征的自然向‘自然的自然性的回归”,也“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东西”,由此,与我们相遇的“自然”本就是在由“此在”的到场所敞开的世界中,而人与自然关系的界定并不能以剥夺人的在世性为前提。陶渊明意识到“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继而“春秋代谢,有务中园”,从“但使愿无违”的辛勤劳作,诗人建构起一个心性独立、平淡融和的人格主体,彻悟了“此中有真意”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恰是不离世俗的“澄明”之境。但诗人归隐田园,只于现实中基本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却从根本上无法达成兼济与独善的统一,借由辛苦挨过劳作和连续灾厄保持了相对的人格自由。诗人心中“贫富常交战”,即使寄望于“肆微勤”,徒然“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诗人尽管半生艰辛,经历百般苦楚,但在生命的最后时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靡王税”“无纪历”“无论魏晋”,人人勤奋劳作、丰产知足的世外桃源社会,“在此中”的人们本真质朴、安居乐业、守望相助。诗人笔下牧歌般的田园生活,正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憧憬。
海德格尔以词源学的分析阐述了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的存在方式,而“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作诗,作为让栖居,乃是一种筑造。”诗意栖居意味着诗化生活,诗意也是栖居的内在本质。当深陷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现代人对自身存在状况进行深刻反思时,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展示的是平和的人生态度,也是追求并保护生命自由的境界。
陶渊明存世于魏晋时期,承袭魏晋诗文风度,其诗文中蕴含璞真。其从艰难磨砺归隐自然,与劳作相偕,借由诗文创作领悟天地维度,达成人与自然和合相悦的诗化至境,筑造永恒的人生自我价值,践行对自由和谐生活的追寻。笔者借由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观,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陶渊明的诗作,可以让我们追本溯源,重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尊重自然,在自然中获得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