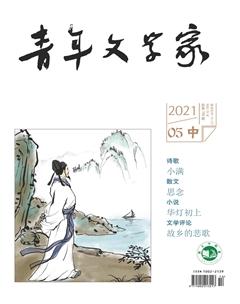消逝的生命咏叹
赵兵战
五十年前的淳化,是贫困和落后的代名词,迁延不绝的子午岭遥远得似模模糊糊的一条围裙,半拥半裹着方圆百里的余脉断岭,奔流东去的泾水冲刷出数不胜数的沟壑梁峁,土瘠民贫,因而缺的是名人雅士、骚人墨客,多的是凡夫俗子、村野乡愚。人窝蜷在山里出不去,山外的东西进不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外只剩下一样事——生娃!生娃就要养娃,养娃就要教娃,山里娃启蒙教育的基本途径就是晚上熄灯后听古经。
冬夜初至,屋外北风呼啸,冷雪急坠,喝汤既罢,钻进热烘烘的被窝,蜷缩在大人胸前的娃娃一时难以入眠,哼哼唧唧的古经声就回荡在温暖的炕边,悬挂在黑乎乎的窑梁上。
说古经、道古经,大人说、碎娃听。爷爷惯讲前朝旧事,父亲喜说当代新典,娃娃最爱听省城气象、口外风光!姑姑的古经一成不变,不是花狐狸扮媳妇,就是美仙女嫁穷汉,讲得自己心旌神摇,热泪烫醒了小侄子,问她为啥哭,姑姑不回答,却讲起了黄鼠偷鸡、老狼叼娃的唬人玩意儿。奶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世代相傳、口口相授的北山乡谣,说法似说非说、似唱非唱、如吟如诵、如泣如诉,既要引人入胜,又能及时引出瞌睡者最佳。
夏日夜短,当家人劳烦一天,头一落枕,沉重的呼噜便已闷雷般炸响在院子里,睡意沉沉的屋里人,唯恐搅扰了掌柜的,撩起奶头,第一时间堵住了娃娃即将出口的号叫,轻轻拍打着娃娃的脊背,慢悠悠哼着:
我娃乖,我娃婵,妈给我娃谝闲传。
我娃婵,我娃灵,闭上眼窝听古经。
秋夜耿耿,萤火般的豆油灯闪闪烁烁,暖和宽展的土炕是学堂,爷爷是老师!窗外呼啸的风,掩盖不住那被老旱烟熏得略带沙哑的声音:
天上下雪,糊里糊涂;下到地上,明里明白。
雪要成水,容容易易;水要成雪,万万不能!
“记下了没?” “没有。”“为啥?” “没意思!”
光溜溜的沟蛋子上“啪”的一声脆响:
“呵呵,狗日的,还挑剔得很!好,爷给我娃说个有意思的。”爷爷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骑驴过桥,糊里糊涂;过得桥来,明里明白。
人要骑驴,容容易易;驴要骑人,万万不能!
“有意思没?” “有……” “记下了没?” “……”
半天不见娃吭声,老汉伸出粗糙的大手在孙子的“瓦盖”头上掩摸了半天,确认碎怂睡着了,取下嘴上的烟锅子,在炕沿上“梆梆梆”敲了几下,“噗”的一声吹了灯,嘴里喃喃骂道:
说古经、道古经,说了古经狗不听。
漆黑的屋里氤氲着幸福、满足和安详。
二三月里肚肠饥,熬到五更难入睡。奶奶温暖而悠长的声音,盖过了咕咕噜噜的肠响:
天上没雨旱死了,沟里没水河干了。
肚里没食咕噜了,没大没妈瞎塌了!
没想到孙子听后燥了:“婆哎,我大我妈好着哩嘛!” “娃呀,婆说的是我大我妈!”“你大你妈在阿达?”
黑洞洞的窑洞里是长长的静寂,过了好半天,那温暖而悠长、遥远而忧伤的声调又哼了起来:
瓮里没水——井塌了,缸里没面——咥光了。
锅底没火——倒灶了, 肚里没食——失火了!
古经是对沉重的喟叹,对苦难的无奈;是生活的真诚写照,是时代的真实素描;是情绪的真挚抒发,浓缩着过往,沉淀着未来和期望。
庙里没神鬼凶了,院里没狗狼来了;天不下雨草枯了,地不养人瞎塌了!
渭北山区山大沟深、环境窘恶,乡人自谓“下苦人”,于是诉说苦痛心酸成了说古经永恒的主题:
割不净碱畔的白莎草……天呀,晒不透路边的铁秆蒿……地呀;
捡不完坡坡的羊粪蛋……哎呀,捣不烂地里的土疙瘩……哎呀呀!
时间一长,孩子们掌握了这类“古经”的窍门,稚嫩的嗓音等不及大人在长句之后展开的气声咏叹,便抢先一步,“天呀、地呀、哎呀呀、哎呀呀”起来。
环境艰苦,过活不易,苦中作乐尤其重要,说古经便不仅仅是为了哄娃瞌睡。对山里人来说,闭上眼睛往往比睁着眼睛要好过些!
睡不上躺椅有板床哩,攒不下硬元有麻钱哩;
种不下大葱有小蒜哩,吃不上饸饹有涎水哩!
孩子一天天长大,古经的理解难度也随之提升,其中的许多道理孩子当时是明白不了的,有些甚至需要他们用一生去感受和体会:
大了小了大大小小了,长了短了长长短短了;
多了少了多多少少了,没了有了没了就有了!
儿时听过太多太多的乡谣,而现在却大多记不起来了,梦中偶尔闪过关于爷爷奶奶的零星回忆时,耳边总是真切地响起或沙哑或清亮、温暖的说古经的声音:
说古经、道古经,说个古经给狗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