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体制理论的社会学解读
阳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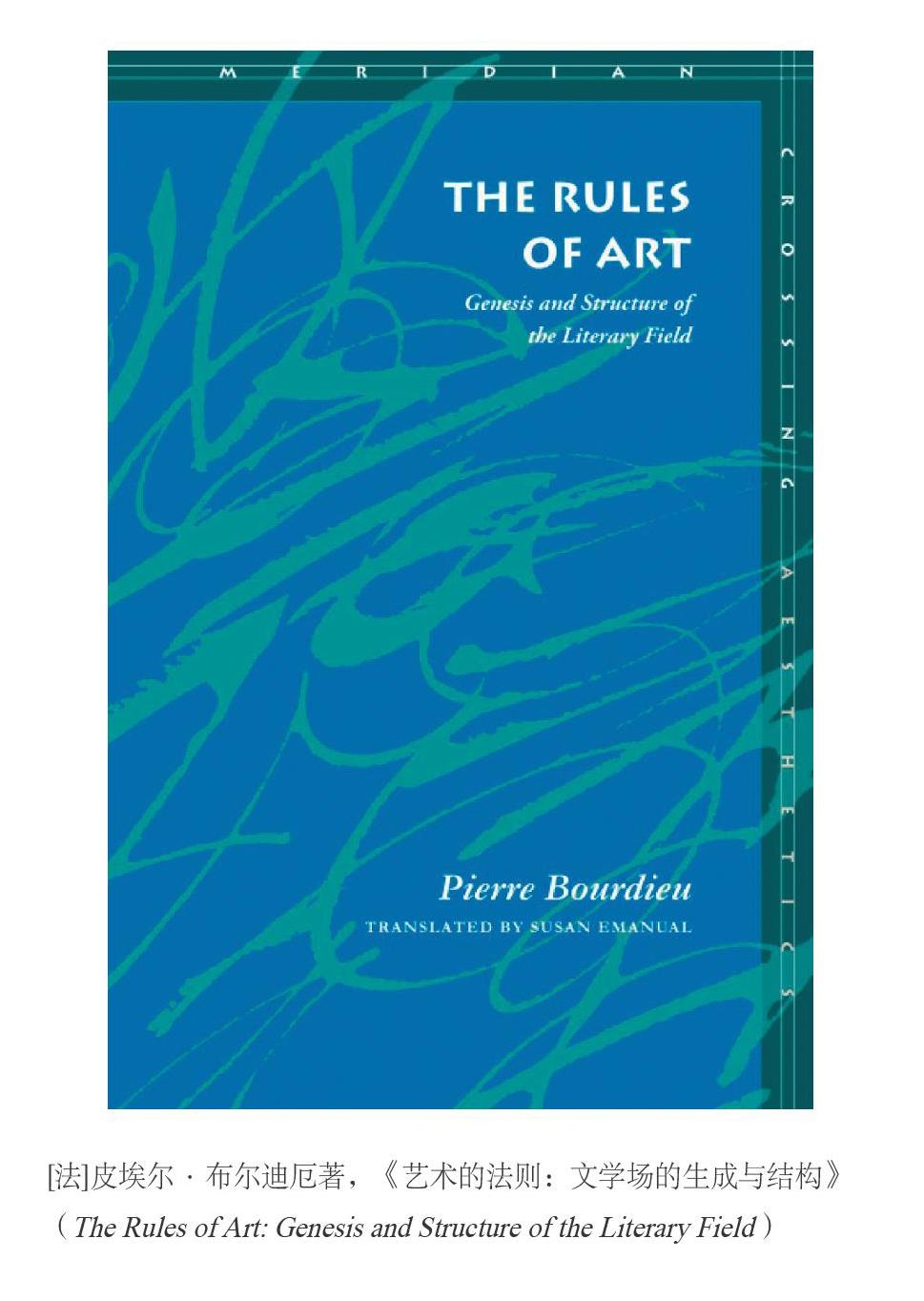
【摘 要】 现成品艺术的出现,使艺术遭遇严重的身份危机,“艺术体制理论”应运而生。尽管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搬出了“艺术界”的授权来解决日常物与艺术品之间的认知危机,却遗留下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例如“谁是授权者”“如何授权”等。从贝克尔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入手,可以对艺术体制理论进行解读和补充。
【关键词】 艺术体制;迪基;贝克尔;布尔迪厄
美学家们一直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艺术的问题,即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是什么;第二,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对于艺术应该采取何种衡量标准,即如何区分“好艺术”与“坏艺术”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有时也可以被合并为一个问题来考量,倘若把“艺术”与“非艺术”看作是轴的两端极值,那么越接近“艺术”一端的应被判定为“好艺术”,而越接近“非艺术”一端的则应被判定为“坏艺术”。
最初,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还算比较清晰,因此美学家们都致力于解决上述第二个问题。以视觉艺术领域为例,衡量艺术的标准经历了多次转变:从强调形似和技术的古典主义绘画时期,到看重作品所表现的自我精神的浪漫主义时期,再到带有自我批判色彩的、强调创新性的现代主义艺术时期。然而,从马塞尔 · 杜尚(Marcel Duchamp)将签上名字的小便池取名为《泉》(Fountain)并放置于博物馆进行展览时起,艺术便遭遇严重的身份危机。小便池也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品吗?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小便池也可以被算作艺术,那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新标准来衡量艺术呢?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艺术体制理论”应运而生。艺术体制理论者认为,一件作品能否被称为艺术品,是由艺术世界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决定的;他们拥有赋予作品以艺术品的身份和价值的权力。艺术体制事实上打开了以社会学观点来看待艺术品价值问题的大门。
然而,尽管乔治 · 迪基(George Dickie)的艺术体制理论搬出了“艺术界”的授权来解决日常物与艺术品之间的认知危机,却也遗留下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本文尝试从霍华德 · 贝克尔(Howard Becker)和皮埃尔 ·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出发,对艺术体制理论进行解读,并对迪基遗留的问题进行补充和回答。
艺术体制理论
艺术体制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迪基,他的理論雏形最早见于一篇发表于1969年的论文《定义艺术》(Defining Art),后来于1971年和1974年发表的著作只是在原有观点上做了小的修正。但是,迪基于1984年发表的《艺术圈:一种艺术理论》(The Art Circle: A Theory of Art)则推翻了他原有的对于艺术体制理论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艺术圈”理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迪基前期的艺术体制理论。
迪基指出,他的艺术体制理论曾受到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艺术界”理论启发。丹托认为艺术与普通物品之间的区别在于一种阐释的气氛,即一种艺术化的语境,“要把一样东西看成艺术品,需要一种眼睛察觉不了的要素—一种艺术理论的气氛、一种艺术史的知识:一个艺术界”[1]。丹托还写道:
当某样东西成为艺术品的那一刻,它就成了阐释的主体。它因此[阐释]而存在,当这种阐释被击破,它就失掉了这种阐释而成为普通物品。这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作品的艺术化语境而起作用:它意味着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依靠于它的艺术史定位、它的前辈等[而存在]。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最终它需要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一件与它完全相似的物品无法维持的,如果这个物品是一件真实物品的话。艺术存在于一种阐释的气氛中,因此艺术品成为阐释的躯壳。[2]
迪基赞同丹托的看法,认为界定艺术可以通过其未呈现的特点(unexhibited characteristics)来实现,即丹托所说的“一种阐释的气氛”。迪基进一步提出要成为艺术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一种人造物;第二,它的某些部分被某些代表着特定社会机构(艺术界)的人赋予(confer)了被欣赏的候选人的地位。”[3]然而,迪基对于这两个条件的阐释却有些语焉不详。一方面,迪基为了把自然物(natural object)也纳入他所讨论的艺术品的范畴,认为“人造物”的身份是可以被赋予的而无须得到工具的改造。[4]“无须得到工具的改造”这一点无疑与“人造物”的一般定义是相矛盾的。迪基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之后的著述中做出更正,承认人造物的身份是不能被赋予的。[5]
另一方面,迪基在“谁能够赋予物品被欣赏的候选人的地位”这个问题上有些前后矛盾。他一开始指出:“[艺术界的]核心人群是组织松散但仍相关联的一群人,包括艺术家、制作者、博物馆馆长、博物馆参观者、剧院参观者、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史学家、艺术理论家、艺术哲学家等。”[6]紧接着他又指出,除了这些维持艺术界运转的核心成员之外,“所有把自己看成是艺术界的一员的人都是艺术界的成员”[7]。然而,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宽泛,甚至走向虚无主义: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授予艺术地位的人,他们可以授予任何物品以被欣赏的候选地位,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换句话说,任何“非艺术”都有可能被草率地赋予“艺术”的地位。
然而,不论是“[艺术界的]核心人群”,还是“把自己看成是艺术界的一员的人”,都遭到了其他学者不同程度的质疑。迪基的后一观点被认为过于宽泛。社会学家贝克尔就曾指出:“如果一个动物管理员决定他是艺术界的一员,并赋予他照料的大象以被欣赏的候选人的地位,那么这个大象就是艺术品了吗?”[8]对于迪基的前一观点,理查德 · 霍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也给出了有力的批判:
艺术界真的能指定(nominate)它的代表们吗?如果可以,这种指定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发生?那些代表们(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依次审核所有要求艺术地位的候选人,然后在赋予一些作品地位的同时,否定其他的作品吗?是否这样的授予被记录下来了,以及是否这些地位会被修正?如果是,在何时、怎样、被何人[修正]?最后,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凝聚着一些社会组织的艺术界,并且它[艺术世界]拥有一些代表、能够行使一些社会一定会认可的指令?[1]
霍尔海姆质疑艺术体制作为一个评判艺术与非艺术的机制是否真实存在。如果这样的机制真实存在,那么它是如何運作的?它是否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革?是否它的“授权”能够得到社会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如果迪基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说明他的艺术体制理论只不过是一个猜想。事实上,对于这样的质疑,迪基在其后期的艺术圈理论中为自己辩护道:“我所说的‘某人或某些人指的是艺术家,[是艺术家]赋予了物品被欣赏的候选人的地位。我这样说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印象—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创造了艺术。”[2]但是这样的修正被丹托评价为“是一种相比于艺术体制理论最佳解释的倒退”[3]。并且这种修正已经不属于艺术体制理论的范畴,在此不做讨论。
迪基对于授权的机制—即一件作品为什么可以被“授权”,授权人选择某些作品成为艺术品的理由是什么—也语焉不详。他认为,“授权”一件作品为艺术品,并不需要授权人真正欣赏这件作品。“这个定义并不要求艺术品必须要被欣赏,甚至被一个人欣赏[都不需要]。”[4]针对这样的观点,科恩提出,是否物体需要具有能够被欣赏的可能性作为前提,它才能被赋予可被欣赏的候选人的地位呢?[5]迪基的回应则是,在他看来,所有的物品都会具有一些可以被欣赏的特质。[6]“为什么《泉》[杜尚的小便池]的那些普通的特质—它光滑的白色表面,它深部所反射出的周围物体的影像,它可爱的椭圆形的形状—不能被欣赏。”[7]在迪基眼中,不仅对于授权人的资质没有认定标准(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授予艺术地位的人),而且对于作品的资质也没有认定标准(小便池也具有可被欣赏的特质)。至此,这套理论彻底走向了虚无主义。
总之,迪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艺术体制是如何具体运作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无法指出在“授予作品为艺术”这一行为发生时,究竟是哪些行为主体在起作用,并且无法解释这种“授予”行为背后的运作机制是什么。
从“艺术界”到“艺术世界”
社会学家也对艺术体制理论表示出兴趣,他们赞成艺术是可以被艺术界定义的,但是他们同时批判了丹托和迪基的结论,认为那不过是缺少社会实证的绝对化假想。贝克尔就指出:“哲学家们倾向于用假设的例子来论证,迪基和丹托所说的‘艺术界这块骨头上并没有太多肉,仅仅为了他们所要表达的观点而达到一个最低需要。”[8]与美学家相反,社会学家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个人经验过快普遍化所得出的假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于社会事实的观察基础之上。他们试图进一步探讨这些利益相关者是谁,以及这个“赋予的过程”是如何达成的。
根据贝克尔的观察,倘若现有的美学理论无法解释某些艺术家正在创作的作品或者艺术的分配机构(如画廊、美术馆等)认定为艺术的作品,那么那些专业的美学家们就会应他们的要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1]西蒙 · 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就曾打过一个比方:“如果说现代艺术家是朝着靶子乱射的射手,那么批评家所做的就是在他的箭附近画上靶子,还点上靶心。”[2]当然,贝克尔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只有美学家才拥有赋予物品艺术地位的权力,他认为在现实的艺术世界中,应该有相应的判断程序和规则,尽管这套规则并不一定完全清晰、合理。“我们还看到,理论上任何一件物品或动作都可以被认可为艺术,但是在实践中,所有的艺术世界都有限制这个认可过程的程序和规则,尽管[这些程序和规则]并不清晰和明了,却可以使一些没什么希望的候选人成功获得艺术的地位。”[3]
贝克尔并未朝着找出这套程序和规则的方向努力,恰恰相反,他试图解构这套权力体系。艺术体制论者认为,艺术界拥有授予一件作品为艺术品的权力,并且能够影响它的艺术价值;而贝克尔以一种更为“民主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认可过程—认为整个艺术世界(art world)都会影响到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4]
贝克尔认为,艺术活动与其他一切活动一样,是一种集体活动(collective activity);他并不认为艺术家比其他人更优越或者更特别,艺术家的产生不过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正如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Victoria D. Alexander)所说:“贝克尔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所有方面都塑造着最终的结果。许多人牵涉其中,一些人直接创作艺术,另一些人从旁协助,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很久以前或在遥远地方的人)则在开发艺术创作所必需的现有材料和符号成分上发挥着作用。”[5]艺术家直接创造艺术,但是他所使用的颜料、画笔、画布、画架等,都需要依靠他人的生产和加工,而这些材料和工具会间接影响到作品的最终呈现。例如,艺术史上便携式颜料的发明,就使画家们可以离开画室,走向户外,从而可以短时间内在画布上捕捉光影,创造出印象派那样的作品。
画家因此要依靠那些画布、框子、颜料和笔刷的生产者;依靠艺术商、收藏家,以及向博物馆馆长寻求展览空间和经济支持;依靠批评家和美学家提供他们这样做的合理性;依靠国家的资助,甚至依靠国家出台的减免税的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促使收藏家购买和捐赠作品;依靠当代的或者过去的其他画家,因为其他画家创造了传统作为背景,使他们的作品变得有意义。[6]
贝克尔认为,一件作品最终要成为艺术品,必须经历生产、分配和接受三个过程。艺术家依靠众多社会资源创作出作品之后,还需要将作品传递给观众,例如依靠画廊、艺术博物馆、艺术博览会、报纸、杂志等分配渠道进行传递。传递给观众之后还不够,观众还必须能够欣赏这些作品。这时就需要某些人(例如美学家)创造和维系美学体系,使艺术拥有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克尔所认为的所谓“授权者”的范围比艺术体制论者们所认为的要广泛得多。如果说艺术体制论者更多关注的是作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在分配和接受这两个层面所受到的影响;那么贝克尔所关注的就是整个艺术世界、甚至整个社会,在生产、分配和接受三个层面对一个作品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
贝克尔最终想要强调的是,艺术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接受体系无一不在约束着艺术家,影响着作品的最终面貌,并对它如何被欣赏造成影响。
艺术场域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中也對艺术体制理论进行了批判:
这是否可以理由充分地声称,如阿瑟·丹托所说,艺术作品与普通物品之间的区别仅仅建立在一种体制上,即赋予它们能被美学鉴赏的候选人地位的“艺术界”?这是一个简单的而非“社会学”的断言,如果某个社会学家允许这种评价的话;它再次生成于一种被过快普遍化的个人经验,它仅仅指出艺术作品的体制(从主动意义上来看)的事实。它省去了对体制(艺术场)生成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而这些[省去的部分]能够完善这样一种体制的效果。即,把那些对艺术作品的认知强加给这样一些人(而且仅仅是这些人),他们(像参观博物馆的哲学家一样)被(应该也被分析其社会条件和逻辑的社会化作用)构造。他们处于这样一种潮流中(正如他们进博物馆所证明的),他们倾向于这样认出作为艺术的作品、以及理解那些被社会选中作为艺术的作品(尤其是通过在博物馆展览的)。[1]
这里再次体现出社会学和美学之间的分歧,美学家们总是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一切艺术,以至于他们的逻辑推理有时容易生成“一种被过快普遍化的个人经验”;但社会学家们需要从现实世界的艺术实践中找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布尔迪厄同意迪基的观点,认为在艺术的场域(field)中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因而存在着占据高位的“授权者”。但在布尔迪厄眼中,授权者并不一定有着“艺术史家”或“艺术理论家”这样固化的身份。他顺着迪基的思路进一步探讨了艺术体制理论的运作机制,并针对“谁是授权者”和“如何授权”这些遗留问题做出了补充和回应。他所构建的艺术场域就相当于一个竞技场,所有参与者在其中奋力获得资本—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迈克尔 · 格伦菲尔(Michael Grenfell)和谢丽尔 · 哈迪(Cheryl Hardy)对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做出了解释:经济资本是“资本极端物质化的形式”,例如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文化资本是“对于具有象征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态度的占有”,例如艺术品的声誉、地位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所构建的人际关系网。[1]当某人在某个时间点所持有的资本使他足以占据高位时,他就成了所谓的“授权者”。由于资本无时无刻不在个人和组织间流动,所以参与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其实是不断变化的。这些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在某段时间内却能达成一种平衡,而这种暂时性的平衡也就是布尔迪厄所称的“惯习”(habitus)。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有几个核心概念:惯习、倾向性(disposition)[2]、场域、关系性结构(relational structure)等。首先,惯习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诸如教条的、机械的、学院的、理想化的、普遍化的等一系列形容词而言的;惯习更多地指一系列实践的经验。惯习具有习惯(habit)一词所没有的含义,因为它具有“主动的、创造性的、创新性的”特点。[3]其次,倾向性和场域这对概念需要放在一起进行理解,“首先这个概念指向一个理论化的姿态,在构建目标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方法的选择(否定的和肯定的一样多)”[4]。举例来说,一个美术馆在收藏艺术品时可能更倾向于它的美学价值,而一个画廊可能会更倾向于它的市场价值。布尔迪厄认为,一个机构或个人是无法单独呈现其倾向性的,因为它必须被构建于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之中(the system of objective relationships)。他把这个客观的关系系统称为一种“关系性结构”,而参与者们的倾向性只能放在这个关系性结构中去理解,存在客观关系系统的空间就是场域。最终,不同的倾向性构成了场域中的惯习;当场域中参与者的站位被改变时,惯习也会随之被调整,或者被新的惯习所取代。实际上,这个惯习就是在特定时期内的艺术的法则,即不同参与者就如何授权而达成的共识。
用场域理论来分析时,还需要注意三个层次:第一,艺术场域在权力场域内部的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艺术场域的内部结构,即分析那些为了自己的合法性而竞争的个人或组织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网;第三,分析这些个人或组织的惯习的形成,惯习即系统化的倾向性。[5]
我们在布尔迪厄的著作《区隔》(Distinction)和《艺术之爱》(The Love of Art)中都可以窥探到他的基本立场。布尔迪厄的《区隔》在1984年首次被译成英文出版(法语版于1979年出版),并于2010年再版。所谓“区隔”,指的是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隔。如托尼 · 班尼特(Tony Bennett)在2010年版《区隔》的引言中所说:“属于相同社会群体的人和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相同地位的人,倾向于在所有形式的象征意义的活动中具有相同品位。”[6]布尔迪厄认为,对食物的品位和对艺术的品位一样,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对艺术有相似品位的人们,对其他东西也将具有相似的品位,例如食物、音乐、电影、电视、运动、家装、舞蹈、衣服和时尚等。布尔迪厄做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其中之一是将人们按职业划分成工薪阶层(手工业者、技术人员、小学老师等)、中产阶层(工程师、工厂或公司雇员、高等教育教师等)和上流阶层,并调查他们对于家具、服饰、室内风格、食物等的偏好。[7]布尔迪厄得出的结论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区隔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品位,而与人们出身的社会地位和后天的教育有关。布尔迪厄的《艺术之爱》也试图证明和《区隔》相同的结论。《艺术之爱》完整呈现了一个社会学调研的过程和结果。这个调研试图证明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们对于参观博物馆的偏好,会呈现出很大差异。[1]那么,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人们对于艺术的品位和偏好(即倾向性)并非天生,而是由他们的先天资本(与生俱来的阶层)和后天资本(教育、职业等)共同决定的。在艺术场域中,人们在先天资本的基础上不断累积后天资本(虽然先天资本所决定的阶层很难被逾越),拥有的资本数量多的人权力大,反之则权力小,这种权力的制衡形成了惯习,即艺术体制论者未能阐明的“规则”。
格伦菲尔和哈迪认为,布尔迪厄一方面关注了艺术的消费端,例如《区隔》所论述的;另一方面也在关注艺术的生产端,例如他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和《马奈和无序的体制化》(Manet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omie)中所讨论的。然而本文认为,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所提到的艺术场域理论实际上关注到艺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或者说接受)的所有环节。如果将艺术场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艺术世界的话,那么不论是艺术的生产者、分配者还是接受者,全部都已置身其中。
结语
艺术社会学除了强调从外部的角度(external perspective)考察外部因素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还应从内部的角度(internal perspective)关注艺术的自主演变。[2]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往往被归于“外部论”。因为迪基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不再来源于其自身的客观属性,而是来源于外部社会对其所进行的构建。如何区分艺术与非艺术?如何区分“好艺术”与“坏艺术”?迪基把这些衡量的任务抛给了艺术外部的授权者—那些有权力授予作品以艺术品地位的个人或组织。即便迪基的理论暂时回答了杜尚的《泉》这样的生活用品为何可以被定义为艺术的问题,但他的理论仅仅提供了一个猜想,并没有进一步回答“谁是授权者”和“如何授权”这两个问题。
艺术社会学家们批判迪基的理论不过是将个人经验过快普遍化,而缺乏现实的依据。贝克尔根据他对社会的观察得出结论:整个艺术世界(art world)都会影响到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贝克尔解构了迪基所幻想的集权主义的“艺术界”,而代之以“艺术世界”的理论。他认为,艺术品的最终形成和价值来源并不仅限于艺术家的贡献,整个艺术世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全都参与了对一件艺术品的创造。对于贝克尔而言,艺术品是由社会集体创造的,而不是某个艺术家的个人成果。因此,迪基把艺术界看作“授权者”,而贝克尔则把比艺术界范围更广阔的艺术世界看作“创作者”,“授权”一说在不知不觉间被这种集体创造消解了。
布尔迪厄似乎续写了迪基没有交代清楚的东西。迪基只说艺术界可以授予作品以艺术品的身份,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艺术界的授权机制是什么。比如,谁来授权?他们通过什么机制获得授权者的地位?他们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授权?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则进一步阐述了艺术界的判断程序和规则。艺术场域(art fields)就像一个竞技场,不同的参与者相互竞争,以期维持或者提升他们的权力与地位。如果说贝克尔的艺术世界理论反对并试图消解艺术世界对待创作者的不平等,那么迪基和布尔迪厄则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在艺术场域中,各个参与者的地位和所持有的资本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导致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的不均衡。这些参与者通过竞争获得更多资本和更高地位,而在场域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他们显然也拥有更多的权力来认定一件作品是否为艺术品。至于授权的标准,就是艺术场域在特定时期内不同参与者就如何授权而达成的共识,即布尔迪厄所说的“艺术的法则”。
[1] Arthur Danto, “The Artworld,” Journal of Philosophy 61 (1964): 571-584.
[2] Arthur Danto, “Artworks and Real Things,” Theoria 39, (1973): 15.
[3] George Dickie, Art and the Aesthetic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34.
[4] Ibid., 45.
[5] George Dickie, Art and Value (Massachusetts&Oxford: Blackwell, 2001), 57.
[6] Dickie, Art and the Aesthetics, 35-36.
[7] Ibid., 36.
[8] Howard Becker, Art World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50.
[1] Richard Wollheim, Painting as 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15.
[2] Dickie, Art and the Value, 53.
[3] Arthur Danto, “Danto Replies,” The Nation (June 1993): 758.
[4] Dickie, Art and the Aesthetics, 39.
[5] Ted Cohen, “The Possibility of Art: Remarks on a Proposal by Dickie,” Philosophical Review 82, No.1 (Jan. 1973): 69-82.
[6] Dickie, Art and the Aesthetics, 42.
[7] Ibid.
[8] Becker, Art Worlds, 149.
[1] Becker, Art Worlds, 162.
[2] 轉引自Edward Skidelsky, “But is It Art? A New Look at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Philosophy 82, No.320 (Apr. 2007): 265.
[3] Becker, Art Worlds, 163.
[4] 丹托提出的是“artworld”,本文翻譯为“艺术界”;而贝克尔提出的是“art world”,本文翻译为“艺术世界”作为区分。
[5] Victoria D. Alexander, Sociology of the Arts: Exploring Fine and Popular Forms (Maleden&Oxford: Blackwell, 2003), 69.
[6] Becker, Art Worlds, 13.
[1]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译本将“artworld”译成了“艺术世界”,本文改成了“艺术界”,方便与贝克尔的“艺术世界”概念进行区分。参见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新修订本)》,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
[1] Michael Grenfell, Cheryl Hardy, Art Rules: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Visual Arts (New York: Berg, 2007), 30.
[2]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译本将“disposition”翻译为“配置”,但依据布尔迪厄在《区隔》导言的注释部分的解释,此概念更适合翻译为“倾向性”。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新修订本)》,刘晖译;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Oxon: Routledge, 2010).
[3]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179.
[4] Ibid., 181.
[5] Ibid., 215.
[6] Tony Bennett, “Introduction to the Routledge Classic Edition” in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Pierre Bourdieu (Routledge, 2010), xvii-xxiii.
[7] Ibid.
[1] Pierre Bourdieu, Alain Darbel, Dominique Schnapper.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 (Polity Press. 1997).
[2] Vera Zolberg,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he Ar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