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郭建设:“我的摄影一定要有烟火味”

2000年,郭建设参加英国举办的世界广告大会。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将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本期嘉宾为著名摄影家郭建设。
访谈/杨浪 编辑/黎立
杨浪: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当中重要的摄影家郭建设。在圈里大家都管他叫郭子,我对郭建设的评价是:中国纪实摄影师里最具有主题意识,同时对自己摄影生涯当中的所有影像档案记录做得最好的之一,这是我的观察。
很高兴有机会请郭子来一块聊聊天,近年一些媒体对郭子的关注是从《红色中国》这个作品说起的,其实在王苗的访谈当中也谈到了把郭子的这个主题推出到国外去巡展。
的确,“红色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讲既是一个色彩的意识,也是一个文化的意识,还是一个政治的意识。一个摄影家用这四个字来命名和描述今天中国的现状,确实是非常贴切的。那么郭子,咱们还得谈一谈红色中国这个主题是怎么出现的?
《红色中国》专题的由来
郭建设:好啊。红色中国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太适合中国人了,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红色是离不开中国人的生活的。
杨浪:从国旗开始。
郭建设:国旗、国徽。离我们最近的,比如说少先队的红领巾,对吧。就说在生活方面也很多呀,比如说最时髦的红包得有吧。
杨浪:婚丧嫁娶,天安门和故宫的宫墙、红灯笼,对吧,就是你一说红色,我们就可以想到非常多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都是特定的具有中国的意味。
郭建设:对,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婚丧嫁娶,比如说丧,中国的丧里边就有喜丧,喜丧的孙子辈的晚辈都要披红的,而不是披麻,不是白的。
现在复古婚礼很多,复古婚礼就是以红为基调,红轿子,从轿子出来了。所以这个题材的由来应该先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题材跨度很大,跨度有40年,从1980年最早的一张片子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往里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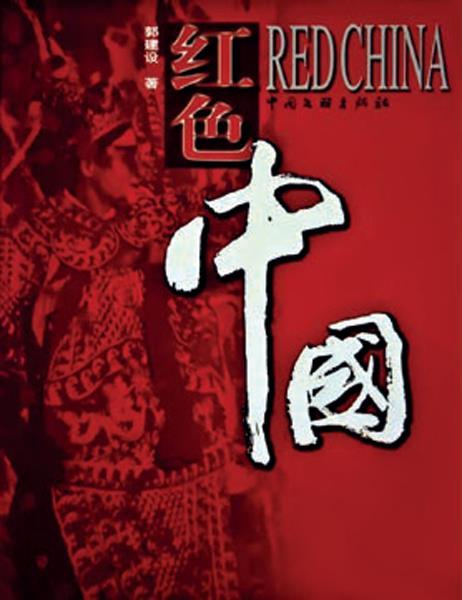
《红色中国》画册封面。
形成这个题材叫“红色中国”也好,叫“中国红”也好,以这个色彩命名这个专题,应该是在2003年,也就是非典那一年。
那一年几个圈里的好朋友,大家一块儿聚会喝大酒嘛,其中有艺术摄影协会前会长刘雷,怎么说呢,他属于文化部的官员,后来到了协会任法人代表,当会长。他就觉得工作中事务性的东西太多了,占用了太多时间。
杨浪:那天喝大酒有你、有刘雷,还有谁啊?
郭建设:还有任国恩、于云天、于志新、王文澜,有没有贺延光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经常去的这拨人。刘雷就说“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我准备用五年时间拍一个大的专题”,这就是他当时的原话,反正大家也没在意。
杨浪:就是说他专职做艺术摄影协会的会长了。
郭建设:对,所以他没有时间拍照,他看见别人拍照自己就手痒痒,他想用五年时间,减少活动,专心拍摄,搞出专题。他那么一说,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很敏感,我是行动派。
杨浪:他说什么?他说他要拍这个专题?
郭建设:他说要拍一个专题,那么我就认真了,我说您拍什么专题啊?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杨浪:反正酒喝到这份上,这都是可以问的。
郭建設:对。他说“我要拍一个‘红色中国”。这太敏感了对我来讲。当时我有点懵,什么叫红色中国?我说用颜色表现?他说那当然了。我说刘雷,咱继续喝酒,拍不拍再说,我把这话岔开了,赶紧岔过去,什么意思?我得消化一下。
杨浪:这事有点意思了。
郭建设:有点意思了,我就跟他说这样吧……
杨浪:其实明白的人对这个题目一点是能开窍的,不明白的人就当酒席上的一个酒话过去了。
郭建设:但是我很敏感啊,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敏感,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从我自己的图片库里,把红色中国调出来,你看看你还拍不拍。”
我认为这个不是五年能完成的专题,这个红色中国你要是用色彩去表现一个国家、表现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五年的概念。一定要有时间跨度的,再一个,有些东西恐怕你已经来不及拍了。
杨浪:刻意地去拍和生活当中的自然积累还是不一样的。
郭建设: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行啊,你有本事弄出来我看看。反正我弄一专题也不容易。
杨浪:在他没有拍出来之前也没有什么版权。
郭建设:对,这也不能说是你的想法,别人就不能拍。
杨浪:也没有著作权、专利什么的。何况是哥们儿呢。
郭建设:对。
杨浪:但人家也清楚,你有没有还是一回事呢。
郭建设:也是,我自己有没有也是一回事。他也没在意。说这话时是2003年,我已经离开报社多少年了,1993年离开的。
杨浪:对,那时候你不在《中国日报》了。
郭建设:我之前有花时间整理自己的东西,而且这回就用上了。这次大约用了一星期,把过去拍的反转片和彩色负片全部调出来了,凡是带红色的,都洗成了五寸的样片。
杨浪:稍等一下,当时显然不存在一款靠一个色彩从底片中挑选、提取图片的软件,那你就得一张一张选。
郭建设:不用,我都洗成照片。
杨浪:反转片不用吧?
郭建设:反转片我也得洗成照片。
杨浪:这个工作量其实挺大的啊。
郭建设:是很大啊,但是也不大,因为我都整理好的,各种视频都在了。
杨浪:对,你这个家伙是自己拍完以后就建有档案的。
郭建设:对,我档案是整理好的,虽然没有电子档,没有变成电子的东西,但是我的底片是按一个省一个省分得很清楚的。
杨浪:这点郭子我真是非常佩服你,其实不妨跟手机前的朋友们讲一个小故事,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潘家园的一个摊上发现了一堆郭建设摄影作品的剪报,至少一二十本,我看完后,就对摊主说,这是哥们儿的剪报。转身我就给郭子打电话,我说郭建设你的那个摄影剪报现在就在我眼前,你如果需要的话我掏钱把它收回去。结果郭子居然跟我说,给他留着吧,哥们儿早就有了,我真是大吃一惊,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流出去,后来说是被偷的?
郭建设:被盗。当时我大概有四五十箱书和我的摄影资料存放在一个朋友公司里边,那些资料也都是我洗成照片的资料。后来我们临时找不到住房,又要换地址就弄丢了。
杨浪:我看到的是你报纸上、报刊上发表的自己剪的一册一册的,至少十几册。这个故事就是说,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说这兄弟,我掏钱给你找回你丟的东西,他说我不要了,对吧,可见郭建设作为一个摄影家,他自己平时的影像档案的积累做得非常完备。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你接着说,你怎么整。
郭建设:然后我把这批片子整理完以后就直放或者扩印小样片,大概应该有个上千张。
杨浪:一把就检索出上千张?
郭建设:对,大概一星期吧,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各个年代的,因为我已经整理得很清楚了嘛。
杨浪:然后你该请哥几个吃饭了。
郭建设:又请大家吃了个饭,我印象中是在北京体育大学还是在哪一个会议室里,因为得摆得开呀,上千张小片子也挺占地儿的。
杨浪:对。
郭建设:当然没有码完,码了大概有几百张,这帮人就陆陆续续来了,我说咱们先看看再吃饭。当时刘雷背着手转了一圈。
杨浪:关键是刘雷。
郭建设:关键别人看不看都不重要,关键是刘雷看。刘雷看完之后当时就说了一句话:“郭建设你这辈子一定要感谢我。这题材我虽然还能拍,但是确实有些东西是拍不到了,但是你是无意当中能够拍到这么多带有红色的,大面积红色的这些民俗和各方面的片子。等于我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符号,而且这能奠定你今后,是你自己的一个标识,一个摄影家的标识。”
杨浪:我们再强调一下这是2003年,那应该是在非典疫情过后。
郭建设:非典应该过了。
杨浪:对吧,大家才会开始聚会了嘛。
郭建设:应该是2004年前后。
杨浪:18年前。
郭建设:说实话刘雷他呢确实把这个题材给了我,而且一直在帮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个展览是在北京朝阳文化馆办的,为什么在那办呢?就是想占着这个题材。
杨浪:把坑先占着?
郭建设:对,我记得是吕老(吕厚民)第一个去,因为没有开幕式,所有的片子都是在曹俭的晶丽达做的,做完之后,大概展出了40幅,在朝阳文化馆。
杨浪:吕厚民去了。
郭建设:他去了,业界去了很多人,当然刘雷是必到的,就不用说了。
杨浪:这就是你从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题材来源的故事。
郭建设:而且我会讲一辈子,因为这个题材确实是人家刘雷的创意,刘雷的题材,只是对于我呢,还是那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杨浪:对。
郭建设:所以我就算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再一个呢,也得感谢朋友,要是没有刘雷的提议,那我不定什么时候才悟出一个“红色中国”“中国红”,对吧?!
另外,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专题弄完之后,我还拿了中国艺术摄影协会的金路奖。
杨浪:刘雷会长把这个题材给了你,这还得再给你一份奖。
郭建设:这有点意思。
杨浪:刘雷真是好同志,片子也好。
郭建设:他拍得也很棒。
杨浪:拍得也很棒。
郭建设:这个展览之后,从2004年到2010年左右,圈里边很快就铺天盖地形成一场红色冲击波。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2004年,侨办要办面向全世界华人推出的摄影展览,由王苗所在的《中国旅游》推送,当年王苗送了三个专题去审,一个是长江三峡的,一个是黄河的,一个是我的红色中国。
杨浪:那显然是这个。
郭建设:最后就选定了红色中国。
我的摄影一定要有烟火味
杨浪:这是一个非常广谱的,无论居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文化谱系,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都可以接受。
郭建设:对。
杨浪:不像其他摄影有些它是老人喜欢、小孩喜欢,有的是比较激情的受人喜欢,有的是比较抒情的受人喜欢,你这个主题是大家都接受,都喜欢的。
郭建设:对。
杨浪:而且它跟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种东西同频。
郭建设:没错。它离我们生活太近了,不管是我拍摄红色中国还是整理这个红色中国,都是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中国人血液里边的那点东西。
我在整理片子时发觉,无论是红色中国,还是其他专题,我的摄影一定要有烟火味。红色中国的烟火味更浓,它不但融到血液里,而且它是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个民俗。
杨浪:我最近经常听到你说这个烟火味,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的烟火应该是人间烟火,你的人间烟火所对应的就是说,有人喜欢拍天上的,比如说虚无缥渺是天上的。
庙堂之上,特高大上,特牛的是天上,让人觉得望而生畏是天上,特别雄浑。而你说的烟火味是在审美上往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贴的那个人间烟火。

1998年,山西某村子的新媳妇。摄影:郭建设
郭建设:真正的人间烟火。
杨浪:你的烟火,OK。
郭建设:不是虚无缥渺的,是我们每天都不可能离开的,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所以我认为就是照片所谓的打动人也就是煙火味很浓,离你特近。
杨浪:这可以说你的红色中国,第一,色彩是一个语言,这是一个选择项,再有一个就是说,在你所有的影像当中选择既有色彩符号语言,同时又偏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郭建设:对,所以说不光是一个颜色的概念,如果要是说光一个颜色,那我觉得就太牵强了,就是玩色彩了。我倒觉得红色中国也好,中国红也好,一定要跟生活有关。
杨浪: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几张。
郭建设:有啊,你比如说这张,大辫子。
杨浪:这是纯粹的乡下你抓拍出来的。
郭建设:纯粹的乡下,无意当中拍到的。
杨浪:人家正好穿红了。
郭建设:人家就是新媳妇,而且我们就是刚过完年就出去采风了,八九十年代那些年的春节,我们都是要出去的。
杨浪:这张贴春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民间存在的色调。
郭建设:红色本身就很打动人,你想村里全是黄土房子,偶尔有一新娘子,一大辫子姑娘,肯定喜庆。
杨浪:互为补色,红黄互为补色。
郭建设:本身就很扎眼。
杨浪:那这张呢?
郭建设:你像这张渔家织渔网。
杨浪:你的拍摄位置是在一个游船上?
郭建设:没有没有,就是平地上,我无非是站着。
杨浪:那是渔网的蓝色?
郭建设:对,渔网。

2001年,山西大寨窗花剪纸。摄影:郭建设

1999 年,织网的渔家女。摄影:郭建设

1984 年,北京某剧团一名演员正对着背面烫印有《红灯记》剧照的镜子做上场前的准备。摄影:郭建设
杨浪:渔网的蓝色,不是水面的蓝色。
郭建设:是渔网。我发现的关注人物的服饰,你看新娘子穿红袄,而且越到陕北、陕甘宁地区,村里边逢年过节那都是披红的。
杨浪:你这三张,刚好就是中国人的服饰,中国人的情绪,春联是中国人的生活。
郭建设:对。
杨浪:那么你在2003年一顿大酒,然后花一个星期时间,就把这个题材抠饬出来,然后办了一个40幅的展览。
郭建设:对,那次是首展。
杨浪:那2003年到今天18年了,你这个题材是不是在不断地丰富?
郭建设:每年都在丰富,都在往里续新的,在这里我必须要说一下,从2003年这个题材出现之前我全是靠编辑,就是过去无意当中拍到的,有了这个专题以后,这十几年再拍的就更主动了,因为作为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专题,而且还是拍不完的一个专题,那我势必就要用点心了,比如发现民间的一些个红色,我势必要问一下这红色是为什么。
之前拍一张按一张就完了,你不会去关心这事。但有这个专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它跟生活有关吗?它为什么出现红色?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在意红色。所以,题材确立前是在编辑,确立后是在有针对性地再创作,这是两个阶段。
杨浪:这个事有意思,就是说从一个摄影作品的形成过程,一开始是你获得了一个主题。
郭建设:对。
杨浪:然后你在自己的积累当中通过编辑形成。
郭建设:对。
杨浪:根据这个主题去形成,但是在那之后你已经进入了一种主动的拍摄。
郭建设:对。
杨浪:对吧。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
郭建设:之前是无意,之后是有意。
杨浪:无意的通过编辑形成,现在你越来越有意地主动地去拍摄这个题材。
郭建设:去找这个题材,拍一些。
杨浪:在拍摄当中关于这个红色背后的文化意韵,反而要更深一步地去采访、记录。
郭建设:没错,如果光是红色我也未必感兴趣,它必须要跟人的生活有关,我就会更感兴趣。
杨浪:我又得对手机面前的朋友们说一句,郭子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在纪实拍摄当中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做好自己的影像档案,获得主题以后去进行归纳编辑;再有一种就是,获得了一个主题以后自己去主动地发掘、补充并且深化。
郭建设:对。
杨浪:而且正像红色这个主题,这真是拍不完的呀。
郭建设:拍不完,真是拍不完。
杨浪:真是拍不完,现在空间站上面还插着红旗呢。
郭建设:对。红色中国里边肯定有国旗,单独编一个国旗专题都够了。但是我表现红色中国时,在题目前边又加了一句“中国百姓的福祉——中国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红色中国有点太官话,是吧?!
杨浪:太意识形态化。
郭建设:对,我倒觉得反映中国百姓福祉的中国红,更贴近我说的烟火味。
杨浪:那么郭子,我刚才有个评价,我说在我眼里你是一个最具有题材意识的纪实摄影家,你的拍摄本身是针对性特别强的,你随时都有一个又一个的主题,有的非常重大,比如说那年的“中国一百个”,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还有你随时在进行的这个对中国摄影家们的影像;再有一个咱俩曾聊过的,我特别想在这里再聊一聊,就是关于那年的红色高棉。
这个专题是鲜为人知的,但是无论在当代世界政治史上,还是在当代亚洲历史上,这段都是绕不过去的,非常特殊的历史,你居然有红色高棉的影像,每当我想起这个事情都很想听你再多聊聊這个事。
镜头下的波尔布特
郭建设:我也觉得你要提起这事,这是1984年的事了,真是几十年了,我离开报社都20多年了。实际上那是一次机会,对我来讲应该说是我一生当中都不可跨越的这么一个事件。
杨浪: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郭建设:绝无可能。而且说实话,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杨浪:有一句话叫可望而不可求,这个事几乎是连可望都没有,一般来讲你望都望不着,想不出来还有这种可能。
郭建设:对。能遇到这种大的国际竞争事件,在我记者生涯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经历那真是够讲一天一夜。
杨浪:别一天一夜,你得在10分到15分钟之内讲完。
郭建设:那么就说我最难得的1984年。
郭建设:1984年不光是去了柬埔寨前线,实际上最难得的是什么?是当时柬埔寨分为三方,正好三方全来参加咱们中国的国庆,1984年建国35周年大庆。
杨浪:对。
郭建设:正好呢西哈努克亲王。
杨浪:就是红色高棉,乔森潘和波尔布特这拨。
郭建设:宋双。
杨浪: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拨。
郭建设:对。
杨浪:宋双的这一拨。
郭建设:对。等于三方全都受邀来参加我们的建国35周年大庆。正好我们要国庆后出发,所以出发前先去了西哈努克的官邸,两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我们三个人去那。然后说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柬埔寨?其实是因为联大,联合国大会。
杨浪:联合国大会。
郭建设:1984年,我们是10月份去的柬埔寨,年底要召开联大讨论柬埔寨问题。
杨浪: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就是说,每年对方国家都要否决民主柬埔寨在联大的席位。
郭建设:好像是。
杨浪:我们每年都要再次重申和支持一遍民主柬埔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主柬埔寨含这三方的席位。
郭建设:对。基于这种背景,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中国日报》这份报纸,大家都希望见到柬埔寨真实的现状是什么样,就基于这个目的,我们就去了。
我们经泰国进入的柬埔寨,前前后后去了大概不到两个月,三方我们也都走了,去了这方撤回来再去那方。
杨浪:那在战争环境之下是有风险的,你们一定得是有人保护的,对吧?!
郭建设:那是。不过,大部分时间文字记者都在后方。
杨浪:根据地。
郭建设:后方根据地,也就是总部。
但是我一直申请去前线,去前边。几天后批准了。当时陪我去前线的大概有70多人,前后左右护着我。我还不能背相机,但发给我了武器,幸亏我当过兵我会用,五四式手枪。
杨浪:发你一把五四手枪。
郭建设:五四式手枪,相机不能背,是让别人背,眼镜也不能戴,那时候我还戴眼镜呢。穿的都得跟那个民警官兵(国民军)差不多。
杨浪:穿着他们的军装。
郭建设:对,穿他们的军装。我踩着前边人的脚印前进,因为怕有地雷。
70多人保护着我,大概走了七八个小时吧。到了前线后,只给我15分钟拍摄时间,其實它这前线也都是丛林嘛,就是从这树缝里能看见对面,说白了也没什么可拍的。
杨浪:你拍不到什么东西。
郭建设:拍不到什么东西,拍了拍在前线士兵吃饭、睡吊床等一些生活细节,比如说临时搭的床,就几个布条,底下全是弹药包,他们睡在那上面。
杨浪:就是前线阵地。
郭建设:基本上就是最前线。那次经历是蛮有意思的,而且是徒步,都是蹚着泥走,在丛林里边嘛,那个时候说实话拍摄也很困难,你想啊,我带的胶片最高感光度是400度,又是在丛林里。那时候没有数码,哪敢想象啊,没有高感的,全是强冲。
杨浪:又不能用灯。
郭建设:不能用灯,强冲,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再一个是难民营。
杨浪:拍难民营。
郭建设:拍难民营我去了,还有前线的医院,临时在茅草屋里边做手术……这些经历之中最让我难得的,是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回到总部的时候,通知晚上有个人要见我们,接受我们采访,其实我们……
杨浪:心里有数了。
郭建设:应该有数了。
杨浪:那肯定是波尔布特呗。
郭建设:果真是波尔布特,他真出现了。波尔布特当时应该说是处于全球通缉状态,对吧?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他在哪儿,只知道他在丛林深处。
实际上我们去的时候他应该是前线总指挥吧。

1984年,柬埔寨丛林,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总司令波尔布特。摄影:郭建设
杨浪:是的。
郭建设:见面时,他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番,我一想这机会我能错过吗?!
杨浪:他通过翻译向你们介绍?
郭建设:通过翻译。
杨浪:他们配的中文翻译?
郭建设:他身后边专门有翻译,那个翻译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据说他小学还是在北京的芳草地小学上的学。
杨浪:那完全可能,当时有一些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在北京。
郭建设:对对对,而且他翻译的很棒。
杨浪:介绍了战争情况?
郭建设:他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指出波尔布特在地图上大致处于什么位置,整个会见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小时。
杨浪:你就拍?
郭建设:我就用反转片和黑白片,反正也暗嘛。
杨浪:晚上?那在总部根据地应该是可以打灯的啊。
郭建设:没有那个条件,只是有照明吧,但是终归是胶片拍摄,四五百度,你顶多提到八百了不得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那次新闻上有了他的影像。
杨浪:我印象里我见过那篇,那像素还没有到很不堪的样子。
郭建设:对,没到那么差,但在素质方面还是差一些,因为毕竟是强冲。
杨浪:拍到了波尔布特,西哈努克方面也拍了。
郭建设:都拍了。
杨浪:西哈努克是他的哪个儿子在那里。
郭建设:对,他的一个儿子,具体是哪个儿子我说不清了。
杨浪:反正是他的儿子你也拍到了。
郭建设:对。
杨浪:还有宋双这边的。
郭建设:宋双这边是由美国支持的,装备就不一样。相反民警国民军这边人员以农民为主,装备很差,文化不是太高。
杨浪:反正都是反对越南的。
郭建设:对。不管怎么样,那次的经历在我的记者生涯里,应该说算是上过前线了,虽然没有遭遇战争,没有对打过,但起码是体验了一把真正的前线。
杨浪:那么这批照片为什么没有成组、成画册?
郭建设:我当时回来的时候,《中国日报》登过一个整版,就为了配合联大的召开。
杨浪:一个整版?
郭建设:一个整版。当时敏感的就是波尔布特,这个人是肯定不能见报的。
杨浪:那个整版里也没有波尔布特?
郭建设:好像没有,在那个年代确实是很敏感的嘛。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的,我们新闻记者都知道世界荷兰新闻摄影大赛。
杨浪:对。
郭建设:它有新闻人物组奖项。
杨浪:上世纪80年代荷赛就已经开始了。
郭建设:对,我当时就想把拍摄的波尔布特投这个,那肯定是世界唯一的呀,当时总编辑就说,你是可以投,但是会造成什么结局,需要掂量……
我一想还是算了吧。别惹这个,得不得奖无所谓,反正自己有过这个经历了。
杨浪:那就是《中国日报》当时发过一版以后,这组片子就再也没有机会得以传播?
郭建设:极少,印象中还有一家法国的杂志刊发过。当时是法国驻中国的文化参赞的夫人,叫燕三三(中文名)。
杨浪:不认识。
郭建设:她见过《中国日报》那版关于红色高棉的照片,知道我手里有这套柬埔寨的片子。她说,我能不能看看片子,并告知使用时不会署名的,不会透露任何有关来源的信息,我说可以。
此外,再也没有刊发过了。
波尔布特在丛林,可以说全世界任何国家的记者都没有见过,只有来自中国的我们仨见到了,而且这组影像只有我这儿有。
《中国日报》编委以上成员集体看过一次这组影像。唯独在外边放过一次就是在王苗家,当时是何康要看,何迪也很感兴趣。
杨浪:所以……
郭建设:所以我就拿着幻灯片,用幻灯机展映。
杨浪:用影像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亚洲政治的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充满戏剧性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边境跟越南也在发生着战争,现在大家都不回避了。
郭建設:对。
杨浪:而那个时候的东盟国家,越南跟苏联的关系,东盟国家跟中国的若即若离的关系,非常微妙。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和东盟关系正常化,伴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民主柬埔寨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国际问题,是世界上两大对立集团的一个重点摩擦,而那个时候波尔布特这个人又是难以界定的,极其神秘,没有什么影像。当然今天的新闻史上是有比较倾向一致的结论:因为在他的任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联合国已经判定他的“反人类”罪行。
郭建设:对。
杨浪:或者说没有特别近期的新闻性的影像,居然有中国摄影家,是以摄影记者的名义近身拍到的,所以他的影像价值是非常珍贵而独特的。
郭建设:是,前一段我还收到好多他年轻时候的资料,包括逮着他以后在医院里的影像,外界唯独没有他在丛林里的那一段。
杨浪:那一段我有一个佐证:大约是在1982年或者是1983年,西哈努克去解放区,《人民画报》出过一个专号,这本专号就是西哈努克亲王视察解放区,是新华社记者杨木拍的。
郭建设:我去柬埔寨的时候,看到过杨木睡的床什么之类的。
杨浪:那就对了,那就杨木在你之前。
郭建设:杨木在我之前,但他没有见到波尔布特。
杨浪:这本画册我收藏着,而且我一张一张的研究了。波尔布特出现在一张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波尔布特的化名叫沙洛特邵。
郭建设:沙洛特邵,有这么一个。
杨浪:对吧。
郭建设:他翻译过来就是波尔布特。
杨浪:在那本画册里,图说里面是沙洛特邵这个名字。
“摄影江湖”
杨浪:郭子,我知道你同步进行着若干个专题,都在哪儿拍摄、积累,而且在我印象里你的专题总是像你说的具有烟火气,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你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中的摄影专题,拍的都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不输于技巧,片子不错,但是他们很难形成有质感的,能够有对历史或者人文记录有意义的主题,而这一点,正是你的特长之处。
郭建设:我可以介绍几个专题。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专题蛮有意思的,虽然也有很多同行在干,但我相信我这干法透露一下也倒无妨。因为想追我也追不上,毕竟有很多摄影家都走了,这个专题叫“摄影江湖”。
杨浪:摄影江湖。
郭建设:我是1977年当兵,1979年在部队里开始搞摄影的,1980年回到了北京,跟着王文澜到了《中国日报》,从那时就跟圈里边的人很熟了,恰恰我又是这圈里边岁数最小的,基本上没有与我同龄的人。
杨浪:对。
郭建设:都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就因为我在《中国日报》这个位置上,无意当中拍了很多前辈摄影家们,比如徐肖冰、石少华,这都是延安时期的了,还有吴印咸、陈勃,这些人都去世了。再后又一批的,是我的大哥大姐们,比如说王苗、文澜、延光等等。
杨浪:其实就是在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这些人。
郭建设:对。最初这个不叫专题。离开报社后,我在整理底片时发现,这件事做成可不是小事,这能反映一个行业。
杨浪:对。
郭建设:所以我在十多年前无意当中就把这些老的胶片、底片找出来,送了几个人,比如说陈勃、吕厚民。
杨浪:你还送给我一张我打乒乓球的照片。
郭建设:对。我发现这事光是他们签名没有意思,干脆我越做越大,我把这专题捡起来,照片一式两张,我签上名送他一张,他在这张照片上提上字,再回过来。那么这件事一做就做了十多年,现在应该说已经……

“摄影江湖”专题之摄影家刘世昭。摄影:郭建设

“摄影江湖”专题之摄影家刘香成(左)。摄影:郭建设
杨浪:有几百人?
郭建设:小200人了吧,而且也不是说是个搞摄影的就送,起码我得认识,得熟悉。我觉得这个专题再过若干年……
杨浪:但我能想到的就是你的摄影江湖不仅是摄影家的一组肖像照。
郭建设:不是。
杨浪:而是摄影家在生活当中的某一瞬间。是他无意当中,有可能他都不知道,然后同时你又用这个经典的收藏类的方式,交换签名,形成了它的孤本形态。
郭建设:对,而且完全是收藏品。
杨浪:这事你的方法交代了,可能有人会学,但是追不上了,好多人都不在世了。
郭建设:追不上了,所以我就说不妨透露这个专题。况且我还在拍新锐摄影师。
杨浪:还有新锐呢。
郭建设:还有新人呢。
杨浪:王福春拍了吗?
郭建设:当然有拍,你能点到的人,基本上都题完字了。
杨浪:我想想啊,很重要的,焦波拍了吗?
郭建设:当然,名都签好了。而且是他和姚明在那儿比高,那张太有意思了,他跟姚明比高,你想想他胆有多大。
杨浪: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专题。再给我们讲讲你的其他专题。
多题并举
郭建设:我还有一个专题,不妨也透露一下——“厕所”。
杨浪:稍等一下,容我想想,如果说这个专题赋予我,我该怎么拍?我不能只是拍厕所建筑上的镜头,那是没有意思的。
郭建设:对。
杨浪:但是厕所这个东西也很难进入到那个坑位里去拍,这好像也不太对。
郭建设:对,当然肯定大部分都是一种建筑外观,或者是标识。
我无意当中关注它是因为什么呢?1987年,我在美国办展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中国,发现他不愿意去乡下,也不愿意去外地,因为解决不了一件事,就是上厕所。
实际上厕所能够反映出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杨浪:对。
郭建设:所以说硬件再好,如果卫生间不行,说实话,这谁都怵。
这十多年来,我还真拍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厕所。比如我曾经在河南拍过一个王爷府里边的厕所,当然现在是保护起来了的,不让用了。
杨浪:你是当作一种文物文化来记录,还是纪实性拍摄,或者是建筑图录式的拍?
郭建设:应该说什么机会都有,也有处理虚的,把人物处理虚了,当然也都是实拍,并不是后期做虚的。
杨浪:那这就是纪实的拍法。
郭建设:纪实拍法。厕所自带的特别的符号,比如说男女厕所的符号,比如少数民族文字反映的厕所,那字不是我们想象和熟识的。
杨浪: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有意趣。
郭建设:还有一种是用图案来区别性别。
杨浪:影像的意趣是存在的。
郭建设:对,不一定非要去拍不能想象的那些东西,是吧,但是厕所文化是可以用影像表现的。
杨浪:好,有趣,到时请观众们看影像。
郭建设:另外,我现在还在拍一个专题,也是跨度很大,我管它叫“中国手工艺人”,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
杨浪:这又是一种文化记录了。
郭建设:别的不用说,有的行业已经消失了,有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变迁……
杨浪:中断了。
郭建设:中断了,你抢救都来不及了,顶多也就是表演式的了,对吧。所以这又是我比较大的一个专题,永远能拍下去,因为有的行业消失,又有新的行业冒出来。
杨浪: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倒是想到了,你的这几个专题都是属于拍不完的。
郭建设:对,都是随时可补充的。
杨浪:一个形态,永远可以补充。
郭建设:你说厕所永远可以拍吧,手工业随时都有手工,你不可能离开双手啊。
杨浪: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意这个专题背后的那种文化信息的丰富性。手艺人显然是如此,厕所背后其实也是如此。
郭建设:是的。
杨浪:就一个攝影家而言,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时刻记录,有几个点是自己关注的,你碰到就举起了相机。
郭建设:对。
杨浪:用这种方式在积累你的影像档案。
郭建设:档案也是我的专题。
杨浪:当刘雷首提“红色中国”这个主题,你马上就整理出来了。后面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符号已经印刻在你脑子里了,你不断地去抓取它的图像。
郭建设:对,你刚才那句话就引起我想说另一个专题——家门口。北京,我生活的地方,这当然是我的专题。

1996 年,江苏周庄的一间公厕。摄影:郭建设

2011年,河南洛阳巩义康百万庄园里的厕所。摄影:郭建设

1999年,浙江某毛笔制作坊。摄影:郭建设

1998年,北京的王鹏制琴行,王鹏强调更要看重心法的修为。摄影:郭建设

1998年的北京街头, 绿军装似乎也是一种时尚。摄影:郭建设

1983年,河北某肠衣生产点。肠衣就是香肠外面用的那一层皮,用猪、羊、牛的小肠或是大肠加工而成。摄影:郭建设
杨浪:你的北京专题。
郭建设:我的北京,应该说这个是我最接地气的一个专题。为了推出这个专题,我到现在每天还在拍照片。
杨浪:这叫影像日记。
郭建设:专题名叫“遇见”。同时,我还在编辑“回家”系列。
北京篇已经都快编完了,马上就要编河南篇了,我都叫回家。我整理底片,陆陆续续整理了20年,发现整理的时候并不能按专题去分,我必须先让所有的影像回家。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自己的国家我应该走了五六遍了。
杨浪:你如果以家的概念,那这个专题又非常丰富了。
郭建设:与其说红色中国是一个国家,那么我现在进行的专题是各个小家,也就是说各个省、市、自治区,我没有空白地,我不能说每个县、每个村我都走过,但是中国版图上大的地方,我确实走了几遍了。
除了拍片子、正常生活,我每天干的事就是让所有影像回家。河南的回河南,河北的回河北,西藏的回西藏,陕北的回陕北,我都先让它们回家以后,今后我就可以按区域推出,比如说回家北京、回家河南、回家云南,就是回家。我拍的影像也是回家,我去哪儿也是回家。
杨浪:郭子,哥们儿之间的聊天就在于每次都有新的感觉,你让我很感慨,原来一个摄影家的生活是这样的。你的生活就是摄影,你的摄影也完全融入你的生活。
郭建设:离不开呀。
杨浪:然后你的专题和你的生活是融在一体,你时时刻刻都在拍摄,成为你的影像日记,同时你又把这几十年以来的影像,以空间为单元进行整理和编辑。
郭建设:对。我现在几个大的“回家”系列马上就要成型。首先是北京,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但七岁进京,几十年的跨度,北京影像不用说了。另一个是河南,河南是我的出生地,有我的父母,这几十年来,没少关注河南。再一个是云南,因为我夫人是云南的,这又牵扯到了。还有河北,河北是我当兵的地方。
杨浪:每一个成长空间。
郭建设:我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在河北拍的。
杨浪:所以你与它的情感联系点在那。
郭建设:大的专题是国家,叫“红色中国”。小的专题是各省,那么再小的那就是“手工艺人”“厕所”等等,这样一来,等于说就没有空白了,所以也不用避讳这风光不拍,那人文不拍,遇见什么拍什么就行了,自然都可以编进去的,也有自己的符号,应该说所有的影像都可以编进专题。
杨浪:有自己的符号,有自己的专题,有自己基于摄影的生活方式。
郭建设:对。
杨浪:这个就像你编专题一样,你这个活法,活到100岁都可以这么弄的。
郭建设:都可以。
杨浪:你就是哪天小刀(郭建设夫人)把你抬到医院去了,医院也可能成为你的一个新专题。
郭建设:这个也可以有。反正你每天都在拍,大不了最后自己給自己拍一套呗。
杨浪:观众朋友们,我一开始就说,郭子在我视野里是中国摄影家里面最具有专题意识,同时也是影像档案管理、编辑最完备的,稍微谦虚点咱们这两个都加个之一吧。但是我其实没有看到过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如此之出色的。
许多人对于摄影存在着神秘感,包括怎么进入摄影,怎么管理影像,我觉得郭建设他的记录方式和他的生活方式是可能给予我们某些启示的。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左二)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外宾。摄影:郭建设
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
杨浪:有观众提问说曾看到郭老师有好多作品是拍领导人的,今天怎么没聊起这个话题。
那我们再聊聊这个话题。你作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摄影记者,并拍了大量的中央新闻。
郭建设:对。
杨浪:这是其他人很难获得的机遇,而且在这中间你有很多经典的可以入史的影像。当时这个过程你可以给我们讲讲。
郭建设:《中国日报》是1980年筹备,1981年试刊,1982年正式创刊的。
杨浪:你是什么时候入职的?
郭建设:我是1980年下半年去的。
杨浪:筹备的时候。
郭建设:对。我去了没多久就试刊了,我等于是穿着军装在《中国日报》干了一年多,1982年正式复员到的《中国日报》。
杨浪:你去的时候就是摄影?
郭建设:是的,我在部队也是摄影师。王文澜跟我在部队就是使用同一个暗房,他在宣传科,我在直政科。
杨浪:后来文澜先到的《中国日报》。
郭建设:对,他又把我给弄到《中国日报》了。所以我们俩到《中国日报》后也是同一个暗房。
杨浪:你到《中国日报》时很年轻。
郭建设:对啊。
杨浪:二十几岁?
郭建设:二十几岁,我28岁时,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办了展览。
杨浪:对,我应该是在1983年前后在贺延光那里见到的你。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原来郭建设那么小。
郭建设:是,20出头吧。《中国日报》正式创刊以后,社里上报的中央组就是我和文澜。
杨浪:所以你就有了很多机会。
郭建设:这个叫常备名单,就是你采访中央新闻必须报备嘛。
杨浪:你的记者证就可以进去了。
郭建设:报名了就行了,那已经就等于有号了,我印象特别深,1982年我拍的第一个领导人是廖承志。
杨浪:当时他是人大副委员长,后来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
郭建设:对,那次是因为斯诺的夫人来中国,廖承志出席的。然后紧跟着我就拍了很多中央新闻,比如1984年的五届人大,我在中央组待了有十多年吧。
杨浪:你认为那个阶段你拍的比较重要的有哪几张?
郭建设:一个是通过新宪法。那个时候《中国日报》用图是个风向標,为什么呢?这个不得不说,因为中央新闻很难突破,我当时虽然拍了一些大家认为很新鲜的照片,其实并不是人家拍不出来,是人家拍了用不出来。
杨浪:用不出来!
郭建设:所以我一直不承认我拍的有多好,只不过是《中国日报》这个媒体能够让摄影记者尝试新角度创作更大胆的图片,且有机会见报。
杨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新闻界整个的状态是非常松弛和活跃的,而《中国日报》作为一个新起的面对外部宣传的媒体,它要更多地考虑受众心理,对吧,所以在图片选取的时候就能够采用你和王文澜的一些影像。
郭建设:没错。比如说五届人大有一张开幕式的照片,实际我就用二〇广角,你说新华社记者谁没有广角啊。但是他拍了不一定能用。
杨浪:你的话很重要。
郭建设:对啊,不是拍不出来。
杨浪:不是说别人拍不出来,是当时的《中国日报》能把你们拍的用出来。
郭建设:是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新鲜,读者也会认为很新鲜。我一直说,那些老记者人家早就有拍过,广角镜头,他怕变形,不规矩,那个时候媒体发东西是有很多规定的,对外的《中国日报》宽松一些,只要影像不要太变形就好。
杨浪:咱说一传播学的道理,就是现在老说讲好中国故事,不光是你主动就算自己讲好了,还要看是不是你的受众能接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包括语言。而《中国日报》那个时候是更多地分析了海外读者他们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
在遵守我们的大的新闻原则这个空间范围之内,更多地去照顾受众。
郭建设:没错,比如说我拍中央新闻的时候。领导给我的要求是一定要出新,什么叫出新?那不就是角度嘛,角度出新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的记者证规定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杨浪:拍摄中央新闻就不能让你到处乱窜。
郭建设:不该去的地儿你也去不了。但是在这特有的情况下,有些时候是可以变通的,比如说有一张片子我印象特别深,得了全国奖,就是钱其琛当选国务委员那张。他是外交部长嘛,他入场前,摄影记者都先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就发现,钱外长进场入座前他先回头跟后一排的同志握了一下手,这个瞬间让我逮着了。
杨浪:挺生动的。
郭建设:让我记下来了。
杨浪:能想到的。
郭建设:好,这时我就琢磨了,这事敢不敢下个赌注,那我只能到保卫处给报社打一电话,给当时总编辑冯锡良打一电话,我说我今天发现一瞬间很有意思,敢不敢赌这张,如果赌这张我现在就调整位置,我是一楼的记者证,我自己跑二楼去拍。
从二楼拍,他回过头来,所有记者不就成背景了,冯先生问,你有把握他能回头,我说宣布他当选国务委员就有可能。我说那您做好用新华社通稿照片就行了,但是你不能认为我犯错误,总编辑同意了。我就到二楼去了。
杨浪:我是冯锡良我也会提出这个问题。
郭建设:我真就拍到了。
杨浪:你怎么能赌到他还会重复这个动作?
郭建设: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会,结果一宣布当选,他第一时间就回了头,一楼的所有记者都成背景了,我啪啪啪拍了三张。第二天刊出头版大照片,钱外长直接派秘书来取报纸,而且让我洗一张照片送他。这不就是预见性吗?
杨浪:这就是预见性。而预见性说来简单,却是有风险的。

1991年,大会宣布钱其琛当选国务委员时,他转身与后排的同志握手相庆。摄影:郭建设
郭建设:太有风险了。
杨浪:所以你跟冯总交代好,大不了就用新华社的照片保底。
郭建设:你用新华社通稿啊,但是你不能说我是犯错误,我没拍照。
杨浪:对,因为你作出预判,必须得转换一个拍摄点。
郭建设:对,我转换拍摄点就拍不到他当选的表情。
杨浪:这个是可以作为新闻摄影的案例来讲,通过教案讲故事。
郭建设:对。我在中央组那十几年,说实话,除了完成正常发稿任务以外,确实是得天独厚的机遇,我拍了很多开国元勋,中外领导人参加活动或是在会议中的表情。
我在中央組那段时间是最宽松的时候,而且《中国日报》又是一个最合适的对外窗口。
杨浪:新华社那个时候并没有作为一个对立派来苛责你们。
郭建设:对,他们也是比较认可的。所以说那一批中央领导人的影像是蛮珍贵的。
杨浪:说来都是故事了,一转眼都是30年以前的事情了。但在今天依然要强调对外宣传要搞好,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很形象化的事情,都是有经验可循的啊。
郭建设:是的。
杨浪:好,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各位朋友,也谢谢大家。
郭建设:谢谢您,跟您聊天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