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像水一样永恒的百年人生
王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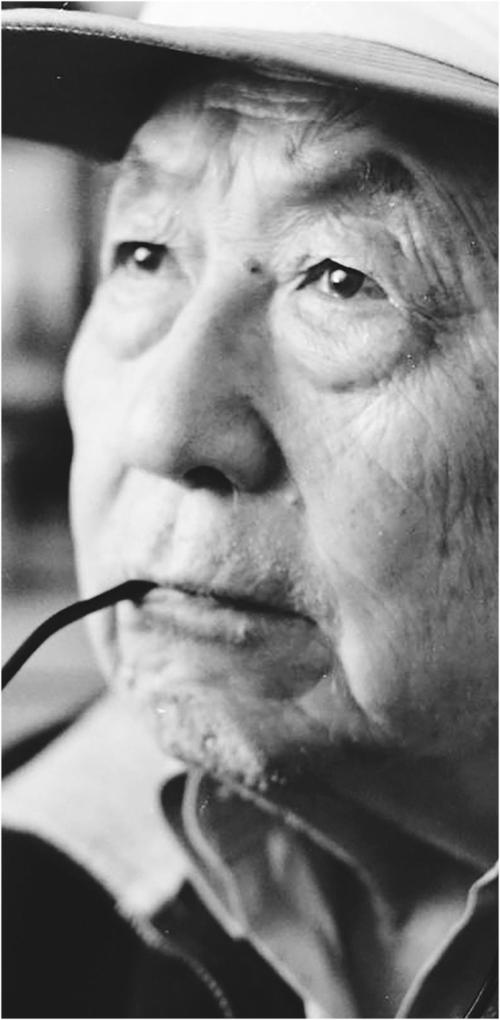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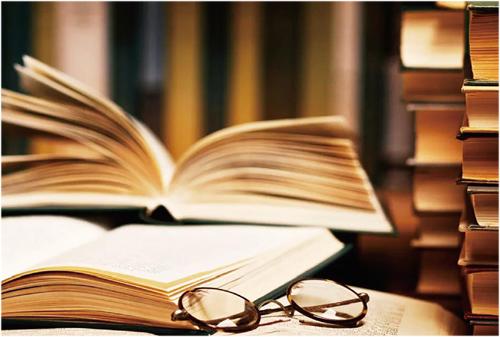
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光芒熠熠的人物,其实和伴随我们的日月星辰没什么区别,平时你总不大会时常想起他们,你总觉得他们永远会在。然而他们却又和日月星辰不同,是西沉了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
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北京逝世,这位百岁老人终究没有等来这一年的盛夏,而他像水一样的百年人生,却在后人心中激起万千浪花。
人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
1921年9月,何兆武出生在北京,彼时的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研究生,他一步步的求学经历见证了日本入侵、国土沦丧、举国抗目、抗战胜利的整个过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读小学五年级。”何兆武回忆道。为了躲避战乱,少年何兆武和家人一起坐火车辗转回到祖籍湖南。然而抵达岳阳后他们发现“南方也未有净土”。在湖南的日子里,何兆武看到了日军的为所欲为。
随后,何兆武回到了北京。在初中求学阶段,何兆武和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时刻生活在日军入侵的恐惧之中:“我还记得有一阵儿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听到飞机在北平城上空盘旋,还有机关枪咔咔咔的声音,大家都在这种不安中醒来。”
1937年抗目战争全面爆发时,16岁的何兆武正在读高中,突如其来的战火让何兆武本就“胆战心惊”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平静,这方战火也一直延续到他读大学。
彼时受战乱影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至长沙,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何兆武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从1939年到1946年,何兆武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回忆起在西南联大上学的时光,何兆武称它为“人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在口述随笔集《上学记·迁徙的堡垒》的开篇,何兆武这样说道。
1939年秋天,何兆武初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彼时他刚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加之当时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何兆武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选择了工科,进了土木系。到大一第二学期的时候,何兆武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建筑学,于是决定改行。
后来,何兆武转入了历史系,谈及为何会选择历史系,何兆武曾说,“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1943年,何兆武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继续读研究生。受同窗王浩(后为著名数学家)的影响,何兆武最终选择了哲学系。在哲学系读了一年,何兆武患了肺病,养病期间他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读了大量的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作品,被那种“暢论天人之际”的精神境界打动,在西方诗歌中,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病愈后就转到了外文系。
在何兆武的葱茏岁月里,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可谓之深刻,这其中,就有西南联大的“自由”。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何兆武说:“联大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何兆武表示,“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何兆武认为,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他在《上学记》中写到,“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在何兆武看来,“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何兆武和《上学记》
2006年,耄耋之年的何兆武将他的求学生涯口述出来,由文靖整理成册出版——《上学记》。尽管这只是1920年代一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透过这本书看那个年代,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年代,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说:“他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
在那个军阀混战、日军进攻的灰暗年代,历史书上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那个年代的“苦难”。然而,在何兆武的口中,那个我们熟悉的、充满着炮火与外敌的年代似乎多了些生活的气息,他将我们在历史书中看不到的烟火与温情糅杂在其中。宛如葛兆光在《上学记》序中所写的,“在何先生(何兆武)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
这份口述史带着何兆武的回忆,使那些已经随历史远去的人物又从历史中走了出来。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以及那些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幸福。
尽管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何兆武却从来不觉得自己不幸福,反而在《上学记》中多次提及“幸福”,他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在何兆武看来,当时他们正处于战争年代,但他们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所以即便那时候物质生活非常苦,但他们仍觉得非常幸福。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兆武曾感慨。但他们的单纯和简单却留下了永恒,他们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成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幸福。
《上学记》对人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但同时这本书又独具个性,在功利滔滔的世界上,何兆武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他在书中谈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何兆武对读书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毫无疑问,他也是热爱读书的。直到90多岁高龄,何兆武依然没有停止每天阅读的习惯。何兆武把读书视为一种享受,“我读书很多时候是跟着兴趣走的,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在他看来他自己是“无故乱翻书”。
在何兆武看来,读书是要有兴趣的,但读书不能光凭兴趣,还是需要有一个宗旨的。他将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功利性的一面,比如消遣式的、趣味性的读书,何兆武称之为“作为消遣,看热闹”。另一方面,他认为读书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他指出读书如果与工作相关,就要认真读,要有明确的目标,阅读是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他表示,“当我们准备做一个研究,或者搞一个课题,或者想弄明白什么、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目标明确、有方向、有系统地阅读就显得非常重要。”
何兆武把读书比作吃饭,他认为书读得好坏和拼不拼命没有关系,读书要适量,也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他不将自己桎梏在读书的条条框框内,但从未迷失过自己,宛如他的人生一般。
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读书为何兆武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青年时对学术书的偏爱为他种下了翻译学术著作的种子。他的译著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影响了几代学人,对国内思想哲学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影响巨大。2015年,94岁高龄时他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何兆武百年生命岁月里,除了翻译工作之外,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着极大的成就。1978年,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出版,全书50多万字,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系统、全面、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思想發展史。在史学理论方面,何兆武不仅在国内筚路蓝缕,开拓了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另外一方面,他阐发自己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文,置之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理论领域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之列。
何兆武认为,“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外着你理解了历史。”
何兆武说,他对于历史问题感兴趣,可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学家是如何来了解过去,从何种角度理解过去,是如何得出单靠史料未必能够得出的观点的。所以说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从年轻的时候就更多带有理论性的色彩。这一切理论的思考当然都会和哲学有着深刻的关联。他在采访中表示:“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哲学感兴趣,觉得没有点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深入的理解。当然你也可以对历史问题做纯技术的考证工作,但那个不等于理解历史。我总是觉得要有点思想的深度才能理解历史。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可以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研究思想史和心灵史。我觉得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这个层次上的理解才是最根本的。”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何兆武在晚年依旧关心的是当下这个时代,希望更深入地理解个体与国家、时代、命运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在接受采访中说道,“何先生的百年人生经历了从北洋政府到新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由于《上学记》广为人知,人们更熟知西南联大对于他人生经历的重要性。我想,他们这一代学者最为关切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特别是人民在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幸福地、有尊严地生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能否处理好19世纪中叶以来就困扰着我们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一直关心的问题。”
何兆武非常喜欢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代和学术发展阶段不同,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研究中学、西学之间的关联,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一生追求自由的何兆武,从不为名利所困。在追名逐利的浮躁氛围中,学富五车的何兆武始终与思想为友,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宁静淡泊。谈及他半生成就,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像是把名字刻在水上,一边刻着,一边随水流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