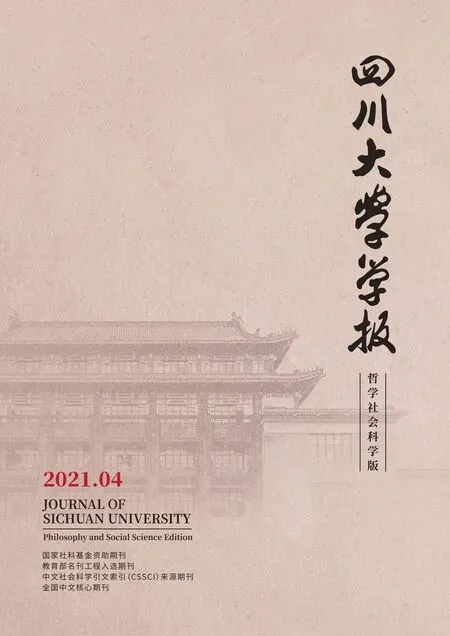比较视野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基于世界结构性原则的论述
郭忠华
一、“大变局”群像
“百年未有之变局”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这一话题首先来源于中央高层的判断。2017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总书记首次对当今世界形势所做出的判断。此后,他还在一系列场合进行了重复和强调。比如,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上指出:“当前,我们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1、428页。在同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这一来自中央高层的政治判断既为学术界提供了鲜活的主题,也引起了热烈讨论。自2017年之后,学术界有关“百年大变局”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论文明显增多。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为例,在2017年之前,有关大变局的讨论仅寥寥数篇,且主要讨论的是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篇名中直接冠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字眼的论文有7篇,但此后便呈井喷式增长,2019年达到80篇左右,2020年则达到100篇以上。如果加上同义的“百年大变局”篇名,统计数量则要翻一倍以上。显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局”?内在有何深层含义?学者们对此的理解见仁见智。
首先,变局的范围:世界抑或中国?大部分学者把百年大变局的范围看作是世界性的。比如,张蕴岭等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变化,其次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衰落和新出现的自发性意识形态的兴起,最后是世界秩序开始进入一个“无人区”,没有谁知道应该往何处去,谁先走出“无人区”,谁就能领导这个世界。(2)张蕴岭等:《如何认识和理解百年大变局》,《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4页。杨蓉荣等人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国际生产关系,并由此带来了国际政治新的动向和变化,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体现”。(3)杨蓉荣、李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机遇与挑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01-106页。但也有学者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中国。比如,朱锋认为,“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复兴征程,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战略含义”。(4)朱锋:《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含义是什么》,《东亚评论》2019年第1辑,第6-8页。郑若辚认为,“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已经是一个共识;而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当然就是中国的崛起”。(5)张维为等:《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方学刊》2019年第3期,第84-100页。
其次,变局的内容:一维抑或多维?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对百年大变局持多维的视角,只是对于维度的理解各有差异。比如,王少泉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稳步推进使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6)王少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与哲理》,《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第68-73页。科技、经济、国际力量、国际体系、文明交流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维度。张蕴岭认为,“百年大变局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力量对比大变局,包括大国间力量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比,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对比的巨大变化;发展范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向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巨变;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转变,主要是具有替代特征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发展”。(7)张蕴岭:《对“百年大变局”的分析与思考》,《山东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1-15页。国家力量、发展范式、新科技革命构成其基本维度。与之对比的是,也有不少学者从单一维度做出理解,如前文引述的杨蓉荣等学者把“国际生产关系”看作是大变局的主要维度。也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如“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8)李杰:《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习时报》2018年9月3日,第2版。还有学者把它归结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今天我们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离不开对近十多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分析,尤其在这期间发生的四件大事不得不提出来进行深入分析,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9)权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表现、机理与中国之战略应对》,《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第9-13页。
再次,变局的结果:积极抑或消极?部分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结果主要是消极性的,因为它使世界面临太多的风险和挑战。比如,史志钦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幅由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安全碎片化所构成的世界政治经济图谱,它使世界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10)史志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身份的变迁》,《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13-20页。但也有不少学者抱持乐观的心态,认为“变局”是传统世界秩序的深刻调整,它给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在权衡看来,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1)权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表现、机理与中国之战略应对》,《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第9-13页。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还是把“变局”看作是中性的,认为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格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抓住机遇和规避风险。(12)杨蓉荣、李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机遇与挑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01-106页。
最后,变局之本质:时间、空间抑或其他?面对围绕“大变局”形成的各种描绘,也有学者尝试将其上升至哲学层次,以此透视其本质。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发表专栏文章“百年未有之变局社会科学汇思”。在这一组专栏文章中,任剑涛从“时间”角度做出理解,通过把时间划分为“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百年”是指从1919—2019年的自然时间,这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含义,要理解这一自然时间段内的“大变局”,关键必须要在“社会时间”上进行审视。(13)任剑涛:《社会变迁的时间尺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4页。郭台辉从“时-空意识”与“人-事意识”角度做出理解,认为“‘变局’包括时间意识之‘变’与空间意识之‘局’两层含义,是时间与空间双重意识的结合及反映,……时间意识是人对外界客观事物渐变、突变、不变、周期变、线性变的感知,而空间意识是人对事物点位大小及其与周围关系位置的心理反映”。(14)郭台辉:《“百年变局”再解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5-8页。邓曦泽则试图从人类、国际、国家和个体四个层面,以“知识生产坐标”“劳动形态坐标”“全球治理坐标”“大国关系坐标”“民族复兴坐标”和“生存竞争坐标”来锚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15)邓曦泽:《我们究竟身处什么样的大变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1-15页。
上述研究把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引向了立体化和深邃化,从而大大丰富了对于这一判断的认识。然而,对于百年大变局的范围与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实际上已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不应存在太多的争议。对于大变局的范围,在2020年1月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537页。从中可以看出,“大变局”的言说对象是“当今世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他的其他一系列讲话中。对于大变局的结果,习近平的论述也是明确而连贯的,即“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17)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代党员》2021年第10期,第3-9页。关于大变局的哲学讨论,目前主要集中在时间、空间或多坐标的提炼上。显然,任何事实都会呈现在时空结构中,时间、空间并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大变局的实质;多坐标系的提炼尝试则容易导致重心的游移,从而无法真正认识大变局的内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现有讨论都只是立足于当前世界,很少有从“比较”角度来进行探讨的情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其明确的时间参考框架,那就是20世纪。如果没有对20世纪的世界格局做出分析,如果只是将注意力聚焦在当下,那将很难真正理解当前大变局的含义。
基于对当前研究状况的评估,本文将从比较的视野出发,在明确变局含义和变局本质的基础上,重点阐明20世纪的结构性原则和世界格局,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当今世界结构性原则的变化和世界格局状况进行重点分析,最后说明大变局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二、何谓“局”?何种“20世纪的世界格局”?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变局”的字面含义是“变动的局面”“非常的局面”,其中的“局”表“形势”“情况”或“局面”之意。从某种意义而言,任何形势变化都可以称作“变局”,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则可称作“大变局”,如果出现一百年、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那就是百年或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这些表面性含义对于理解当今世界之大变局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要达到对变局的真正理解,必须求助于学科性的专业知识。“形势”“情况”“局面”不过是社会现象的呈现,属现象学的范畴,但任何现象都不过是事物本质的外化。从社会学专业知识的角度来看,社会现象是由构成该社会的结构性原则所决定的。因此,潜藏在“变局”后面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原则”(structural principles)。所谓结构性原则,就是承载特定社会类型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社会中通常具有深远的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明显的制度化特征。(18)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185.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任何社会都不是建立在单一结构性原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彼此关联的一系列原则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彼此关联的结构性原则称作“结构丛”(structural sets)。从结构性原则的角度来看,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就是通过其结构性原则来整合其各方面要素,并且已形成了相当持久的时空伸延的系统。结构性原则如果发生变化,社会也就相应出现变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巨变的另一种说法。
尽管特定个人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变迁很少有明确的感知,但如果以专业的眼光且将眼光投向漫长的历史,则很容易发现,人类社会经历过诸多沧桑巨变。对于人类历史上漫长的社会演化,思想家们已将其划分成形形色色的社会类型,承载这些社会类型的正是思想家们所设定的各种结构性原则。例如,马克思把整个人类社会按生产方式划分成“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四种类型,(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塑造这些社会类型的根本力量则是“生产力”。“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基于社会整合的方式、时空伸延的能力和行政监控的能力三种结构性原则,吉登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等三种类型;(21)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184.基于心理学层面的个体心理事实、政治学和法学层面的规范以及共同生活的法权基础等结构性原则,滕尼斯将人类社会史划分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两种类型,前者指以血缘、地缘和精神等“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形态,后者则指断绝了一切自然纽带而建立在“独立个体”和“契约精神”基础上的人类生活形态。(2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61页。可见,尽管同样处于“时局”当中,不同思想家基于不同的结构性原则,所看到的“局”也是不同的。
与上述思想家放眼整个人类历史不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将眼光回溯一百年,考察当今世界与前一个百年相比所发生的改变。显然,要理解这种改变,首先依赖于我们对20世纪的世界格局形成总体性认识。不论对于哪一种类型的社会而言,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都是形成该社会类型的结构性原则,我们因此可以以这些原则来达到对20世纪的世界格局的理解。
首先,从政治角度衡量,20世纪是世界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先是该世纪上半期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催生民族国家的关键事件。根据“战争相关研究项目”(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Version 2016)的统计数据,当前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48个国家建立于1914年之后,占世界国家总数的76.48%,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中的民族国家有大约4/5是在20世纪以后建立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而赢得国家独立。此后,20世纪晚期冷战格局的终结又成为催生新兴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关键性事件。在前苏联的基础上产生了15个独立国家,在前南斯拉夫的基础上产生了5个独立国家,其他则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解等。与20世纪前期的“去殖民化”不同,“国家解体”成为这一波民族国家建立的主要方式。(23)郭忠华、谢涵冰:《民族国家建立的方式与轨迹:基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分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第99-112页。及至21世纪初,世界政治体系已演变成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体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城邦国家、农业帝国、游牧帝国、征服帝国、殖民帝国、联合帝国等形形色色的国家形式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以明确的领土边界、独立的国家主权和对内事务的排他性管理等为基本准则的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共同体中的基本单元。(24)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121.
其次,从经济角度衡量,20世纪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扩展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了以庄园、土地和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摧毁了西方殖民帝国的掠夺型经济模式。世界从此进入到真正现代的经济模式阶段,呈现为两大经济模式并驾齐驱:一是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载体的市场经济模式;二是以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进入1970年代末期以后,如罗伯达·达尔和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所言,传统形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都遭遇重大挫折,两大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在政府计划与市场调节两种取向之间变得越来越倚重于后者。(25)Robert Dahl and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Hamper, 1953.具体而言,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生对凯恩斯主义的倒转和对欠发展经济体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反动,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开始浮现和壮大;(26)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8页。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开展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且最终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而完全融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及至21世纪初,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转的根本原则。
再次,从文化角度衡量,20世纪见证了主要意识形态的千帆竞渡和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表面胜利。20世纪先是见证了殖民主义的终结和法西斯主义的短暂崛起。在国家建构的历史上,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曾经是两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前者,西方各主要国家曾或多或少地奉行这一意识形态而对亚非拉等广袤地区进行殖民侵略,试图建立起殖民大帝国,其中以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帝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同时,出于20世纪上半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等国相继崛起,试图建立起一种种族至上的法西斯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终结了这两种意识形态和建国尝试,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短暂高涨。但接踵而至的则是“两极”格局的出现,表现在政治文化领域,两极格局体现为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并且在20世纪中期达到白热化。及至20世纪晚期,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也迅速消退,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似乎获得了表面的胜利。其时,涌现出大量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著作,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该书的结尾,福山用一种略带惆怅的“马车”比喻来表明,意识形态斗争业已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将是人类思想的最终归宿。(27)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5-457页。
最后,从科技角度衡量,20世纪主要是一个传统工业化大生产和初步信息化发展的阶段。工业主义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它使传统工场手工业转变成机器大生产模式,集中大生产、机器大生产、严密的劳动分工等成为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基本特征。工业主义的生产模式不仅带动了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还带动了世界市场的兴起,工业化大生产在推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伴随着殖民统治的全球扩张,工业主义也在全球范围内支流四溢,它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农经济、家庭小手工业等传统生产模式。吉登斯将现代性的面孔刻画为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2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2页。“工业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主要面孔之一。这种生产方式变革同样反映在中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刺激下开始了现代化转向,出现了第一批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化工厂,及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曾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基本目标。但此时的现代化主要还是以电力和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及至20世纪晚期,通过积极加入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新兴科技也开始在我国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中得到普及。
至此,我们可以对“变局”的含义和本质有所理解,“变局”就是格局和形势的转变,本质上是“社会结构性原则”的转变。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四条结构性原则,我们可以对20世纪晚期的世界格局做出总体性勾画,那就是:以主权独立、平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以私有化、市场化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以自由化、民主化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以及以工业化、信息化为基础的世界生产体系(如图1所示)。通过这些结构性原则,人类在政治上已经摆脱了城邦、帝国等传统政治形式,在经济上已经摆脱了传统经济模式,在文化上已经战胜了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在生产上已经摆脱了小农经济、传统手工业等束缚,而开始进入到一个“纯粹现代”的阶段。但这是一个风险与机遇交织的阶段,现代世界并没有如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最初设想的那样带来安全与福乐。1999年,站在20世纪的终点上,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莱思系列讲座,他把20世纪末的世界称作“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29)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Profiles Books Ltd, 2002.通过全球化、风险、民主等宏观或微观主题,他已开始窥见即将到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缕缕微光。

图1 20世纪晚期的世界格局
三、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相较于此前漫长的古代和封建时期,20世纪的世界格局称得上是一个大变局,因为它彻底告别了人类此前所经历的传统或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阶段,而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纯粹现代的阶段。但是,现代性一旦斩断了与传统的藕断丝连,便基于对自身的连续反思性重构而获得了不可遏制的动力。(30)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4页;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7页。这种动力推动各个领域不断出现一日千里的变化。时下,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尽管仅二十个年头,世界却正迅速告别20世纪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格局而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前文表明,学术界已就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象进行过各种勾勒,但由于没有设定比较的底色,这些勾勒从而无法凸显当前大变局之“大变”。本小节将依据前文设定的结构性原则和参照20世纪的世界格局框架,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轮廓进行勾勒和做出比较性说明。
首先,政治维度上从“极化格局”向“群体格局”的转变。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极”格局瓦解等重大事件催生了一个以主权独立和平等为基础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但是,这种独立、平等的主权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是始终得到遵守,具有较强实力的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指出,在从17到20世纪的这段时间里,世界先后出现过以荷兰、英国、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大国,这些国家曾对各自时代的世界秩序建构产生过根本影响。(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章。即使放眼于20世纪,也很容易地发现,先是英国在该世纪初形成的支配性影响,然后是美国和苏联的迅速崛起以及“两极格局”的形成。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争霸之后,随着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世界格局进入到“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除美国之外,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政治体也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总体而言,20世纪的政治格局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两极”或“一超多强”格局,西方世界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晚期赢得了国家独立,并且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但受制于西方国家已经建立的国际政治框架。
但反观当前,这种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单极、两极或者一超多强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变得势不可挡,全球政治力量的对比正趋于均衡,世界和平的基础更趋于坚固。(32)赵磊:《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4-121页。美国尽管仍然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包括美式价值观、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以美国为基础的世界制度基础(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已越来越面临内外挑战。同时,经过英国脱欧、国际移民等一系列挑战,欧盟也正经受着内部再整合的新考验。但与美欧范式性力量趋于下降形成对照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其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推出“一带一路”项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议程设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中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主要推动者。比如,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化,使世界上五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中国与俄罗斯和广大中亚国家在地区事务上的制度化合作机制;由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项目,则为全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平台。总体而言,“政治维度”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概括为:20世纪所确立的以美欧等西方力量所主导的世界格局正趋于式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不断增强。
其次,经济维度上从“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直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都主要囿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民族国家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国民经济与国家政治、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国家边界内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民族国家构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主要节点。如哈贝马斯所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经济秩序主要体现为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对内经济和对外贸易。(33)J·哈贝马斯:《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张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经济联系完全是孤立的,由于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不同的经济实力,它们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比如,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集团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但这种支配权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终结,美国取代欧洲而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支配者。在此后的50年里,美国尽管面临了来自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模式挑战,但这种挑战随着20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烟消云散,美国的支配权从而得到进一步强化。(34)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第30页。与此相适应,到20世纪末,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表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开始横扫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提出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国企私有化、保护私人产权和放松政府管制等政策主张,对20世纪末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5)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页。与之相对照,中国在20世纪晚期尽管也大力推进市场化和国企改革,但并没有完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范式,而是继续保留了公有制经济在关键经济领域中的支配地位,同时维持政府对于主体经济的调控职能。
但是,伴随着20世纪中后期“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运转模式和表现形式也出现根本性变革,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即国民经济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樊篱而实现全球融合,民族国家的经济转变成一种超国家经济,跨国公司取代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经济运转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政府对于自身经济的驾驭能力显著减弱。如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全球时代的到来使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后民族国家”时代,在这一时代,以资本的不断自我膨胀、产品的不断自我增殖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势能,已远远超出于任何旨在遏制和改变其运行的民族国家政体。(36)Zygmunt Bauman, 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55.“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基本概念,无论学术界对于该概念存在多少争议,经济全球化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二是“经济金融化”,即经济越来越摆脱与传统产业的关联而变得虚拟化,体现在股票、债券、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的发展上,金融化侵蚀了实体经济的肌体,使经济主体从金融业当中获得的利润比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更多。迈克尔·曼把20世纪末的金融化转型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37)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第188页。然而,金融化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也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和世界性,这一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已有明显的体现。总体而言,“经济维度”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概括为:经济体系越来越摆脱民族国家的樊篱而演变成全球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载体而变得虚拟化和金融化,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具有毁灭性和世界性。
再次,文化维度上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向“多元化”意识形态的转化。前文已经表明,随着20世纪末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似乎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从“承认”这一哲学高度来论证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出,塞缪尔·亨廷顿则出版《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从实证的角度表明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纪晚期获得全球性胜利。(38)参阅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但此后的历史表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并不是如那些思想家所设想的那般前景光明、春光无限。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变得不断极化。(39)佟德志:《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及其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第64-72页。2016年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及其随后政策则表明,作为自由民主之灯塔的美国自身也越来越陷于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煎熬中。(40)庞金友:《大变局时代保守主义向何处去: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的未来》,《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第3-16页。
更具体地说,进入21世纪以来,自由民主不仅没有支配整个世界,而且其本身也处于消退中,全球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色彩愈益明显。拉里·戴蒙德将1999年巴基斯坦政变看作是“第三波”民主化退潮的起点,根据其实证研究,到2006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已有26个出现民主崩溃,民主退潮尤其出现在非西方国家,在23个主要非西方国家中有8个出现退潮,2013年则是第8个民主退潮超过民主改善的年头。(41)Larry Diamond, Spirits of Democracy, St.Martin's Griffin, 2009, p.63.转引自刘瑜:《第三波民主化失败了吗?》,汪丁丁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5-126页。与自由民主回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等意识形态的兴起。据“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近年来公布的有关十大国际思潮的调查结果,2018年,十大国际思潮的榜单依次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新自由主义、生态主义、种族主义、女性主义、普世价值论。(42)参阅http:∥www.rmlt.com.cn/2019/0115/537380.shtml,2021年1月20日。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已沦落榜单之末。及至2019年,这一榜单变成: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多边主义、民族主义、科技本位、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43)参阅http:∥www.rmlt.com.cn/2019/1225/564949.shtml,2021年1月20日。其时已见不到自由民主的身影。而到2020年,这一榜单进一步变成:反全球化、霸凌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右翼、国家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反智主义、平等主义和生态主义。(44)参阅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952276213636519&wfr=spider&for=pc,2021年2月2日。这些榜单反映出,当今国际政治文化处于持续变动当中,政治文化家族的主要成员表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特征,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成为当今政治文化的主要潮流,自由民主文化的影响力则持续下降,已退出了主要政治文化的行列。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将当前文化维度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趋于式微,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格局则已初步呈现。
最后,科技维度上从“工业化时代”向“智能化时代”的转变。前文已经表明,20世纪是一个工业主义获得充分发展和初步信息化的世纪。在20世纪的前期,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成果也被扩展到整个世界,确立起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时的世界秩序格局主要体现为“中心-边缘”的依附性结构,即殖民地国家对占中心和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关系,具体体现在“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等三个方面。(45)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9-311页。20世纪中期科技革命再一次发生,出现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及至20世纪80年代,微型计算机已开始广泛应用于生产、管理、国防和生活等领域。同时,到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也得到发展,人类社会的“时空结构”发生巨大转型。其中的突出现象莫过于吉登斯所指出的“脱嵌”(disembeding),即互联网技术把各种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抽离出来,实现与遥远的社会关系的重构。(4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8页。但总体而言,20世纪主要还是一个以“工业主义”为主导的世纪,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影响相对有限。
但是,当今世界已经打破20世纪的工业生产格局而进入到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时代。2005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敏锐地把握到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这一短暂阶段的沧桑巨变。他用“世界是平的”来概括互联网、工作流软件、社交软件、搜索软件等新技术给世界所带来的最本质影响。弗里德曼把这一大转型称作“全球化3.0”时代。在这一时代,世间的一切事件都被数字化、虚拟化和自动化,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都被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国家和公司不再构成这一网络的主体,而是变成以“个人”为中心,人人都能参与全球化,人人都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互相联络、互相竞争、互相合作。(47)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9页。弗里德曼所捕捉到的是21世纪转折时期的世界变化。但就在他做出“世界是平的”论断不久,旋即迎来第四次技术革命,使“世界是平的”转变成“世界是智能的”。德国于21世纪初制定“工业4.0”战略发展方案,确立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高科技战略发展项目。此后,中国也推出《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确立科技创新、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的强国战略。时至今日,以制造业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核心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彼此渗透,实现整个工业领域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技术革命仍在昂首前行中,技术智能化时代已显现雏形。至此,我们可以对当今科技维度上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做出总结,那就是:从工业2.0和3.0向工业4.0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工业制造从机器生产和信息化向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转变上。
综合前文论述,我们可以以比较的方式把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含义,通过下表的形式得到呈现。

表1 比较视野下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四、当前大变局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前文已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争论、20世纪的世界格局以及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接下来所要处理的两个问题是:导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下一步的国家建设将带来何种影响?作为全文之结尾,本部分拟就这两个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对于当前大变局的主要原因,目前学术界尚鲜有系统之解释。部分学者简单地把它归结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所导致的结构性困境和矛盾。(48)权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表现、机理与中国之战略应对》,《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第9-13页。这种解释显然失之偏颇,因为它没有看到大变局的合理和机遇一面。前文已指出,当前的百年大变局本质上是构建世界的“结构性原则”的转变。那么,导致结构性原则变化的动力又主要有哪些?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少思想家们提供过答案,有些甚至试图从根本上做出回答。比如,黑格尔把“理性”看作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世界历史过程也就是“理性”不断展开自身的过程。(4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9页。但这是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解释。按照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才是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终决定性力量。(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因此,必须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角度来做出解释。
具体而言,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结构性原则的转变上。其中,经济原则的转变处于最主要地位,科技原则则内在于经济原则中,是推动经济原则发生变化的最活跃动力。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其中,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表现得尤其突出。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中国 GDP总量达到101.5986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51)参阅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2021年1月20日。是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且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比较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则表现出持续颓势,在遭受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晚近全球疫情等事件的连续打击之后,西方经济总体处于停滞状态、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守主义、霸凌主义等保守思潮不断抬头。南北经济的发展差异带来了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变化,即前文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群体性崛起、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持续衰落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势头的持续增强等。
对于第二个问题,当前大变局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也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如特朗普主要从贸易保守主义和反全球的立场做出应对,中国则从拥抱全球化和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的立场做出应对。从总体而言,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冲击,以下几方面的策略转变尤其重要:
第一,认识上的转变。从全面、比较和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任何政策和行动都基于相应的认识,认识方面的挑战因此是最大的挑战。针对这方面的挑战,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自觉:一是从“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当前的大变局。前文已经指出,对于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解,有些甚至将其归结为某种单一的维度。但当今世界之大变局是一种全方位的变局,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因此必须从全面的视角出发来加以理解。二是从“比较”的视野来认识当前的变局。谈到当前之大变局,不少学者便对当前世界的某些突出现象加以刻画,企图表明那些便是大变局的表现。但如前文所表明的,只有在与20世纪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今之变局的真实内涵。三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当前的大变局。即变局是持续进行中的,其中的诸多维度当前尚未全面展开,因此也就意味着对于大变局的理解不是一次性或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保持对大变局的持续理解,并将其持续理论化。
第二,策略上的调整。提升执政党对于大变局的判断力、适应力和驾驭力。大变局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过程,伴随着调整而来的则是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资源分配权等的重新布局,调整会带来混乱,混乱中则隐含着大量机会和风险。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52)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代党员》2021年第10期,第3-9页。这种形势对执政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提升对于当前世界形势的判断力、适应力和驾驭力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些方面,可以通过发挥各类智库和智囊的作用来提升对于形势的判断力,通过各种政策调整和改革来提升对于新形势的适应力,通过提升执政党组织的战斗力来提升对于复杂国际形势的驾驭能力。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和全球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中,通过执政党的沉着应对,已经营造起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执政党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力、适应力和驾驭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变局远未完成、挑战也远未结束,这需要执政党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和定力,在已然有利的基础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第三,国际角色的转变。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前文已经表明,当今之大变局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于世界事务的主导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国际力量不断趋于均衡,世界和平的促进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秩序尽管本质上是一种“霍布斯秩序”,民族国家之上不存在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但这也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民族国家)可以恣意妄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义原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重要。这一点在过去数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诸多政策中已经得到体现。对于中国而言,大变局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转变,即从过去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学习者”“模仿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韬光养晦者”的角色,向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角色的转变。这意味着,面对当今诸多全球性问题,中国不仅要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而且还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良好的发展理念、范式和支持。(53)史志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身份的变迁》,《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13-20页。在当前动荡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当积极扮演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促进者角色。
回望历史,百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且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世界转型,未必如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千年甚至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般巨大。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每一次变局也就是一次大考,不容有任何疏忽和闪失,只有提交了合格和优秀答题的应考者,才能不被变局所淘汰,才能在变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从理论上廓清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是做好这份答卷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