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仁增新生代藏医博士成长记
孙芮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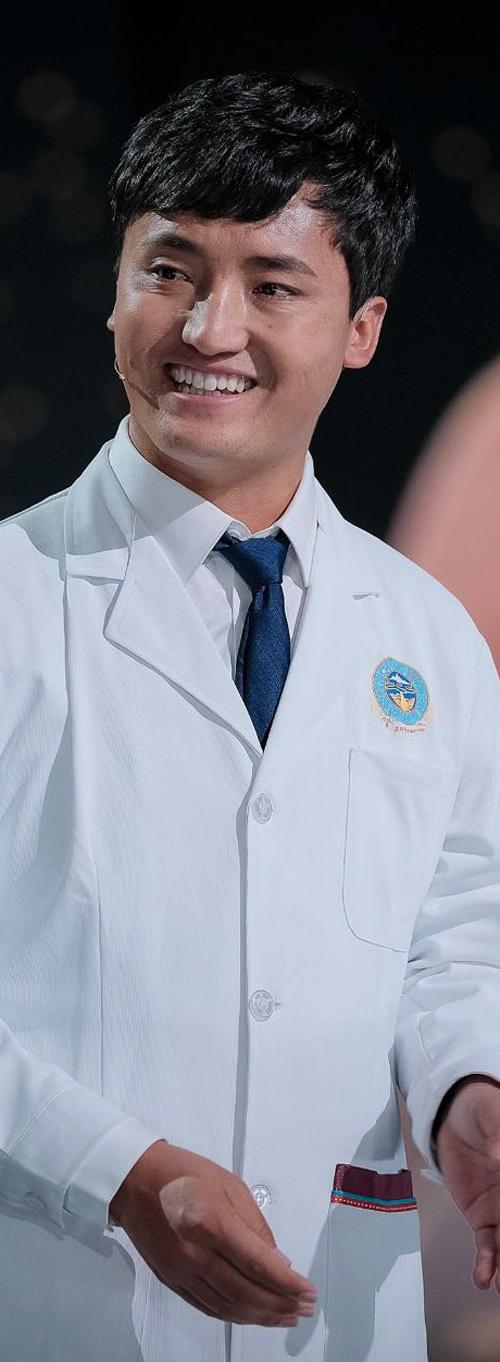
他是仁增,是博士、是藏医、是翻译家,也是一位让学生如沐春风的老师。
他13岁开始学习藏医,毕业的时候是当时国内藏医药学界最年轻的博士。
藏医界曾有翻译阿育吠陀经典的传统,一度中断长达300余年,他重新开启古老的《妙闻集》梵译藏的序章。
他喜欢研究语言学,熟练掌握四门语言。多次在西藏社科院的期刊上发表贝叶经研究相关的文章。
他给学生教授藏医、梵文知识,也和同事一起登上CCTV《国家宝藏》,向全国人民介绍博大精深的藏医药文化。
珠峰脚下出生的孩子
仁增的家乡在日喀则定日县扎西宗乡曲宗村,那是一个距离珠峰仅20公里的村庄。最近几代人中,这个村庄从未有过大学生,也没有出过藏医。
爸爸、妈妈、姐姐和他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太富裕的普通小家庭。作为出家人的舅舅是当时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他一直鼓励年幼的仁增多读书,好好学习。
尽管家乡因为一项登山运动而闻名全世界,仁增并不打算像村子里其他年轻人那样靠给登山队充当向导、背夫或者开商店营生。他更愿意安静地待着,阅读一些讲述藏族历史的书籍、学习文化知识。他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
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高鼻子的外国人、白皮肤的内地人,还有一些他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人像候鸟一样每年固定的时间扛着器材、装备出现在这里。13岁以前,仁增从未踏出过乡里半步,但他见过很多生活在城市中的同龄人没有见过的东西。

十世班禅大师与边雄藏醫学校校长强巴赤列(仁增的第一位藏医老师) 供图/仁增
漫漫求学路
六年级寒假的一天,舅舅和父母突然告知仁增下周就把他送到十世班禅大师创立的边雄藏医学校学习藏医。因为从小就见过很多外地人,仁增并不抗拒这次远离家乡的求学活动感到很兴奋。
因为聪明好学,仁增在校时各项成绩都十分优异,老师们常告诫他说:你的基础很好,应该继续学习。完成三年的学业后,学校给合格的毕业生颁发了开诊所的许可,仁增的大部分同学们都回到各自的家乡开起了诊所。在舅舅的经济支持下,仁增怀揣着老师们的嘱托远赴拉萨求学。
几年之后,仁增的同学们大多都经济比较富裕,在自己的家乡成了比较有名气的医生,彼时仁增还在读大学。有一天,仁增的同学给他打了个电话。“同学问我在干吗,我说我在拉萨上学,他说你上那么多学干吗,除非你要考博士啊,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如果我不能读一个博士的,上那么多学干吗?”仁增回想,同学当时那个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点醒了他,开始思考读书更远的目标。
那段时间,仁增刚好读到一本书,其中的内容引起了他深深的共鸣——如果你有一个梦想或者目标的话,你要把它分成时间段去完成。比如说你的目标需要十年来完成,那你就要想五年之内我要做什么,两年之内做什么,……近到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

国家宝藏节目现场 图/彭程
大学刚毕业,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决定先参加工作,其间他和妻子相爱并结婚。回忆到这里,仁增感慨道:“我后来读研、读博都离不开我的妻子和家人的支持。”工作两年后,仁增报名并顺利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再次回到藏医学院,脱产学习后他的工资折半,但学习藏医的信念并未折损。“读研究生期间,我发现学的越多不知道的就越多,藏医是需要不停学习的。”这个理由加深了他继续学习的想法。
掌握四门语言的研究者
也许跟童年特殊的成长环境有关,后来仁增学英语、梵文时,似乎比其他同学都快一点。他也渐渐发现了自己在语言学上有一些天赋。工作之后,他仍然保持看语言学相关书籍的习惯,研究和自己专业关联不大的领域,近几年在西藏社科院的期刊上发表有关贝叶经研究的文章。
汉语和藏语是上学期间必须掌握的语言,而英语和梵文则是仁增后期的选择。刚从日喀则到拉萨的时候,仁增只是打算学好英语回到老家去给外国人看病。但这其实为他后来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基础。
仁增博士研究课题与一部古印度阿育吠陀的医典——《妙闻集》有关。历史记载,过去西藏有很多医学家前往印度、尼泊尔先学习梵文,然后把阿育吠陀的医典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传统。阿育吠陀三大医典中的两部已经完成了翻译,只剩下《妙闻集》。近300年来,国内几乎没人再去做这个事情。
“我一开始想用英语去研究《妙闻集》,但是后来发现必须要学会梵文,不懂梵文的话就没法研究下去。”为了完成博士课题,也为了将这个传承延续下去,仁增在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梵文。最终将《妙闻集》的前五章全部内容及其他章节重要内容翻译成藏文,为以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做好铺垫。

义诊现场 图/索朗
在西藏藏医药大学教授米玛老师和央嘎老师等藏医和梵文相关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仁增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答辩,还受到论文盲审专家及答辩专家的高度评价。
“如果只做一个藏医的医生或者老师,他不一定需要懂这四门语言。但如果想做一个现代的研究者,读懂国内外藏医药学相关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文献,必须掌握这四门语言。”仁增通过自己的学习经历,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经验。
门孜康最年轻的博士
大学刚毕业时,仁增被分配到昌都边坝县加贡乡卫生院,博士毕业后被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借调,2019年年底通过公招考试正式调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顶着“最年轻博士”的光环再次回到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门孜康),仁增最开始被安排在文教处工作。日常工作给仁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在医院领导及前辈们的支持下,仁增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科研项目,做了很多藏医药知识宣传推广的工作。包括参与编撰《索瓦日巴(藏医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中的瑰宝》、推出藏医院的防疫视频,以及参与西藏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
還在文教处的时候,他参与了藏医药浴申遗后的传承保护相关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药浴标准建设等药浴科研工作,医院安排他回到临床。这也是从基层临床岗位走来的仁增所希望的。
回到外治科以后,像普通临床医生一样,他每天需要完成接诊与治疗病人的工作。短短的时间内,仁增已经收到许多经他诊治后康复的病人送来的锦旗。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地为科室申报西藏的区域外治诊疗中心和西藏自治区藏医风湿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两个项目。仁增告诉我:“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腰椎间盘突出、各类皮肤病等都是藏医药浴治疗的优势病种,但目前,藏医药浴临床疗效科学研究处于初始阶段,未来需要用大量病例及更长时间去精确验证临床疗程多长,疗效能达到什么程度。”
和药浴中心同事共同努力开展全面的人才培养工作也是仁增的工作内容之一。这就引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老师。
仁增希望成功申报的两个项目,既可以用来申报相关的研究课题;也可以成为一个在科学的评价体系下开展临床评价研究的平台。
学生噶玛眼中的老师仁增
藏医主要以家庭中父传子的方式和学校常见的师徒教育方式来传承。教学方式有三大方法:授权(相当于佛教里面的灌顶)、口传(由老师把藏医的典籍念给学生听,重点讲解陈述)、讲述(现代大学里常见的老师在讲台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作为传统教学工具而诞生的《曼唐》(医学唐卡)是为了让藏医学生们学习起来更加直观,但现在大学里基本上已经用PPT取代了。实践方面与过去的藏医教学方式一脉相承:认药采药、学习藏药的炮制工艺、跟师学习是每一个藏医必经的阶段。仁增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通过藏医的传统和现代两种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所以他的教学方式也会灵活多样一些。
到自治区藏医院工作之后,仁增陆陆续续带了很多学生:本科、规培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藏医,他们跟着仁增学习的时间通常是几周到几个月不等,大多是讲述式教学。只有一个叫噶玛俄热的学生从前年冬天开始一直跟着他以最传统方式学习。今年仁增申请到日喀则昂仁县藏医院驻村,他的妻子和8岁的儿子在那里。分隔两地后,仁增给噶玛俄热的教学通过视频的形式来进行。噶玛俄热以前常说很“怕”老师,尤其是背书的时候。见老师之前可以倒背如流,一见到老师就“吓”得什么都忘了。现在隔着屏幕,不再那么紧张了。“每次见到老师灿烂的笑容,觉得格外的亲切和温暖。”噶玛俄热给我形容道。
噶玛俄热是专程从老家德格来找仁增学习藏医的。他过去曾是青年诗人、歌词作者……眼下,他全身心投入只想做好一个藏医学生。他曾说,“我对很多事情都没有信心了,但对藏医的信心没有失去。”这份信心大部分是源于他的老师仁增博士。

仁增和学生噶玛俄热 图/噶玛俄热
刚认识仁增博士那会儿,噶玛俄热觉得自己的老师是一个外表不太起眼、性格有点木讷的人。有一次,师徒二人上完课不知不觉已经很晚了,刚拿下驾照不久的仁增坚持开新买的车送噶玛俄热回家。因为天黑视线不好,车况又不太熟悉,仁增好几次身体前倾靠到方向盘上去观察路况,噶玛俄热看在眼里,心中百感交集。
相处时间越长,噶玛俄热越发觉得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令他折服,尤其是他讲课的时候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而且总能耐心地找到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把复杂的问题剖析得干净透彻。
去年冬天,噶玛俄热的父亲生病,仁增通过视频接诊,给噶玛俄热的父亲开了一些药。今年年初,因为区域诊疗的项目,他去了一趟德格考察,专程去检查了噶玛俄热父亲的病情。噶玛俄热把自己和老师的合影洗了出来装裱,挂在了家里的照片墙上。
仁增曾说过一句话,令噶玛俄热印象深刻:“尽管医学基础理论并非特别扎实,在临床上医治某些病人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但是医学理论基础扎实,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既会得到病人的好评,也会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因此当一名理论和实践兼备的医生很重要。”这是仁增奉为准则的一句话,也包含了他对学生噶玛俄热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