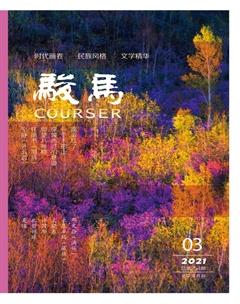那缕皂角香
刘万祥
1
剛刚四月中旬,窗外的知了就兴奋地从黑暗静谧的土中钻出来高唱夏日赞歌。高温将路两旁香樟树叶绿色的血液蒸腾出来,让老旧发霉的小区里弥漫着一股掺着陈腐气味的幽香。
乔镜顶着一头蓬松的羊毛卷短发,在电脑上看见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故事,被那个所谓的“编辑”骗走了大纲和样章,改头换面地出现在某小说网站的新文推荐榜单上。她气得像一只开了水的壶,对着那编辑遗照一样的灰色QQ头像狂轰滥炸,却追问不出一丝的公平正义。
那天晚上老妈要加班,乔镜只好在恼火中出门去给自己寻摸晚饭。她家住在大学城旁边,乔镜拐进大学城里的小吃街,记忆中好像是吃了一碗酸辣粉,还是凉粉。她只记得正吃得有点开心的时候,对面“呼呼”吹着的风扇突然就掀翻了一次性的塑料碗,把她的白T恤和牛仔裤用辣椒汤汁染成了一片热情洋溢的红。
闷热的城,嘈杂的店。乔镜心里的恼怒像一只锯了嘴的葫芦,无处发泄,无可排除,憋得她心里难受。可就在这个时候,她耸着鼻子闻到了街边飘过来的一点甜。那是焦糖和糯米混合在一起的香味。乔镜寻着这一丝慰藉的甜味,看见了一个卖糖油粑粑的小摊。
那是晚上九点多的样子,小摊上剩下十几个糖油粑粑,棕黄的焦糖外壳,糯米做成软软胖胖的身子横陈在小铁架上,香甜诱人。乔镜立刻朝它们走过去,刚刚张嘴叫了一声“小哥”,就被人撞了一个侧身,男生趿拉着一双人字拖,急吼吼地朝小贩说道:“快给我把糖油粑粑包上,全部!全部的!”他还没忘了对身边惊讶的乔镜道歉:“对不起,小兄弟,我跑得快。”
这一句“小兄弟”仿佛是一把刀,把乔镜堵在心里一葫芦的恼怒劈开了瓢,她顿时化作愤怒的小鸟,一声不吭地往男生肚子上狠狠撞过去,将那男生撞得跌在地上,四仰八叉地翻了个翻。
乔镜丧心病狂地扑上去对着那人又拍又打,那男生立刻伸出一只手抵住乔镜,让他的身体与乔镜保持了一臂长的距离。乔镜完全没有什么所谓的打架套路,手脚乱踢,两只胳膊抡划桨一样隔空挥舞着,一边尖叫道:“骗子!大骗子!大骗子!你抢我的糖油粑粑!你抢我的糖油粑粑!”
乔镜一头蒲公英成精了似的蓬松短发,瘦小干瘪的身体前后一样平坦,陈亦权抵着乔镜好一会儿才搞清楚这个主动找架打的“小兄弟”其实是个“小丫头”。陈亦权虽然长得结实,可面对这样一个撒泼的疯猴也实在无处下手,混乱中他突然惨叫一声,两腿并拢,一脸痛苦地蹲到了一旁。他痛得缩在小摊旁边,脸色煞白地骂道:“我抢你个粪球粑粑!你这个神经病!”
那是个,不打不相识的夏天。
2
乔镜不太确定,老妈发布的那些小广告是否真的能找来家教老师。因为自己有个偶尔才回家,回家就偷钱打人的爸,所以老妈在招工要求上赫赫写着“不怕打架”四个字。这样也能找来家教老师才怪。乔镜翻了个白眼。事实上,乔镜也不希望这件事办成。
乔镜不是个很努力用功读书的学生,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能普及,她整天拿着个巴掌大的MP4来看小说,在别人拼命在书山题海里苦苦挣扎的时候,她悠闲得令人发指。
乔镜对待高考的态度,仿佛是迎接一次无从推诿、不可避免的月经。所以对于老妈自作主张找家教老师的事,她觉得完全是多此一举。
“人都找好了,明天你就开始上课。”老妈不顾乔镜的反对说道:“我跟你们班主任说好了,以后你晚自习不去了,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那老师给你上两个半小时课,中间休息半小时。”
“妈,你何必呢,犯不上。”乔镜叹了口气。
“犯不上?我犯不上?为谁犯不上!”妈妈瞬间提高了嗓子:“还有一个多月就高考了,你看看谁周末还像你这样悠悠荡荡的?谁不是抓紧最后一点时间……”
“妈!”老妈的声音让她觉得好生头疼。
“你嫌我啰嗦是吗,你就不想想,你难道想像我这样活得累死累活……”
“我从来没让你累死累活过。”乔镜皱起眉头:“你花了好几千给我买的那个复习资料,那玩意有用吗?还有那个什么补脑的,那就是骗人的你知道吗?你花那么多钱,你问过我吗?请个家教,还一对一,得多少钱?你想过我的感受吗?你要把自己累死了,让我一辈子愧疚吗?”
“啪!”一个响亮的巴掌落到乔镜脸上,老妈气得浑身发抖,她两鬓的头发落下几缕,散乱地贴在脸颊上,不知道是因为汗水,还是脸上横流的眼泪。“混账!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你跟你爸一个样!你……你……”
“唉……不会的,妈,不会的。”乔镜叹了口气,走上前轻轻擦掉母亲的眼泪,把她拥进怀里。“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心疼你,我怕你累着。”
“我为什么,不是为了你呀?这一辈子就看这一个多月了,我想要你活得比我好啊,你怎么不能努力呢?你倒是,你倒是给我争点气啊!”妈妈紧紧抱着乔镜瘦小的身躯,她抽噎着,滚热的眼泪流到乔镜蓬松的短发上,乔镜觉得头皮痒痒的。
窗外的蝉鸣在黑夜里一声高过一声,乔镜觉得心里好像醉了酒,困顿而燥热。
3
乔镜对她高中三年的班主任没有半点好印象。她至今仍然记得,当她对那个四十几岁带着黑色眼镜框的中年女人说出晚自习缺席的请求时,她眼中流露出了毫不掩饰的鄙夷。那个女人甚至没有等乔镜把办公室的门关好,就迫不及待地和同事们讥讽起笨拙的她。乔镜低下头抿了抿嘴,默默地从办公室门外走开了。
连老师都觉得她没救了,不知道老妈为什么非要挥霍那一分一分赚来的血汗钱来找家教。只剩一个月就考试了,自己平时读书读成什么样,难道她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这个城市的夏天闷热而潮湿,校服永远黏黏地粘在身上。如果戴上蹼,或许就能在潮湿的空气中游起来吧。
乔镜拖着毫无激情的步子走到家门口,当看见等在门前的家教老师时,更觉得老妈的钱是打了水漂。
“小丫头,再看我要收钱了。”乔镜记得,陈亦权在昏暗的楼道里,对发愣的自己说道。那天他穿着一件柠檬黄的T恤,带着大大的向日葵图案,夕阳的余晖透过缓台上小小的窗子照在他的侧脸上,周围的灰尘星星点点,轻轻地漂浮在他脸颊边,显得他的睫毛很长。
乔镜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只好机械地开门,把她新鲜出炉的家教老师让进了屋。她木偶一样地把书包放在屋里,又去厨房倒了一杯冰箱里的大麦茶,并趁机给母上大人发了一条短信:“你给我找的家教老师是个男的?”
“谢谢。”陈亦权接过乔镜递过来的麦茶喝了一大口,他随意地坐在乔镜的写字台前晃着椅背:“咱俩见过,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你这小孩挺有意思的,我喜欢。”
乔镜翻了个白眼。
陈亦权的第一节课,十分理所应当地跟乔镜宣布:“今天不上课,咱俩聊聊。”
乔镜讽刺地哼道:“你这钱也赚得太容易了。”
“今天不收钱。”陈亦权笑了,露出一口白得晃眼的牙,“明天再正式上课,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哦。”乔镜应了一声。从抽屉里拿出试卷夹子,她把近两个月以来的周考试卷一张一张地摊在陈亦权面前,“你在这‘知己知彼吧,我去那边写作业。”
“回来回来,我不是这个意思。”陈亦权叫住她:“先聊聊天嘛,哎,你妈妈一般什么时候回家?”
乔镜圆圆的眼睛瞪得更圆,她凶狠地问道:“你想要干什么?”
“哎,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这小孩儿。”陈亦权尴尬地摆摆手。
“小孩小孩的,你比我大几岁啊?”乔镜愤愤地回嘴。
陈亦权叹了口气,“你脾气真怪,我大不了你几岁,就在旁边大学念书,你也不用管我叫老师,要是看得起我,你就管我叫一声‘亦权哥,要是不乐意你就喊我‘老陈吧。哦,我叫陈亦权。”
4
第一天上课,陈亦权真的是来聊天的。他问乔镜,平时妈妈几点回家,早中晚怎么吃饭,喜欢吃什么,在学校有没有好朋友,一个人在家喜欢干嘛,有什么爱好,有什么愿望,有没有偶像。
喬镜没搭理他,陈亦权就滔滔不绝讲起自己的生活来。他说他家乡的风土人情,特产美食,说他大学里面天南海北的室友,有趣多彩的社团。他去过山区支教,去过公园义诊,还和朋友踩单车骑行了几百里去穷游……
现在想起来,乔镜能接受陈亦权来辅导功课,可能和他的皮相有很大关系。陈亦权喜欢穿各种各样的运动装,他能把普普通通的一条运动裤穿得帅气逼人,也能把十块钱一件的棉布T恤穿得骚气拉风。
乔镜觉得陈亦权是发着光的。他整个人那么丰富,那么耀眼,和灰扑扑毫无色彩可言的自己完全不同。“其实越好的大学,这些文体活动越丰富,社团越有意思。我看过你的试卷,你语文和英语都很好,只是理综和数学弱一些,这是你的方法问题。数理化是互通的,只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肯下苦功,捡回来五六十分不是问题,这分你要不要?”
乔镜看着陈亦权撅撅嘴巴,说:“你少吹牛了。”
陈亦权这个家教当得太尽心了,他用一个新的笔记本细细地梳理各科的知识点,一笔一划写好了交到乔镜手里,三令五申威逼利诱乔镜要把笔记本上的内容全都倒背如流。他还自己去书店里泡着,抄下各种典型例题,手写各种有针对性的卷子给乔镜来答,也会在每次周考之后帮乔镜把各种相似题型用彩色笔标注好,帮助她理清思路。
两次周考之后,乔镜的理综成绩往上爬了将近三十分。乔镜反复看了三遍卷子,又自己核对了分数,还是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能答出来的卷子。她把卷子给陈亦权拿回去,夸张地瞪着眼睛:“是不是我们老师给你漏题了?”逗得陈亦权哈哈大笑。
5
那段时间,陈亦权比乔镜自己还着急。他总是不停地嘟囔着:“哎,时间太短了,时间太短了……”可每次乔镜的周考成绩出来,陈亦权都会奖励地摸一摸她蒲公英一般的短发,说一句“不错嘛!”乔镜就得意洋洋地昂起下巴,鼻尖轻轻地嗅着陈亦权身上那掺杂着夏日体香的皂角味道。
乔镜房间里的写字台正对着窗户,陈亦权给乔镜讲题时就坐在乔镜左边,有时夕阳透过窗子给陈亦权高挺的鼻梁镀上一层金边,他支起一条长腿伸在写字台外边,像是漫画里完美无瑕的男主角。
家里没有空调,陈亦权常常热得不行,他对着乔镜家的风扇呼啦着宽松的T恤衫,乔镜去冰箱里给他端来一杯冰镇的大麦茶。陈亦权很喜欢,说比外面买的还好喝。
乔镜喜欢陈亦权坐在她旁边,喜欢陈亦权一边用草纸写下密密麻麻的演算,一边在她耳边低低地讲解。每当这时候,她就把头凑过去,正大光明而又贪婪无休地嗅着陈亦权身上独一无二的皂角香。
陈亦权对着草纸上的一堆数字口吐莲花,讲得鼻头上聚起了小小的汗珠,可一回头,他竟然发现乔镜在发呆,气得他拿笔朝乔镜的脑袋戳过去,“集中一点!集中一点啊,小屁孩!”
“我不是小屁孩了。”乔镜红着脸小声说。
陈亦权看着乔镜,突然间沉默了。安静的房间里只有风扇傻呼呼地摇着大脑袋,两个人都不吭声。
突然间,客厅里传来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乔镜的妈妈不可能下班这么早,她疑惑地回过头往门口看去,陈亦权也随着她的目光一起看向门口。客厅没有开灯,只有乔镜的房间里漏出一小片灯光映在外面。昏暗的客厅开了门,一个矮瘦的男人从外头贼头贼脑地探进来,看到乔镜房间的灯光,动作又一瞬间地停顿。
“呵,又没钱了?”乔镜看见那男人的一瞬间突然浑身僵硬发抖,手不自觉地握起拳头,“嚯”地起身冲到门口挡在男人面前。那是个电子货币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乔镜不太能理解老妈为什么总是把钱存在同一张存折上。就算存进去,就不能改密码吗?那个男人一次又一次拿走老妈的血汗钱挥霍,再把空存折顺着门缝扔回来。每次老妈看见门口扔着的空存折,都会坐在饭桌旁长久地发呆。
乔镜很排斥她的父亲,冷冷地说:“出去。”
“你怎么在家?”男人看着乔镜,全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他的目光越过乔镜,看见了站在乔镜房间门口的陈亦权。发出戏谑的长音,“哦——往家里领男人了?你妈把你教得可真好。”
“嘴巴干净点!”乔镜冲上去狠狠抽了那男人一个嘴巴,她瘦小的身体抖得犹如筛糠。
那男人明显被抽愣了,反应过来之后,他一把抓住了乔镜蒲公英一样蓬松的短发,骂骂咧咧地带着她瘦弱的身体往墙上撞去。
早在男人伸手过来的一瞬间,乔镜便下意识地闭上眼,但预料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一个有着皂角清香的怀抱将她接住。撞击通过陈亦权的胸膛传递到乔镜身上,虽然不痛,但她仍然倒吸一口凉气。
只一瞬,陈亦权就放开了乔镜,他动作利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左手抬起挡住男人打下来的拳头,右手揪住了男人的领子把他往外搡了一大步,在男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陈亦权顺势扭住男人的手腕往后背一别,那男人顿时跪在门口“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那男人一叠声地求饶,待他手一松,屁滚尿流地跑了。
乔镜控制不住地颤抖,她冲着男人的背影狠狠地砸过去一个什么,尖叫着:“王八蛋!”
陈亦权回过头来,他看着乔镜,毛茸茸的头顶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她瘦小的身体好像暴雨中飘摇的蛛丝,摇摇欲坠。他回身关上门,走过去帮她把蓬乱的头发整理好。“别哭了,小丫头。”陈亦权说:“洗把脸吧,咱们去接你妈妈下班。”
乔镜抬起头,陈亦权逆着她房间的灯光站在乔镜眼前,只有一个黑蒙蒙高高大大的影子。她突然扑进他的怀里嚎啕大哭。陈亦权尴尬地抬起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才好。
6
晚上八点多的城市,路边还热热闹闹,熙熙攘攘。陈亦权看了看迈着小步跟在他身后的乔镜,她一脑袋的羊毛卷,像一朵云飘在女孩白皙的额头上,又大又圆的眼睛低垂着,仿佛对路边的小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亦权停了两步,和乔镜并肩走着。
“你恨他吗?”陈亦权问。
“恨吧。我常常想,如果他能死掉就好了。”乔镜抬眼看着陈亦权,笑着说。
“嗯,我懂你。”陈亦权试探着把手放在乔镜后背,见她没有意见,便这样与她一起往前走。“我爸,他爱喝酒,北方人嘛,爱喝酒挺常见的。但是他酗酒,然后他会打我妈,我小的时候,他也打我。”
乔镜吃惊地盯着陈亦权。
“别这样看着我,我没在编故事,那时候我很小,其实我不太记得,但我记得那种感觉。”陈亦权笑了笑:“我知道你家里情况,不然也不会给你当老师。”陈亦权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亦权吗?我妈说,怀我之前她根本不想要孩子,可是她的婆婆想要,就带着我妈去算命,那瞎子说,我妈马上就会怀孕了,怀的是个贵子。”陈亦权低头看着乔镜,“然后没到一个月,就怀了我。我妈说我是有权而生的。”
“我本来还以为你名字里藏着什么詩呢。”
“什么诗啊,我爸妈都没什么文化的。”陈亦权说。
“如果不是生了我,我妈早就和我爸离婚了。但是我妈为了我,一直留在那个家。她说,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没有爹。”陈亦权摸摸乔镜的头,“所以我很恨我自己,我觉得我不该生出来。”
“怎么会呢?你,你这么好……”乔镜着急地说。
陈亦权温柔地笑了。他重新把手放在乔镜后背上,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瘦小的背脊。“我不好,小傻瓜。你想听我的故事吗?”
乔镜和陈亦权走到老妈打工的超市门口,两个人在路边的花坛坐下。陈亦权把故事说得很简单,他的妈妈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一直逆来顺受维系婚姻,忍受酒后家暴的丈夫,但是事情被陈亦权的舅舅意外发现,舅舅二话不说地把妹妹领回娘家,强迫两口子协议离了婚。陈亦权很多年也想不通,明明是那样一个糟糕的丈夫、糟糕的父亲,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留着他干嘛呢?
乔镜说:“我其实早就跟我妈说,不要跟我爸过了,我们娘俩也能过好,可是我妈就是不听。她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被我爸爸奴役似的。”
陈亦权笑了。
乔镜看着陈亦权,低下头小声问道:“你来当家教,是同情我吗?”
“不是。”陈亦权说:“不是同情你。是告诉你,你还有很大一部分精彩的人生没有经历,你还有很光明的未来,只要你踮起脚够一够就能够得到,并且带着你的妈妈一起。”
乔镜双颊发烫地嘀咕道,“是吗?”
“你想,你妈妈为什么不肯放下过去呢?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啊。你,小丫头,你就是你妈妈的希望。等你有了光明的未来,你就变成了一个太阳,能照亮你的母亲,照亮别人。”陈亦权看着超市的门,对下班出来的杨妈妈招了招手。
乔镜盯着陈亦权,在心里说,你就是我的太阳。
7
高考来临的时候,陈亦权比乔镜还紧张。陈亦权跟杨妈妈一起在厨房里,嘀嘀咕咕神神道道地让乔镜受不了。
“你明天穿这件,我新买的。”杨妈妈给乔镜拿过去一个灰色带黄条纹的半袖,乔镜被那亮眼的黄条纹闪瞎了眼睛,她尖叫到:“我不穿!太丑了!”
“不行,这叫‘走向辉煌,你必须穿,就丑三天没人看见你,祖宗!”杨妈妈不由分说地把衣服扔在乔镜脸上。陈亦权在一旁帮腔,“穿吧,小丫头,得图个好意头!”乔镜咂咂嘴,忍住了没把那件衣服扔进垃圾桶里。
最后一天出考场的时候,杨妈妈去上班了,陈亦权来接她,说,“考完了什么都不想,我带你玩去吧。”
那是乔镜第一次走进陈亦权的校园。是个医科大学,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与其他综合大学相比,这里的学生看起来好像更朴素一些。乔镜本来以为陈亦权要带她去什么好玩的地方,结果她那不靠谱的老师给她领进了标本馆。
乔镜觉得,带小丫头去医科大学标本馆庆祝高考结束这事,不像是个正常人能办出来的。
陈亦权带着乔镜从各种骨头和各种切面的标本面前走过,一边走还一边滔滔不绝地给她讲,这是你的什么什么,那是你的什么什么。乔镜听得后背炸起一排汗毛,“这不是我的!你别说了!”
陈亦权很大声地笑,露出能迷死人的虎牙。
乔镜后来考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师范。升学宴的前几天,乔镜和老妈彻夜长谈,第二天一早,老妈在一家麻将馆里找到了老爸,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在乔镜拿着菜刀疯狂地控诉与逼迫下,老爸才终于放开了老妈,同意了离婚。
老妈说:“丫头,你吓死妈妈了。”
乔镜说:“现在,你再也不用怕了。”
标本馆之后,乔镜再也没见过陈亦权。她和妈妈搬出了那间她住了十几年的老旧房子。那房子判给了老爸。他们去区县里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了。外公对于妈妈突然离婚的事情很是吃惊,他们回去之后,外公对着两个人叹了好多次气,外婆听见,便拿一个大簸箩一叠叠地拍在外公背上,“你叹什么气呀!你女儿回来过好日子,你叹个什么气!”
“哎哟,你个疯老太婆子,不叹了不叹了!”外公嚷嚷着躲开了,乔镜看着他们老两口没心没肺地笑了。
从市里搬到外公外婆家之后,乔镜从来不敢主动找陈亦权。尽管她在无数个夜里梦见过他穿着黄色向日葵T恤,站在楼道里迎着夕阳的样子,也无数次地在半梦半醒中闻到过他身上掺杂着夏日气息的皂角香。
陈亦权是有女朋友的。他无数次地给乔镜显摆过自己的女朋友,多么好看,多么温柔。做饭一流,跳舞超美……
不像自己,乔镜想,干干瘪瘪,顶着一头永远也不安分的羊毛卷。但是乔镜强迫自己马上释怀,她一直记得陈亦权的话,她还有那么长的很精彩的人生要过。陈亦权,他是她希望的太阳,可他也是别人幸福的太阳。她怎么能冒着让另一个女孩子失去晴天的危险,去抢她的太阳呢?何况,陈亦权那么喜欢他的女朋友。陈亦权不过是她起航路上的那一抹朝阳罢了。她相信自己会遇到一个新的太阳的。她会自己成为一个太阳的!
二零一二年九月中旬,乔镜离开家,拖着行李箱去新的学校报到。天气有些阴,闷热的学校里弥漫着一股香樟树的幽香,就好像她住了十几年,又在最后一刻搬走的那个小区一样。她站在校门口,往远处望了一望,天阴沉沉的。乔镜感到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忽而刮过一阵微凉的风,雨水紧接着便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乔镜赶紧拖着箱子躲进新生等候区的棚子里。大雨冲散了香樟幽深的味道,给闷热厚重的空气撕开了一个清凉的口子。雨点打着树叶“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洗净了它们身上蒙蒙的拂尘,变得绿油油,闪亮亮的。
乔镜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眼,嘴角扬起温暖而满足的笑。陈亦权说:“报道了吧?今天是新的起点,美好的未来等着你这个太阳把它们照亮呢。”
“嗯。”乔镜在心里说,“像你一样。”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