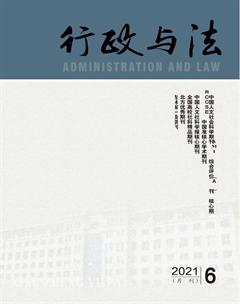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竞争法规制
吴楷文 王承堂
摘 要: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可分层为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手段行为和优待自营业务的目的行为。该行为会侵害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权益和公平竞争利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并影响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两反法”有其规制的重点,手段行为造成的损害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匹配,而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目的行为更合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框架下,手段行为可能符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或一般条款的构成要件;在反垄断法的语境下,目的行为可能触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差别待遇的规定。
关 键 词: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自营业务;竞争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1)06-0120-10
收稿日期:2021-04-06
作者简介:吴楷文,扬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竞争法学;王承堂,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一般项目“电子商务平台非中立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FH2020B011。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數字技术不断成熟的大背景下,平台经济的总体地位日益提高,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甚至是最主要力量,不断涌现出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商业巨头,而数据则是推动这些平台企业不断向前的核心动力。对于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各方主体来说,更多数据意味着更大的竞争优势,数据既可以帮助平台经营者优化平台服务,也可以为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提供指引。传统平台经营者仅以提供平台服务而非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为根本遵循,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更新,平台经营者亦开始从事自营业务并参与平台内市场的竞争,这也为其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侵害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权益和公平竞争利益埋下了伏笔。虽然谷歌曾因将自家比价服务置于搜索结果的优先位置被欧盟罚款24.2亿美元,但巨额罚款并没有将此类行为扼杀在摇篮中,平台企业的自我优待行为仍有不断扩张的态势。[1]在美国众议院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报告》中,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GAFA)四大平台巨头均涉及自我优待行为,其中有关亚马逊通过访问第三方卖家(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使第一方业务(自营业务)获益的调查占据了大量篇幅。[2]在大洋彼岸,欧盟则认为亚马逊将第三方卖家数据用于优化自营业务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3]
与欧美向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频频出手不同,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部门尚未关注到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现实可能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风险。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我国势必不断重视其中可能存在的垄断和其他反竞争问题。《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出台更是为规制此类行为提供了微观指引。鉴于此,本文拟聚焦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在我国竞争法的框架下探寻有针对性的规制路径。
二、 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检视
(一) 检视基础: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分层
数据与算法在平台经济时代相辅相成,二者的协作是电子商务平台内以平台经营者为代表的各方主体作出正确决策的技术基础。在欧盟副主席维斯塔格发表的声明中,亚马逊首先将平台内经营者的产品和数据实时反馈到其算法中,并基于算法输出的结果优化自营业务的产品和价格。[4]虽然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在平台基础架构和算法的协助下可以实时完成,整个过程或许只需要一秒钟甚至更短的时间,但这短暂的一瞬却让平台经营者实际上走完了“获取数据——分析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全过程,并基于此实现了使自营业务在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竞争中占据优势的目的。
为了分析的方便,笔者将上述行为分层为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手段行为和优待并使自营业务拥有竞争优势的目的行为。与竞争法不同,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分层评价在刑事司法中已运用地较为广泛和成熟,其原因在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可能会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并侵害不同法益。以“套路贷”案件为例,无论案件多么复杂,其基本形态都是一个由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所统领的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组成的有机体。[5]当然,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分层评价并不是刑法的专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其亦可在竞争法中适用。即使刑法与竞争法规制的法益不同,但二者的落脚点均在行为评价上,而且一些违反竞争法的行为也可能被刑法处以否定评价。通过将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进行分层,可以分别评估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全面的竞争法规制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该行为在分层的基础上被单独评价,但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并非完全割裂,仍为一个有机整体。
(二)手段行为检视
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是平台经营者实施的手段行为。平台经营者为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搭建了交易的桥梁,从而实现了二者的快速匹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电子商务平台的存在不仅可以创造大量交易机会,还为消费者节约了搜寻成本。电子商务平台虽然是互联网中的虚拟平台,但并非“海市蜃楼”,它和传统商场一样需要一定的基础架构支撑,只不过支撑传统商场的是钢筋混凝土,电子商务平台的基础架构则是由代码和互联网通信协议构建的。互联网的基本通信协议等技术构造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基于互联网信息系统的电子商务平台则像互联网中的一个个“岛屿”,同样具有技术能力和权力。[6]在电子商务平台这个“岛屿”上,平台经营者不仅拥有整个“岛屿”的产权,还能够依托平台基础架构和其他技术工具掌控平台内发生的一切。
平台经营者拥有整个电子商务平台的基础架构,而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则依附于平台架构,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为平台经营者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此外,根据《电子商务法》第31条的规定,平台经营者负有记录、保存信息的义务,并需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信息保存義务是一把“双刃剑”,该义务一方面通过留存证据的方式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平台经营者储存平台内经营者数据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增加了平台内经营者数据被不当获取的商业风险。数据获取后,平台经营者可以借助算法工具深度分析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从而为优待自营业务贡献推理和预测的基础。而且与人相比,作为机器的算法不仅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理解”与“学习”,还可以排除情感的干扰,为平台经营者提供最符合经济学假设的理性选择。
(三)目的行为检视
优待并使自营业务拥有竞争优势是平台经营者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目的。当平台经营者从事自营业务时,它不再是仅提供平台服务的中间人,在法律地位上也与平台内经营者无异,并须承担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开展自营业务是平台经营者纵向一体化的方式之一,而且平台业务和自营业务同为平台经营者的盈利来源,平台经营者也可在优待自营业务中获得更多利益,因为只有提升自营业务的竞争力才能使其成为推动平台整体不断向前的新动能。
在欧美的调查中,亚马逊主要通过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手段优待自营业务。不管是对于平台经营者抑或是平台内经营者来说,数据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市场竞争中,竞争优势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因而在数据优待的场景下,自营业务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获取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提升自营业务的竞争力。大数据分析以海量数据为前提,尽管相对于平台内经营者,平台经营者的数据资源更为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经营者的数据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借助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平台经营者可以更好地优化自营业务并提升其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数据被获取的事实减损了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竞争力,从而达到间接增强自营业务竞争优势的效果。数据承载了平台内经营者的诸多关键信息,甚至包括直接影响其经营根基的商业秘密。虽然数据具有非排他性并可以被无限复制,但平台经营者不仅可以针对特定竞争对手的数据“采其所长,补其所短”,还可以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竞争劣势定向打击以削弱其竞争力。
此外,平台经营者的平台管理权限和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好地为其优待自营业务的目标服务。根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平台经营者在负有提供优质平台服务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管理平台内经营者的权力,而为了保证平台内市场的交易安全和有序运行,平台经营者也有足够的动机实施管理行为。除此之外,《电子商务法》第2章第2节中对平台经营者的诸多义务性规定更是强化了其行使管理职权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平台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意味着“权力”。[7]不过良好管理的另一面却是权力可能被滥用,平台经营者同样可以在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后利用管理权限为优待自营业务服务。
三、 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在给自营业务提供竞争优势的同时,也给平台内市场带来了严重的现实损害,为此有必要在分层检视的基础上明确该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当然,正如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仍为一个有机整体,二者对市场的影响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各有侧重,不能完全割裂。
(一)行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影响
⒈侵害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权益。如果要对数据进行保护,就必须明确主体对数据享有是利益还是权力,因为二者代表了不一样的保护强度。数据在平台经济时代的价值不言而喻,但高价值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强度最高的财产权对数据予以保护。从现实立法来看,《民法典》第5章在规定各种权利的同时并未明确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保护方式,只在第127条规定将数据和虚拟财产交由其他法律解决。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一系列数据爬虫案件时同样没有认定主体对数据的财产权,而是将行为置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框架下分析。如一审和二审法院在“淘宝诉美景案”中均否定了淘宝公司对涉案数据的财产权,并承认了其对数据享有“竞争性财产权益”。虽然平台内经营者对数据享有的是财产性权益而非财产权,法律也不能为其提供绝对化的权利保护,但这并不等于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的行为没有侵犯到平台内经营者的任何权益。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它承载了平台内经营者的产品、价格等诸多关键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平台内经营者来说是则经营活动的生命线。在性质上与网络爬虫案件类似,平台经营者利用自己的基础架构地位和技术优势获取数据的行为同样侵犯了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权益。
⒉损害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平台内经营者是平台经营者利用其数据优待自营业务行为的最大受害者:一方面,平台内经营者数据可以被随意获取的事实意味着其公平竞争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优待自营业务的目的行为更使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无力与自营业务竞争。借助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平台经营者不仅可以取长补短、实现自营业务的不断优化,还可以针对竞争对手的关键劣势予以打击,从而让自营业务在平台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一方得利的同时必然有另一方受损,自营业务的竞争优势也就预示着平台内经营者业务的竞争劣势。竞争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获利,竞争中产生的损失也只能被视为纯粹经济损失,不过该论断必须以公平竞争为前提。
与优待自营业务所产生的竞争优势相对应的是,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公平竞争利益是经营者根据自身主体性所享有的利益,其内涵在于“公平竞争资格、不受不正当竞争行为排挤和损害的地位、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利润的能力”。[8]申言之,在公平竞争利益的保障下,每一个竞争者都可以凭借价格、性能或质量在竞争中击败竞争对手并获取利润,且在面对不当竞争行为的排挤和损害时可以寻求法律救济。不过,平台经营者优待行为的实施路径是在获取竞争对手数据的基础上为自营业务取得信息优势,而平台内经营者在数据被随意侵犯时很难获得真正的“公平竞争资格”。
平台内经营者不仅很难获得真正的“公平竞争资格”,而且因巨大的经济压力也无力与平台经营者抗衡。如果说平台经营者基于服务协议和法律规定获得的只是管理平台的权利,因为平台内经营者可以随时根据协议约定退出平台,那么在巨大经济优势的扶持下,平台经营者的权利很有可能真正蛻变成具有支配力的“私权力”。权力意味着支配,即一个行动者可以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9]尽管离开平台对于平台内经营者来说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但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其在面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及自营业务的竞争优势时不能充分地自由选择。
(二)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⒈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数据是平台经济时代市场主体最大的财富,而平台经营者借助技术手段随意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行为则是对竞争秩序的公然蔑视。为了防止平台经营者对其数据的不当获取,有能力的平台内经营者势必同样会通过技术手段构筑自己的数据城墙以保证数据安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无序的市场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只要数据保护的成本大于数据被获取的损失,理性的平台内经营者就有足够的激励设置数据壁垒。但相对于那些规模效应下有能力采取技术手段的大企业,无力负担高额数据保护成本的小企业才是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写照,而且他们根本没有资本与平台经营者谈判或对抗,只得任由自己的数据被平台经营者获取后用于优待自营业务。此外,数据城墙的构筑不仅会让平台内经营者背负额外的数据保护成本,还会阻断部分有益的数据获取行为、阻碍数据的正常流通,并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流失。
不宁唯是,平台经营者的数据获取行为还会影响平台内经营者的创新激励。创新是分析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比如在欧盟委员会看来,创新虽然不是在认定反竞争行为时唯一甚至关键的核心价值,但其仍为一种以补充方式体现的政策价值。[10]数据是平台内经营者的核心资产,更是其创新的动力源泉和成果体现。为了提升竞争力,平台内经营者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数据收集和产品更新。但是一旦数据轻易被他人非正当获取,在市场竞争秩序混乱、其劳动成果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形下,平台内经营者收集数据和更新产品的激励便会大大降低。
⒉影响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受损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意味着平台内市场的竞争机制无法充分发挥。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没有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的自我调节运行也以国家所确认和保护的竞争为前提。[11]在平台内市场的竞争中,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与自营业务并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自营业务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然而,该优势并非来自于产品的更低价格或更高质量,而是平台经营者在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基础上实施的优待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之间存在单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个人的选择有赖于充分的信息,经营者的决策同样如此。信息经济学的成果表明,信息的完全性是作为经济学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12]在利用平台内经营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场景下,平台经营者可以为自营业务提供竞争对手的完全信息,与此同时平台内经营者却还处于“信息迷雾”中无法发现正确的方向。在市场竞争下,一方拥有完全信息不会带来美好的“完全竞争市场”,只会让市场竞争机制在单方面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下进一步失灵,无法发挥应有功用。
(三)行为对消费者的影响
如上所述,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会对平台内经营者和市场竞争造成影响,而这一切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损害消费者利益。当面对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的手段行为时,平台内经营者增加数据保护成本或减少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会投射到消费者身上,减损消费者福利。与手段行为类似,平台经营者自我优待的目的行为同样会减损平台内经营者创新或优化产品的积极性,因为只有当平台内经营者付出加倍努力时才有可能抹平其业务与自营业务的差距,而数据能够被轻易获取的事实则会让其陷入更深层次的死循环。不仅如此,平台经营者获取竞争对手数据的终极目标在于仿制并取代平台内经营者的产品,这在美国众议院对亚马逊的调查报告中已有所体现,且已遭到大量平台内经营者的抗议与控诉。上述事实表明,自营业务的出现看似在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之外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但实际上却会导致消费成本的大幅上涨并严重限制消费者在自营业务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
不仅如此,消费者在消费选择时还会由于信息不充分和自身的认知局限存在被误导的可能。为实现消费者与商品的快速匹配,平台经营者通常会借助智能算法和搜索排名工具帮助消费者节约搜寻成本,然而自营业务因优待行为产生的竞争优势在算法的帮助下却极易导致信息不充分的消费者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消费者想打破信息困境,则需要付出更多搜寻成本。而且即使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决策也是高度情景化的,他们通常只会关注那些显著信息。[13]在为其量身定制的用户画像及场景的干扰下,消费者基于自身的认知局限只会关注那些借助平台内经营者数据及智能算法生成的显著信息。此外,消费者的数据隐私权也可能因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行为受到不当侵害。平台内经营者为了优化服务和自身发展需要,会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基础上收集消费者的行为、喜好、习惯等数据并进行整合,与此同时平台经营者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行为并不一定取得消费者的授权。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经营者的行为极易侵犯消费者的个人数据利益和数据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隐私权。
四、 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竞争法规制路径
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虽然在我国尚未爆发出系统性的反竞争风险,但该行为对平台内经营者、平台内市场的竞争和消费者的不利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在我国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背景下,有必要未雨绸缪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探讨该行为在现行竞争法语境下的规制路径。
(一)“两反法”的适用竞合与选择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反法”)共同构建了我国竞争法的规制体系,两法也有其各自的规制重点。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解决竞争过度时市场道德缺失导致的竞争失序问题,《反垄断法》则更关注因竞争受限而导致的竞争不足问题。[14]两法的侧重点不同意味着同一行为在我国竞争法的语境下既可能被《反垄断法》调整,也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上文的分析表明,不管是手段行为还是目的行为,都会对平台内经营者、平台内市场的竞争和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这也意味着“两反法”均可作为规制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行为的法律依据。
与“两反法”有其各自的规制重点相对应的是,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各有侧重。虽然平台经营者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手段行为既侵犯了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权益,又影响了其公平竞争利益,但该行为造成损害的侧重点仍在数据权益上,而公平竞争利益只是数据权益受损的反射利益;优待自营业务的目的行为使得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无法与自营业务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该行为相对于手段行为对公平竞争利益的损害更为明显。此外,手段行为并不能限制平台内市场中的竞争,只是由于市场道德的缺少会导致竞争的失序与紊乱,而通过优待并使自营业务获取竞争优势,平台经营者能够掌握平台内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得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手段行为造成的损害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匹配,而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目的行为则更合适。当然,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属性意味着在判断其中某一行为的合法性时也时常需要考虑到另一种行为的性质。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以手段行为为中心
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果要将第9条用于规制平台经营者的手段行为,就必须从两方面进行讨论。其一,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可以被界定为商业秘密。从第9条的定义中可以得出商业秘密的三个属性,即秘密性、保密性和价值性。因此,只要契合这三个属性即可将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数据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已不言而喻,平台经营者亦通常会对作为核心资产的数据采取保密手段,故秘密性或者说“不为公众所知悉”才是界定相关数据商业秘密属性的重中之重。一般而言,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台内经营者本身拥有且以非公开为目的的数据,另一类则是它在平台中进行交易活动时搜集的公开数据。从数据的分类可以看出,那些非公开数据本身就为平台内经营者私有,是其赖以经营的根本,只不过是为了交易方便平台内经营者将这些信息作为数据在平台基础架构中储存。在没有技术手段的帮助下,这些数据中承载的经营信息和产品信息根本不可能为一般公众和平台经营者所知悉。此外,即使是平台内经营者公开获取的信息也可以具有秘密性并部分成为商业秘密。因为数据具有结构秘密性的特征,部分数据公开不意味着全部公开,或者说任何用户都不可能整体获得全部数据。[15]其二,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的手段不正当。平台经营者拥有整个平台基础架构,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则在平台基础架构上储存和流通,但储存不代表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此外,《电子商务法》第31条要求平台经营者需要确保信息的保密性,在立法者看来,此处的“保密性”指平台经营者对其保存的信息负责,防止泄露的主体也仅为第三方。[16]然而,笔者认为将“保密性”针对的主体仅限于第三方过于狭隘,应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将针对主体扩大到平台经营者自身,要求其仅在法律规定的用途内使用这些信息。第31条的立法目的在于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留存证据,而平台经营者获取相关数据为己所用的行为明显与上述目的不符,其利用这些信息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违反了保密性的要求。只有将“保密性”的对象扩大至平台经营者本身,要求其将信息仅用于证据保存,并将平台经营者超出上述目的获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行为视为非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⒉一般条款规制。对于那些难以构成商业秘密的平台内经营者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亦可以为其提供竞争法保护。首先,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间存在竞争关系。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原本处于不同层次的市场之中,平台内经营者则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平台经营者则为平台内经营者及消费者搭建交易的桥梁,二者之间非但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甚至还存在典型的合作关系。但当平台经营者通过自营业务进行纵向一体化时,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与自营业务则同在平台內市场中竞争并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为了争夺消费者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其次,在判断涉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时,通常需要考虑数据价值、积累数据的成本、获取和使用行为是否正当及数据的使用方式和范围。[17]在这四项标准中,前三项判断标准上文均已论及,故此处着重讨论第四项标准即数据的使用方式和范围。数据的使用方式和范围与数据获取后的目的行为相关,如果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的目的在于实质替代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那么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相结合给数据原拥有者造成的损害会比单纯的手段行为更大,因而手段行为也更容易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的目的即在于优待并增强自营业务的竞争力,虽然自营业务不可能完全替代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但其不仅可以提供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类似的商品或服务,还能够在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后的使用方式及范围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存在明显的重合,因此平台经营者的手段行为也应当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反垄断法规制:以目的行为为中心
在“强化反垄断”的政策引导下,我国必定会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尤其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执法工作,但在加强执法的同时却仍存在两个问题无法得到良好解决,其一是平台经济特殊性导致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题,其二是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制度绩效仍有待观察。为了消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困境,不少学者主张使用全新的规制工具应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然而这些主张却无法充分回应制度绩效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为了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的平衡,不宜滥用市场支配权,随意引入新的规制工具,而是应当在传统分析框架下进行方法革新。换言之,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仍应当从界定相关市场出发,再分析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在各个模块内部面向电子商务平台的新特点进行方法革新。最新出台的《平台指南》也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从微观上为平台经济反垄断提供了指引。
相关市场界定方面,明确相关市场可分为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其界定是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逻辑起点。与微博、脸书等纯粹吸引注意力的双边非交易市场相比,电子商务平台这类双边交易市场的相关市场界定相对容易,而且可以将平台的两边作为整体考虑。换句话说,在双边交易市场中,只需要界定一个市场而非两个市场。[18]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应当从替代性分析的角度考虑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和商业模式,并需要关注平台的主要用户群体,因为两边的用户才是平台赖以发展的基础。除了关注线上平台,还需考虑直播带货、微商等新型交易方式及线下市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影响。此外,在物流和仓储系统的支持下,一般而言应当根据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将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
市场支配地位方面,传统意义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通常以市场份额因素为出发点,辅之以其他因素的考量,我国《反垄断法》也有依据市场份额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但通过动态观察平台经济时代的市场变化可以发现,很多曾经占据大量市场份额的企业因无法持续创新被迫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而那些看似市场份额较小的企业却有强大的市场控制力。因此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场景下,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因素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市场份额因素的作用不断弱化。[19]换言之,在判断平台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时,应当更多考虑网络效应、数据能力、用户粘性、技术壁垒等符合平台经济特点的新型因素。当然,市场份额因素的作用弱化并不意味着其作用为零,至少该因素代表了相对固定时间内企业的市场力量。而且,由于平台经营者更多以促成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真实交易而非出售用户的注意力牟利,相较于注意力平台或者说双边非交易平台,市场份额因素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场景下更容易获取和计算也更加重要。
滥用行为方面,平台经营者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让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的业务无法在平台内市场中公平竞争,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差别待遇。从私法自治的角度来说,平台经营者给予任何一方优待条件均属于合同自由,而且自营业务是平台经营者业务的纵向延伸,平台经营者也有动机让其在与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当平台经营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消费者选择和竞争机制的互动能够让其在网络效应的压力下消除优待行为;但当上述两个条件成立时,平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能够支持其优待自营业务而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却无可奈何。
当竞争机制和私法工具无法发挥作用时,反垄断法需要介入以矫正市场失灵。《反垄断法》第17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实施差别待遇,《平台指南》第17条则根据平台经济的特点对差别待遇的考虑因素进行了细化。从行为类型上看,平台经营者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虽然不涉及价格上的差别待遇,但可将其归入到“实行差异性规则、标准、算法”项下予以规制。此外,《平台指南》还细化了交易条件相同的判断标准,这也为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提供了依据和准则。[20]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虽然平台经营者利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在我国尚未爆发出系统性的反竞争风险,但在“强化反垄断”政策背景下,我国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将平台经营者的数据优待行为分层为获取并分析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手段行为和优待并使自营业务拥有竞争优势的目的行为,并以此为主线探讨了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在规制路径的选择方面,以行为对市场造成的损害与“两反法”的匹配度为标准,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可以被分别置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框架下予以规制。当然,平台经营者自我优待行为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仅选取了一个切面,更多的研究仍有待在未来展开。
【参考文献】
[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信息研究所.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2020年)[EB/OL].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http://english.catr.cn/kxyj/qwfb/ztbg/202005/P020200530560741723821.pdf.
[2]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EB/OL].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3]Alexei Alexis.EUantitrust case against Amazon centers on unfair use of third-party data[J].2020WL6624956.
[4]康恺.反垄断调查“第二季”:欧盟再撕亚马逊或进一步加强立法[EB/OL].新浪网,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11-12/doc-iiznezxs1363905.shtml.
[5]梅傳强,张嘉艺.“套路贷”犯罪罪数认定问题探析[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2):52-62.
[6]薛虹.论电子商务第三方交易平台——权力、责任和问责三重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39-46.
[7]高薇.弱者的武器:网络呼吁机制的法与经济学分析[J].政法论坛,2020,(3):80-92.
[8]朱一飞.论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J].政法论丛,2005,(1):66-71.
[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84.
[10]Pablo Ibanez Colomo.Restrictions on innovation in EU competition la[J].European Law Review41 2016:201-219.
[11]孫晋,李胜利.竞争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4.
[12]G.Stigler.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9,1961:213-225.
[13]Russell Korobkin.Bounded Rationality,Standard Form Contracts,and Unconscionability[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70,2003:1225-1226.
[14]张守文.经济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96-397.
[15]卢扬逊.数据财产权益的私法保护[J].甘肃社会科学,2020,(6):132-138.
[16]电子商务法起草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05.
[17]刁云芸.涉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J].知识产权,2019,(12):36-44.
[18]时建中,张艳华.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与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55.
[19]陈兵.互联网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再探[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80-88.
[20]陈兵,赵青.开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新局面[J].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0,(12):21-23.
(责任编辑:赵婧姝)
The Regul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on Using the Operator Data
in the Platform to Treat Self-Supporting Business
Wu Kaiwen,Wang Chengtang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platform operators using the data of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to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ir own busi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means of obtain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and the purpose of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ir own business.This behavior will infringe the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 and the interests of fair competition,disturb the order of market competition,affect the full play of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and ultimately lead to the loss of consumer interests.The two “anti-monopoly laws” have their own key points of regulation.The damage caused by means behavior is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and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regulate the purpose behavior through the anti-monopoly law.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means behavior may meet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infringement of trade secrets or general terms;In the context of anti-monopoly law,purposeful behavior may violate the provision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abusing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Key words:platform operator;operators in the platform;self operated business;competition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