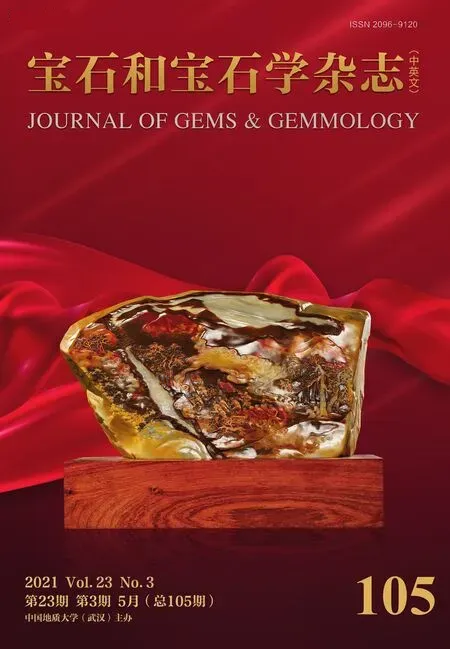中国汉代玉器的工艺进步和艺术创新
——以安徽出土的汉代玉器为例
吴 沫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623)
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1],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汉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促进了玉雕技艺的蓬勃发展。因此,汉代玉器常常呈现优良的质地、精湛的工艺、优美而新颖的形式和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其中,不少精品无论是在工艺制作,还是在艺术创新上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将中国玉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安徽地区在汉代虽然不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却出土了多件珍贵、稀罕的汉代玉器精品,其中个别玉器甚至是目前绝无仅有的珍品,体现了汉代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2]。这些玉器是汉代玉器工艺进步和艺术创新的重要见证,值得我们重视和探究。
1 汉代制玉工艺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质工具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到战国中期,铁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铁质工具成为手工业中主要的生产工具[3]。至汉代,冶铁技术在战国时期的铸铁和铸铜技术基础上更有所进步,铁质工具不断获得新的发展[4],这为当时的玉匠提供了比青铜材质及早期铸铁材质更加坚硬、耐用和锐利的制作工具,使当时的玉器工艺向着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方向发展,并促使汉代玉器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5]。在安徽地区出土的汉代玉器中,相当多的出土玉器具有精良的工艺,个别玉器集浅浮雕、高浮雕、平雕、镂雕、阴刻、活环、掏膛等多种工艺于一体,部分玉器出现了多层镂雕工艺和精细的镶嵌工艺,显示当时的制玉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准。
1.1 复杂工艺的综合应用
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了1件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Zhī)(图1),被公认为是代表了汉代制玉工艺最高水平的杰作,其形体相对巨大、造型独特、工艺复杂、雕琢精细、纹饰繁缛,是国内已发现王侯一级墓中都未曾发现的珍品,堪称汉代玉器国宝[2]。

图1 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6]Fig.1 The jade vessel (Zhi) of a Zhu-que stepping on a Chi-long
卮是战国至汉代流行使用的一种圆筒状饮酒器具。《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可知,玉卮在汉代相当珍贵。目前已知的出土和传世的汉代玉卮至少可见8件,除前述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外,另还包括: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朱雀扳指玉盖卮1件、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勾连纹玉盖卮1件,湖南省安乡县黄山镇西晋刘弘墓出土龙凤纹玉卮1件(该件玉卮虽出土于西晋时期墓葬,但从其造型、纹饰、风格等判断,这件玉卮应是西汉早期的作品[7])、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赵昩墓出土带盖铜框镶玉卮1件、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2号汉墓出土带盖铜框镶玉卮1件、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巴家墩墓出土玉卮1件和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汉代带盖夔凤纹玉卮1件。
比较以上汉代玉卮的体量(表1,图2),如果仅考虑整玉雕琢的玉卮,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的体量最大,尚未计入卮盖高度,其通高已达13.1 cm,口径达7.9 cm,同墓出土的另一件朱雀扳指玉盖卮通高和口径分别为11.6 cm和6.7 cm,均小于前者;而墓葬规格远高于北山头1号汉墓的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带盖玉卮通高尚只有9.8 cm,口径为6.7 cm;西晋刘弘墓中出土的汉代玉卮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汉代玉卮虽高度分别达12.9 cm和12.3 cm,口径分别达7.6 cm和6.9 cm,都已属汉代大体量玉质容器,但在体量上均未超过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南越王赵昩墓和马王堆2号汉墓出土的铜框镶玉卮均采用铜框镶玉片的方式组合而成,分别各在铜质框架上镶嵌9片和8片玉片,从侧面反映在汉代要获得块度较大且无裂、无绺的玉料并非易事,因而玉工采用了这种组合、拼接的方式来间接制作较大体量的玉质器皿;同时也说明前述3件由整玉进行深掏膛并磨制出厚度均匀器壁的玉卮在汉代应是相当珍贵的物品。杨建芳[8]在《安徽古代玉雕的超前性》一文中指出:“按一块玉料雕琢的(汉代,笔者注)玉卮,无论出土物或传世品,都是甚为罕见。”
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所用的工艺集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镂雕、活环、掏膛和薄胎等工艺于一体。这件玉卮由整玉雕琢,玉匠事先应已进行了缜密的设计,提前预留出各部位的玉料,然后以深掏膛工艺去除玉卮圆筒内的料芯,以薄胎工艺将卮杯壁磨制成厚薄均匀、厚度仅有0.3 cm的器壁,以高浮雕工艺、镂雕和阴线刻工艺相结合雕琢出卮杯一侧的朱雀和螭虎、另一侧的环状扳手和立雄以及两侧的夔龙等造型,以活环工艺在朱雀嘴部雕琢出绞丝纹活环,以浅浮雕、阴线刻工艺雕琢出卮杯外壁和外底部的纹饰。这件玉卮不仅工艺复杂,而且雕琢得十分精细,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一丝不苟的处理,其工艺的复杂程度和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制作这件玉卮的汉代玉匠具有十分高超、娴熟的雕琢技艺。
比较其他出土和传世的汉代玉卮(表1,图2),它们虽也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汉代玉器佳品,但未有任何一件能同时将如此多而复杂的工艺运用于一身。它们多数仍主要通过浅浮雕繁缛的纹饰来彰显卮杯的高贵和华美,但却缺少以高浮雕、镂雕、活环等工艺来表现的像生形象,因此在视觉上沉稳有余,生动之态和雄浑之势却有所不足。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无愧是汉代玉器中的艺术极品。

表1 汉代玉卮的尺寸和制玉工艺Table 1 The sizes and handcraft processes of some jade vessels (Zhi) in the Han Dynasty

图2 不同来源的汉代玉卮[6-7,9-12]:a.北山头1号汉墓;b.狮子山楚王墓;c.西晋刘弘墓;d.南越王赵昩墓;e.马王堆2号汉墓;f.故宫博物院;g.甘泉巴家墩汉墓Fig.2 Jade vessels (Zhi) in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different tombs:a.Beishantou No.1 Han Tomb;b. Lion Rock Tomb of King Chu;c.tomb of Liu Hong in Western Jin Dynasty;d.Nanyue King’s tomb of Zhao Mo;e.Mawangdui No.2 Han Tomb;f.the Palace Museum;g.Bajiadun Han Tomb in Ganquan
1.2 多层镂雕工艺
战国时期的玉匠已将镂雕工艺运用得得心应手。例如,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佩和战国晚期的安徽长丰杨公墓中出土的镂空龙凤纹玉佩、镂空龙凤纹玉珩、镂空双龙纹玉珩等都具有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工艺,是当时镂雕工艺的杰作。汉代玉雕继承了战国时期的镂雕技法,但多数仍基本是限于单个层面上的镂雕。纵观中国玉器发展史,成熟的多层镂雕玉作一直到宋、金、元,尤其是元代才开始大量出现,宋代之前多层镂雕工艺的玉作则十分罕见。但是,安徽省怀远县唐集汉墓出土1件镂雕三螭玉韘(Shè)形佩(图3),长7.00 cm、宽4.27 cm、厚2.88 cm、孔径1.70 cm。这件玉韘形佩已明显突破了战汉时期镂雕玉器惯用的单层镂雕技法,采用了多层镂雕工艺,造型特殊,工艺精巧,堪称汉代镂雕工艺的精品[13]。

图3 镂雕三螭玉韘形佩[6]Fig.3 The hollow engraving jade pendant (Shexingpei) with three Chi engraved on it
玉韘形佩由玉韘演变而来,是汉代流行且特色鲜明的玉佩饰,主体大致呈椭圆形片状,正面微鼓,背面略凹,上端常作三角形尖状,中间有一较大的圆孔[7]。汉代的玉韘形佩形式多种多样,其变化主要体现在附加于韘形佩主体以外的透雕装饰上。这些装饰通常附于韘形佩的一侧或两侧,还有部分附于韘形佩的顶端、或下部、或大圆穿孔内。无论如何变化,这些玉韘形佩的主体造型通常是清晰可见、一眼即明的。但是,唐集汉墓出土的玉韘形佩透雕3只螭虎首尾肢爪相连相接,完全包围在韘形佩主体之外,使整体形成一个近似的椭圆形球体[6]。从正面一眼看去,很难分辨出这件玉器本是一件韘形佩,但仔细观察发现韘形佩近椭圆形片状的主体和特征的圆形大穿孔。这件韘形佩由于主体的正背两面完全由透雕的螭虎包围,再加上自身也有较大的圆形穿孔,因此整体形成了一件名副其实的多层镂雕作品,结合韘形佩上螭虎扭头摆尾、弯曲有度的优美造型,整体看上去玲珑剔透、精美绝伦。
目前,可做比较的是江苏徐州北山洞楚王墓中出土的1件五螭玉韘形佩(图4)。这件玉佩的中间部分可见带有较大圆形穿孔的近椭圆形片状体,上端具有三角形尖角,显示其为韘形佩无疑,其正面镂雕3只螭虎,背面雕有2只螭虎,也可视为一件多层镂雕的作品,但由于这件韘形佩前后的螭虎是紧密贴附于其主体之上,因此层次不如唐集汉墓中的三螭玉韘形佩的分明和复杂,工艺难度也逊于后者。

图4 五螭玉韘形佩[14]Fig.4 The jade pendant (Shexingpei) with five Chi engraved on it
《灵动飞扬——汉代玉器掠影》一书曾指出:“汉代的镂空技术十分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镂空不仅是完成表现母题的一种技法,也是可以欣赏的纹饰部分。汉代玉工对镂空形状的重视,比其他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体现了他们对玲珑剔透之美感的喜爱与追求。”[15]安徽怀远唐集汉墓中出土的多层镂雕的三螭环绕玉韘形佩正是对这种审美趣味的高度体现,也是迄今所发现的能反映汉代玉雕中镂雕工艺最高水平的作品。
1.3 金属嵌玉工艺
金属嵌玉工艺在夏代二里头遗址中已有发现,多见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小片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在青铜嵌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成熟的铁器嵌玉、金器嵌玉等工艺[16],镶嵌的玉石不止有绿松石,还有透闪石质软玉。汉代玉匠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制作出技艺更加精细和高超、形式更为别致和华美的作品[13]。
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1件镶玉铜熏炉(图5),口径8.6 cm、高8.2 cm、腹径10.8 cm。这件铜熏炉器身分别镶嵌4件圆形云纹玉片、4件近长方形兽面纹玉片和7件水滴形玉片,三足上各镶嵌1件水滴形玉片。铜炉上用于镶嵌玉片的位置和形状均在铜炉浇铸前已预留出来,铜炉成形后再将玉片镶嵌于预留位置上。熏炉上用作镶嵌的玉片平整规则,与镶嵌预留位严密合缝,显示出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17]。这件镶玉铜熏炉盖子由玉石制成,圆形,略上鼓,其上镂雕和阴线刻勾连云纹和弦纹,盖下缘套于环状铜边框内,铜框上口铸有3个等距分布的叶状卡片,用来扣住玉盖,使其不得脱落,铜框一侧还置一凸隼,可与炉身上的凹槽相套和,同时还贯以铜枢轴以供开合,设计得十分巧妙,可谓独具匠心[17]。汉代考古发现了大量金属和陶质熏炉,但以玉和金属结合的熏炉,目前仅见此一例[7]。这件镶玉铜熏炉将玉的温润和青铜的厚重完美结合,使整器显得沉稳而不失雅致,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也正是汉代玉匠在制玉时赋予作品所特有的时代特点。

图5 镶玉铜熏炉[18]Fig.5 Copper incense burner inlaid with jade ornaments
2 汉代玉雕艺术的创新
汉代玉器,尤其是西汉早期玉器,较多地承袭了战国时期楚国玉器的风格,显现出浓厚的楚文化元素,常具有精巧的设计、奇异的想象,华丽的纹饰和高超的雕琢技艺。同时,汉代玉器还受到秦代严谨务实的审美文化以及道家、儒家等思想文化的多重影响,因此对浪漫、奔放和理性、写实的审美情趣都有吸纳和融合。与战国玉器相比,汉代玉器在玉雕艺术方面又有诸多创新,其形式往往表现得更富人性化和功能化[19],更加强调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统一,同时在一些作品中以写意的手法,更加追求简约灵动的造型,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又以写实的手法追求细致、逼真的刻画。这些艺术特点在安徽地区出土的汉代玉器中都可见到典型的代表作品。
2.1 功能与审美的统一
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衔环踏螭虎玉卮代表了汉代玉器最高的工艺水平,而它的形式也极富创新,完美地体现了功能与审美的统一。
这件玉卮在造型上和汉代的其它几件玉卮都有所不同,最引人瞩目的是在卮杯一侧高浮雕朱雀踏螭虎的形象。朱雀是汉代四神之一,但是,这里与其说是朱雀踏螭虎,不如说是凤鸟踏虎的形象[20]。汉代继承了楚人尊凤的习俗,继续把凤作为造型和装饰艺术的主体[19]。凤鸟踏虎的形象在楚文化的漆器艺术中多有见到,如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出土的虎座飞鸟、江陵望山1号战国墓出土的彩绘虎座鸟架(图6 )都表现为凤鸟踏虎的形象。由于楚人在楚国早期战胜了巴人,因此“凤鸟踏虎”的形象常被认为是意在表现以凤为代表的楚人战胜了以虎为代表的巴人;同时,楚人笃信巫神,相信动物能沟通神明,因此楚人常以凤鸟作为引魂升天的神性动物。由此或可以认为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螭虎玉卮正是在西汉早期仍保留了较浓郁楚文化背景下制作的一件将特殊的审美情趣和使用功能结合起来的器皿。它较可能已不是作饮酒之用的饮器,而是一件盛装特殊液体、希求籍凤鸟引导灵魂升天的的神秘器物。

图6 彩绘虎座鸟架[21]Fig.6 Painted lacquer shelf of a pair of birds stepping on a pair of tigers
同时,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螭虎玉卮的把手在造型上也实现了功能与审美的巧妙统一。这件卮杯的把手采用了立熊和单环结合的造型:单环附于卮身一侧,立熊背附于单环外侧,右肢上举,左肢扶胯,双腿直立,整体如擎天状,并以上下两端附于卮身侧部,和单环共同组成稳定的三角形构图,既为卮杯提供了手指穿握的部件,又丰富了卮杯的形式,从而使这件玉卮更富有文化内涵。和汉代其它几件玉卮的把手造型相比较,除了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卮采用了朱雀和环状把手结合的造型,其它的玉卮基本采用的都是单环状把手附垫指板的造型如图2,狮子山楚王汉墓出土的玉卮甚至只有筒状杯身而没有把手。由此可见,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螭虎玉卮的确是一件十分富有创新性、并能将审美意趣和具体功用完美结合起来的艺术杰作。
2.2 简约灵动的写意造型
安徽省天长市三角圩汉墓出土1件龙形玉环(图7a),直径4.5~5.5 cm,厚0.4 cm。这件玉环通过写意的手法塑造出一只首尾相接、灵动飞扬的玉龙形象,玉龙身体表面没有过多细致的纹饰刻画,仅以简单的两个卷云纹示意龙鳞,在造型上也没有采用战国时代常见的、几近程式化的S型或复合S型的玉龙造型,而是通过简单的环形卷曲的身体和弯卷的上唇及飞扬上卷的鬣毛相互呼应,从而突出了整体强劲和灵动的态势,使人过目难忘,这种简约、写意的风格和战国时代普遍注重彰显富丽、华美的风格明显不同,但在汉代的雕塑作品中却相当流行,这应该与汉代社会流行的审美趣尚有关。汉代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精神高昂的帝国时代……汉代的文化总体上是有力的,是民族奋进精神的反映”[22]。汉代社会崇尚阳刚大气、奔放进取,因此汉代的艺术造型往往更注重表现事物内在的生命力和动感,表现方法虽然简洁,但所塑造的形象却有着出乎意料的生动[23]。
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龙形玉环(图7b),直径7 cm、孔径5 cm,其形制和三角圩汉墓出土的龙形玉环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相比较,定县40号汉墓中的玉龙无论在纹饰、还是在造型上都略复杂于三角圩汉墓中的玉龙,尤其是前者由环形身体两侧伸出的示意性的龙的肢体,大大弱化了整体的流畅态势,而后者在整体上则明显具有更加优美的造型,更加婉转、生动的线条,显示出更高的艺术价值。

图7 龙形玉环[6,24]Fig.7 The dragon-shaped jade ringa.三角圩汉墓出土; b.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
2.3 趋向写实的造型和纹饰
安徽省巢湖市放王岗1号墓出土了1件首尾相接的环形玉龙(图8a),造型别致,纹饰特别,外径4.8 cm,厚0.6 cm。这件玉龙在纹饰和造型方面都更趋向写实和具象,龙身上满饰“双勾鳞纹”(由双阴刻弧线来表现的鳞片纹),鳞片的大小依龙身体由细变粗再变窄而相应地由小渐大再渐小,鳞片排列紧密有序、繁而不乱,张开的龙嘴露出上下两排多颗牙齿,身下伸出前后肢,肢体前方又伸出多只弯曲而尖锐的利爪、似禽爪。汉代多数,尤其是西汉早期的玉龙在造型和纹饰的细节上仍较多地承袭了战国玉龙的特点,在龙身上满饰装饰性纹饰而非龙鳞纹,如谷纹、勾连谷纹、勾连云纹等,部分龙的肢体仍和战国玉龙常见的示意性的扉牙状肢体相似,也有部分显现出简化的鳞纹和肢爪,但都不如放王岗1号墓中出土玉龙的肢爪这样清晰、完备。
有学者指出:“汉代是龙的真正的定型期……凡后世龙身上所有的器官、肢体,如角、齿、须、发、胡、四肢、鳞、鳍、肘毛等都已完备。”[25]这种细节较为完备的龙的形象在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T形帛画[26](图9)中清晰可见,但在汉代的玉龙上尚难全部见到。放王岗1号汉墓中出土的环形玉龙身上的双勾鳞纹是目前玉器上所见的最早的双勾鳞纹,而其趋向写实的表现手法也是,具有类似鳞纹和相似形象的玉龙另在安徽省庐江汉墓和潜山汉墓(图8b)中各见1件,都集中于安徽省境内,但在全国其他省区却尚未有见[2]。再次显示安徽地区出土的汉代玉器常具有特别之处,值得关注。

图9 马王堆1号汉墓T形帛画的线图[26]Fig.9 The line drawing of the T-shaped silk painting of Mawangdui No.1 Han Tomb
此外,安徽省阜阳市涡阳县稽山崖墓出土的1件玉人(图10,图11)也具有趋向写实的造型和纹饰,通高5.80 cm、宽3.40 cm、厚0.15~1.08 cm。这件玉人头戴冠帽,冠下露发,脸庞宽大,五官清秀,神情肃穆,肩部如有一对肩章式装饰物,身着交领宽袖长袍,双手相接于腹部,腰间系带,带上垂挂1件玉环,足下着履,无论是冠服,还是五官、头发都具有细致的刻画,塑造出一位汉代高级贵族官员的形象[27]。汉代玉人多见平面片状辅以阴线刻和镂雕的作品,少见圆雕作品;多见玉舞人形象,少见贵族形象,而且玉舞人在形象上往往仅有寥寥数笔的表现,给人以粗犷之感。相比之下,涡阳稽山崖墓出土的玉人则以神形兼备的形象、协调的身体比例、华美雅致的服饰和一丝不苟的精湛工艺,给人以高贵、庄严之感,显示出汉代玉工在对真实对象的模仿表现方面同样具有高超、娴熟的本领。同时,汉代流传下来的能反映汉代贵族人物真实形象的图像资料非常有限,而这件玉人则为现代人了解汉代男性贵族的形象、冠服、佩饰及礼仪生活习俗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27]。

图10 玉人[6]Fig.10 The jade figure

图11 玉人线图[6]Fig.11 The line drawing of the jade figure
3 结语
汉代玉器在工艺进步和艺术创新方面曾取得辉煌的成就,同时安徽地区出土的汉代玉器对于研究汉代的玉雕艺术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汉代是中国玉雕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汉代玉器蕴含着丰富的美学韵味。它们或浪漫奔放,或雄浑豪放,或生动写实……但无论如何变化,其艺术风格的差别又都统一于汉代雄浑饱满、蓬勃向上的盛大气象之中。回顾汉代的优秀玉雕作品,可以为我们当今的玉雕艺术设计提供借鉴的范例和创新的源泉。如何将汉代玉器的艺术精神和现代的艺术完美结合,如何塑造和强化当代玉雕作品的民族性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