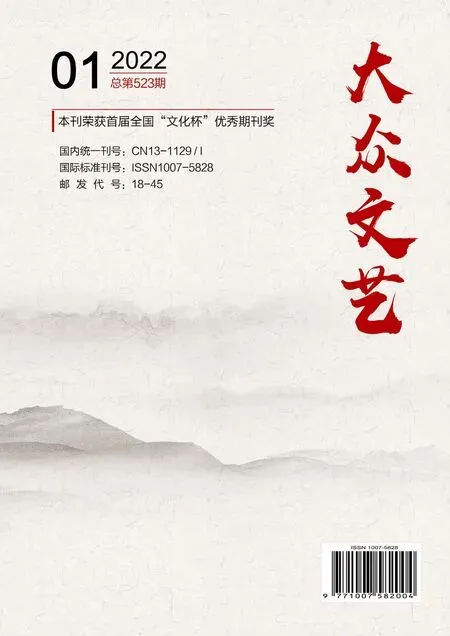从生态批评视角浅析中国动画电影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
随着全球生态形势的持续恶化,生态危机俨然成为各国不得不思考的重大命题,如此背景下,生态批评逐步发展成为艺术文化领域的一个永不缺席的理论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载体,动画电影不仅仅是屏幕中简单变幻的影像,还饱含人文理念与文化内涵,其明晰的受众定位与传播目的使之成为上层生态意识与广大受众的沟通枢纽,帮助大众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取向,成为从文化层面缓解生态危机的途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动画电影不仅在技术、审美、市场运作等方面落后于美、日等动画巨头,电影中所蕴含的生态主义思想也与之存在显著差距。因此,有必要从生态批评视角检视中国动画电影的生态意识,加快构建有机生态价值导向,以促进中国动画电影生态价值观与生态审美的纵深传播。
一、生态批评视角下中国动画电影的价值导向问题
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动画电影积极把握信息化传播红利,多数作品在弘扬主流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表现优异,但生态伦理价值导向与生态审美指向存在不足。早年的中国动画电影多数仅仅将生态作为另一种社会进行娱乐演绎,如《小猫钓鱼》《四只小野鸭》《聪明的鸭子》等,即使有意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基本上未脱离环境主义的窠臼。但环境主义并非生态主义,其虽呼吁保护环境,反对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但被视为一种更开明、更为弱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主义强调网状的物质关系,人类并未被置于特别优先考虑的位置,一旦环境主义与人文艺术相结合,生态批评便应运而生。
(一)二元对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以人的利益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原点与评判依据,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具备意识的人类方为主体,自然仅仅是客体,其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人,人的所有活动均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因而自然万物均应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而生态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提倡以平等尊重的心态与自然万物共存,可见,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主义根本对立。尽管很多中国动画电影试图以“领风者”的姿态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与可持续的发展,但受人类中心主义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影响,很多动画电影创作者仍倾向于将人作为价值评判中心,这导致很多动画电影并未真正摆脱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现实。以动画电影《黑猫警长》为例,影片中人类抽离出去,动物成为森林主人,而以黑猫警长为代表的森林警察永远是正义一方,包括白猫警士、白鸽警探等,代表正义的均由与人类亲近的动物担任,反面角色的“一只耳”等则是人类所厌恶的老鼠,还有很多人人喊打的不良分子如搬仓鼠、蝗虫大军等依然是“害虫”们,人类从某种程度上仍依据自身喜好对天然种群进行划分、对自然进行书写,并未抛弃评判生态自然万千事物价值尺度的人本观念,仍将人与自然置于了二元对立的立场下,在动画电影“寓教于乐”的期待下,原本猫食鼠的生物链被人类中心主义放大成为权力链,不得不令人唏嘘。
(二)中心转变——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思
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反人类中心的哲学理论,后者以人为中心,被视为引发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生态中心主义刚好相反,其强调生态的中心地位,强烈反对与仇视人类中心主义,该理论过于偏激,虽较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非科学的生态意识。在与环境难题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上,生态中心主义仅仅体现了生态主义的核心价值与最高标准,但这却并非中国动画电影的终点,一切对于生态平衡的恢复所进行的变革都要落在人身上,因此,中国动画电影在意识到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必要性之后,必须从责任视角重新回归于人。如动画电影《熊出没之雪岭熊风》中,故事以熊二的自白“那时的天蓝蓝的,森林一眼望不到底……”开始,为观众描绘一幅和谐唯美的生态画面,点名生态主题,随后又直接呈现伐木工一边肆意砍伐树木,一边高歌“大树倒下,路坦荡荡,建设家园,靠大家……”的画面,揭示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看到伐木场景,熊大、熊二无奈叹息:“他们又来了”,一个“又”字饱含无声的谴责与痛斥。在与小光头强的对话中,熊大脱口而出:“都是你们这些伐木工,俺们家的树越来越少了,你们都是坏蛋……”这些质朴的语言潜移默化地向观众传递了朴素的生态主义思想,而生态与人类之间的矛盾最终通过在小镇上建滑雪场得以解决,这又强调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挽救。
二、中国动画电影生态价值导向的构建
新媒体背景下,中国动画电影所蕴藏的生态价值导向俨然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桥梁,因此,推进中国动画电影生态价值导向的构建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要求。
(一)基于非人类中心:以生命共同体建构精神生态
一部动画电影作品,无论目标受众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立意与价值取向,“一件艺术作品涌动着多种文明的活力,传达了某种自由而高贵的梦想。”艺术作品固然是创造出来的,但创作者的艺术风格与生态观念均会从作品中溢出来,因此,国产动画电影要注重艺术与生态意识的融合,将最契合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共同体理论作为动画电影的价值导向预设,借由电影展现生态文明的活力,帮助受众构建非人类中心的精神生态。宫崎骏曾提道:“在繁茂的森林中生存的仅有动植物吗?对于一颗敏感的心而言,事实也许远不止如此,总有神秘的事物从树后暗暗窥视,因为自然本就是一个无限深邃的存在。”正是这份对生态的敬畏与尊重,使得宫崎骏动画电影作品的生态质感总是显得格外抢眼,无论是《幽灵公主》中对自由自在穿梭于原始森林的小精灵们的塑造,还是《千与千寻》中试图告知观众的“万物有灵”,抑或《龙猫》中对人与自然心灵契合及矛盾消解的探究,宫崎骏动画电影将宏观真实世界中理想的生态伦理体系意识压缩、凝练放入虚拟的动画世界中,这是国产动画电影所需借鉴和参考的重要部分。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中,中国动画电影《藏獒多吉》无疑是优秀的,小男孩田劲意外与藏獒多吉成为朋友,田劲救了身负重伤的多吉,而当田劲被风雪冻倒之时,多吉又救了田劲,然而高原生态异常复杂,多吉只是生态的一部分,还有居心叵测的强盗、怪兽“罗刹”等,三方混战下雪崩的发生,多吉再一次用生命挽救了田劲,整部电影中,多吉犹如一个义无反顾的救赎者,就像大自然对人的反哺,而田劲在被多吉拯救后,成为草原上的一名牧医,从初到时的不适应成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典范。
(二)引导生态审美:基于生态美学的视听表达
生态审美是生态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生态意识的发展势必会推动生态审美的改变,而生态审美的改变又促进了意识变革,二者始终维持这样的能动交互关系。作为艺术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画电影的价值导向构建绝不能单纯局限于主题所指向的生态立场层面,还要致力于以特殊的生态审美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对于中国动画电影而言,构建生态审美导向需要从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出发,以传统生态审美为创作根基,注重生态景象的重现与生态的拟人化、泛灵化表达。一方面,中国传统生态审美经验为动画电影视听形式的创新注入了无限活力,也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身份认同,20世纪中叶,我国历史最悠久、片库量最大、知识产权最多的国有动画企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敲喜剧样式之门”的创作方向,引领广大艺术创作者探索民族艺术文化与动画电影的融合之路,并打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学派风格“美术片”,如我国首部彩色动画电影《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传统花鸟画风格的《布谷鸟叫迟了》、经典水墨画风格的《鹿铃》与《牧笛》、敦煌壁画风格的《九色鹿》等,此类动画电影无论是角色塑造,还是场景创设,抑或色彩配置等均立足传统生态审美经验,以散点透视表达自然山水、以画面留白引导观者思考,以虚实疏密、浓淡干湿、轻重缓解等要素的和谐统一追求角色、场景等的平衡性,加上角色适当地夸张与变形,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生态审美体验,促进了中国动画电影预设生态价值导向的普及;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固有的理解思维决定了其面对不熟悉事物时总试图将其向自身所熟知的事物靠拢,以既有思维解读成功后方可接纳它,因此,针对观众不甚熟悉的抽象自然或具象动物,要注重将其进行拟人化表达,以人格语言加以解读,如此方可引发受众共鸣,继而感动到他们,例如,上文提及的国产动画电影《布谷鸟叫迟了》,就是将布谷鸟赋予了人格化特征,使之像人一样能说会道,每当布谷时节来临,就会飞到村里告知农民伯伯:“快点布谷,快点布谷……”生态拟人化表达是一种使人们将其他事物置于与自身相同位置重新思考的便利方法,要将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意识依托动画电影传达给观众,就必须借助这种处理拉近生态与受众间的感情距离。
三、结语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并非复杂晦涩,但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生态批评在现实社会中却举步维艰。直至今日,人们面对生态问题仍试图以金钱、科技解决之,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征服自然观、唯发展主义观依然矗立不倒。在如今这个科技至上的时代,人们需要一种方式与生态达成和解、完成自我心灵的救赎,动画电影就是这样一种途径,其以独特的展示方式将话语权转移给自然、动物,道出了人类为一己之私掠夺和破坏生态的种种恶劣做法,较之其他电影形式而言,动画电影所蕴含的无穷想象力将生态因素更生动地呈现出来,是对传统生态批评理论的延伸与拓展,对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挥着积极效应,其所勾勒的“诗意栖居”的梦想蓝图,有助于唤醒更多人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自然与人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