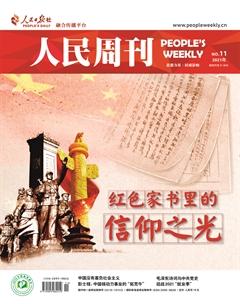不记年
张金刚

我問父亲,村子有多少年历史,出过多少有成就的乡亲,那棵老槐多大树龄,地里种过多少茬庄稼……
父亲一脸茫然,继而一脸淡然,摆摆手:“谁还记这些?春天来了就种,秋天来了就收;花开了就看,结果了就摘;风调雨顺乐着过,有了灾荒扛着过。我们这年纪,活着干,死了算,每天过好就是福,不想那么多喽!”
话虽糙了些,但理儿很精。这让我想起清代袁机《感怀》中的两句诗:“乌啼月落知多少,只记花开不记年。”想想父母一辈子守着村子,应着时令耕作,伴着岁月生活,看过几多花开,容颜已苍老,却活得更通透。
曾去山里拜访过两位老人。他们的人生前半程,我不过问,只当下养鸡、种花、作画、写文的日子,就足以让我艳羡。那日,院中的老梨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梨子,树下我们一起包饺子,谈笑风生。饭罢,阿姨展宣作画“墨梅图”,大叔深情朗诵“田园诗”,二人相互帮衬、相互欣赏,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在万寿菊、鸡冠花丛中流连了一番,老人又嘱我攀上梨树,摘了几袋梨,给来客带上,并恭敬赠予他俩的《耕药园文集》,想必这小院便是“耕药园”了。我们再次邀约,来年常来,赏梨花,赏牡丹;摘桑葚,摘枣子;炒鸡蛋,炒时蔬。篱笆旁的二位,笑得像孩子。
虽时隔多年,亦不知老人是否还在山里,境况如何,但那从容诗意的生活却一直让我铭记,更记得大叔云淡风轻的一段“笑谈”:“我俩也是在风浪中拼过命,才安全上岸的。人这一生,除了筷子放不下,其他的都能放下。人呀,说到底,活到底,就是好好吃、好好过,不记年龄,不记太多。”
经历多了,自然也就记得多,当然也要忘很多。这样才更轻松,不至于将有限的内存占满,令生活卡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很欣赏“镜子”的,只照当下,不记过往。
结婚纪念日,我与妻穿越半座山城,又去看当年结婚时租住的小院。那棵老椿树青翠如昨,院外的牵牛花仍在吹奏,它们该是已不记得我们,或从来就不曾记过我们。十七年,弹指一挥间。余生,我想牵紧妻的手,珍惜每天的一餐一饭、一日一月,甚至一场冷战后的微笑和解。
我问过父亲,你和我娘结婚多少年了,吵过多少架,看过多少场戏……父亲照旧一脸茫然,继而一脸淡然:“记这干啥?每天就那样过,一天又一天,白开水一样呢!”曾经不会做饭的父亲,刚蒸了一锅馒头,拿一个给做了一辈子饭、现在却做不动饭的母亲:“赶紧趁热吃吧!”两人眼前,热气腾腾。
吃完,父亲坐在院里的枯树桩上神情木然地抽着烟,望着山。父亲屁股底下那棵老杨树的圈圈年轮,此时像是时光之河的圈圈水晕。时光无言,却在似水流年里回答了所有问题。恍惚间,水晕旋动起来,将父亲一点点旋进去,他拉着母亲,母亲拉着我们,将一切年华过往、身外之物悉数归还……